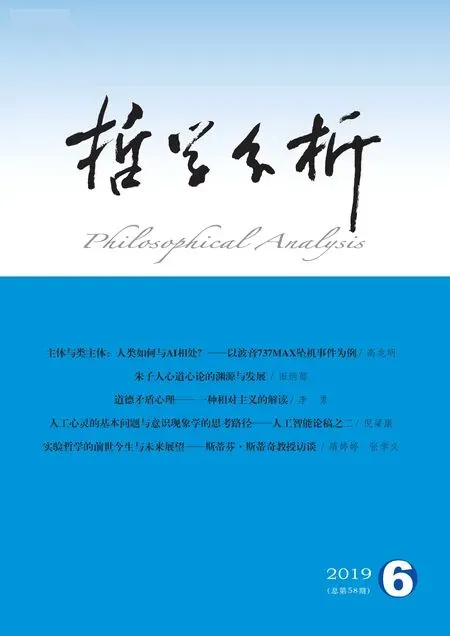时空观重塑视野中的贺麟“新心学”
刘 勇
贺麟先生(1902—1992)是近现代中国著名的川籍哲学家与翻译家,以翻译并研究斯宾诺莎和黑格尔哲学而闻名于学界。贺麟不只攻于西方哲学并取得丰硕成果,同时因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贺麟对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宋明儒学的思想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代表作有《近代唯心论简释》 《现代中国哲学》 (1989 年后改成《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文化与人生》等。尽管他并没有像熊十力、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有系统的儒学思想,但是贺麟作为现代“新心学”的开创者,仍旧成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近代唯心论简释》这一论文集是贺麟的“新心学”思想构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名为“近代唯心论简释”的第一章是该书的同名标题,紧接着的第二章是“时空与超时空”a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主要研究这个话题的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湛晓白:《民国学术界关于“时间”的哲学认知》,载《兰州学刊》2018 年第10 期;陈松:《“时空”与“超时空”视域下的贺麟人生哲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李承贵:《中国传统哲学开出科学知识之尝试——以贺麟“时空即理”为例》,载《学术研究》2011 年第5 期。,但是让人好奇甚至不解的是,时空、超时空与其“新心学”到底有何内在关 联?
一、理在心中
贺麟为了论证“理在心中”的结论,他分别通过对时空即理、时空乃心中之理展开具体论 述。
贺麟批判了几种混淆的时空观。一方面,物或事与理对立。时空是经验上的物或事还是先天原则?从常识上讲,时间和空间似乎是具体的物,如浪费时间、留点空间。“绝对的空间,它自己的本性与任何外在的东西无关,总保持相似且不动,相对空间是这个绝对空间的度量或者任意可动的尺度(dimensio)……”b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赵振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第7 页。贺麟进而认为牛顿的时空是绝对均质性的、独立的、无限的时空,时空为实际存在的物(这里的物可以从实有的角度来理解)。相对论者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时空为事(event)。非均匀的时空与物不能截然分开,它在经验中表现为事。简而言之,以上均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理解时空框架中具体的物与事而非时空本身。如果从哲学视角来考察时空,贺麟比较推崇康德的时空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部分认为时空并不是我们经验到的现象,而是使人类这些经验得以可能的先天直观形式。c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21—40 页。在康德看来,时空并非是经验性的事或物,也不是概念性的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而是人类的先天认识形式。时空是人类的先天原则或法则,它使得感性杂多统一起来。由此,贺麟认为从科学角度来理解时空,只是去研究时空框架中具体的事与物,而非理解时空本身。哲学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提,其旨趣在于研究作为决定具体事与物产生条件的时空,所以贺麟站在哲学立场上认为时空既非物,也非事,而是理。贺麟特别研究了康德的时空观,并进而细分了三层,即时空不是物自体或自在之物;时空是主体的认识功能或理性原则;作为人类普遍必然的有效原则的时空为个人经验奠定基础。d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12—13 页。很显然,在这一点上贺麟基本接受了康德在认识论意义上的时空观,为他进一步论证时空即理奠定了哲学基 础。
另一方面,时空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对立。贺麟借用了柏格森的“绵延说”,将不确定的时间称为绵延,将不确定的空间称为扩张(extension)。贺麟运用柏拉图的“理念说”简要地批判了柏格森的时间观。在贺麟看来,永恒是绵延的理念(本体),绵延是永恒之现象,柏格森似乎有将永恒与绵延模糊的意味。贺麟认为只有经过主体衡量的时空,建立了有限的客观标准,才能说是确定性的时空。至于非确定性时空,它具有三种含义:一种是无限定(unlimited)的时空;一种是无穷的(endless)时空;一种是普遍性和永恒性的时空(真理)。至于其中第二种含义,因深受黑格尔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贺麟认为无穷的时空为“坏的无限性”而排斥了这个含义。黑格尔认为在时间上的无限延长,空间上无限扩展的思维实质上是知性思维的虚妄或者是站在知性形而上学立场上思考问题。a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200—203 页。但是有限与无限并非绝对对立,而是自己与自己相统一的否定关系。无穷的(endless)时空并非出于理性而是出于想象和不遵从理性规范的滥用而导致的结果。在知性思维之中的无限,自以为超出了有限的限度,但是这种“想象”从来也没有离开有限事物的范围。有限与无限本是一回事,与有限相对的无限并非真的无限,它还是受到与之相对的有限的限制,真的无限与有限是统一的,它能够在融合的时候保持其自身,而有限才会被扬弃。因此,我们可以对贺麟的时空观点稍作分类,即作为有限的时空,作为绵延和扩张的无定时空,以及作为普遍和永恒的无限时空。接下来,贺麟着重论证了后两类时空即理且是心中之 理。
我们需要知道贺麟是如何认识“理”的?贺麟对理的分析包括:理是共相,理是解释经验的原理,理是规定秩序的法则,理是理想的范型,理是事物遵循的标准,理是衡量的尺度。贺麟比较看重后面两个含义。贺麟先从西方哲学三段论的形式予以证明时空是理。b贺麟认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必是理,其他哲学家未必同意这个观点。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22—23 页。然后他进一步从中国哲学史去论证这个问题。他列举了《诗经》上所说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句话隐藏着“物者理也”的思想。当然,他也承认这只是一些思想片 段。
以上外证并不具有必然性,他最后提出了作为内证的先天证明。不过笔者认为贺麟这一先天证明似有“模仿”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论证的痕迹。c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年版,第62—73 页。黑格尔在“感性确定性”这一章,论证了特殊的“这一个”(这时和这里)如何成为普遍的“这一个”过程。“这时”指的是某个时间。时间一直在变,但是保持下来的“这时”本身是一个否定的和间接的东西。通过这个否定过程,“这时”是一个非“这时”,既是“这时”又是“那时”,此种单纯的东西成为了普遍的东西。“这里”也是如上所证明的那样。它们共同证明了以自身为中介而达到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对于原始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其实可以称之为此时和此地的观念。此时和此地的具体所指始终处于绵延或扩张的情形之中。但是作为共相的此时此地却保留下来,并且具有衡量其具体所指的标准和尺度。标准与尺度是人主观设定的,或者说是主体衡量经验事物的先天法则,并非出自经验,从而为时空为心中之理的论证提供了先天性的证明。因此,在贺麟看来,时空的概念成为自然知识或现象的原则或标准。时间与空间是主体(此心)整理或排列感觉材料的总法则(理或原理)。贺麟模仿康德的论证方式,又进一步论证时空是先于自然知识或现象的。在这其中,贺麟创造性地引出了“感念的时空整理”概念。a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30 页。在贺麟看来,感念不是介于感觉到概念之间(时—间或空—间)的知觉,而是在概念之上。用概念去指称某一个感觉(物),感觉进而成为感念。这里的感念类似于天台宗智者大师智 的“一念三千”,“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则已,介尔有心,即具三千”b智 :《摩诃止观》卷五,第54 页,《大正藏》第46 册,转引自郝金广:《天台“一念心”的教观分析》,载《中国佛学》2017 年第1 期,第157 页。,心在一瞬间的活动中呈现的却是整个世界的空间大小与时间长短。也就是说,“一念”将此时此地结合起来,既能扩充也能收敛概念的范围。这个扩充或收敛,实际上就是极短暂、极微小的时空排列。任何材料都必须经过这种“一念”的整理。只有经过有序、有效、有机地整理后,我们才可能获得自然知识。感念的时空整理有复杂和简单之分,科学知识成为可能,必须经过主体复杂的、精确地整理。受到康德的启发,贺麟提出了三种时空标准,第一种是感觉的时空标准,第二种是权断的时空标准,第三种是理性的时空标准。c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第33 页。这三种标准是衡量自然知识的前提条件。在贺麟看来,前两种时空标准与事物本来的真正次序符合只具有或然性,只有第三种是比较可靠的,它是纯粹自然科学知识产生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纯粹自然科学知识需要理性的时空标准加以排列。对感性材料加以理性的时间排列,被他称为因果律。既对其进行时间排列,也对其空间排列(对其部位和关系加以客观地排列),被称为自然律。贺麟认为自然律是以理性的原则为体、时间和空间为用来把握自然的法则,这个法则不是后天经验的,而是先天的法 则。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诗经》中早已隐藏着“心者理也”的思想。贺麟又借用了陆象山、王阳明“心即理也”的理论资源。陆象山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d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273 页。统理宇宙的理并非外铄而在心之内。没有心的存在,世界等于是无分别的一团漆黑;没有心的统摄,宇宙是杂乱无章的材料堆砌;不从认识本心(良知)着手,一切都是支离骛外。同样,吾心已经具有了宇宙万物的权衡和尺度。王阳明说:“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e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0—141 页。这里的灵明指的是心或良知,人有了这个灵明,能够认识世界,赋予世界以价值和意义。不过,这种论证是宋儒擅长使用的直觉上的论证,具有某些神秘主义的气质。因此,贺麟借助西洋哲学史的材料,并提供了又一个“外证”。早期希腊哲学家将物之具体特性视作物之法则,直到苏格拉底才扭转这一方向。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他们将人的理性视作权衡万物的原则。近代哲学中康德作为调和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哲学家,提出了又一个证明。“康德崛起,一方面,把握住理性派的有普遍必然性的理,一方面又采取了经验派向内考察认识能力的方法,但先天逻辑的方法代替了心理学的方法……”a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第26 页。贺麟认为康德发挥了“心者理也”的思想,将时空视作心中先验之理,而非经验性的具体事物。时空是自然知识所以可能的心中之理或先天标准,了解外物须从了解自我开启。进一步来说,作为善良意志的道德之理也源于心灵的道德意志的内在发动,不在心之外。总之,从中国和西方哲学史来看,理在心中。结合时空即理的前提,可以推导出时空乃吾心中之 理。
时空除了上文所论证的是自然知识何以可能的心中之理或先天标准,而且也是道德行为之所以可能的心中之理或先天标准。原始人的本能行为依据的是时空的准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正描述着原始人的生活状态。贺麟认为这种自然的时空标准,一方面是大自然的规律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人类从感官上直观感觉与大自然的合拍,可能他们自己对此没有意识,也以为自己的行为并非由自然所决定。另外,贺麟认为任何具有实用意义的行为,也必须遵循权断的时空标准。自然的时空标准是不违时令,而权断的时空标准遵循的是公共的实用性。而这种公共的实用性是保证社会秩序运行的必然的先天的条件。倘若个人在公共场所不遵守这种权断的时空标准,那么其他人的公共生活将受到严重影响,反过来也会制约个人利益的存有和发展。贺麟还认为时空为艺术化的行为之所以可能提供了原则或标准。中国哲学中大量蕴含着时空标准与道德行为之关系的思想片段。我们在家庭中的婚嫁丧祭、社会上日常交际、国家的祭祀礼仪都遵循着时空标准,它虽然有自然的时空标准成分,也有权断的时空标准成分,但是最终由作为理与情的合一的理性时空标准所决定,所以“礼者理也”。艺术化的自然行为,如礼和乐、礼与艺术均遵循着理性的时空标准,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同样道德行为更不能失礼,也就是说,仅有道德动机而不遵循理性的时空标准,道德行为也不一定符合礼。因此,贺麟认为中国的礼产生于时空的准则与纯道德律的合一。“孔圣人被奉为‘圣之时’,即因为就空间而言,他的行为可以无入而不自得,就时间言,他的行为可以无时而不自主。”b同上书,第39 页。从表面上看,孔子的行为是由时空所决定的,但是时空即理,实质上也是由理性所决定 的。
贺麟之所以在时空观上比较赞同康德的时空观,主要原因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中国人的时空观浸透着生命哲学,时空不能离开心而单独存在,时间与空间并不是独立于人认识之外的客观实体,而是融会了人的悟性与灵性的直觉对象。也就是说,尽管时空属性与形式在变化中体现了客观性,遵循某种宇宙的“道”或“理”,但是这种“道”或“理”本身并不具有实体性,而是“万物皆备于我”。中国传统的时空观强调了人的主体作用,只有人之心才能认识时空的存在形式与属性,而康德的主观时空观突出了时间与空间的主体化,从而彰显了时空的生命意蕴,这与中国传统的时空观具有契合的一 面。
二、心中有理
贺麟的时空观确实受到康德的时空思想的影响,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贺麟的时空观已经将其从康德的认识论领域扩展到道德和艺术领域。a宛小平:《论贺麟新心学的美学维度》,载《哲学研究》2011 年第9 期。在贺麟看来,理性的时空标准是自然知识和道德行为的先天条件,人类认识自然规律,践履道德行为须在一定时空尺度内。这其实已经突破了康德单从认识论的领域谈论“时空”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它也把人类的认识和道德实践领域限制在具体时空之间。如果仅仅停宿于此,囿于具体时空之围,并不能显现贺麟“新心学”的独特旨趣的另一面。也就是说,如何才能达到东方(中国)哲学追求的超时空的境界,这才是贺麟“新心学”的真正关注所在,同时也是他与康德的时空哲学的重大分歧所在,这也凸显了中西思想文化在时空哲学上的差异 性。
比较遗憾的是,贺麟在该文下篇中对超时空着墨不多,而且此篇短文是手稿,未曾发表。所以从超时空的角度来研究新心学显得材料并不充分。不过,也留给后人很大的发挥余地。因为西方哲学的认知理性是难以达到宗教意义上的超时空的境界的,所以西方哲学不得不求助于上帝才能实现这个目标。上帝不在时间空间中,相反时空为上帝所创,上帝是超时空的存在。这种思路的实质是哲学宗教化、神秘化,其后果是遮蔽了哲学和科学的理性特质。因此,贺麟认为不受时空尺度规定的纯存在如上帝不能谓之为超时空。尽管贺麟在留学海外之时受过基督教思想的影响,然而贺麟看到了西方思想文化在圆融圆通上的短处,尝试借助中国哲学来推进对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即人能够不借助神而达到超时空的境 界。
贺麟对作为一种形而上追求的普遍的、永恒的“超时空”的内涵做了具体分析。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理解超时空的关键在于知时空。如果人对时空知识不了解,也非超时空。只有人能够研究时空,用理论解释时空,时空是人认识外界的功能或形式。与此对应的超时空也并非无法到达的虚无寂灭之域,而是与人的心、性、知、行密切相关。此外,在贺麟看来,不能以时空次序排列的抽象概念称之为超时空,如数学知识和形式逻辑的三条定律。因此,并非所有“真理”都是超时空的。只有活的真理,感动人的真理是超时空的真理。“超时空的真理是与生活打成一片的真理。”a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第43 页。也就是说,与生活打成一片的真理是一种生活体验,一种生存方式,一种道德实践。贺麟进一步发挥了中国哲学上的道体、性体、仁体思想,它们与体道、识性、得仁是一体两面,不可离分。如果只讲前者,那些不过是一些桎梏人的抽象概念或“抽象统治”,与贺麟新心学所倡导的践行活泼的精神境界相悖。同样从形而上学的视角来看,世间万物都是超时空。万物既在时空之中,又在超时空之中。顶天立地即是说这种具体事物既在时空之中,又超越了一时一空之狭小的自由而崇高的境 界。
由冯契担任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从哲学立场上对贺麟的时空观做了宏观诠释。“新儒家(这里指贺麟——笔者注)思想的哲学把时间空间看作先验的、超现实的理,心中之理或先天标准,认为理是第一性的,而作为物质存在形式的时空,反而是第二性的、从属的、派生的,这完全是本末倒置。超时空的观点,也反映了新儒家思想的哲学宣扬主观唯心主义。”b冯契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1072—1073 页。尽管说贺麟的“新心学”一定程度上宣扬了主观唯心主义,但是批判它的这个理由是不充足的,即这个基本判断并没有抓住问题的症结。贺麟真正凸显的是“心”的第一性作用,而非时空或理的第一性作用,当然“心”的第一性作用仍旧属于“心”之“用”系列,并非是“心”之“体”。通过论证时空是心中之理,贺麟将“心”提到了宇宙万物中主宰的地位,而这个主宰地位是由时空或理来支撑的。贺麟突出了理性的时空标准的地位,其用意旨在生发“心”的理性功能——纯粹理性、实践理性或知、行。但是“心”的理性功能只是“心”之“用”,“心”之“体”仍旧处于未发之前。也就是说,心中有理,并非停留在“心”之“用”上的 理。
“心有二义:一、心理意义的心;二、逻辑意义的心。”c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第1 页。前者的心是物,后者的心才是贺麟要突出的“心即理也”的思想核心。时空只是人认识事物的形式,但是万物的本性并不由时空决定,而是由永恒的超时空来决定。贺麟认为性是一物之所以成为一物的实质,也是一物将要成为现实的理想或范型。“性是永恒的、超时空的,必自超时空的观点或从永恒的形式下观认方可把握。”d张学智:《贺麟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84 页。也就是说,性是具体的共相或共同性中包含着差别性,与西方形而上学抽象的共相有别。仁、义、礼、智、信是人的性质,人与禽兽同样具有其他相同的性质。孟子讲到人性之善端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根本特质,“人性”本身由其特殊性来规定,但是孟子并没有详细解释人性的特殊性由什么来规定,正如朱子所言,“孟子不曾推原原头,不曾说上面一截,只是说‘成之者性也’”a朱熹:《朱子语类》 (第一册),黎靖德编,湖南:岳麓书社1997 年版,第63 页。。“不曾推原源头”并非西方形而上学向前无限溯至世界本原,也非贺麟用后推之“理想”来予以规定,前溯与后推是线性时空观在人性上的体现。也就是说,前溯与后推只能单向度地解释人性的特殊性由什么来规定,特殊性的背后究其根本还有特殊性。朱子借用《中庸》的“天命之谓性”和《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思想,实际上是把人性与天道从整体上(上下、前后)贯通起来,这凸显了中国传统的循环时空观在人性上的观点。人与禽共同构成一个自然界,人性不能规定禽兽,反之则亦然。人性与动物性在天理处相同,但在气质之性上并不相同。理充塞在宇宙自然之中,两者都由理所规定。因此,“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b程颢、程颐:《二程集》 (第一册22 卷上),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292 页。。人的特殊性为理所规定,性只是理的一部分。人的本性(性质)由超时空来决定,理以超时空的逻辑形式存在。因此,情非心的性质,理是心的性质。在朱子看来,仁义礼智是性,四端是情,心依靠理来统性情。“横渠云,心统性情,此说极好。”c朱熹:《朱子语类》 (第四册),黎靖德编,卷第五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版,第1286 页。超时空寓于具体事物之中,所以理在事中而非事外。心具备运用逻辑形式的能力去分析与整理杂多质料的独特潜能,而这种潜能并非外铄而在心之内,显出理在心中,所以心灵能够发现事中之理、心中之理。有学者指出:“贺麟所讲的‘逻辑的心’就是‘心即理也之心’,具有理性和理想,本体的主体性是通过本体的理想性体现出来的。”d李维武:《心理之间:本体的主体性与本体的理想性——以熊十力、冯友兰、贺麟为中心》,载《社会科学战线》2018 年第2 期。与其说本体的主体性通过本体的理想性而体现,还不如说本体的主体性通过本体的理想性而被引导或疏导。贺麟也称他的“新心学”为理想唯心论、道德的理性主义,指引主体把握、超越、改造现实。本体的主体性是本体将要实现的理想,但是本体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逻辑主体的意义上。显然,贺麟的哲学立场并非仅仅突出西方哲学的理性形式或者突出主体的逻辑性,而是以中国哲学独特的理想主义来调剂中和,使得理性生发出“主动力”——心中有理。贺麟心中的理想既可以认识事物之法则,也可以作为改造现实之自由,“故用理想以作认识和行为的指针,乃是任用人的最高精神能力,以作知行的根本”e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第6 页。。心中有理,意味着此心并不局限于、停滞于、执着于哪个事物,这种天性是实现自由自得境界的内在理据。心中有理,理中有心,它是一体两面,心与理不可分离,互相观照,从而得出心与理一的结论。心与理一可以视为“新心学”的基本原则,也是“心之体”的要 义。
贺麟意义上的“心之体”分为两个方向——程朱理学体现为横向的格物,陆王心学体现为纵向的居敬。贺麟的视野也并非局限于用陆王心学统摄、主宰、组织、评判程朱理学,从知识论上“贯通”理学与心学。贺麟的机巧处在于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所诉诸的“心”均是一个“道德本体”,这一“道德本体”将西方哲学中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审美功能融入此“心”之中。因此,笔者部分同意这种观点:“传统哲学有整体而无本体概念,缺乏对时间的本体论视角审视,西方哲学的传入刷新了这一认知惯性,促使中国现代哲学家们转而注重时间之‘体’的探究。”a湛晓白:《民国学术界关于“时间”的哲学认知》,载《兰州学刊》2018 年第10 期。此处,我们以贺麟为例,贺麟确实吸收了西方哲学、宗教的精神注重对时空与超时空的知识论研究,但是这并不必然导向贺麟以时空与超时空做纯粹西方式的本体论研究。更进一步来说,无论是知识论研究,还是本体论研究,这终究是体道、识性、得仁的一种“手段”,并非是贺麟的真正趣旨,贺麟真正的用意是凸显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德本体”,或者更为明确地说是“理想的道德本体”。当然正如前文所言,如果“道德本体”是静止的存在,即便它显示出“真”,那么它就并非真善美的合一。正好相反,这一“道德本体”的良知不断激励并指引着我们对“至善”道德理想主义的追寻,难道我们不能说这种道德实践不是美的吗?因此,可以说贺麟的“新心学”的“心”负重着程朱、陆王、认知理性、实践理性、审美体验、宗教信仰等精神的东西而一路艰难前行。这体现出贺麟在学术上不拘门户之见只求追求真善美的无畏精神与宽广胸怀,体现出他对当时生活的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与真切体会,也体现出贺麟作为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对国家与民族的责任与担当。贺麟说:“惟有精神才是体用合一,亦体亦用的真实。”b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第222 页。心与理融合成为一种精神,文化则成为精神的产物。“新心学”新在以精神为体、古今中外文化为用,这也为儒学的现代化开创了一条开放进取、平行公正的地平线。“新心学”并不排斥外来文化,它主张兼收并蓄,与其他文化展开积极对话,它比传统陆王心学的对话面更广,比牟宗三对外来文化(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心态更为主动开放。“新心学”坚持了以“道德本体”作为出发与落脚处,运用了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对外来事物与文化保持着开放探索的精神和态度,更能引领整个心学乃至儒学向更广的领域拓 展。
贺麟在比较朱熹和黑格尔的一文中认为绝对精神就是理性精神的大全,而太极是理之大全,绝对精神即是太极。c开尔德、鲁一士:《黑格尔:黑格尔学述》,贺麟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284 页。贺麟推崇逻辑的心,主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贺麟所说的逻辑的心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最为接近,不过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贺麟所称的逻辑的心(心与理一)是通过直觉把握的,而不是黑格尔所推崇的从分析的、辩证的方法得来的。此外,作为纯直观形式的时空,并非通常理解的经验性直观。经验性直观有作为质料的感觉,而纯直观没有。但是纯直观都是感性的,即限于我们为对象所刺激的范围内。贺麟通过赋予时空更多主动的、积极的意义,旨在将康德的纯直观形式发展成“发明本心”的直觉法。这也是贺麟在《近代唯心论简释》的书中重点研究时空与超时空的主要原 因。
三、心与理一
“五四运动”之后,在近代中国盛行的西方实证论和科学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注重直觉aintuition 兼有直观与直觉之意,贺麟对直观与直觉,直观法与直觉法没有明确区分,可以通用,即观察中有觉解,觉解中有观察。不过,在汉语语境下,两者之间有些许差别,直观侧重于人在空间性中“观”的动作行为,直觉侧重于人在时间性中“觉”的心理状态。的思维方式产生较大矛盾。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均探讨过直觉这一重要方法。贺麟之所以对直觉尤为敏感并进而发扬之,是因为整个心学体系是从本心、良心、良知这一道德本体出发的,而体认这一道德本体的不二法门在于直觉,从孔子的“为仁由己”、孟子的“反求诸己”、象山的“读孟子自得之”、阳明的“吾性自足”、熊十力的“良知是呈现”等都是如此。理想道德的本体的自明性是由直觉来把握的,不需要借助超出它之外的理性的知识或论据。但是到了明代中后期,心学流弊充分暴露出来。牟宗三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以性体限制心体,但他并不主张用理学加以调剂,因为“朱子言全部实功,合下只能落在格物致知上说”b牟宗三:《心体与性体》 (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403 页。。此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似乎更认可康德所谓“智的直觉”,但是牟宗三理解的“智的直觉”是不借助时空和范畴就能“直指本心”,这显然是陷入了某种唯我论的“意识形态”之中——理性与理想绝对同一。贺麟推崇的直觉恰好是科学地把握这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也就是说,理性与理想是有差别的统一而非绝对的统一,而把握这种有差异的同一性正是借助直觉法。直觉具有辩证性,所以它能够把握对立统一而不褊狭,这说明其理性的一面;直觉具有直观性,所以它能够诉诸道德的直觉、心灵的自由,这说明其理想的一面。贺麟分别考察了中西哲学家对直觉的理解,并希望将直觉由一种个人体验发展成具有一定具体普遍性的方 法。
从“理一”的角度,康德原本希望将感性与知性统一起来,但是对物自体与现象界的二元划分造成了人类缺乏“理智直观”(或译为“智性直观”“知性直观”)的能力的后果,这与其说结果与他的初衷相悖,还不如说为信仰上帝留出地盘。理智和直观是人类具有的两种认识能力,但是各有各的缺陷:直观无概念则显得被动,思维无内容则显得空洞。在贺麟看来,在科学认识活动当中,直觉的思维活动与理性的思维活动是同时并存的,直觉和理智并不矛盾。直觉将理智的分析和综合联系起来,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贺麟认为直觉既是直观的又是理智的,当然这免不了有折中主义或神秘主义之嫌;还有一种疑虑是“直觉方法普遍性不足的问题终将造成其理论困境”c黄信二:《论贺麟新儒学之建构与反思》,载《哲学与文化》2011 年第5 期。。为了打消这些疑虑,贺麟进一步将直觉分为前理智的直觉、理智的分析、后理智之直觉。a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第86 页。这三种分别对应康德的感性、知性、理性阶段。前理智的直觉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感性直观,尽管它能偶然地实现主客统一,但是只能形成混沌的经验而非真正的认识方法。理智的分析阶段超越了具有一定神秘主义的感性直观阶段,它应用形式逻辑方法分析整全事物,具有抽象的思维特征,但是得到的是科学知识而非哲学知识。也就是说,即便理智的分析能面面俱到,不借助直觉,理智也难以体认与表象到宇宙的整全或全体。分析只有与直觉结合才能达到对无限、绝对的认识,否则只是停留在外部反思的知性思维阶段。在贺麟看来,后理智之直觉高于西方哲学的逻辑理智以及中国哲学的感性直观。在这个阶段直觉不仅是对认识论的本身的认识,也是对道德本体的领会——宋儒所说的“豁然贯通的直觉境界”。这也是所谓的“即工夫即本体”,直觉实现了对整全的领会,既能认识到对象,也能体会到认识对象与主体的合二为一。直觉能够实现主客交融、物我相忘、怡然自得、天人合一的超时空境界。因此,有学者认为直觉法恰好是理解贺麟唯心论的关键。b张祥龙:《逻辑之心和直觉方法——〈近代唯心论简释〉打通中西哲理的连环套》,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 年第2 期。
贺麟进而对直觉法做了具体研究,一方面直觉法可分为向内反省、反求本心的方法,一方面分为向外透视、格物致知的方法。c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第87 页。陆象山与朱熹恰好是这两方面的代表。在贺麟看来,与朱子的修养工夫相比,陆象山的方法像宗教家点化世人那样有促使人幡然醒悟的效果。陆象山更侧重尊德性,德性乃人之根本;而朱子更推崇道问学,朱子说:“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之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d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项平父》卷54,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 (第23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第2541 页。朱子通过格物致知来研究“气”的时空属性与形式,这是道问学的一种体现,但是在程朱理学看来,“理在气先”“理生气”,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是一个进阶的层次,道问学归根结底是道世间“天理”、除“过剩”人欲。贺麟更为推崇朱子“虚心涵泳,切已体察”的直觉法,虚心涵泳即勿偏执而无成见地玩味领会,切已体察即将自己融入物中而非站在物外,将物与自己平等地、理智地、同情地对待。朱子的直觉法以文化精神、生命、真理为对象,既能取精用宏、培养品格,也能“心与领会,自然浃洽”,也能细致揣摩,心同理同。此种直觉境界也相近于艺术的直观境界。在他看来,只有朱熹才能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不用无不明”e王国轩译:《大学·中庸》,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版,第17 页。的最高境界。总而言之,贺麟将直觉分为前理智的直觉、理智的分析、后理智之直觉,使直觉的思路本身具有一定的阶段性与清晰性;直觉成为一种审美或艺术方式,需要经过“积理多、学识富、涵养醇”的人生历练;直觉法注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直观与逻辑分析的统一;生活体验与逻辑规则的统一;唯理论的方法与经验论的方法的统一;逻辑的心与直觉的心统 一。
连黑格尔也说:“即使当他只在直观的时候,他也是在思维。”a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95 页。这些无一不向我们证明了直觉法的思辨性。贺麟不仅注重直觉法的思辨性,同时还对辩证法的直观性予以关注,这是一体两面。贺麟将辩证法与辩证观做了一定区分:辩证观是在精神体验中达至对立统一的直观,但是辩证法需要严谨细致的论证,并将此种直观发挥到一以贯之的体系。贺麟认为:“辩证法自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辩证法一方面是方法,是思想的方法,是把握实在的方法。辩证法一方面又不是方法,而是一种直观,对于人事的矛盾、宇宙的过程的一种看法或直观。”b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第117 页。也就是说,辩证法在应用到其他领域、场合的同时也需要运用到自身,这实际上涉及辩证法的本性,而这个本性的“直指”正是借助直觉,否则辩证法本身会陷入二元或多元分裂的境地。首先,贺麟认为辩证法最初的意思是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辩难方法。c开尔德、鲁一士:《黑格尔:黑格尔学述》,贺麟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64—165 页。贺麟认为我们根据日本学者翻译的“辩证法”(Dialektik)应统一翻译为“矛盾法”,他的理由是Dialektik 只是消极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非要“证明”某个命题和假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容易将辩证法理解成两个事物,即一矛与一盾,显然辩证法是指一个事物的两面性或同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或者是超越两面性(两个阶段)的第三个维度。其次,他还认为辩证法以激发世人的道德直觉意识、培养道德人格为目的。他以苏格拉底和孟子为例。苏格拉底善于利用这种“接生法”,通过层层引导,让对话者陷于与自己先前接受的观点自相矛盾的境地,自己主动更正自己的观点,并进而最终寻求关于德性的知识。孟子从人性善出发,揭示齐宣王隐藏的不忍人之心。并通过“牛羊祭祀”的例子,具体展示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矛盾,促使齐宣王意识到自己的仁心并推行仁政。再次,贺麟认为辩证法是追求形而上学的方法。他主要列举了柏拉图的辩证法的例子。辩证法注重对立中求统一,由现象界深入理念界,并最终追求理念界之终极实在。最后,贺麟认为辩证法的最高峰是黑格尔所攀登的,他是辩证法的集大成者。《精神现象学》从逻辑和历史统一的视角考察了精神生活样态的辩证历程。黑格尔的逻辑学即辩证逻辑,实际上是对形式逻辑的抽象性、主观性的超越。在贺麟看来,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确立了正反合的形式,遵循自我否定的规律,具有内在的也是超越的特 质。
物极必反的消极理性与相反相成的积极理性是为一体。前者意味着将辩证法与直觉法看作对立的关系,而后者将其视作对立面的统一关系。贺麟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注重事物内部的统一性,只有辩证法将两者运用到自身上面,它才可真正被称为实现自身。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具有直观性。辩证法的直观性,是一种永恒的范型下观认万物的数学式直观,它超越功利,阐幽显微。直观者在静观真观念中发现自己的本性,坐忘自身。此处的真观念,即贺麟借用的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实体是“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a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3 页。。真观念是关于事物本质的真理性认识。真观念不需要其他观念来证明自身的真理性,也不需要外物与其相符合。真观念是其他观念成为真的基础。对于真观念的认识,贺麟认为我们应该通过直观来认识真观念,直接从最完满的观念开始,由最简单的定义或公理出发。贺麟将逻辑的心当作实体,此实体是通过直觉去把握理性的时空标准而获得的,从而实现了“直觉的心与逻辑的心同一”。最后综上所述,虽然贺麟整个“新心学”在体系上并不系统,但是贺麟在时空哲学上通过直觉最终实现了“新心学”——心、性、理在本体论上的大体统 一。
四、小 结
“时空与超时空”这一章节是整本书的拱心石。它将认识论、形而上学、道德、伦理甚至艺术结合起来,使得贺麟的“新心学”的时空观是一个相对完整而成体系的理论。但是就问题本身来看,贺麟认为理在心中,心中有理,从而得出心与理一的结论,前者的理是理性形式,而后者的理是理想主义。无独有偶,我们从宋明理学史上也了解到,在朱陆之辩中,陆九渊曾经质疑朱子对“无极而太极”的解释,朱子也把“极”解读成两种字意。前者的“极”是形之意,后者是理之意,即无形而有理。如果从“新心学”的立场看,贺麟这一解读实质上是将心之用的理性与心之体的理想“合为一体”,他自然而然地借助了传统中国哲学的直觉法。不过,这种直觉法也吸收了黑格尔和新黑格尔主义的思想资源,将理性思辨与道德直觉统一起来,留给后人对“新心学”做进一步研 究。
当时中国深处于动荡不安的年代,落后挨打的教训产生了全盘西化的“文化危机”,都让他感触颇深,并砥砺思考中国未来的走向。精神是文化之体,他的“新心学”精神准则可以概括为心与理一。它激发了个人意志,激昂了民族精神,提升了国家的文化自信心,这些都尤为可贵!贺麟在一个国力衰微、亡国灭种、文化危机的特殊年代以“新心学”来“背负沉重的历史负担”的方式表达出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这样的精神至今仍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生活在历史上最接近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兴的新时代,我们可以轻装上阵,更为自信从容地去承担历史赋予这一代的使 命!
——斯洛特与王阳明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