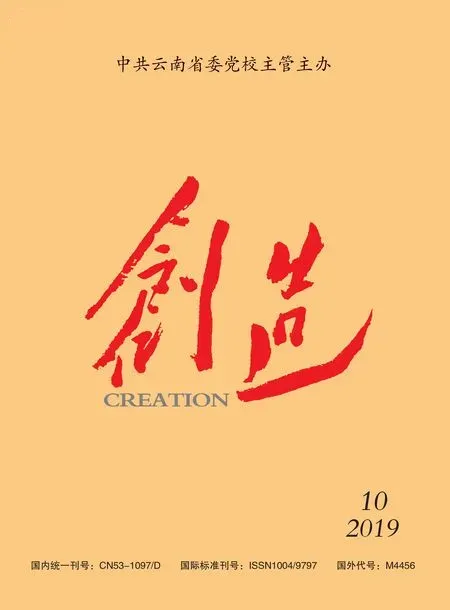从唯物史观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演化
当前中国迈入了新时代,如何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重中之重。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巧妙的运用石榴籽喻指我们的民族关系,提出了对新时代中国民族工作的要求。其中着重强调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把这一重要理论论断写入党章。这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新时代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和谐的内在需求,是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动力保证。
在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对社会意识的研究,也必须以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为出发点。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站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过程和思想渊源,把握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和外延,为做好新时代的民族工作、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
“共同体”所描述的是一个群体概念而非个体概念,群体要存续下去,必须得有一个核心。共同体意识就是这个核心,像绳索一样牢牢维系着整个群体。民族这一概念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人类共同体”,是世代延续,具有强烈认同感的群体,由于同一民族的人们经常生活在同一地域且拥有相同的语言,容易形成命运与共、祸福相依的亲切社会关系网络,所以他们常常具有强烈的痛痒相关、同舟共济的认同感与一体感,这是这个社会实体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即我们常说的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有共同意识的血脉相融、荣辱与共的自觉实体,是一个经历五千年历史风霜锻造形成的“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费孝通先生说过:“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这就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意识层面对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实体的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对社会各方面互通互融的情感认同,是对56个民族守望相助、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认同,这种长期的共同心理认同促使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
一、共同起源:“华夷之辨”的多元统一
一个民族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客观存在的,有着自己的起源与发展。每个民族都会有关于本民族族源的故事、传说,这些故事从情感上支撑着民族认同观念的产生。中华大地孕育了中华民族和优秀灿烂的中华文化。虽其发展过程吸收了许多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但就起源来说,中华文化是完全发源于中华大地的,这一点可以从中华远古人类及其文明中得到证明的。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证明了在我国人类进化可以建立较完整的进化序列。而新石器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文化区的形成可以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新石器时期中华文化主要呈现出多元区域性发展的特点,中国最早的人类文明出现在以旱地农业文化为代表黄河中下游的东西文化区,而以水田农业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东西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黄河上游文化区等,则是以土著文化为基础,吸收邻区文化影响形成的,这些文化区都不同程度的反映文化汇聚和交融现象。其中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其发达的农业,向四周辐射影响着新石器时期的其它文化区,以黄河中游的文化区为主干,中华新石器时期的文化不仅呈多元区域性发展,还具有相互统一、相互交融的特点,尤其在新石器晚期,诸文化区已呈现区域一致的趋势了。丰沛多元的源头文化,为之后形成层次丰富、内涵深蕴、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文明奠定了根基。
中国的历史,是从夏朝之后开始进入阶级社会的,在夏之前的时期,还属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这段时期在历史上称之为远古时期。在有文字记载之前,远古的先民都是通过神话传说来传颂历史的。除了天地开辟、人类来源的传说之外,较为重要的是有关本民族祭祀族神的神话传说。例如洪水过后伏羲与女娲兄妹成婚的传说,不仅在汉族流传至今,在我国南方的苗、彝、布衣、黎、水、拉祜、侗等其他少数民族中也有传说。这种类似的情况不计其数,这说明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民族文化重合区,这是中华大地各民族长期经济文化交融的结果,虽各有特色,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推动者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
同一演化过程会形成两个不同的侧面,远古时期的各部落相互斗争的结果,是导致这些部落的分化与融合。以炎、黄为代表的黄河中下游部落与两昊为代表部落在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夏、商、周三族,而三族在经历夏、商、周的历史发展后,相互之间的融合不断加强,逐渐形成华夏民族的雏形。另一方面,黄河中上游的一些部落向着黄河上游的甘青大草原发展,生活方式慢慢由原始农耕转变为游牧,经过历史的不断发展,形成了后来的西北氐羌民族。而另一部分则由西北向西南迁移,受环境影响,孕育了各具特色的氐羌苗裔。至于夏商周时期的东夷各族,则是由两昊集团中位于泰山以东至海的各部落发展而来。
到了西周晚期,随着西边戎狄势力的不断崛起,对中原周王室的侵扰和掠夺日益加深。血与火的教训,使中原的华夏民族意识到华夏的生存与周边的蛮夷戎狄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从此时起,华夏与蛮夷戎狄间开始有了明显的界限。春秋战国时期,“尊勤君王,攘斥外夷”[2]“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3]“裔不谋夏,夷不乱华”[4]等主张,都是基于周王室的衰落,四方势力不断入侵,华夏文明受到威胁之际产生的,华夏诸族强调华夏在文化体系、礼仪制度上的完备性和优越性,主张“以华变夷”,用华夏的文化礼仪去影响蛮夷的文化制度,把四方之民纳入华夏文明的范围内。“华夷之辨”是诸夏在面临共同外敌威胁时所产生的维护华夏文明的民族意识,其主张学习华夏先进文化,抵制落后的蛮夷文化的思想,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当时影响巨大。正是有了这种强大的民族意识,才能使华夏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屹立不倒、绵延不绝。
二、共同孕育:“大一统”背景下文化的交融与汇聚
“华夏”概念是不断扩大范围的,它既是时间概念,也是空间概念。春秋时期,华夏这个称号是相对于诸夏而言的,华夏即周天子亲戚封地所居地,而战国,由于诸侯争霸,七雄也并入华夏范围,这时华夏相对的就包含了“四夷”,即周边少数民族,这时华夏不仅有空间概念,也包含了时间概念,即现实与原始,中原拥有先进的现实文化,而少数民族是落后的原始文明,但两者又可转化,中原通过教化,可把少数民族同化,这时“华夏”这个概念又会与新的空间相对。春秋战国的500年,是华夏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育成时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而告终。
以秦朝为开端至鸦片战争,横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是中华民族一体性自在发展的历史阶段。这段时期,中国经历了两次大分裂,而每一次分裂都会促成以南北为界的众多民族的统一,从而将多民族的矛盾冲突转化为两大王朝的对峙。进而一方胜出,襄括另一方,实现更高层面的全国性的大统一,因此,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下,民族之间相互融合更为常见。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中,思想观念层面也在逐步融合。抗敌卫国的古典爱国主义也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得到了认同与发扬,最终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形成与确立。在这段历史时期,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开端、发展、确立,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属于开端时期。秦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从此统一的格局成为了历史的主流。从秦到汉是大一统形成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皇帝”这一称号、以郡县制为主体,民族地区为边裔的地理观等,都包涵了华夷一统的含义,在这种统一的历史趋势下,华夏民族经过融合与发展,逐渐演变为汉族,并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称谓一开始都为“他称”,但根据语境的不同,受政治、政权、民族迁徙的影响,最终转为“自称”。在汉代及其之后的华夏族和周边外族人的接触中,产生了“汉”这个族名,汉人也已事实上形成一种民族实体。汉族的形成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核心凝聚力,对此后中华民族的产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的少数民族迁移到了中原地区,其中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主,并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地方政权。这些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开始改牧为农,与当地的汉族杂居相处,逐渐融合。特别是到了北魏时期,十六国分裂局面得以结束,民族融合之势不断显现。孝文帝继位后,开始进行汉化改革,通婚、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话等措施,加速了习俗易化的过程,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从“五胡十六国”到北魏,虽然国家的掌权者大多为少数民族,但为了在政治上维护自身的统治,都沿袭了前朝制度中的农牧民族“胡汉分治”,以小农经济为立国之基,以汉文化为主流思想,这说明历史是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并不会因为少数民族成为统治阶级而被阻断,相反,在促进农牧两大类型民族的统一与农牧文化相融的基础上,不断促进和巩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历史的完整性,不断得到促进和巩固,并最终达到更高程度的融合。这体现了中华历史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传统,同时也表明,“华夷一统”“华夷共祖”的思想一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中持续着、实践着。
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发展时期是到了隋唐。唐王朝的繁荣是建立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的。在当时,朝廷并不只有汉人统治,由于唐朝开明的用人制度,唐人中很多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不断被唐涵化。其次,制度影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唐朝极为推崇州县制度。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的羁縻府州制度便以这种制度模式为基础。《新唐书》中就说到:“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5]“中华”一词,最早起源于魏晋的天文学, 《唐律疏议》 中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6]本意为,只要在文化意识、礼仪制度上认同中国的,都可谓之为中华。这时中华既指地域名称,又作为文化与民族的称谓。此外,西藏的统一与吐蕃的兴起,表明中华民族在这个阶段获得了重要发展。唐朝与吐蕃关系的发展,不仅留下了文成公主入藏的美谈,更是夯实了西藏成为中国版图一部分的历史基石。
辽宋时期,边疆王朝众多,其中以南诏、西夏、辽等为代表,虽雄踞一方,有较强的民族独特性,但其上层建筑却是仿照两宋的,不仅在政治上宣扬“华夷皆正统”的思想,在文化上也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到了13、14世纪,元朝统一了中国,由于推行行省制度,全国的民族地区都置于中央的直接管理之下,这时中央通过开垦荒地、人口迁移、商业互通等在各民族地区形成了一个点线相连的网络系统,把边疆地区的各民族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整体和大一统的格局。不难看出,这一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呼之欲出之势。明清时期,中国不仅有了明确的国家疆域和稳定的地理边界,还形成了明确而稳定的依据不同民族、文化、地域等特点,以不同政策行使管辖的地方行政制度,在大一统格局中以不同社会习俗生活的各民族,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这一认同的实际情况,不仅在皇帝的训诰、大臣的奏议、私家著述、乃至词书及国际条约等都已得到反映。”[7]如清朝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 已呈现主权国家之间划界国际条约的水平。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各民族祖国观念的民族意识开始显现,东南抗倭斗争、郑成功收复台湾、雅克萨反抗沙俄入侵者等活动,都表现了中华民族爱本民族与爱中华民族一致统一的古典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中华民族民族意识一体性形成的萌芽阶段。
从秦到清的两千年间,中华各民族的内在联系不断得到发展,民族一体性不断得到加强。只是由于当时没有一个强大的外部力量对各民族共同利益进行威胁,所以中华各民族尚未自觉的意识到这种内在的一体性。但当帝国主义开始显露瓜分中国的野心时,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的民族认同意识,就在帝国主义这种外部威胁面前觉醒了。
三、共御外敌:从自发到自觉的联合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我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是求生存、求独立、求解放的近代史开端。从1840年到当前,是中华民族从自发到自觉联合的历史阶段。
近代以来,西方通过资本主义革命,建立了以单一主体或数个民族为国家主体的民族国家,这不仅使得民族国家发展为世界主导的国家形态,同时也使得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高涨。中国自秦以来,就一直以封建主义中央集权作为王朝国家的国家形态。当现代西方民族国家遇上传统的封建王朝,传统的东方大国必然面临着变革国家制度的抉择。对于2000年来未被外来文明隔断、具有超强稳定性的中华文明来说,放弃原有的封建礼制,融入时代潮流显得并不容易。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华民族深感中国正遭遇严重的民族危机,变革图强的民族认同感空前高涨,民族意识觉醒的中国开始了民族国家的构建。
从1840年到1919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华民族由自发到自觉发展的历史过渡时期。这一时期,近代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较上文所述的古典爱国主义精神已有了显著的变化。从开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早期的变革者认为只需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即可,不需触及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但甲午战争的失利,北洋水师尽数毁灭的惨痛教训,使得变革者认识到只学技术是行不通的,所以维新派以“戊戌变法”登上了历史舞台,为此,光绪皇帝颁布了数道诏书,以求变革腐朽的封建制度,虽然百日维新最终以失败收尾,但这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民意识的觉醒。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写到:“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这是“中华民族”一词的首次使用,但当时梁启超对“中华民族”一词的内涵界定并不清晰。在之后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先生对“中华民族”的内涵又进行了补充,他认为中华民族不单指一个民族,而应是由多个民族混合而成的,“中华民族”具有多元的特点。他认为只要遇到别的外族时,“我是中国人”的思想能够在脑海中马上浮现的人,一定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这使得“中华民族”一词,不仅在内容上得到丰富,在层次上也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一论述是梁启超根据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契合了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的愿望,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来源。
1905年,同盟会成立。在其纲领中,“中华”再次成为政治标语,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句话取意于明太祖“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所表达的华夏民族意识。这时候的“中华”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而是特指华夏族。但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先生明确了当下社会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对峙,对“民族”一词又有了新的诠释,他在1924年发布的《关于建立反帝联合战线宣言》中呼吁世界被压迫民族一起“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之掠夺与压迫”[8],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同时,区别于此前“反清”“排满”的思想,孙中山还提出“五族共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主张,将合在一起的国家政治共同体称为“民族”,而各族群则称之为“族”,把汉、满、蒙、回、藏等中华各民族视为同呼吸共命运的统一整体。随着国内反帝反封的矛盾斗争的激化,中华民族日益自觉地结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而中华民族实际上包含中国各少数民族、中国各民族在根本利益上具有相同性和密不可分的联系也不断被彰显。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合力抵御外敌,共同保卫了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在此过程里中华民族意识也逐渐从一个自在意识转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伴随五四运动,我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时也开启了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新篇章。十月革命的胜利,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得到传播。革命先驱李大钊对于患难与共的中华各民族命运共同体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要从国家政治层面积极塑造独立的中华民族精神,在处理民族问题上要坚持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分析了世界各国在社会运动中联合的历史实践,肯定了中华民族联合的可实践性,号召中国各民族效仿他国成功的例子,达到中国民族的大联合,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这些思想为之后革命斗争中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国人“命运与共”的民族意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得以增强的。这也使得“中华民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由于中国共产党贯彻1924年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新“民族主义”,强调中国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提倡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主张在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各民族团结一切力量抗日救国,使得全体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加强。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揭示了近代中国的民族革命是:为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国内的民主革命则要:反对民族压迫,达到各民族平等。在这之后,又提出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道路是:在中国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之后,在民族地区实行统一的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样不仅从纲领层面,还从政策层面以及道路层面等,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升到理论高度,也标志着民族意识发展到了自觉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华全民族抗战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同时也为今后我国的民族团结工作积累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共同发展:铸牢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中国成立至今,是中华民族在获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之后,民族共同体意识蓬勃发展的历史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称号已经包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含义了。除此之外,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后,为实现我国各民族平等,党中央组织专业团队对我国境内的民族进行了民族识别,近30年的民族识别工作,实事求是地确定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属性,给予了历史上那些长期遭受民族剥削、民族压迫的少数民族受法律意义保护的民族身份。这一工作不仅确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体成份,还在很大意义上,强化了各民族对本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感。同时在各民族地区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平等权利与地位,极大的满足了各民族参政议政的需求,增强了各民族的主人翁意识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改革开放以后,各民族在党中央的带领下物质生活不断提高,同时党中央针对民族间的关系问题提出的“三个离不开”思想开创了解决中国实际民族问题的中国特色方案,赢得了各民族的拥戴。1988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不仅为当时民族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对此后我国处理民族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现代化的民族国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在党中央的带领下,我国各民族空前团结,但国内外的反华势力依然威胁着我国的民族团结稳定,国内民族问题依然存在。2014年5月,习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各民族树立“四个认同”的要求。紧接着,在同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着重强调了培育这一意识的重要性。2015年,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在此前“四个认同”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即: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中,习近平站在历史发展的新高度,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表述,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内涵,同时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者的新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从“自在的民族意识”到“自觉的民族意识”再到现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中华民族从历史到现实的认同过程。这个历史过程说明了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是由56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进行民族融合所创造的,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当前,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处理好“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还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以“五个认同”为基础,推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