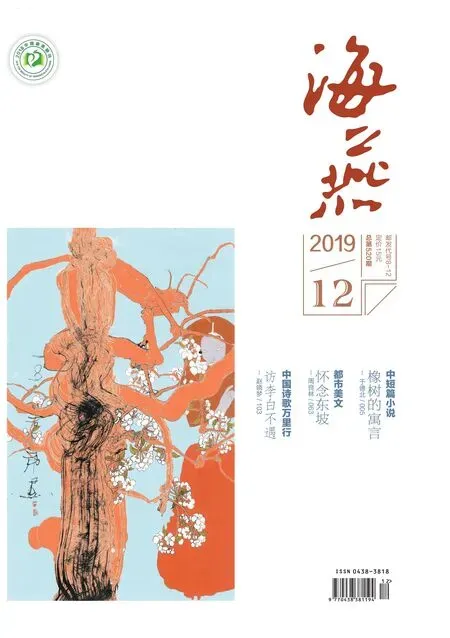简省与物恋的美学合唱
谈到梁久明和他的诗,不能不谈及鱼米之乡对他的滋养。三肇之地,历史文化传统悠久,江河带来的农耕文明由来已久,这些催生诗歌创作的因素极为重要,在此不再赘述属于诗歌地理学的事。
诗人梁久明的气质恰如“人淡如菊”,他黑瘦、清矍的模样更像深秋的老向日葵了——外表朴实自然而将灼灼其华藏在壳里,蕴含着岁月的幽香。梁久明默默地读书和写诗,不主动邀名逐利,也不故作诗人通常身挟的狷狂、任性。他更愿意冷眼旁观,一个人置身大自然,凭一辆单车丈量世界。他却不是遗世独立,还是深深爱着生活,愿意做一个美的歌唱者。梁久明不算谙熟世事,却活得通透,偶尔从嘴里迸发出些许幽默的语言,显示了他面对生活的达观心态。
梁久明的诗歌创作有着三十多年的积淀,公开出版了两部诗集。诗集《从1963年开始》多以记事为主,写的是 “人事”;诗集《土地上的居住》多以描物为主,写的是“物事”。人事与物事的交融,囊括了他诗歌写作的全部精神指向。细心打量,梁久明述写人事、描摹物事的致思基点不在当下,而是回望“过去”。与史家笔法不同的是,诗人其意不在展现真实,表现心理上的履痕才是核心所在。历史一旦发生结束,对它的任何描述都有主观性的色彩。若说梁久明的诗歌与历史的触碰,当是在“似真”与“拟真”之间徘徊。完全地再现真实,先是一厢情愿的徒劳,再是费力不讨好。这就涉及诗人如何处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因为历史本身就是现实之一种。林莽先生在写给梁久明的书信中认为:“梁久明的这部诗集不光是具有诗歌作品的审美价值,同时具有独特的社会学价值,它是一部有人文价值与文学品格的诗歌作品集”。
大抵概观,梁久明写自己历经的“人事”,在艺术上可总结为“小”“轻”“真”。以细小来表现宏大事件,这让久明的诗歌更容易切近历史;小切口,大视野,这种视角增多了诗歌的人间属性,也增添了诗歌的艺术魅力。轻,在梁久明诗歌里是一种音调,就像讲述者轻柔的嗓音,但这更是一种艺术态度——化沉重为轻逸;苦难常成为诗歌表现的主题,而“诉苦”的方式极为关键,惟其如此诗歌才能感心动耳撼人魂魄。艺术上高度自觉的诗人肯定会使出浑身解数来实现艺术的“轻逸”,梁久明的诗性努力有三:一是减轻词语附带的重压,也就是拒绝使用圣词大腔,尽量使用个体语言方式;二是在讲述口吻和叙述基调上不滞重,也就是不装神弄鬼,尽量自然地说话;三是革新形象上的象征意义,也就是不人云亦云,尽量客观地复现真实。以上三种,在诗集《从1963年开始》俯拾可见,有兴趣者可从这部诗集中一一寻觅寻找例证。
梁久明在讲述历史事件时常求“真”,借助轻度叙事和场景描述,他乐于吹去事物上面的灰尘,显露事物和事件本身的光影;而将“真实”当做“镜中之物”来描摹,类似画影子的笔法,使得久明的诗歌空间张力强大。梁久明不是照相机式的诗人,他不光亮出事物的骨头和血肉,还坚持追索灵魂的声音。他不是歌咏其时,也较少在现场当即发声,用的方式类似小说的延宕或悬置。延宕是润滑剂,抚平急于和盘托出、一览无余的毛刺;悬置则是增能剂,为主题增光添彩。这实际上是梁久明突破诗歌体裁局限的一种艺术化的努力,它增添了诗歌的阅读性。梁久明一直关注中国诗坛的好诗人与好作品,他也一定从中学习了诸多要义,但是,写作永远必须带着鲜明个性化的风格;诗人写作时当抛弃熟悉的写作前史路数,克服影响的焦虑,尤其要克服一上来就主题先行诗歌言义的重压。梁久明的诗歌有进入自由之境的翅膀,让翅膀飞起来首先要“减负”,就是在诗歌言说中淘汰渣滓。《筛谷子》一诗表层意思极易理解,也可视为诗歌创作的汰选过程的隐喻。促成这首诗作的质素在于诗歌的减法的应用。诗歌中的“减法”,就是去掉多余皮肉,亮出骨子里的银白,以少量文字描写来求取含蓄和韵致。郑板桥画竹主张削尽繁冗,并在画作上题诗“敢云少少许,胜人多多许”。优秀的诗歌并不提倡写出事物全部的实存关系,而“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则成为一个诗人走向不凡与自信的标志。是的,梁久明就是这样拥有自信的诗人,天性的阔达与思索得来的睿智共同玉成了精神品格。
实现如上的诗意与诗艺,梁久明走的是与众不同的路子。与浸淫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诗写者迥异的是,梁久明更注重整体上的陌生化效果,表面上看放弃了词语选择、意象锤炼,读来轻松而平常,却深藏了一种“智”。别的诗人在文字的花拳绣腿上耗费无穷精力,终究泯然于千诗一面,而梁久明注重“练眼”,从不同侧面打量同一事物。别的诗人选择唯陈言务去,梁久明唯新意才求。故此,梁久明的诗作佳句难以句摘,浑然一体的诗意是常态。他的诗歌总是在搜求富有原始感觉和诗性特征的灵感。梁久明常常以意为先,而后组织的整体象征极像有灵性的艺术言说。他将意象的选取放在物象上,颇似“缘情造景”。故而他的观景揽物,着力点是主观“物态化”。非要从他的诗歌中剥离出来的“意象”,其实是梁久明主体心灵的客观对应物。他的心灵强大而无拘无束,象征意象也随之而动,万物“为我所用”。梁久明诗歌并不热衷描述外部世界,更愿意呈现心灵世界的广袤。他的意象往往不单是对外部世界的直接观察、感知得来的,而是对主体心灵的自我认识后,寻找客观对应物而得来的。明代王世贞所说的“外足于象,而内足于意”,时常为梁久明活用。尽管梁久明真的频繁踏入旷野,与自然风物毫不相隔,但他的诗作读来并非古代田园诗那般恬静,而裹挟着强烈的主观化色彩。这里的艺术效果要求的不是机械的“再现”,而是充满主观化的“表现”。
借助整体主义,不断制造惊奇感,这是梁久明诗歌的魅力所在。诗歌只有不断制造惊奇,才能挣脱日常的无意识化和自动化心理。正如华兹华斯推崇诗的目的主要是给庸常事物“加上一种想象的光彩,使日常的东西在不平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面前”,梁久明绝不轻易说出赞美,他表现的日常实际上是艺术化后的日常。去蔽,是梁久明多年的诗性努力,也就是竭力打破习惯的麻木性,唤醒超自然的感觉。诗集《土地上的居住》不断刷新既定的经验,前置主体的感受,从而获得全新的审美经验。

梁久明诗中的“物事”描述,始终围绕“物恋”做心灵的环绕运动。“万物美好,我在中央”,梁久明对乡村风物的观察一如既往。久明擅长做静态的摹写,即让观察对象由“心入于境”而抵达“神会于物”。作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一直身在学府教书育人,诗歌地气丰沛,想象方式几与农人一般,却不能说他具备原始思维,称为仿原始思维更为贴切。他注重在大自然中找寻独立自由的精神。复归,不是单向度的遐想,而是身心历经淘洗后的领悟,重新确立熟悉事物上的意义。
综上,梁久明不跟风诗坛流行的写法,而是坚持与乡村物我同哀,做一个乡村的咏叹者。他诗歌所达到的精神高度目前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确认,这有待于时间的慢慢淘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