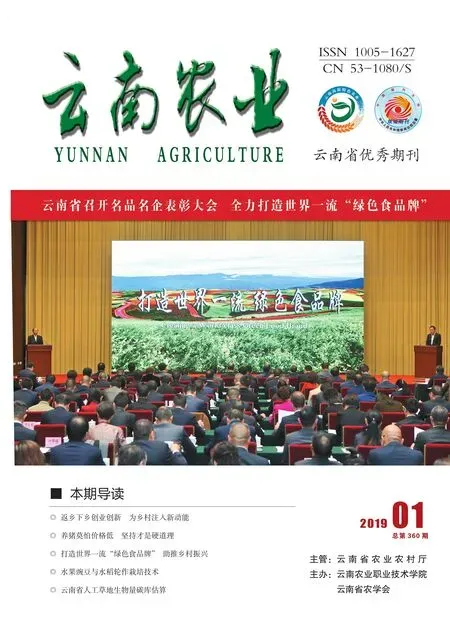鱼趣
子 心
我于鱼的兴趣,仿佛记事时就开始。小时家门口有条河,天晴时清澈见底,有各种叫不出名的小鱼。上小学前我只能或蹲或站在河边,看着哥哥姐姐们在河里捉鱼,尽享其乐。我能独自下河捉鱼,始于10岁左右,小学三年级吧,四五年级时尤好之。暑期白日里的时光,大部分都在村前屋后的小河边、水塘里度过了。便是学期间放学后,许多的时光也被耗在河塘里,为此没少被父母训斥。
那时捉鱼我用得最多的方法是“溜鱼”。 “溜鱼”的主要器具是“溜床”,我只在老家见过,小指粗宽的竹棍或竹片,用麻线串编起来,就像古时竹制简书,只是要长些。7、8月,雨天是最好的,在河堤两岸支三根木棍,顺流第一、三根低于水面一个拳头,沿第一根上游往河里填上土块,以木棍为水平,筑一个土坝;第二根水平要低些,低多少要根据水流大小确定;将“溜床”平铺在第二、三根木棍上,水流会带着鱼儿从土坝流到“溜床”上,水流落下,鱼儿留在“溜床”上。几个小伙伴,蹲在河岸,满怀期待地盯着“溜床”,突然看见鱼儿蹦蹦跳跳地落在“溜床”上,迅速扑过去,把鱼儿抓到竹篓里,要是晚了,鱼儿就会蹦跳到“溜床”外或逆流游走,满怀的喜悦瞬间会被冲涮得干干净净。除了晚餐时可以享受爽口的酸辣鱼,急切的期待、短暂的兴奋、悠长的满足,这样的心理感受大概是我小时喜欢“溜鱼”的原因吧。
除了“溜鱼”,还有其他方法,但都没有“摸鳅”有趣。顾名思义,“摸鳅”就是用手摸抓泥鳅。滇西老家,夏种过后刚移栽完水稻秧苗的田块,如镜的水面下,大大小小的泥鳅都从软软的稀泥里,赶集似地冒出来,享受这暖暖的阳光。如我这样的“摸鳅”人,绕着田埂走一圈,看到人来,泥鳅们纷纷嗖嗖地钻回泥里,水面一阵骚动之后,泥面上留下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洞眼。下到田里,用食指从洞眼顺着泥鳅钻出的路径摸下去,指尖碰到泥鳅,连泥带鳅捞到盆里,滑溜的泥鳅便成为囊中之物。现在想来,这活技术含量很高的,关键看手指的敏感度,能否感知水与泥阻力轻微的不同,探寻到泥鳅钻洞的路径。记忆中全村没几个人能做到的,我行,但成功率不高。
这样捉鱼摸鳅的快乐时光,进中学后就越来越少了。大概是年龄大些了吧,或是乡村药肥用得多了,鱼呀鳅呀已不多见,又或是河塘少有人清理,杂草丛生,找不到儿时的情趣了。
大学时值守实验室,捡回丢弃的干燥器用作鱼缸。到花鸟市场买几条狮子头回来,用放置过夜的自来水,再去校园的池塘里寻点水草,连同金鱼放入鱼缸,摆在书桌一角,常被来访的同学羡慕不已。大概一年多光景,鱼死了又买换了三四次,终于因金鱼的频繁死亡更新而放弃。其间有同学跟我说过“养鱼先养水”的道理,只是那时二十出头,没有理会此言的意义。
参加工作若干年,住房条件慢慢改善,买了个大的鱼缸,配有灯光、过滤等装置,买了消毒剂等。冷水鱼、热带鱼,狮子头、锦鲤,还有各样的水草,换了一批又一批,常为换水、洗缸、清杂忙得不亦乐乎,但始终不得其法,没有一批鱼儿能持续养上半年,想来还是“水”没养好。
年近天命,闲暇时光多了不少,养鱼的兴趣又在心底滋生。趁着房子再次装修,请师傅在空余地面上做了个鱼池,垒了座假山。查询了各种资料,去花鸟市场买了水泵、过滤装置,还有消毒液、消化细菌等等。按各类器材、药剂使用说明,经过一段时间摸索,补水、清池、投食、添药等摸出了规律,鱼池的水不再发绿发青,这才买了十余条锦鲤放入池中。这样养了一年多,鱼儿一条没死,还长大了不少。每每在家,我会在池边坐坐,看着各色的鱼儿自由的游弋,觉得自己也变成了鱼儿,安安静静地、自自由由地、彻彻底底地做回了自己……
此时我想我是终于明白“养鱼先养水”的道理了。
其实,养鱼是这样,谋事育人又岂不是这样,环境好了,人能育成,事能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