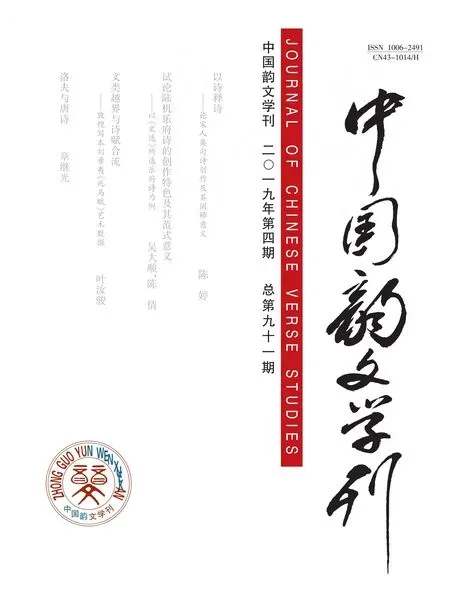论谢元淮的词韵观
杜玄图
(内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四川 内江 641199)

道光二十八年(1848),湖北松滋人谢元淮编成《碎金词韵》四卷,附刻于其《碎金词谱》十四卷之后。该书与戈载《词林正韵》同属于“十九韵部”派系,且比戈韵晚出28年,堪称清代词韵殿军之作。《碎金词韵》集中体现了谢元淮独特的词韵主张,编订中,谢氏充分吸收前代诸家编韵特点,但就对后世的影响力而言,谢氏韵远不及戈载《词林正韵》。相较于《词林正韵》,《碎金词韵》有何特质?谢氏是如何将其词韵主张融入韵书编订中的?这些都值得探讨。挖掘谢元淮词韵观,不仅有助于明确《碎金词韵》在词韵史上的地位,而且一定程度上能窥视到清末词韵的独特状态。
谢元淮的词韵观集中地体现在《碎金词韵》中,部分观点和论述散见于其词学论著《填词浅说》和《碎金词谱·凡例》。通过考察,谢氏词韵观大体可归纳为三。
一 “古无词韵”与古词用韵有一定标准
古无词韵,非曰古词无押韵特征或无用韵标准,而是指两宋以来,填词选韵并无可供参考的词韵专书或词韵规范。此论由来已久。清初沈谦编订《词韵》,毛先舒为之作序,即称“近古无词韵”,谓元代周德清所编《中原音韵》“曲韵也”。而明代谢天瑞《新镌补遗诗余图谱》《乐府通用中原音韵》和胡文焕《文会堂词韵》,“稍取《正韵》附益之,而终乖古奏”。称“索宋元旧本,又渺不可得”,即宋元以来并无指导时人填词用韵的指南。继之者,邹诋谟云“词韵本无萧画,作者遽难曹随”,仲恒、戈载等亦称“古无词韵”。
谢元淮编订《碎金词韵》,承前人“古无词韵”之论,并对前代所传《词林韵释》的性质加以考辨:“今所传宋绿斐轩《词林韵释》刊自绍兴二年,为最古。然考其分韵,与元周德清《中原音韵》相同,以上去入三声配隶平声,仍是曲韵,非词韵也。词韵平声独押,上去通押,间有三声通押者,而入声断无与平上去通押之理。绿斐轩韵与宋沈义父《乐府指迷》符合,似专为北曲而设,恐系后人伪托,非真宋本矣。”与前人观点相同,谢氏所谓“古无词韵”,亦指宋代本没有词韵专书,此前所传宋代词韵书不过是后人所撰曲韵书。旧词并无统一的选韵指南,在清代已是不刊之论。
前代既无可资参考的词林旧典,如何编韵,便成了清代词学的重要课题。词韵是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树立统一的填词用韵规范,是清代词学发展中必要的一环。在复兴词坛的时代背景下,清人言词必宗宋。于是,诸家多主张以两宋旧词的用韵情况为依据,“古无词韵,古人之词即词韵也”。清人通过考察旧词用韵发现:“古人用韵非必尽归画一,而名手佳篇不一而足。总以彼此相符灼然无弊者,即可援为准的焉。”至此,清代编订词韵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旧词“灼然无弊”的用韵标准中达到了统一。
谢元淮继承了前人主张,认为宋词是有一定的选韵标准的,这一标准虽未呈现于古人某一词韵书或词韵指南中,但隐然存于宋代作词者的头脑中。在谢氏看来,据该“标准”,“词韵平声独押,上、去通押,间有三声通押者,入声断无与平上去通押之理”。当然,就其“入声”之论而言,显然有违宋词的实际情况。因为受方音、取便等因素影响,宋词用韵存在着阴声韵与入声韵相押的现象。鲁国尧先生曾“对现存宋词两万首作了穷尽式的搜辑,得阴入通叶约70例”,涉及的入声字有116字,使用194次。万树、戈载、王国维、夏承焘等人早已讨论过这种现象,如戈载:“曲韵不可为词韵也,惟入声作三声,词家亦多承用。”并于《词林正韵》阴声七部后附“入声作平声”“入声作上声”“入声作去声”例,以反映旧词中的这类“例外”通叶现象。
谢元淮也注意到了宋词中的入声与三声相押的实际情况,便于《碎金词韵》入声五部之外,另立“入声作平声”“入声作上声”“入声作去声”三类,附于韵书之末。谢氏“入作三声”的安排与其“入声断无与平上去通押之理”之论看似自相矛盾,实则二者完全出于不同的考量。一方面,“入作三声”的安排出于便览旧词的需要,旨在“庶览者一目了然”,同时,也是对旧词实际用韵“例外”的尊重。另一方面,与“入声断无与平上去通押之理”之论相合,入声分作五部,犁然有别地体现于其十九韵部中。此举完全出于制定统一用韵规范的需要,“规范”不允许有“例外”的存在,必须对纷繁复杂的用韵加以人为的整合。就旧词错杂的用韵情况而言,其“例外”者,不过少数,大体上还是有一定之法。就人为整合而言,亦当有所依据。
韵部分合方面,谢元淮的“整合”依据主要是通过梳理诗韵、词韵和北曲韵关系提出的。
二 “以诗韵为准”与融合北曲韵成分
谢元淮认为诗、词、曲三体是一脉相承的,其用韵也有相承的关系。在诗韵、词韵和曲韵关系的梳理上,谢元淮主张“词为诗余,填词自应以诗韵为准”,基于此,在对诸小韵的整合方面,谢氏注重参考诗韵。最终,其《碎金词韵》“合之为词韵,分之仍诗韵也”。同时,“曲为词余,自应用词韵”,谢元淮认为词韵与曲韵一脉相承,曲韵源自词韵,两者必有其可通之处,故其“入声字作平、上、去三声,则从元周德清《中原音韵》”。
当然,在“尊体”的时代背景下,清人同时强调诗、词、曲有别,即所谓“词之为体,上不可入诗,下不可入曲。要于诗与曲之间,自成一境。守定词场疆界,方称本色当行。至其宫调、格律、平仄、阴阳,尤当逐一讲求,以期完美”。故词韵不可径以诗韵(平水韵)、曲韵(以《中原音韵》为代表)为之,不然,词之体无存。因此,探讨诗、词、曲相承关系的同时,谢氏还强调三者用韵的差异。“词韵异于诗,曲韵又异于词”,“词韵与诗韵不同,曲韵又与词韵有别”。词韵与诗韵的差别,谢氏认为主要在于“近体用今韵,不许稍有出入;词韵则三声互叶,上去并押,已较诗韵为宽”。词韵与曲韵的差异,谢氏认为在于“词韵宽于曲……词付歌喉,抑扬顿挫,其板眼不必定在押韵处,是以三声通押。北曲本弦索调,字多声促,与今之弋阳梆子、二簧等腔,筋节略相类。故押韵处亦严,此《中原音韵》之所由作也。至若南曲,声调宛转悠扬,一字有下数板者,读之知其有韵歌之殊,不以韵为断也。”从前述谢元淮考辨《词林韵释》是后人所撰曲韵而非词韵,以明确“古无词韵”之论,也可以看出谢氏是不主张径以曲韵为词韵的。
所以,谢元淮在处理词韵与诗韵、曲韵的关系时,只是将部分诗韵、曲韵成分融入词韵编订中。曲分南北,谢氏认为北曲更重韵,故其曲韵的融入主要体现在北曲上。
诗韵成分的融入,主要表现为使用平水韵标目和部分韵部的整合。标目使用上,不同于《词林正韵》和《学宋斋词韵》,谢元淮借鉴沈谦《词韵略》和仲恒《词韵》韵目标法,以平水韵韵目为基础,舒声十四部取平水韵平、上二声的第一个韵目字,入声五部则取平水韵入声的前两个韵目字,以“××韵”的形式标目,如“东董韵”“江讲韵”“屋沃韵”等。使用平水韵目,必然导致以平水韵为词韵编订的基本单位。所以,在词韵韵部的整合上,就无法考虑到某一平水韵下所辖206韵在旧词用韵中的实际所属。如平水韵“元”韵包含《广韵》平声元、魂、痕三韵,除少数例外,两宋旧词中多以魂、痕二韵与真、谆、臻、文、欣五韵相押,以元韵与寒、桓、删、山、先、仙六韵相押。谢氏既以平水韵为基本单位,在处理这种情况时,只能将“元”韵分半割用。以已合并之韵,重又割半,看似多此一举,实为其主张融入诗韵成分使然。当然,谢元淮融入诗韵成分,不排除与沈谦有相同的考虑,使时人“只需熟悉诗韵……便能满足创作用韵的需要”。
北曲韵的融入,主要体现为平分阴阳和以《中原音韵》“入派三声”整合词韵中的“入作三声”。
“入作三声”方面,就旧词实际用韵情况而言,确实存在舒入相押的现象。如宋柳永《尾犯》“夜雨滴空阶”一词,全词以“索、貌、落、却、诺、约、酌、博”为韵。其中,“索落诺博、却约酌”分别为入声铎、药韵,“貌”为舒声(去声)效韵。这种舒入相押的情况,在两宋旧词中虽然只是个别现象(谢元淮《碎金词谱》《碎金续谱》中收旧词859首,仅5首舒入相押),谢元淮在编韵时还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认为应当以附“入声作平上去三声”的方式体现出来。柳永《尾犯》中的舒入两类韵,在《碎金词韵》中,前者属觉药韵,后者属萧篠韵。所附“入声作平上去三声”部分,“索”作上声,字音“桑早切。又桑蟹切,入蟹韵,又思寡切,入哿韵”;“落”作去声,音“郎到切。又郎播切,入箇韵”;“诺”作去声,音“囊到切。又囊箇切,入箇韵”;“博”作平、上二声,音“巴毛切。又巴磨切,入歌韵,又作上声……邦卯切。又巴我切,入哿韵”;“却”作上声,音“邱杳切”,“约”,入上、去二声,音“衣皎切,又作去声”;“酌”作上声,音“之卯切”。若据“入声作平上去三声”部分标注的反切音,“索落诺博却约酌”皆可入萧篠韵。是则,该词押萧篠韵,与谢氏舒声十四部归部相合。
同时,他注意到“入声字作平上去三声,均有一定,并非入声字概可作三声用也。今人遇平声字多以入声代之,大悮”,所以,必须对“入作三声”之法予以规范。而规范之依据,就是体现北曲用韵的《中原音韵》。
平分阴阳方面,谢元淮认为:“盖平声字,阴阳清浊不同,出口便可定准。其上去入三声字,则皆随平声而定者,虽亦可分阴阳,而其声由接续而及,介在两间者居多。即如东同韵中,‘风’字,阴平也,其调四声曰‘风琒凤拂’。是‘琒凤拂’三字,随‘风’字牵连而属阴声矣。而‘冯’字阳平也,其调四声亦曰‘冯琒凤拂’,是‘琒凤拂’三字,又随‘冯’字牵连而为阳声矣。将何从而定其阴阳乎?他如‘葱虫’‘通同’‘烘红’等字,皆阴阳同调。此外各韵,难以遍举。前明会稽王伯良著《曲律》,谓平声字亦有阴阳兼属者,引元燕山卓从之所著《中原音韵类编》,每类于阴阳二声之外,又有‘阴阳通用’之一类。如‘东’之类为阴,‘戎’之类为阳。而‘通同’之类,则阴阳并属。谓为五音中有半清半浊之故,其说亦颇有理。”
平分阴阳是近代汉语语音中,中古平声字依据声母清浊分化为阴平、阳平二调的一条音变规律。就两宋旧词的押韵情况而言,并未明确地凸显出平声阴阳的痕迹。所以,清代诸家词韵的编订都未作平分阴阳的声调安排。独谢元淮有这样的主张,并将此主张呈现在了《碎金词韵》中。《碎金词韵》每部先依平仄分列所统平水韵韵目,各平水韵下再分阴、阳及阴阳通用。如平声“东韵”分“东阴”“东阳”和“东阴阳通用”,“东阴”下统“东中忠衷冲翀盅终”等韵字,“东阳”下统“同铜桐峒筒童虫崇融”等韵字,“东阴阳通用”下统“戎茙绒隆笼聋胧珑”等韵字。这样的安排看似是“平声分阴阳”的声调体现,但就全书体例而言,并非如此。一方面,平声除分阴阳外,还有对“阴阳通用”的安排。“阴阳通用”即半清半浊。另一方面,除了平声韵,三分的格局还出现在上、去、入三声中。如上声“董韵”分“董阴”“董阳”和“董阴阳通用”,“董阴”下统“董懂孔桶总汞”等韵字,“董阳”下统“动洞挏硐”等韵字,“董阴阳通用”下统“拢笼”二字。
可见,谢元淮分阴、阳及阴阳通用,其旨不在声调,而在乎声母的清浊。词韵专书的编订,当以韵部的划分为目的。谢氏关注声母清浊,用意何在?
作为谢元淮词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碎金词韵》的编订深受谢氏词学思想影响。有别于清代诸家词学思想,谢氏词学特别主张打通词体之韵、律、乐诸要素的关系。谢氏深谙音律,为了恢复词之音乐体性,一方面订谱、编韵,一方面提倡以曲歌词。虽然词乐已亡,但谢元淮认为曲乐(尤其是南曲)源于词乐。如“十三调者……惟南曲有之。变之最晚,调有出入。词则略同,而不妨与十七宫调并用者也”,“填词家……本不必旁及曲韵。惟既以笙箫度所著词,即与歌时曲无异”。谢氏认为歌词与歌南曲之法相似,板眼皆“不必定在押韵处”,“不以韵为断”,这是其“以曲乐歌词”的理据来源。有了以曲乐歌词的合理性,道光二十四年(1844),谢元淮受许宝善“以词代曲”的启发,先是搜集许氏所遗《回纥怨》《误桃源》《渔夫词》《长命女》《四国朝》等词调,然后更正《念奴娇》《阳关曲》诸调,从《九宫大成》中摘录词乐谱一百七十余阕,编订成《碎金词谱》六卷,左注平仄,右注工尺、板眼,予以刊行。道光二十六年(1846),又邀请汪汝式、吴同午、胡晋、胡卫清、汪元照等人听其所谱《碎金词》。道光二十八年(1848),谢元淮邀请陈应祥、范云逵、路启镗等曲师,以昆曲给旧词谱以工尺,编订成二十四卷《碎金词谱》,共收词五百余首。
谢元淮以曲歌词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词恢复了其合乐可歌的特点。但词之音乐体性不单需要乐律,还应体现在合韵上。因此,将以曲歌词的词学主张融入《碎金词韵》的编订中,是符合谢元淮的词学思想和实践需求的。无怪乎谢氏在其《填词浅说》中有如下论述:“词曲既播管弦,必高下抑扬,参差相错,引如贯珠,而后可入律吕。倘宜扬也,而或用阳字,则声必欺字。宜抑也,而或用阴字,则字必欺声。阴阳一欺,则调必不和。欲诎调以就字,则声非其声。欲易字以就调,则字非其字。窘矣。故凡填词者,先辨宫调南北,再遵南北音声,斟酌下字,庶不为知音齿冷。”又“以歌曲之法歌词,亦冀由今之声以通于古乐之意焉耳。按宋人歌词一音协一字,故姜夔、张炎辈所传词谱,四声阴阳不容稍紊。今之歌曲则一字可协数音,曼衍抑扬,萦纡赴节,即使分刌节度,不能如宋词之谨严,亦足以协谐竹肉矣”。谢氏认为歌当时昆曲与歌两宋旧词一样,“四声阴阳不容稍紊”。因此,为满足其以曲歌词的实践需求,编韵必须明分声母清浊。
但在《碎金词韵》的编订中,谢元淮还是对平声的分阴阳做了单独处理。《碎金词韵》中仄声韵的反切基本来源于《广韵》,平声韵的反切则按“以阴切阴,以阳切阳”的原则加以改良。平、仄的区别处理,客观上形成了与《中原音韵》“平分阴阳”及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声调系统相同的格局,满足了其“盖平声字,阴阳清浊不同,出口便可定准”的歌词需要。
三 配合入乐与融入南曲声韵
出于整合词韵规范的需要,谢元淮在韵部划分和“入作三声”的安排上,“以诗韵为准”的同时,融入北曲韵成分。出于歌词实践的需要,谢元淮主张融入北曲特征,平分阴阳。实际上,谢氏基于歌词需要所融入的曲韵特征,并不限于北曲,还有南曲韵成分。主要体现在“小韵归属融入南曲韵成分”和“声类描写兼顾南曲发音特征”两方面。
(一)小韵归属融入南曲韵成分
谢元淮精于音律,当其论词,自然非常强调声律,哪怕是再小的韵律细节,也不容有失,唯此方可完美地配合其以曲歌词的实践。在一些小韵的归属方面,他认为应当细加甄别,表现为:“平声十灰、十三元,上声十贿、十三阮,去声九泰、十卦、十一队、十四愿,沈氏皆割分其半,以声相属,源本《洪武正韵》,于填词尤为允当,今从之。”相比于《中原音韵》,《洪武正韵》“与当时的南方方音更靠近一些,有‘南化’的成分,于是就有‘南宗《洪武》之说’,明代南曲作者多参照它来定韵”。其实,不止明代南曲宗《洪武》,清代亦是如此。谢元淮即主张“北曲宜准《中原音韵》,南曲宜准《洪武正韵》”。
谢氏一方面主张“南曲宜准《洪武正韵》”,一方面吸收《洪武正韵》中的小韵融入词韵系统。显然,这与谢元淮以昆曲歌词的主张是分不开的。
南曲韵适合以昆曲歌词之法,那么前述北曲韵成分的融入,是否就一定与“以昆曲歌词”相冲突呢?未必。明代魏良辅对昆曲的改造,既包括唱腔,也包括昆曲语音,改良之后的昆曲仍以吴音为基础,但同时融合南北声腔,已吸收不少北音成分。其“韵白押韵是按照当时的标准官话中州音为准的,只有个别的字面音还带有吴语的特色,如保留了入声、浊声母,分尖团音等”,当时的曲音又称“中州韵姑苏音”,清代“江南曲界,一直在遵守着清沈乘麐的《韵学骊珠》,因为他基本反映了‘姑苏音的中州韵’及昆曲音韵的实质”。而沈氏《韵学骊珠·凡例》中则曰:“此书以《中州韵》为底本,而参之以《中原(音)韵》及《洪武正韵》。更探讨于《诗韵辑略》《佩文韵府》《五车韵瑞》《韵府群玉》《五音篇》《海南北音辨》《五方元音》《五音指归》《康熙字典》《正字通》《字汇》诸书。”明代以来,“曲韵必南从《洪武》,北问《中原》”,莫衷一是。乾隆年间,沈氏用了五十年的时间,七易其稿,“合南北为一书”,其中自然夹杂不少北音。虽然一直存在南曲、北曲的分法,但随着几代的改良,两者已互有交融,这使得谢元淮虽以南曲歌词,却同时融入南北音成分。
今人提及《碎金词韵》则言其“归纳诗韵,又融合了许多曲韵的因素,是一部诗韵和曲韵的混合体”。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但略显片面。其所谓“诗韵”因素,实囿于谢氏词韵观,《碎金词韵》中主要表现为使用平水韵目。所谓“曲韵”成分,非曰本意立足于吸纳曲韵,不过是谢氏基于其“以曲歌词”主张下的综合考量,也是调和“乐”与“韵”关系的一种尝试。
(二)声类描写兼顾南曲发音特征
谢元淮以昆曲歌词,需要调和的还有昆曲唱腔和汉字音节之间的矛盾。
通常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包含“声”“韵”(包括调),日常语流中,声韵的组合是连贯融合的。但昆曲是“水磨调”的唱腔,在演唱过程中并非“一字一声”(除引子外),而是“极悠扬顿挫之妙,有一字填写六七工尺者”。因此,以昆曲歌词,必然使得汉字音节被切割为几个部分,其中“‘计算磨腔时候,尾音十居五六,腹音十有二三,若字头之音则十且不能及一’,字头所占时值既少,往往容易为曲家和听客所忽略”。字头即声母,字音始出,而声母不过“几微之端”,“一点锋芒”,“似有如无,俄呈忽隐”,若含糊不清,黏滞不净,则谓之“装柄”“摘钩头”或“字疣”,乃曲家大忌,这就是唱家所谓“出字难”。
鉴于此,谢氏非常强调字头(声母)的精确。“凡敷衍一字,各有字头、字腹、字尾,谓之声音、韵声者。出声也,是字之头音者……一点锋芒,为时曾不容瞬。歌者字音始出,各有几微之端,似有如无,俄呈忽隐,于‘萧’字则似‘西’音,于‘江’字则似‘几’音,于‘尤’字则似‘移’音,此一点锋芒,乃字头也。”所以,谢元淮在《碎金词韵·论例》中明确提出书中声类“字分宫、商、角、徵、羽五音,从黄氏《韵会举要》,其平分阴阳及阴阳通用,则从燕山卓从之《中原音韵类编》暨明吕坤《韵事》,其实皆本诸宋司马文正之《切韵》也”,采用前人五音标注法专门注明声类,而所注声类大体反映当时昆曲声系特征。
与前述谢元淮关注声母清浊安排一样,谢氏编韵特别标准声类,已突破了词韵专书编订的传统范式,用意实际在于配合其“以曲歌词”的实践,使词韵专书全面地满足入乐的需求。
四 余论
谢元淮词韵观中,“‘古无词韵’与古词用韵有一定标准”符合谢氏的编韵需求和编韵可能性,“‘以诗韵为准’与融合北曲韵成分”是其“词为诗余”“曲为词余”的词学观所决定,“配合入乐与融入南曲声韵”是其“以曲歌词”、追求词之可歌性的词学主张使然。三方面逐层递进,互为补充,构成一个完整的词韵理论系统。“古词用韵有一定标准”决定了谢元淮以归纳旧词用韵为基本编韵方法,“‘以诗韵为准’与融合北曲韵成分”是其整合诸多小韵的辅助编韵方法,“配合入乐与融入南曲声韵”则是体现谢氏编韵的终极目的,融乐于韵,完整地重现词之音乐体性。
相较于清代其他词韵,《碎金词韵》最大的特点是配合入乐、融入南曲声韵特点。清人编订词韵多是怀揣“求合于古”的原则。谢氏选择以南曲歌词,除了当时昆曲正盛这一因素外,或许也看到昆曲之韵与宋词之韵并非不可兼容,至少昆曲之韵比北曲韵更合于古。谢元淮以曲乐歌词,是时代寻求恢复词的音乐体性使然,开创了乐律研究的新局面,有筚路蓝缕之功,却不幸被后人视作徒劳之举。有幸的是在其词韵研究中,给我们留下了诸多财富,《碎金词韵》一书中,韵部的安排主要代表了其词韵观,声类的处理体现了其特有的词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