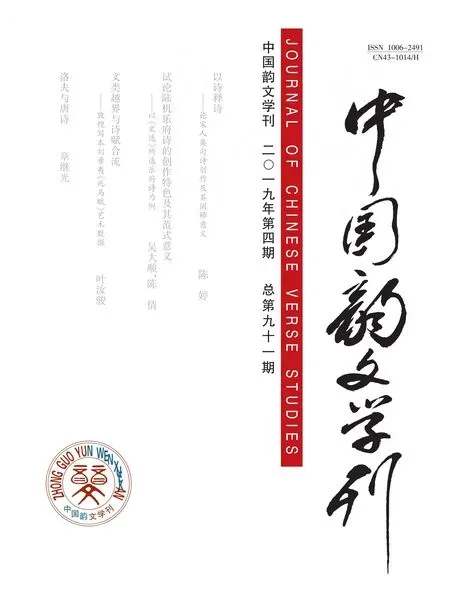扶衰与继绝:潘岳与西晋四言诗学
林宗毛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学界对于潘岳诗歌的研究多集于五言一体,而对于其四言则鲜有措意,个中缘由概如王澧华《两晋诗风》所云:“潘岳才如江海,后世所重,每在其五言佳构。”诚然,自南朝以降,潘岳与西晋五言诗的关系便一直为后人所揄扬,如《文心雕龙·明诗篇》云:“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尤其是《诗品》中将其列为上品并誉其为西晋诗坛的“五言冠冕”,直接奠定了潘岳在西晋五言诗坛上的地位。正是因为这两部文论导源在前,后此对于潘岳诗歌的讨论始终是围绕其五言诗而展开的,如《隋书·经籍志》云:“爰逮晋氏,见称潘、陆,并黼藻相辉,宫商间起,清辞润乎金石,精义薄乎云天。”直到现代一些学者的论著中也是如此,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即云:“其中以潘岳、陆机、张协为代表,说明五言诗由于建安以来诗人的努力,已无疑地成为最普遍的文学形式,而太康的诗人们,就在各方面把五言诗煅炼得更为得心应手,或者更为精致,或者更为流畅,或者言情,或者写景,在整个生活中,乃无往而不是五言诗了。”然而,正如徐公持所云:“自数量方面观,西晋五言诗不占优势,四言体完全可以与五言颉颃。此情况与建安、正始诗坛相比,似乎五言并无进展,甚至有些倒退,四言体则颇有回潮之势。”佐藤利行也注意到了这股诗歌的回潮,其云:“在西晋文坛上,确实存在着以传统的《诗经》为基点尝试着创作诗歌的文人集团,如果给它一个名称,我们称之为‘古典派’。”可见,在西晋诗坛上并非是五言诗一枝独秀,四言诗也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部分。综观潘岳现存诗作中不仅有四言诗的创作,而且部分四言诗还被《文选》所收录,这就说明潘岳的创作在体现时代风气的同时也取得了卓异的成就。当然,更为关键的是潘岳不仅创作了四言诗而且还提出了四言诗的审美理论,据此而论,较诸其对于五言诗仅有创作而缺乏理论无疑是一种超越。
一 西晋四言诗的创作与“四言正体”论的提出
建安以降,诗歌“由先秦两汉古朴之四言而开五言之新格局”,正如《文心雕龙·明诗篇》所云:“暨建安初,五言腾踊。”到了西晋,五言诗更是迎来了“中兴”,《诗品》描述这一盛况云:“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此期五言诗的大兴必然对四言诗的生存空间有所挤压,正如缪钺所云:“四言至汉代,其势已尽,魏晋已降,作者不多,亦鲜佳什。”然而通观逯钦立所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西晋诗作,可以发现西晋诗人多有四言诗的创作,据檀晶统计,“西晋太康时期共创作诗歌 390 多首,其中四言诗136 首,占其创作的 34%。而西晋一朝共有 182 首,完整的 139 首,可见西晋四言诗创作几乎全集中在这一时期”。这只是就整体而言,具体到个人则是部分诗人现存的诗歌中四言诗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诗体,如陆云“四言占绝大部分,五言仅有七首,自数量看,陆云四言诗写得颇为熟稔,凡应命赠答祖饯等场合,几乎皆有所作,且措词从容,间出徽音,可谓西晋一朝最大四言诗作者”。当然,某种诗体有着大量的创作还不足以说明其在当时风行程度,作为补充还需要看这种诗体是否有着大量的接受群体。关于此点,葛洪《抱朴子·均世篇》似有所透露,其云:“近者夏侯湛、潘安仁并作《补亡诗》,《白华》《由庚》《南陔》《华黍》之属,诸硕儒髙才之赏文者,咸以古诗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贤之所作也。”葛洪虽是就潘岳等人四言诗创作而立论,但却也透露了两点关于四言诗在当时的接受情况:一、从“诸”“咸”可以知晓当时四言诗的受众很多;二、从“硕儒高才”可以看出四言诗的受众基本为文学素养较高者,这就从侧面印证了檀晶对于西晋诗人四言诗创作的统计分析,因为那些“硕儒高才”绝大多数就是保留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的西晋诗人们,而他们的接受和创作是相辅相成的。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即西晋的诗坛虽是五言诗大行其道,但四言诗却也在悄然而兴。至于四言诗兴起的原因,吴淇《六朝选诗定论》于此有详尽之分析,其云:“地气自北而南,诗运亦然。西晋以期作者,尽在西北,东晋以后作者,尽在东南。……故诗运之南不在元帝渡江之后,固已在陆机赴洛之日矣。诗肇于西北,自北而南,始于晋南渡,盛于宋齐梁,至隋伐陈而复归于北,及唐而南北合。分南北者《选诗》之运,合南北者唐诗之运。若夫《三百篇》之运,全在西北故无楚风。”这是就诗运与地理关系展开的论述,西晋诗运尚处西北,楚风不竞,故《诗经》之四言体仍有其生存的空间。当然,除了诗运转捩之外,还有一点中国文人的依恋心态在作祟,正如朱东润先生所言:“按魏晋而后,五言转繁,至于齐梁,遂称极盛,然诗体虽定,而评论之士,或眷恋故昔,不忍遗弃,历隋及唐,至开元间,李白尚有‘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说。无他,一部《诗经》横亘胸中而已。”
一种诗歌实践的兴起,必然促成与其相应的理论的产生。就此,西晋诗坛上四言诗创作的热闹景象,自然也就激发了西晋文人对于四言诗审美理论的探讨。环顾当时的西晋诗坛,第一个站出来发声的似是皇甫谧,其《三都赋序》云:“故孔子采万国之风,正雅颂之名,集而谓之《诗》。”后起之陆云似亦有对于四言诗的评价,如其《与兄平原书》云:“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然而都是随性之言,并未对四言诗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真正完成此项时代任务的应是挚虞,其《文章流别集论》云:“《书》云:‘诗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谓之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书。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挚虞从“诗言志”的逻辑出发探索各种诗体的起源与演变后进而认为诗“以四言为正”,至于三言至九言的诸体诗歌则是“曲折之体,非音之正”。挚虞的理论一经提出,便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如《晋书·挚虞传》云:“(挚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今文章类聚区分三十卷,名为《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既然挚虞的《流别论》在当时广为时人所重,那么可以推知他的“四言正体”之论应在当时具备一定的受众基础,并且被此受众群体所看重。
当然,如果我们深究挚虞“四言正体论”何以会在“晋世群才,稍入轻绮”的五言诗创作阻击下成功突围并且还收获了一批数量可观的追随者,那么就不得不涉及当时多数人心中的一个敬畏《风》《骚》的传统。风,指《国风》,亦即《诗经》,而骚则为《离骚》,代表《楚辞》。这两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两大源流,故历来备受推崇,如晋人檀道鸾《续晋阳秋》云“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檀道鸾此论不仅是后来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原其彪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的先声,更是指出了“潘、陆之徒”的“宗归不异”从而揭示了西晋时人普遍尊崇《风》《骚》的传统。而四言诗正如钟嵘《诗品序》所言“文约义广,取效风骚,便不可多得”,故也就完美地契合了时人的这种敬畏心理,借此而获得广泛的受众基础自在情理之中。
二 潘岳的四言诗创作及其理论
正如前言,在西晋诗坛上,无论就四言诗的创作规模、接受程度甚至理论准备都是具有一定基础的,那么这种风气就不能不影响到当时诗坛的代表诗人潘岳。
(一)“非徒温雅,别见孝悌”观的提出及其来源
由于西晋末年的永嘉动乱,致使西晋一代文籍荡然几尽,即如深为时人所重的挚虞《文章流别论》流传下来的也只是保留在诸多唐宋类书中的只言片语。是故,当时人是否也有如《文章流别论》那样涉及阐释四言诗的理论著作,我们并不能遽下论断。因此,我们只能从文献的零星记载中去爬梳潘岳对于四言诗的审美理论。据《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潘以此遂作《家风诗》。”这里,潘岳对于夏侯湛所作周诗的评价值得我们细绎。“温雅”,温指“温柔”,是指诗歌表现得含蓄委婉,即是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所谓的“《诗》主言志,训诂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颂,故最附深衷矣”。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潘岳对于四言诗的审美仍是汉儒所一以贯之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雅即雅正,是指诗歌的文辞雅丽典正。综合这两点来看,潘岳是就四言诗的外在形式而论,其要求四言诗要表现出温柔的风貌和雅正的文辞。在提出了对于四言诗的形式审美要求之后,潘岳更进一步又提出了对于四言诗内容上的要求,即是“别见孝悌”。“孝”和“悌”都是儒家传统的人伦思想,即是子女对于父母的孝心和兄弟之间的友情,归结于一点即是一种浓浓的血亲深情,这一点当直承《诗经·小雅·蓼莪》和《诗经·小雅·鹿鸣之什》等诗的相关主旨。由此可见,潘岳虽是就他人诗歌评价而言,但实质上“非徒温雅,别见孝悌”却很好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四言诗的审美要求,非如刘熙载《艺概》所云“为不知诗矣”。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将“非徒温雅,别见孝悌”作为潘岳对于四言诗审美的理论总结。如果我们把潘岳的四言诗理论与同时期其他人(如挚虞)的理论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则会发现潘岳的四言诗理论与同时期其他人的四言诗理论实际上可以用数学上全集与子集的关系来表达,这就说明潘岳的四言诗理论具有一种集大成性。而这种集大成性,体现了潘岳对于同时代人四言诗理论的不断借鉴与融汇。首先,就形式方面的“温雅”理论而言,潘岳就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西晋时期其他人对于四言诗求雅求正的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挚虞。因为挚虞《文章流别论》中即有“温雅”一词,当然这是挚虞对于《应宾难》文风的概述而并非是就四言诗而发,但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评其述怀之作“必循规以温雅”,则可以见出“温雅”确为挚虞文学创作的旨归所在。另外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也有专论四言应求雅正的观点,其云:“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关于挚虞的这个观点是如何被潘岳所吸纳的,大概正如朱东润先生所云:“泰始、太康之间,仲洽身在洛下,亲与张、潘诸人酬对。”除了挚虞外,另有二人不可忽略:一为与潘岳“坐则接茵,行则携手。义惟诸父,好同朋友”的潘尼;一为“与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舆接茵,京都谓之‘连璧’”的夏侯湛。潘尼和夏侯湛较诸挚虞对于潘岳四言诗应求“温雅”审美理论的形成更多地体现在创作风格在交游中的间接影响而非审美理论在交游中的直接诱发。首先,潘尼的创作充满了儒者气息,故《尼别传》云其“少有清才,文辞温雅”。关于此点,后此的诗评家似乎达成共识,如陈祚明云:“潘正叔诗手笔高苍,情绪警切,而轨于雅正。”而夏侯湛,据《文士传》知其“善补雅词”,不仅如此,他还发表过一些对于雅正文风言论,据《晋书·夏侯湛传》载其自云“仆以竭心,思尽才学,意无雅正可准,论无片言可釆,是以顿于鄙劣,而莫之能起也”。可见,夏侯湛是十分注重在文学创作中追求“雅正”的,所以他补作的《周诗》自然也是以“雅正”为准则。再次,就内容方面的“孝悌”而言,对于潘岳有所影响的或仅夏侯湛一人而已,据《晋书·夏侯湛传》载其作《昆弟诰》以阐发“惟仁义惟孝友是尚”的孝悌观。但是,夏侯湛文中的孝悌观毕竟是就创作内容而言,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而言,故而只能对潘岳四言诗“孝悌”的审美理论具有间接的影响,这一点似可从《晋书》史臣评价夏侯湛《昆弟诰》之语中窥出,《晋书》史臣曰:“作诰敷文,流英声于孝悌,旨深致远,殊有大雅之风烈焉。”诰自然是指《昆弟诰》,由于此诰意在阐发孝友之道,故《晋书》史臣将潘岳对于《周诗》的“孝悌”之评移接于此来评价此诰,可见在《晋书》史臣看来,此诰虽然体现了“孝友”的内容,但并未在理论上对于潘岳有何影响,故而仍需借助于潘岳的“孝悌”之评。如此看来,对于潘岳四言诗“孝悌”审美理论的形成,则或是远承《诗大序》中关于四言诗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的主张。这既是对同时代人的突破,也是对四言诗传统的一种因袭。纵观潘岳四言诗理论的内涵和渊源,我们可以认为潘岳的四言诗理论典型地体现了西晋一朝四言诗理论的集大成性。
(二)四言诗的创作实践及其影响
1.对潘岳四言诗创作实践的整体认识
对于一个诗人诗歌创作情况最为直观的认识无疑是通过定量的比较分析来得出结论,故通检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可知潘岳五言诗共八题十五首(包括三则残句),而四言诗共九题(包括六首完诗和三则残句),若就诗题的数量而论,潘岳的四言诗创作是多于五言诗的,这恰符合前述西晋诗坛四言诗创作的风气。然而,我们知道潘岳的集子早已散佚,现存的诗歌是明人辑佚所得,所以很难保证不存在四、五言诗散佚比例失衡的情况。如此,我们对于诗人诗歌的考察就有必要转移到一些后世评论和经典选集上来,虽然这两个方面无法从数量上进行直观的分析,但是却可以从性质上归纳出一些初步的结论。首先考察的是檀道鸾的《续晋阳秋》,此书对于西晋及其以前文学的流变略有专论,其云:“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从檀氏此论中我们能窥知关于潘岳四言诗创作的一些情况。首先檀道鸾此论的大意是说潘岳等人的文学创作因为宗归风骚的传统而显得质文有别,理解了这一层,就不难进一步推知潘岳在创作中是风、骚并效的,以此反推他对于集中体现《诗经》的四言诗体的创作应是不会少于其他任何一种诗体的。然而一个诗人有创作并不表明其作品有水平,所以还需借助选集的收录情况来一探其诗歌之成就,故再看潘岳四言诗在《文选》中的收录情况。《文选》“诗甲·献诗类”收录了潘岳的《关中诗》,而后“诗丙·赠答二类”收录了潘岳的《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献诗类”《文选》只选了三首,另两首是曹植的《上责躬诗》和《应诏诗》,可见在《文选》的编纂者看来潘岳的《关中诗》是西晋诗人在献诗这个类别中的翘楚。综观《续晋阳秋》《文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我们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潘岳的四言诗创作是丰富的,不亚于五言,而且部分四言诗较诸同时代的人更胜一筹,如《关中诗》。
2.潘岳四言诗对其四言诗理论的实践
正如前言,潘岳有着自己的四言诗审美理论,那么他的理论必然影响着他的创作实践。这里不妨捏出几首作为典例来做一番考察。先看《关中诗》,关于此诗写作缘由,李善注引岳《上诗表》云:“诏臣作《关中诗》,辄奉诏竭愚作诗一篇。”据此可知潘岳写作此诗的态度即是奉诏为帝王作颂歌,而泛览全诗语句基本上是“于皇时晋,受命既固”和“明明天子,视民如伤”的腔调,这不仅使得整首诗“字字典重”,而且也鲜明地体现了潘岳关于四言诗“温雅”的审美理论。又如潘岳《为贾谧之意赠陆机》一诗,吴淇论此诗情感云:“此诗见潘安仁满腹轻薄、满怀倾险,总生于一妒。……便有万分不快处,因而作诗以轻薄之也。”诗之情感既明,则诗之用意即显,然而此诗在表达上却并非流于“讥笑怒骂”,而是相当端庄得体,充分体现了“温柔敦厚”和“风雅之正”的诗教传统。再看《家风诗》,此诗之作完全是因为潘岳有感于夏侯湛的《周诗》,故而其对于夏侯湛《周诗》的审美要求自然也在此诗中有所体现。首先,全诗语言“辞甚高雅”,读之自有典雅之气,这就很符合潘岳对四言诗需在形式上具有“温雅”的要求。再者,“别见孝悌”这一点在此诗内容上也有所体现。纵览全诗之内容正如刘孝标注所云“载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但对于父母之恩情却也在字句之间有所体现,如“靡专靡有,受之父母”。众所周知,“孝子思亲”是《诗经》情感的重要类别之一,如《诗经·魏风·陟岵》就是“孝子之思亲也,三段中但念父母兄之思己,而不言已之思父母于兄,盖一说出,情便浅也。情到极深,每说不出”。故而,潘岳的《家风诗》的内容虽有颂诗的倾向,但诗的感情却是真挚深切的,与《诗经》中的“孝子思亲”诗可谓一脉相承。
3.四言诗创作对潘岳他类文体的影响
潘岳的四言诗创作因为体现着他的四言诗理论,故而其创作过程中就不可避免的沾染上一种浓厚的“拟经”味,这主要分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在潘岳诸多的四言诗中的有一首显现了浓重拟经气息,此即《东郊诗》,这首诗不仅模拟了《诗经》四言体的句式,而且还模仿了《毛诗序》的写法给这首诗写了小序,其云:“东郊,叹不得志也。出自东郊,忧心摇摇。遵彼莱田,言釆其樵。”当然,这种做法并非只是潘岳一家,据《文选》李善注引《补亡诗序》云:“晳与同业畴人肆修乡礼,然所咏之诗,或有义无辞,音乐取节,阙而不备。于是遥想既往,存思在昔,补著其文,以缀旧制。”又《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曰:“湛《集》载其《叙》曰:‘《周诗》者,《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有其义而亡其辞。湛续其亡,故云《周诗》也。’”可知束晳和夏侯湛的四言诗都是有小序的。此外,陆云有《赠郑曼季诗》四首,其中《谷风》《鸣鹤》《南衡》分别有小序,另郑丰有《答陆士龙诗》四首,其中《鸳鸯》《兰林》《南陔》也分别有小序。可见潘岳的《东郊诗》模仿《毛诗序》体式并非偶然,应是时代风气使然。另一方面是大量的袭用或化用以《诗经》为主的儒家经典来增强四言诗的庄重和雅正,如《关中诗》全诗十六章,据李善注知其引儒家经典 65 处,其中《诗经》的引用次数为最高,达 16 次。可见以《诗经》为主的儒家经典是潘岳写作四言诗的主要语典来源。正是因为语辞上大量的袭取儒家经典(尤其是《诗经》),从而致使他的文辞风格偏于简练,正如《续文章志》云:“岳为文,选言简章。”
文体之间往往是相互影响的,即如夏侯湛而言,其《昆弟诰》被晋书史臣评为“孝悌”,而其《周诗》也被潘岳评为“孝悌”,故而可以看出“孝悌”贯穿于夏侯湛的不同文体之中。以同理推诸潘岳,既然他的四言诗创作有着上述两方面的特点,那么其在创作其他文体的过程中就或多或少地受到其四言诗创作的影响。首先来看属于诗之流调的五言诗。以常情度之,魏晋以来四言正体和五言流调的区分界限明显,二体固不应相互影响,但五言创体之源却又与《诗经》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叶燮《原诗》云:“汉苏李始创为五言,其时又有亡名氏之《十九首》,皆因乎《三百篇》者也,然不可谓即无异于《三百篇》,而实苏李创之也。”明此,则不难理解潘岳的四言诗创作对于其五言诗理当有所影响。如同样被《文选》收录的潘岳《河阳县作二首》,据李善注可知其引用儒家经典 26 处,其中引用《诗经》达 7 次为最高。再如同样被选入《文选》的潘岳《在怀县作二首》,据李善注可知其引儒家经典 18 处,同样是以引用《诗经》的 7 次为最高。如此来看,则不能不说明潘岳四言诗的拟经手法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五言诗创作,尤其是五言诗的语典这一点几乎和四言诗取径相同。当然,如果说个人的知识储备运用到不同的诗体中还不足以说明不同诗体之间手法的互相借鉴,那么一种题材在不同诗体之间存有接续也可说明二者之间的影响,潘岳的《悼亡诗三首》是对妻子的悼亡之作,而悼亡之作的源头则是《诗经·唐风·葛生》和《国风·邶风·绿衣》,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云:“《悼亡》三首,于《风》斯合。”手法与题材分别属于形式和内容,若二者仍不能说明问题,则风格的互渗或能作为关键的补充。如前所述,潘岳的四言追求雅正之风,而这种雅正之风却也常出入于其五言诗中,如《河阳县作二首》,何义门云其:“此从历仕及河阳,以令名自勖,不失雅正之义。”又如《悼亡诗三首》,孙月峰云其:“此情来之调,却是雅正之音,故妙。”综上可见,潘岳的四言诗无论就手法、题材或风格而言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其五言诗。当然,诗体之间的影响往往是互渗的,五言诗对于情感的书写也渗透到了潘岳四言诗中来。关于此点,王夫之早有察觉,其评潘岳《哀诗》云:“率尔处犹是西晋颓风,而拣意不烦,遣章不猥,还觉古风未坠。自《三百篇》以来,但有咏歌,其为风裁一而已矣。故情虽充斥于古今上下之间,而修意挈篇必当有畔。……情懈感亡,无言诗矣。……搜括潘集,可存者此二篇尔。非谓徒工,盖亦章程之未裂也。”今检索潘集,以四言之体而兼五言之情者有两首最为突出:一为《离合诗》用四言体写儿女私情,暗含了“思杨容姬难堪”的感慨;二为《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叙述了作诗的目的即是表达一种对于陆机的“分著情深”。如此看来,潘岳在创作四言诗和五言诗的过程中是互相有所借鉴的。
再来看潘岳赋作与其四言诗的关系。诗与赋的关系本身就颇为紧密,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了魏晋以来文人的共识,如皇甫谧《三都赋序》云:“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 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又挚虞《文章流别论》云:“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当然,最具代表的还是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所云“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由此可见,中古时期对于赋源于诗这种认知是普遍的,正如葛晓音所云:“在西晋文人看来,诗、赋、颂都是同体的,……尽管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诗、赋二体皎然可辨,但这种观念确也造成了部分诗歌反过来成为赋、颂之流的现象。”既然诗能成为“赋、颂之流”,那么两种文体间的创作手法必有一定程度上的重合,正如邝健行所言:“大概魏晋人叙事,或叙国事,或叙家风,或说个人及朋友的经历际遇,作者既是士大夫,本身的经历际遇又往往和家国社会有关,这样采用《诗经》《雅》《颂》本来具有的‘赋’的传统叙事,既有成规可循,又显得古雅庄重。”于此可知既然赋所具有的铺陈叙事的手法被西晋文士运用于四言诗的创作中,那么四言诗的手法必然对于西晋文人赋的创作有所反哺。以此考察潘岳的诗、赋可以发现,他在赋的创作中有意识地运用其四言诗的创作手法,而其中较为典型的手法就是化用《诗经》等儒家经典中的成句以供其赋体逞才炫博之用,如《籍田赋》。此赋篇幅适中,但据李善注可知全赋化用儒家经典高达 104 处。再如《秋兴赋》,虽属于抒情小赋,但据李善注可知全赋化用儒家经典也高达 39 处。如此高频率的引用绝非偶然,唯一合理的解释恐是潘岳在创作赋的过程中也借鉴了四言诗大量汲取儒家经典的手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潘岳这种以四言诗法入赋的创作较诸时人如陆云的“四言、五言非所长,颇能作赋”的狭隘创作观显得更为宏通。当然,除了诗赋外,潘岳的哀文在创作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其四言诗创作的影响,关于此点,刘勰《文心雕龙·哀诔篇》早已指出,其云:“及潘岳继作,实锺其美。观其虑瞻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詹锳注引王金凌云:“潘岳哀辞全为四字句,而无任何长句,比较起来,毫无调节的余地,因此称其‘促节’。促系指节奏较快。缓则相反。缓句,松懈之句。”今检潘岳现存的哀辞作品共有九首,其中《景献皇后哀策文》《为杨长文作弟仲武哀祝文》《京陵公主女王氏哀辞》《阳城刘氏妹哀辞》《为任子咸妻作孤女泽兰哀辞》《金鹿哀辞》共 6 篇哀辞全为四言,而《伤弱子辞》和《悲邢生辞》则并非全为四言而是局部为四言,至于《哀永逝文》则全篇皆无四言。以是观之,王金凌先生所云“潘岳哀辞全为四字句”固有失察之嫌,但就潘岳哀辞整体的创作情况而言则大体是不谬的。如此,潘岳哀辞中甚多四言短句而甚少缓句的实际创作情况,不能不让人认为潘岳在结构哀辞时曾大量地模仿了四言诗的句式特征。
三 “古诗三百,未足以偶”——潘岳四言诗的诗学意义
五言诗是魏晋以后诗坛的新宠,这不仅表现在曹植、陆机和谢灵运这三大诗坛领袖的接力创作,更表现在从五言诗创作理论的先声声律论到开五言诗批评先河的《诗品》的相继产生。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进行一种逆流创作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文学史的流变历程已经表明,一股逆流文学的涌动虽能得到后世同情之理解,但绝对会受到当时严厉之拒斥。然而潘岳的四言诗创作却与此认知恰为相悖,他的四言诗为当时多数文人所肯定。《抱朴子·钧世篇》即云:“近者夏侯湛、潘安仁并作《补亡诗》,《白华》《由庚》《南陔》《华黍》之属,诸硕儒髙才之赏文者,咸以古诗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贤之所作也。”而后世虽有王夫之赞赏潘岳四言诗“束晳、夏侯湛迫相刻画生理尽,何有于潘岳?”但更多的是批评与詈骂之声,如许学夷《诗源辨体》云:“若潘陆四言,联比牵合,荡然无情。……子建,仲宣四言,虽是词人手笔,实雅体也;至二陆、安仁,则多以碑铭为诗矣。胡元瑞云:‘说者谓五言之变,昉于潘陆,不知四言之亡,亦晋诸子为之也。’”又如沈德潜《说诗晬语》云:“四言诗缔造良难,于《三百篇》太离不得,太肖不得,太离则失其源,太肖只袭其貌。……张华、二陆、潘岳辈,恹恹欲息矣。”文学的逆流与文学史认知的反差无疑说明了一个问题:潘岳的四言诗对于西晋诗坛是具有一定影响的,而这种影响对于西晋诗坛的贡献表现为一种补充的作用。正如佐藤利行先生定义西晋文学的内涵时所云:“因此,一方面凝聚文辞的雕琢,一方面未失《诗经》《楚辞》风尚,所谓的‘西晋文学’产生了。”同理,对于诗歌一体而言,如果只有五言的藻饰,而没有四言的雅正,那就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西晋诗歌。
正如四言诗对于西晋诗坛具有补充作用一样,潘岳的四言诗理论对于西晋诗坛的贡献也多是体现为补充作用。西晋诗坛上,陆机因五言诗的创作而与潘岳并驾齐驱,但是“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故而潘、陆优劣之争也由此聚讼纷纷。但是纵观中古潘、陆优劣论的演变可以发现陆机似乎占据了上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陆机在丰富的诗歌创作之外还创作了《文赋》,而赋中“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论更是使他成为时代的标志,正如万绳楠所云: “西晋文风,就基本方面说是世族所追求的绮靡文风,陆机《文赋》所主张的文风。”而潘岳的四言诗理论,无疑弥补了我们素来对于潘岳诗学思想认识空白的遗憾,从而使得潘岳在与陆机的优劣之争中有了一个势均力敌的砝码。当然,这是就其理论对于个人意义而论,而对西晋这个时代而言,似乎更需要潘岳的四言诗理论。正如前引佐藤氏所云《风》《骚》传统是西晋文学的重要内涵,所以此时代自然也需要能够代表这两大文学传统的理论来指导文学创作。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论主张“情”与“精妙之辞”,显然更多的是受到《楚辞》文学传统的影响,而潘岳的四言诗理论则是受到了《诗经》文学传统的影响,正是这两种受不同文学传统影响的诗学理论才构成了整个时代完整的诗学。基于此,我们有必要站在佐藤氏的肩膀上更进一步地指出:受《风》《骚》文学传统影响而创作的诗歌加之受《风》《骚》文学传统影响而形成的诗学理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晋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