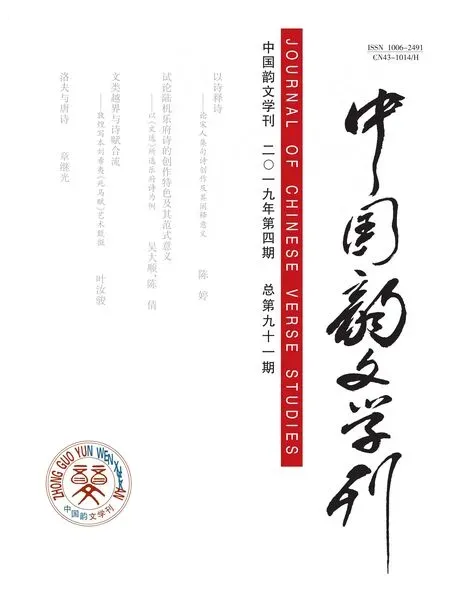白鸠、白鹭、白鸥与李白之“白”新探
——从人格范式与理想旨归解读《夷则格上白鸠拂舞辞》与《古风》其四十二《摇裔双白鸥》
谷维佳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李白爱白,亦爱鸟,尤爱白鸟。据李浩统计,李诗中出现过的鸟类名称约有60余种,其中大多鸟类形象都具有比兴象征的意蕴。《夷则格上白鸠拂舞辞》及《古风》其四十二《摇裔双白鸥》篇中,“白鸠”“白鹭”“白鸥”三种白鸟的象征意味尤为明显。分列两诗如下:
《李太白全集》卷五载《夷则格上白鸠拂舞辞》:
铿鸣钟,考朗鼓。歌白鸠,引拂舞。白鸠之白谁与邻,霜衣雪襟诚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噎
,性安
驯。首
农政,鸣阳春。天子刻玉杖,镂形赐耆人。白鹭之
白非纯真,外洁其色心匪仁。阙五德,无司晨,胡为啄我葭下之紫鳞。鹰鹯雕鹗,贪而好杀。凤凰虽大圣,不愿以为臣。卷二《古风》其四十二《摇裔双白鸥》篇:
摇裔双白鸥,鸣飞沧
江流。宜
与海人狎,岂伊云鹤俦。寄影
宿沙月,沿芳戏春洲。吾亦洗心者,忘机从尔游。但《夷则格》篇的特殊意义在于,通过对“白鸠”热烈歌颂,而对“白鹭”激烈贬责,向我们昭示了李白又并非爱所有的“白鸟”。与李集其他诗歌中的“白鹭”形象作比,会发现“白鹭”在此篇中的特殊性,李白对其情感变化显得尤为极端和矛盾。《摇裔双白鸥》篇中,李白又着意刻画了“白鸥”这一形象。“白鸠”“白鹭”“白鸥”三种白鸟,在两篇作品中通过鲜明的对比形成了一个带有极端化情感的指向,由恶及善的层进式抒写,赋予各自不同的人格特质和比兴象征意味,带有明显而强烈的李白个人好恶倾向。结合两首作品编年和创作背景,从对意象的隐喻性人格范式的解读出发,揭示其背后隐藏的李白“否定式”与“进化式”的理想旨归,可以见出李白对“白”的双重标准和“白”之于李白的更深层意涵。
一 三种不同书写方式与李白潜意识中的三重人格范式
“白鸠”“白鹭”“白鸥”三种白鸟形象,在两篇作品中的写作手法各有不同,象征了李白潜意识中的三重不同人格范式。
(一)白鸠:依题立意,着意加强,赞美的对象,“贤人”的象征
“白鸠”承接传统寓意,“依题立义”,是李白歌颂的对象。白鸠珍贵罕见,性情温顺善良,用心专一,仁爱有德,历来被视为祥瑞。《诗经》中就有歌颂白鸠的篇章,如《召南·鹊巢》《曹风·鸤鸠》等。史书及野史轶事中多载凡有“亲丧子孝”之事,则有白鸠来集,如《搜神记》就记载新兴刘殷因至孝得神赐粟,西邻失火不殃,后白鸠来巢,以及“白鸠郎”郑弘因孝得官等异事。《唐六典》谓其为“中瑞”之一,是子孙孝顺的象征,唐代贤相张九龄身上就曾发生白鸠来巢的灵异事件。民间亦有向朝廷献白鸠的传统,以此颂扬政治清明,在位者敬老有德。对统治者而言,“白鸠见”更是祥瑞的象征,汪绍煐按孙氏《瑞应图》曰:“‘白鸠,成汤时来,王者养耆老,尊道德,不失旧则至。’”《稽瑞》载唐时有“山阳白鸠,京师青雀”的俗谚,并附:“《襄阳耆旧传》曰:黄穆为山阳太守,有德,白鸠见。”
白鸠象征“贤人”。《夷则格》开篇以钟鼓齐鸣状白鸠拂舞之盛大,营造了一个隆重赞颂的环境。继而从各个侧面专写白鸠:外形上,以霜雪盛赞白鸠羽毛之洁白,“白鸠之白谁与邻,霜衣雪襟诚可珍”,已足令人珍视,有洁身自好之表;然又非徒白,品行端方正直,“含哺七子能平均”,哺育七子,却能做到平均如一,不偏不倚,有仁爱均一之心;性情温驯安适,“食不噎,性安驯。天子刻玉杖,镂形赐耆人”,于是天子将其形象镂刻于王杖顶端,以赐老人,有重老敬贤之德;更难得的是能“首农政,鸣阳春”,暮春时节,到了播种谷物的时候,雌雄相飞,拂羽相鸣,提醒农事,有应时及物之功。白鸠有如此种种德行,足为“贤人”之代表。李白虽从各个方面极力刻画赞美白鸠的高尚形象,但这些形象均渊源有自,是承接传统白鸠形象而来,并未增添新的特别意涵。
《夷则格》篇,从音律上讲,题目中的夷则格,即为“亲贤臣,远小人”的君臣关系隐喻,“夷则”为阳律之一,在乐器上以“磬”为代表 ,“磬”“琴”“瑟”三者主礼之贵贱、尊卑、亲疏有别,五音属宫商,而“商”曲属臣。李白在题目中用“夷则格”,又于篇末言:“凤凰虽大圣,不愿以为臣。”明显提醒在位者及掌权者宜严守君臣之礼,修德尊贤,远离奸佞。
(二)白鹭:贬斥的对象,临时性颠覆重塑,“小人”的象征
“白鹭”在《夷则格》篇中乃是奸佞“小人”的象征。李白在后半段开篇便定下了对白鹭进行批判的基调:虽外表洁白,色似白鸠,然性“非纯真”。外虽相似,内心“匪仁”,伺机延望,暗藏杀机,只为啄食芦苇下鲜美的游鱼,和贪婪嗜杀的鹰、鹯、雕、鹗同属一类,乃急功近利、迫害无辜的奸佞之徒,是不祥之鸟。
李白以前,传统的白鹭形象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一是百官缙绅之象,《禽经》曰:“鹭,白鹭也,小不逾大,飞有次序,百官缙绅之象。《诗》以‘振鹭’比百寮雍容,喻朝美。《易》曰:‘鸿渐于干于盘。’圣人皆以鸿鹭之群拟官师也。”显然是赞美之意,并延伸出以白鹭之“延颈远望”喻求官者的义涵,甚至以之为官名;二是虽写白鹭捕鱼,但并无嗜杀之意,如庾信《寒园即目》“苍鹰斜望雉,白鹭下看鱼”,只属客观描写,不带有强烈的感情褒贬色彩;三是预示不祥,《宋书》载“晋成帝咸康八年(342)七月,白鹭集殿屋。是时康帝始即位,此不永之祥也”,但出现次数不多,亦无对“不祥”之缘由的明确解释。李白之后,刘禹锡有《白鹭儿》,也无任何负面意涵,反赞美白鹭不谐于俗、遗世独立的高格。故李白在此篇说白鸠“心匪仁”“阙五德”,与“鹰鹯雕鹗”同属一类,“贪而好杀”,只是在特殊语境中对以往传统“白鹭”形象的一个“临时性”改造。沈德潜也认为此篇“非必有恶于白鹭,借以讥外洁内汙者耳”。这从李集其他篇章中出现的“白鹭”形象之迥异不难见出。此篇之外,“白鹭”在李集中还出现过12次之多,大多仅作为普通意象来用,并无明确的情感褒贬指向。其中有3次作为地名以“白鹭洲”的形式出现,如《宿白鹭洲寄杨江宁》:“朝别朱雀门,暮栖白鹭洲。”《送殷淑三首》其二:“白鹭洲前月,天明送客回。”《登金陵凤凰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大多时候只作为一个笼统的形象出现,主要取其外形之飘逸,姿态之优美,如《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三:“渌水净素月,月明白鹭飞。”《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白鹭映春洲,青龙见朝暾。”有时又主要取其颜色之洁白,如《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宣》:“白若白鹭鲜,清如清唳蝉。”对比可以发现,《夷则格》篇中“贪婪嗜杀”的“白鹭”与其他诗歌中“白鹭”形象差距之大不啻云泥,乃此篇中所独有,且在李白集中仅出现这一次,具有极大的偶然性。
此诗中“白鹭”之形象,表面上看似矛盾,内在却有一定特殊性。李白在这两首诗中,为表达自己明确而清晰的感情褒贬倾向,对白鹭和白鸥做了固定化和类型化处理,在特殊语境中故意突出并放大了白鹭“嗜杀”这一特性,与李白其他诗中“白鹭”形象大相径庭。与“白鸠”和《古风》中的“白鸥”仅指具体的某一种鸟不同,此处的“白鹭”代表的是具有嗜杀属性的一类鸟,已部分地脱离了其本原形态,向后文“鹰鹯雕鹗”的涵义靠近,与之同类,并一起演变成了一个模糊的类型化特殊符号,且此涵义只在这一篇中有效,不具有普适性。李白做这样的处理,只是为了与“白鸠”形象作明显对比,表达对这类虽外表形似,颜色洁白,却内心“匪仁”,贪婪又嗜杀的虚伪白鸟的痛恶。也就是说此篇中的“白鹭”并不能与现实中的“白鹭”,以及其余李集中的“白鹭”形象画等号。
这种意象的“矛盾性”不仅出现在李白这一首诗中,也不只针对“白鹭”一个形象。李白在此诗后半段歌颂鸡能司晨,有五德,在《古风》其四十《凤饥不啄粟》篇,却对鸡持嘲讽态度:“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显然和“白鹭”一样,属于在特殊语境中的“临时性颠覆重塑”,突出其众多性格中的某一缺陷,并极力使之向极端化方向发展,以此来申述己意。同样的例子在李诗中还能找到很多,此不一一。
(三)白鸥:着重加强寓意,“逸人”的象征
白鸥属着重加强寓意。《古风》其四十二《摇裔双白鸥》篇对“白鸥”的描写,源自《列子·黄帝篇》中的一则寓言:
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
《列子》寓言结尾只写到平日里与白鸥在海上相嬉相亲的人,有了捕捉的“机心”后,白鸥“飞而不下”。李诗开篇着重描写白鸥在海上自由翩飞的优美姿态,接着通过与“云鹤”的对比写其自由自在的神韵,以及休歇嬉戏之地的幽美,最后于篇末发愿:“吾亦洗心者,忘机从尔游”,从原本的“海人相游——萌生机心——白鸥不下”因果模式,拓展到“白鸥翱翔——海人相狎——吾亦洗心——忘机从游”的循环模式,即在简单的“海人”“白鸥”之间,加入了一个“我”,延续到自身,从而完成了对寓言的加强。这既是对“白鸥”形象的强化,也是对自我内心渴望成为一个“忘机者”的书写。
白鸥隐喻“逸人”。其性爱自由,难以被人驯服,终日自在逍遥,在海面遨游,远离喧嚣的人群和是非之地,偶有纯洁无机心之人到来,才会与之相互嬉戏。它不像云中之鹤,为了追逐功名被人所乘骑,而是一生追求自由自在。一旦人萌生逮捕它的念头,就会立刻升起警惕之心,远远逃离。它的休歇之处在远离人群的月色下、沙洲旁,嬉戏游玩的地方也在芳草丛生的幽静小洲之间,不染尘垢,引来诗人欣羡之情。李白表明自己也愿做一个洗心之人,涤荡世俗之尘埃,与白鸥忘机远游。
李白之前的唐诗中以白鸥歌咏高蹈逸人者并非鲜见,陈子昂《感遇》其三十就有“唯应白鸥鸟,可为洗心言”,称赞白鸥为洗心者;《春台引》也说“恨三山之飞鹤,忆海上之白鸥”,追忆遨游江海之白鸥的闲逸:然皆不及此篇对“白鸥”形象的更深层强化。李白之后,唐人咏白鸥者有许多,如刘长卿《福公塔》:“谁见白鸥鸟,无心洲渚间”;钱起《送包何东游》:“果乘扁舟去,若与白鸥期”;韦庄《婺州屏居蒙右省王拾遗车枉降访病中延候不得因成寄谢》:“怪得白鸥惊去尽,绿萝门外有朱轮”;晚唐陆龟蒙也写过《白鸥并序》,黄滔有《狎鸥赋》等,大都沿着李白“欣羡白鸥——愿与之游”这一线索发展,使“与白鸥游”成为“忘机者”的象征。
以上,除外形的相似与颜色的“洁白”之外,其余无论是性情品行、生活方式,还是象征寓意,三种白鸟都有较大差别。对白鸠、白鹭、白鸥三种白鸟的刻画,实际上不仅是写白鸟本身,而是赋予了其强烈的李白自身潜意识中的三重不同人格范式。白鸟形象本身只是表象,“贤人”“小人”“逸人”才是其实质。安旗也认为此篇的创作方法乃“以诸禽类喻人也”。
二 创作背景与“否定—进化”式的理想旨归
李白在这里两首作品中,对“白鸠”“白鹭”“白鸥”的态度极其明确:直接否定“白鹭”,一生追求成为“白鸠”,功成身退后,希冀成为超脱的“白鸥”。
这两首诗歌表达的理想与其创作背景、作年息息相关。然这两首作品虽寓意甚明,却通篇比兴,引譬连类,无一字能明确联系现实,似不好确论。詹锳在《李白诗文系年》中系《夷则格》篇于天宝三载(744),认为“似指貌似君子而阴为讪谤者”。安旗系于天宝六载(747),认为隐射李林甫大权独揽,重用酷吏,“屡兴大狱,滥杀朝臣”。此诗之作年虽不确,然大抵在天宝年间无疑。如果说外表洁白而内心非仁的“白鹭”象征在位之奸相李林甫的话,那么“鹰鹯雕鹗”嗜杀而贪婪的个性则明显隐喻其手下狰狞的酷吏及贪腐的官员。仅就寓意而言,詹氏与安氏之说似皆有理,但从白鹭“嗜杀”这一李白“临时性”强加,并颠覆其传统形象的人格特性来说,明显有所实指,安氏之说较为可信。如詹氏之论,仅指“谗言者”和“讪谤者”,似不足以当“贪而好杀”之恶评。
若依安氏之言,后半段批判白鹭乃激烈指斥李林甫及同党,则前半段也当有所隐喻,非纯写自然界之白鸠。从“白鸠”之寓意来说,似指开元末年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前已言,张九龄母丧,曾发生过白鸠、白雀巢于家树之异事。其在位期间,声名显赫,奖掖后进,直言敢谏,维护了开元盛世最后的繁荣,并预言安禄山将反。死后玄宗每有任命,便问受任者是否有“九龄风度”。后“安史之乱”爆发,其预言果成谶语,玄宗奔蜀时忆及张九龄之言,追悔莫及,曲江凭吊。张九龄去世于开元二十八年(740),时李白40岁,与此同时,开元盛世结束,天宝纪年开始。史书中虽不见李白与张九龄有直接交往,李集中也并无直接呈给张九龄之诗文,然张九龄之声名显赫,其生前逸闻轶事李白定当有所耳闻。二人前后文风相继,皆倡导复古,李白《古风》《感遇》等篇,无论从风格、语言,还是叙事、内容,与张九龄《感遇》诗都极为相似。张九龄《感遇》其四《孤鸿海上来》篇,以孤鸿自喻,以翠鸟讽刺其政敌李林甫,意存双关,寄托遥深,可与《夷则格》篇相参读,且与李白有亲密交集的杜甫在《故右仆射相国曲江张公九龄》中也称张九龄“千秋沧海南,名系朱鸟影”,亦可作为旁证。由此,先追忆已逝的“贤相”,后指斥在位的“奸臣”,篇末警醒天子任用贤臣,远离奸佞,前后关涉,似较为通。
《摇裔双白鸥》篇,萧士赟认为乃供奉翰林时所作:“太白少有放逸之志,此诗岂供奉翰林之时,忽动江海之兴而作乎?不然,何以曰‘吾亦洗心者,忘机从而游’者哉?飘逸不可羁之气,白心声之所发欤!”徐祯卿则认为不当系年,有板滞之嫌:“大抵白志在疏逸,不在禄位,故有是言。至谓供奉翰林之时,忽动江海之兴,则滞矣。”安旗系于天宝三载(744),正是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还之时。若言两篇皆作于是年,从表述上看,《夷则格》指斥奸佞,情词激昂,而《摇裔双白鸥》篇则较为闲荡舒缓,太白被“赐金放还”之时,似不应有如此平和之心境。萧氏认为供奉翰林之时“忽动江海之兴”,不无道理。
不论是天宝三载,还是天宝六载(747),大唐时局已开始滑入乱政的深渊,“安史之乱”一触即发。面对如此时局,李白在“白鸠”和“白鹭”之间,做了一个 “肯定”和“否定”的选择,这是其性格中极端激烈、黑白分明一面的呈现。
白鸥,既是李白人生得意、前途光明之时所期待的圆满美好结局,又是李白人生失意、前途晦暗的时候聊以排遣的自我安慰。李白终其一生追求的,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并于诗歌中反复表达此愿。“身”“名”被深藏之后做些什么?在李白而言,一是炼丹求仙,但这个愿望明显不具有现实可实现性;二是像范蠡一样,告别朝堂,泛舟五湖,做一个像白鸥一样飘逸潇洒的“逸人”。李白在他的诗歌中一再通过“白鸥”这一形象申述此心愿,《鸣皋歌送岑征君》曰:“白鸥兮飞来,长与君兮相亲。”《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曰:“明朝拂衣去,永与海鸥群。”由贤德于政的“白鸠”到逍遥天地的“白鸥”,由“朝堂”到“江海”,完成现实人生“入世”的阶段,再跳脱出来,进入成功之后“出世”的阶段,这是一种“进化式”的理想旨归。
从“白鹭”“白鸠”到“白鸥”,李白在诗歌中完成了由“否定式”到“进化式”的理想旨归,这也是李白终其一生所追求的最完美的人生路径。但李白最终也没有实现自己“明主贤臣”的志愿,徘徊挣扎在“入世”“出世”的泥淖中无法自拔,在“白鸠”和“白鸥”之间摇曳不定,痛苦抉择。
三 李白之“白”的双重标准与深层意蕴
李白秉性好洁净,喜欢一切“白”的事物。白色意味着极致的纯洁、高尚,不同流合污,不与现实的黑暗浑浊妥协;意味着一种从身体到精神,由外而内的执着坚守。“白”是李白诗出现频率最高的颜色词,杨国娟曾统计,在423句诗中出现过425次,其诗中出现过的白色动物就有白龙、白马、白鹿、白鹤、白雉等,其他如白虹、白雪、白云、白沙、白露等,不胜枚举。前人研究李白与“白”,只注意到李白爱“白”之一面,全然没有对不同的“白”加以区分。
在广义的层面上,李白对“白”没有好恶之分,对自然界中没有生命的事物,如白日、白云、白雪、白羽等,因为它们没有好坏之分,善恶之别,可以说李白是全部热爱的,这一部分在李诗中占有相当大比例。但这个说法又是不准确或不全面的。
从狭义象征层面来说,正因李白爱“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其诗中对大部分白色事物的描写是带有寓意的。一旦涉及深层性格,在“白”之进一步精神层面上,则有明显的好贤恶凶、好善厌恶之别。这既表明李白之于“白”有着自己的双重标准,同时又显示了“白”之于李白的特殊意义。
尤其是对有生命力的白色动物,李白对其好与坏、是与非、对与错、贤与恶的强调和要求,远远超越了因其自身天生外表颜色“洁白”而喜爱的层面,更看重其内在某些美好品德属性。李白对这些有生命、有象征意味的白色动物,有着极高的要求和标准,不仅要求外表洁白,而且要内在“纯真”,有德有仁。徒有表面的洁白,但却内心险恶的白色之物,代表着虚伪和狡诈,是李白所深恶的。白鹭在《夷则格》篇中作为一个反面的凶鸟形象,就是李白所厌恶甚至贬斥的。其他如《行路难》其二“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犬赌梨栗”[2](P168),《赠宣城赵太守悦》“自笑东郭履,侧惭狐白温”[2](P526),皆属此类。虽然这类白色的凶恶之物出现不多,但我们却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以及李白对他们激烈而明确的批判态度。其出现次数不多的原因,大抵是李白性好贤善,除在某些特殊语境中为了与“仁善”之意象对比,达到批判的效果时才会偶有使用,而在诗歌创作时潜意识里对这类白色的恶物作了规避。
综上,《夷则格上白鸠拂舞辞》和《古风》其四十二《摇裔双白鸥》篇,李白不仅对白鸠、白鹭、白鸥三种白鸟形象做了不同的传承、改造和加强,赋予它们明确的人格范式,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隐喻“贤人”“小人”和“逸人”,表达其“否定式—进化式”的理想旨归。尤其“白鹭”形象的临时性“颠覆改造”,既提醒我们李白诗歌中对同一意象运用的矛盾性和特殊性,更警惕我们李白对“白”有着双重标准,并非爱所有的“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