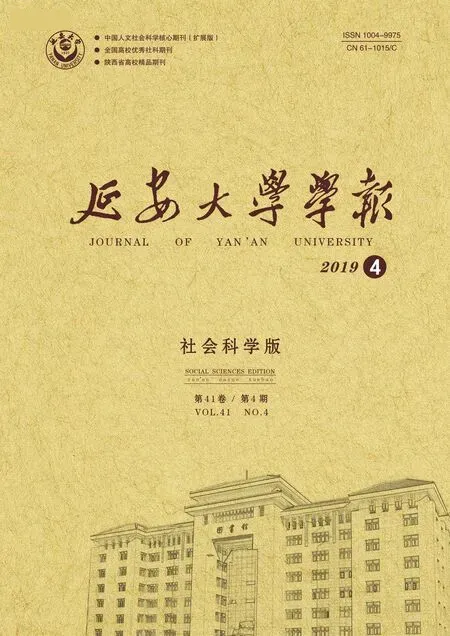性别空间的重构及其共同体想象
王华伟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郑州450046)
空间是现实存在和个体生存的基本样态与内在尺度,与显性的时间相比,空间多是处于被遮蔽、被遗忘的隐性状态。20世纪末以降,空间在福柯、列斐伏尔、苏贾、巴仕拉和迈克·克朗等人的推动下逐渐由幕后走向台前,空间转向的发生对美学、地理学、艺术和文学等领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空间批评主要关注空间中个体的生存境遇,尤其聚焦个体的生命意义及其现实命运。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将空间元素融合于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范畴,有助于推动并深化文学理论的创新。这其中,空间和性别之间多维而复杂的叙事关系在文学作品中多有体现,某种程度上讲文学所呈现的空间具有非常明显的性别化倾向。多琳·马西在《空间、地方与性别》中深度建构并透视了空间与性别的关联性,详细阐释了从时空区分和性别划分传统二元对立认识论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哲学思辨,并有力推动了性别空间的概念化与学理化。
作为英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和女性主义空间理论家,多琳·马西以英国现实空间为主要面向,特别关注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与空间关系。维多利亚小说中女性人物的生存境遇与现实命运之所以备受读者和研究者关注,与空间的性别化不无关系。但是,与女性角色受到的热烈推崇与深刻解读相比,男性及其空间表现与体验则整体上显得较为寂寥和平淡,这既是由空间的现实生态所决定,也是由空间的共同体想象所造成。
一、性别化的空间
性别空间自古以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只是人类看待性别空间的习惯造成其在场性的缺席。西方性别观的形成建立在生理决定论的基础上,由生理差异造成的性差异在历史上根深蒂固。有关两性差异的讨论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男女有别的性别二元论观念一直被沿袭至今,虽时有波动与震荡,但总体趋势依然是差异大于趋同,甚至是男尊女卑,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背景下这一传统性别观不断遭遇质疑、破坏和颠覆。亚里士多德曾经直言,“女性是不完全的男性,女性的身体就像是孩子的身体一样是不完整的,女性在本质上是虚弱的、冷的,因为她们缺少关键的热量。……在人类的生产过程中,女性只是容器,掌握胚胎的完全是男性。女性是被动的,男性是主动的。女人的性格中有某些自然的缺陷,女人在欲望上比男人更少节制,因为她们是更弱的性别。虽然都有美德,但他们的气质不一样,男人和女人,男人表现为命令,女人表现为服从”。[1]亚里士多德关于男女两性的言论如同一把利剑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画出一道割裂彼此的鸿沟,开辟出两个不平等甚至相对立的空间,性别的差异直接造成男女两性生存空间的不同,以及他们在空间中身份、地位和权力的不同。
性别空间(genderspace)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男人或女人在现实世界中所拥有的地理背景或物理环境,而是深受男女两性特征、观念和意识影响与铭刻的复杂空间,更像一种关系场。具体而言,性别是一种关于空间关系的营构,同时空间是一种承载性别内涵的表征。不论现实世界还是小说世界,厨房和闺房等家庭空间均被贴上女性化的标签,客厅、酒馆、矿井和旅店等公共性的空间则被赋予男性化的含义。如此看来,空间不仅是社会化的,也是权力化的,更是性别化的,恰如马瑟所言“空间既反映也影响着我们社会中性别建构与理解的方式”。[2]空间上的阻隔,造成男女两性在生存、身份和观念上的冲突甚至对立,并具体凝聚在自然环境、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各个方面。空间影响着我们建构性别的方式,也左右着我们看待性别的眼光;性别影响着我们进入空间的路径,也决定着我们体验空间的感受。正因如此,男性拥有自己的空间秩序和话语权力,并赋予空间男性化的内涵;女性拥有自己的空间界线和话语体验,并赋予空间女性化的特质。无论中西,不论古今,男主外女主内的基本空间界定与内涵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性真理,历史上虽有来自女权主义运动的持续抗争与不断颠覆,但对性别空间格局的改变既不彻底也不深刻。当然,女性空间一直以来给男性空间带来的日益增强的威胁与冲击不可小视,一定程度上已经引起男性的性别焦虑症和想象困难症。
在一个深处社会发展转型期或深受工业与科技文明影响的特殊时期,性别空间的生态往往也会在水深火热的现实中出现摇摆、破坏和动荡,维多利亚时代正是一个看似传统却充满着性别激荡的社会大转变、观念大斗争年代。在维多利亚时代,男性并非一直可以牢固守住由自我支配、领导的父权空间,同时女性也并非一味地被动接受父权空间对自我的铭刻、控制,表面上稳固如初的“男尊女卑”性别格局下暗流涌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改变。女性通过自我在空间中的反传统、反性别“斗争”试图打破长久以来存在于两性之间的空间秩序与身份规定,而男性则在已经形成的稳固性别生态中渐失保持平衡的力量,性别空间正在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意义,性别生态正在面临解构和重构。性别空间的二元对立不断受到性别模糊、融合、倒错甚至一元化性别观念的挑战,女性空间开始变得不再被边缘,男性空间逐渐变得不再稳固,就像一块儿蛋糕一样正在被重新切分。
二、想象与越界
维多利亚时代处在一个传统与现代、道德与叛逆相糅合的转型期,它依然被铭刻着“旧英格兰”的明显印记,同时“新英格兰”逐渐锋芒毕露,那个时代的英国城乡“处于一个文化的边界上”。[3]旧的东西还在被人坚守着,但新的事物也不甘示弱,它们一起见证变化可能带来的危机与希望。所以,这是一个充满传统与保守的社会,更是一个充溢流动与突破的社会,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们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不断寻求自我在空间上的突破,性别生态整体上的稳固难以掩盖局部上的动荡。如此的时代空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今英美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性别生态,我们从索尔·贝娄、托尼·莫里森、多丽丝·莱辛和爱丽丝·门罗等代表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似乎窥见到了遥远的维多利亚女人,并和她们一起想象、共同越界。
寻求自我空间上的突破必然要付出现实的代价,那些所谓的时代新女性常常被称作“魔鬼”,她们到处游荡却无安身立命之现实空间。因为女性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公共空间,一旦僭越必将受到惩罚、得到报应,这正是维多利亚社会对女性空间的权力化规训和对男性空间的符号化界定。“女性即使在自己家里也无法找到归属感:家庭不过是服务他人的场所,尽是毫无价值也不受认可的琐事,被奴役的女性自我在其中消磨殆尽,家庭成为暴力和虐待的空间,是女性受迫害、被隔离的空间。”[4]虽然被定义为温暖与安全的港湾,看似由女人“主导”的家其实原本就是限制、禁闭妻女等处于弱势地位的女人们的狭小空间,它虽不及监牢之可怕,却为女性垒砌一道不得轻易逾越的高墙,不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但是,空间既可以成为禁锢的手段,也可以成为反抗的工具,女性空间意识的觉醒正是她们抗争的根本表现。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们开始想象并渴望拥有更多更广属于自我的生存空间,她们不再愿意被那些拥有道德话语权和空间支配权的同时代人称为“魔鬼”,也不愿意继续做他们眼中所谓的“天使”,相反想要打破的正是由女性共享并限制女性的共同体载体“家”,因为所谓的避风港及其中的“家庭天使”(Angelinthehouse)仅仅是为了维护跟风上流社会价值取向与道德理想的面子。
对于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而言,家代表着她们最直接最真实的空间性存在,巴仕拉眼中的厨房、闺房、阁楼、地窖、窗户和抽屉等家宅意象已经呈现出显著的女性化表征,女人退缩到家宅的各个角落以获得某种保护或安全感,家以外的几乎所有主要社会角色均将女性排除在外,男女空间分隔观念根深蒂固。“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5],但这种摇篮般的保护实际上更多地造成了女性自我身份认同的迷失,家看似女性专属的城堡与港湾,实则是她们封闭的深渊与牢狱。女性作家艾米莉·勃朗特曾如此深刻地体会到同时代女性所经历的空间境遇,她通过自我独特的现实洞察力与文学想象力,试图为女性寻求一种跨越空间的性别共同体想象。但事实上,性别空间的重构甚至反转让女性付出了超乎想象的代价,她们变成徘徊在荒野上的幽灵。《呼啸山庄》中的凯瑟琳为了摆脱由男性主导的山庄空间,借助想象完成了自我作为女性在荒野空间上的超越和在幽灵身份上的认同。但是,如此之结局并非完美的生存境遇与期望,这仅仅是作家以空间想象的形式为现实中的女性所建构的“游牧”式共同体幻景,这也是艾米莉·勃朗特试图反叛、背离维多利亚时代充满悲剧色彩性别空间的个人努力。
不只是女性作家在为女人们写作、呼吁,男性作家同样在为女性的主体性空间建构发出属于他们的另一种声音,托马斯·哈代在《还乡》中成功塑造了极具空间叛逆精神和性别反抗意识的尤斯塔西雅。与身边传统的维多利亚女性完全不同,尤斯塔西雅向往大城市巴黎的繁华,渴望无拘无束的自由,她喜欢所有“令人激动和兴奋的东西”。[6]311这一切在埃顿荒原都难以实现和获得满足,因为尤斯塔西雅浑身充满“逆女”的欲望和骚动。与之相反,托马沁、约布赖特太太和苏珊等与尤斯塔西雅有着密切关联的女性人物,均能够很好地遵守以男性空间为主导的传统风俗习惯与道德观念,她们绝不像尤斯塔西雅一样与周围的荒原格格不入、冲突不断,相反都心无它念地坚守着“天堂”般的威塞克斯家园。但他人眼中的“天堂”却成为处处阻碍、时时妨碍尤斯塔西雅想象、向往外面世界的“地狱”。不论是在外公的住所,还是在婚后与丈夫克莱姆租住的婚房,尤斯塔西雅一直没有放弃摆脱威塞克斯人习以为常的荒原共同体的种种努力,她想要逃离男性的监督与固守。不能前往自己朝思暮想的大城市巴黎,尤斯塔西雅就无法得到真正幸福的生活和浪漫的爱情,而这样被困于荒原的生活对其而言就剩下孤独、愤怒和失望。
除了尤斯塔西雅,哈代还为读者塑造了有着类似空间经历的拔示巴、范妮和苔丝等经典女性形象,其作品对这些具有性别空间反抗意识的女性人物充满溢美之词,哈代在《远离尘嚣》中直言,“在这个娇弱的身体中蕴藏着完全能够从事伟大的巾帼行为的力量与实现这些行为的能量”。[7]然而,在维多利亚空间共同体背景下,恐怕尚缺少容许女性实现远大理想抱负的现实空间与性别话语权,哈代正是通过非同一般的艺术创作实践为女性想象背离传统束缚的空间性僭越。可惜的是,美好的愿景只能归于大胆的想象,囿于时代的局限,哈代无法为自己的女主人公们建构一个完全超越时代共同体范畴的女性空间,所以才有了一连串女性悲剧的发生,尤斯塔西雅最后丧命水底,范妮最后死于难产,拔示巴经历丈夫的背叛,就连集传统与背叛于一身的“新女性”苔丝亦屡遭命运的折磨和现实的锤击。
女性主义批评经典文本《简·爱》中的女主人公简,同样难以完全摆脱男性权威在现实空间中的影响力与控制力。虽说夏洛蒂·勃朗特赋予简表达自我、展示自己的叙事空间,但是这看似中心化的女性空间话语权建构的背后隐藏着女性在生存空间上强烈的依附感与边缘感。从孤女到“逆女”,在简的身体中虔诚与反抗并存、保守与叛逆同在,她的性别意识并不清晰,抗争之路充满纠结。从盖茨海德碍脚碍手的外人到劳渥德的撒谎者,从桑菲尔德躲在窗帘后面的人到芬丁庄园里的爱人,简一直在努力为自我争取社交的空间,只是最后却在被人忽视和遗忘的边缘空间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的幸福。简赢取空间话语权的途径其实很单一,那就是不断地与周围的人讲话、交流,正是通过建构自我的“话痨”身份逐渐使得简获取亦真亦幻的认同感和存在感,但这同时表明简在现实世界里缺乏安全感和话语权,渴望获得独立和权力。在主动建构空间话语权的过程中,简不忘告诫自己“我要是……不在他们的心底赢得一个位置,我是绝不会罢休的”。[8]玛格丽特·霍曼斯、苏珊·兰瑟等女性主义批评家对简讲述自我的毅力与能力大加赞扬,认为她不论从外表还是内心均承载着同时代其它女性所不具备的强烈性别意识与强大的空间精神,因为简极度渴望进入那原本就不属于穷人的共同体圈子。这样的阐释明显有着特里·伊格尔顿的影子,伊格尔顿通过将简定位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新女性”而实现对其性别的模糊化处理。正是这强烈的共同体冲动,才促使简在面对排挤、逼迫与流浪时不忘对梦想的追求和对美好的想象,单从这一点来讲,简就是自己时代“追梦人”的典范。
三、退守与破灭
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是“家中的天使”,而男性则是家之内外空间的权威和中心,正如罗切斯特在简·爱的心中像一头充满阳刚气质与强悍气场的狮子一样,他代表她的整个世界与希望。这种性别意识根深蒂固,哪怕位高权重的维多利亚女王亦是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地成为那个时代传统女性的典范,因为即便是对女英雄的赞美与歌颂也是建立在服从父权、夫权的基础之上。男性需要在外拼搏、养家糊口,以功成名就;女性需要操持家务、养儿育女,以辅助丈夫。所以说,维多利亚时代是属于男性的时代,更是成就男性的时代。但是,“女性的迁徙确实对于传统的父权秩序造成了威胁,无论是19世纪的英格兰妇女走出家门工作,抑或是威尔逊提到的在记录城市妇女生活时所遇到的困难,都体现了这种威胁”。[9]17传统意义上的性别空间生态并非自始至终稳定如初,男性长期主宰的背后一直暗藏着女性的骚动,女人们从未完全放弃在边缘中寻求突围、在束缚中争取解放的努力,由男性单一空间共同体主导的现实正在遭遇来自女性的威胁甚至破坏。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晚期,随着妇女运动带来的不断增强的女性觉醒与解放意识,女性走出家门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冲动与需求日趋强烈,而男性逐渐表现出空间上的退守与萎缩。
与尤斯塔西雅对埃顿荒原的厌倦与憎恨相比,克莱姆在荒原体验到的是促使自己走向美好未来的力量与期许,他打算在这里开创一番大事业,以证明自己从浮华的巴黎回归到穷乡僻壤并非错误之举。俗话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迷恋上强势而又不安分的尤斯塔西雅,克莱姆注定会在建构自我性别空间话语权的努力上败阵下来,几乎失明的双眼也预示着他悲剧性的婚姻和充满缺陷的男性性格。克莱姆心中理想化的男性空间就这样被不幸的婚姻一分为二,一半儿充满男性化的坚决与激情,一半儿充斥去男性化的盲目与克己。从克莱姆的遭遇,我们似乎看到了《简·爱》中罗切斯特从天堂跌入深渊的厄运,一场由疯妻点燃的大火瞬间将罗切斯特的世界化为乌有,身受重伤、双目失明则预示着其男性空间由强到弱的倒置与毁灭。
天生自带荒原狂野气质的克莱姆,只愿意生活在埃顿荒原的群山中,而不愿意被淹没在失去自我的繁华大都市巴黎,因为群山象征着自然的原始生命力和身体的强大本能,它可以让作为男人的克莱姆永葆激情与战斗力,恰如尼采眼中的查拉图斯特拉。正因如此,怀揣梦想与追求的克莱姆才毅然决然地放弃巴黎珠宝店最女子气的无聊工作,回到荒原做一个“配称作男人的人”,而不是将“时光虚掷在这种娇柔气十足的事情上”[6]211,这时的克莱姆厌恶女性化的生存空间,浑身流溢着独特的荒原野性。但是,一纸婚姻逐渐抹去了荒原给予克莱姆的气魄与勇气,也将荒原由克莱姆心中的“天堂”变为现实空间中的“监狱”,两个性格各异、理想不同的荒原年轻人就这样被哈代碎片化地置放于一个共时性的戏剧化空间中。克莱姆的经历告诉我们,空间体验“无论从其普遍形式还是从其特定内涵上,都与性别紧密联系”[9]14,尤斯塔西雅逃离荒原过程中的溺水身亡,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作家对维多利亚时代非主流理想化性别空间想象的嘲讽,任何想要彻底打破传统性别空间二元对立秩序的做法都将付出相应的代价。
哈代为笔下的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设定了特定的存在空间,它像古希腊神话用庙宇安顿诸神一样,给予他们接近真实生活的地方感与存在感。与克莱姆浓重的“乡愁”相比,《无名的裘德》中的裘德显然已经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文明的影响,他想方设法离开几近“消失”的乡村,摇身一变成为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但是,在城市残酷的现实面前,看似华丽转身的背后隐藏着诸多无力与无助。裘德在持续不断的空间变换中,有时候甚至连温饱也成了问题,更不用说进入只有一墙之隔的克里斯特敏斯特大学实现自我伟大的求学梦。裘德的悲剧在于无法准确想象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空间。用来维护中产阶级尊严与体面的大学,虽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因为那一道由石头砌成的围墙正是富足的中产阶级与贫穷的工人阶级的空间分界线。从申请大学被拒的那一刻起,裘德的城市悲剧之旅便拉开帷幕,先是游牧般的石匠生活,后是与淑因未婚同居的东躲西藏。在裘德抛弃了乡村之后,自我也被城市无情地抛弃,边缘人的定位无法给予他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感,裘德完全被排除在由传统宗教文明和新生工业文明主导的城市共同体之外。作为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乡村男人,裘德努力进城追梦的行为本身无可厚非,只可惜城市还是无情地给了他沉重一击,再大的城市也没有属于他的一席之地,终使裘德在碎片化的想象差异化的定位中渐失自我的空间存在感与身份认同感。
与裘德像似,《远大前程》中皮普的生活轨迹与现实体验再现了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空间位移模式。狄更斯精准地捕捉到同时代维多利亚人对空间变换的无限想象与积极追求,通过男主人公皮普从乡村到都市的横向空间跨越和从底层到上流的纵向空间跳跃,描绘出近代英国城市化进程的全景图。原本打算以做铁匠为人生的奋斗理想,但为了获取尊贵而优雅的埃斯塔娜的芳心,皮普怀揣实现“远大前程”的梦想奔赴伦敦接受上等人的教育,渴望以“绅士”的上流身份迎娶埃斯塔娜。但是,皮普所追寻的“绅士梦”实际上是自我“对不断增加的失败感、无用感和孤立感的一种反应”[9]280,它暗示着男性所面临的性别空间危机与身份认同焦虑。“绅士”一词在英国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代表着贵族和骑士阶层的空间表征与身份象征,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已经变成一种符号共同体,它不再代表任何阶层,它更多地承载着处于沉寂与没落中的富足之人与优雅之士。皮普所追求的绅士梦,只是借助外力实现成功的幻想,也是徒有皮囊的绅士做派,并无多少绅士的德行与内涵,所以直至被绞死皮普也没能找到空间上的归属感和身份上的认同感。“绅士梦”的破灭不仅表明绅士正在成为被废掉的一代,而且象征男性正在走向跌下神坛的道路,这在皮普性情温和、胆小怕事的姐夫乔身上同样获得印证。
男性作家眼中的维多利亚男人们呈现出悲剧的命运,那么女性作家又是如何呈现她们心中的男人呢?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经典女作家,乔治·艾略特的文学成就堪称卓越,为19世纪的英国小说留下异常浓重的一笔。在《织工马南》中,艾略特成功塑造了被空间控制和摆布的男主人公马南形象,因无法与自我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内部成员建立有效的沟通与相互的信任而一次次选择逃离。在灯场被好友污蔑偷盗,在小石屋被自己封闭起来,马南被围困于来自上帝和自我的双重监视,一次次的空间“逃逸”带给马南的只是越发封闭的空间,他在对共同体的想象中逐渐变为“独体”的存在。“地理空间按照不同的方式分类,而这些方式象征着社会地位”。[10]不同的空间对什么样的事情该在什么样的地方发生做出了性别与道德上的双重判断,触犯规矩、打破约束的任何举动都会遭受惩罚。无论是在灯场,还是在小石屋,马南都难以逃脱“监狱”般的来自共同体内部的权力规训,这样的经历因而预示着其在权力共同体重压下自我男性空间的坍塌和男性权威的弱化。但是,随着养女艾比的偶然到来和被盗金币的失而复得,马南又主动向自己之前选择背弃的宗教共同体靠近,心中再次燃起对上帝的尊敬之情与虔诚之火,这是马南在努力尝试重建男性空间共同体之后的再次退守与返场,终是没有逃离由教会主导的权力共同体藩篱。
通过空间定义性别,依靠性别体验空间,对性别空间的共同体想象已经成为文学叙事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与表现手法,这恰好与性别地理学(gendered geography)倡导的观点相吻合,同时彰显共同体观念的强大叙事功能。作为西方文学的源头性经典人物,《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通过充满冒险精神与英雄气概的空间位移让其在男性世界中突显出来,但与日俱增的回家冲动与急切心情同时表明男性权威的背后蕴藏着被威胁和被削弱的危机与焦虑,潜藏着女性试图流动、反抗和“越狱”的萌芽与迹象。巴邓-坡威尔认为,文明与城市正在打破西方社会的性别共同体,作家应该转而去边疆和蛮荒之地寻找并书写真正的男子汉,因为城市文明将会带来不道德、堕落和男人的退化,而维多利亚时代刚好处在一个乡村没落与城市突起并存的社会转型期,不同性别在城乡二元空间中的位移、转换和交织就显得尤为繁杂和敏感。实际上,这一时期的男性和女性均受制于空间上的差异与重构,这些空间经历很大程度上凸显出西方社会中真实的性别共同体想象,以及它带给男人和女人的全新空间体验,由此很可能造成非此即彼的性别空间格局在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营构中遇到更大的挑战甚至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