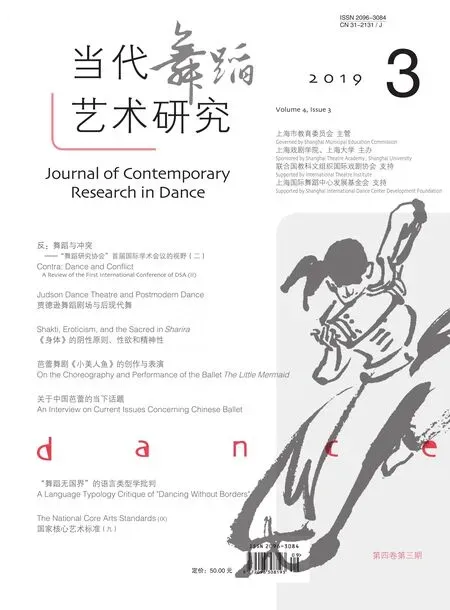探寻鄂西土家族喜丧仪式歌舞的乡土味
张玉玲
对乡土的探讨,在全球现代化与文化大量进入消费的当下,似乎是一个边缘性的话题,但将其置放到民间艺术(包括民间歌舞)现代化的场域中,则又成为一个严肃而重要的话题。因为中国乡土民间歌舞在专业剧场演出与职业歌舞教育双重需求的推动下,经历层层的剥离、改造,正一步步实现了向舞台民间歌舞的华丽蜕变,然而,华丽意味着与乡土的渐行渐远,就像我们在剧场观看一场民间歌舞演出后,往往会说,“美是美,但总觉得似乎少了点儿什么味道?”其实,这种让人说不出的味道就是乡土的味道。那么,这里所说的“乡土”指的是什么呢?费孝通先生在《乡土本色》一文中说,“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蔑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1]1也就是说,“乡土”是一个与“泥土”亦可以说是与“乡村”紧密关联的地域概念,因为我们看到城市已然用钢筋水泥的现代文明覆盖了原始的泥土风味,所以当我们用地域的概念来辨识乡土时,同时也在“城市代表革新,乡村代表守旧……城市代表当下,乡村代表传统”[2]的观念中体会到乡土在时间纬度上的辨识度。如此,乡土似乎成了土里吧唧、传统落后的与“丑”关联的代名词,而随着21世纪初王岳川、肖鹰、张法等美学与哲学专家汇聚一堂针对“乡土美学”展开大讨论,“乡土”——这被大多城里人所回避的字眼重新被审视,并以化“丑”为“美”的态势出现。那乡土何以“美”起来了呢?笔者以为,只有长时间浸染在乡村,才可能深刻感受到乡村山水林田、屋舍桌椅,还有乡民一举手一投足、一声言语一个眼神所散发出的味道、所透射出的美。下面,本文以鄂西土家族喜丧仪式歌舞“花鼓子”与“撒叶儿嗬” 为具体的案例,尝试以民俗述描的方式与读者一起从乡容、乡音、乡情、乡韵这四个方面漫步感受民间歌舞质朴动人、焕发生命力的乡土一面。
一、乡 容
乡容,即乡村容貌,具体到民间歌舞,就是指这种在乡村表演的歌舞外在显现出来的容貌,除了包括歌舞者的服饰、妆容、道具、精神面貌等,还包括歌舞所依附的仪式以及周边的环境,这些看似与歌舞无关的环绕因素恰恰是其乡土属性的基本标识,也是构成民间歌舞“乡土味”最表层也是最基础的因素。
鄂西土家族有自己的传统民族服饰:男子一般身穿琵琶襟上衣、大脚大腰长裤;女子一般身穿衣袖较宽大的左襟大褂、镶边筒裤或八幅罗裙,男女皆有头缠青丝头帕的习俗。但是,随着近代社会打破了封建时期“汉不入洞,蛮不出境”的民族隔离与羁縻制度,加上新中国鄂西山区交通闭塞的局面得以改善,土家族与外界互联互通日益频繁,土家人也随之逐渐被“汉化”。目前,村落里也只有极少数七八十岁高龄的老人还偶尔穿本民族服饰,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已不怎么穿了。所以,除了近几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推动下兴盛起来的乡村商业表演队,为了显示队伍专业规范、追求现场表演效果而穿着经过改良的土家族传统民族服饰之外,乡里百姓参与土家族喜丧仪式歌舞“花鼓子”和“撒叶儿嗬”,绝少专门穿着土家族传统服饰来表演的。他们一般身着日常劳作服饰,在舞到尽兴处脱了上衣赤膊而舞,当然更不会专门为表演而化妆。一般的情形是这样:倘若某家有喜事或是丧事,邻里乡亲、亲朋好友都会去给东家“热闹”一下,他们在干完农活或家务之后,约上同一个屋场(几户人家聚居在一个场地)的人一块儿去,如果在去的路上遇到他人行路返家或是在路边的田里干活,也会邀约对方一起去,因而,“赶情”(喜事)或“看信”(丧事)的人从回家路上或田间地头直接去东家也是常有的事。到了夜晚,作为喜事或丧事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主事者(喜事主事者称“知客司”,丧事主事者称“都管”)引导下,大家会主动上场为东家跳起“花鼓子”或“撒叶儿嗬”。自始至终,乡亲们都保持着生活中的本来面貌,率性叫歌、尽情舞蹈,虽然没有专业演员刻意修饰的精致,但其味道就在于没有丝毫装腔作势的感觉,反而显得格外质朴动人。
乡亲们跳“花鼓子”或“撒叶儿嗬”,不仅个人不作修饰打扮,就连歌舞的环境也很少用商业成品来点缀,大都由给东家帮忙的亲朋好友自己动手制作饰物来布置场景。如有丧事,置于堂屋正中的棺材多为本地木匠在亡人健在时手工制作而成;搁置棺材的桌子、长凳为平时吃饭用的八仙桌;棺材前面的“岁签子”,是临时用刀劈成细细的富有弹性的篾片裹着剪成碎花状的花花绿绿的榜纸,以根数来表示逝者的年岁;棺材前摆放的灵位,是当地的道士或文化人按照祖上传下来的规矩手书纸糊而成;早年的花圈,也是人们用篾片、柏枝及手工纸制白花做成,近些年改用商店买来的成品花圈;堂屋外墙上贴着一张大白纸,上面用毛笔写着主事和帮忙的人员名单及各自的职责;屋外宽阔平坦的稻场上用木头和塑料布搭成临时性的大棚,拓展了白事活动的空间……至于结婚、生子、做寿等喜事,则在堂屋里用两三张八仙桌蒙上红色喜庆的桌布拼成一个“大香桌”,上面摆放着东家自制的各式糕点糖果(喜事有期,东家会早早做好准备),桌子四周摆一圈长长的板凳,请尊者(做寿为寿星,结婚则为新娘的送亲代表,生小孩“接家家”则为新生儿的外婆)坐在上席,陪客的亲朋列坐其次,乡亲们也以香桌为中心围成里外几层,在领歌人的带领下大家一起唱“花鼓子”歌,唱到尽兴时,就起身在“大香桌”前两两组合边唱边跳了起来,仔细一瞧,舞者手中的道具居然是新毛巾。再者,东家的堂屋外墙上也会贴一张用毛笔写着具体分工的大红纸;整个屋场各家各户的大小门框上都贴满了当地文化人手书的红色喜联……凡此种种,在乡亲们亲手营造与维系的仪式氛围中歌舞,自能散发出一种无以名状的乡土味道来。
总之,鄂西土家族喜丧仪式歌舞“花鼓子”和“撒叶儿嗬”,无论是参与者个人之“容”还是整个仪式现场之“容”,都具有“生气远出”“妙造自然”的美感,处处流动着朴实、亲切、自在的乡土气息。
二、乡 音
民间歌舞常常是歌、乐、舞浑然一体的艺术形式,鄂西土家族喜仪歌舞“花鼓子”(一般不用乐器伴奏,极少时候也用锣鼓或一把二胡为间奏)和丧仪歌舞“撒叶儿嗬”(以鼓为伴奏乐器)便是如此。鄂西土家族人不乏唱歌的好手,名曰歌师,他们唱起歌来音色好、调门高、热情洋溢、收放自如,这有山大人稀需要呼喊应和的因素,也与土家族喜丧仪式活动频繁不无关系。“花鼓子”和“撒叶儿嗬”虽然出现在喜悲不同的仪式场合,但其乡音在本质上是趋同的,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声腔歌调上的主要特征,是女声假音、男声女腔。 “花鼓子”多唱些“郎”“姐”之类的情歌,一般为男女搭对边唱边舞,但近年来跳“花鼓子”的男子越来越少,就出现以女性为主即女女搭对的普遍现象。与其他擅长歌唱的少数民族不同,土家族的女性在唱“花鼓子”歌时,多用假音,与平时说话相比像换了个人似的,颇有些“表演”的感觉。更有趣的是,男性唱“花鼓子”也保持与女人同样的音调,不仅如此,动作也模拟女人,柔媚多情;至于“撒叶儿嗬”,口中所唱亦都是男声女腔,因为叫歌要求男歌师“嗓高八度”,以达到“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同时也显出叫歌之人率性洒脱、大方自如的表演状态来。当然,这种“男嗓高八度,无疑需要用假声(小嗓)发音。”[3]所以,无论是婉转抒情的“花鼓子”,还是高亢凌厉的“撒叶儿嗬”,歌其不变者,女性腔调也。
文辞风采上,则礼、理、趣三者交融,相映成辉。“撒叶儿嗬”在开跳前,掌鼓的师傅接槌叫歌,一般会说几句恭维孝家或自谦的话,如“一打亡人好衣服,二打亡人好棺木,老倌子死哒好享福”,又如“各位歌师傅都请坐,听我叫一个开台歌,年纪虽老掌不好鼓,声音不好喊不好歌,全凭客们抬举我”,颇讲求礼数。当然,唱词中也有类似《姐劝郎》重在说理的段子,以教化后人,如“一杯茶劝郎,劝郎进书房。诗书勤苦读,文章可在身。二杯茶劝郎,劝郎色莫贪,烟花巷里少夭亡”,等等。当歌舞至深夜,大家有些困倦时,歌师就会开始唱一些“风流歌”来打趣,如“远望姐儿对门来,胸对胸来怀对怀。胸对胸来亲个嘴,怀对怀来红脸腮。亲个嘴,红脸腮,快些快些怕人来。”这些性事荤歌看似放荡不羁,实际上“反映了土家人对人口增值的渴求”。[4]不仅“撒叶儿嗬”的歌词礼、理、趣相互交融,喜仪上的“花鼓子”也同样如此。“花鼓子”是结婚陪亲家和生子陪“家家”(土家人称外婆为“家家”,音gā)的重要环节。仪式开始,双方亲戚先围绕香桌坐好,开场由东家开始,然后相互唱一些客套和恭维的话,如,“石榴开花叶儿密,堂屋里扯起万字席。远来的客们都请坐,我在旁边把酒酌,听我唱个开台歌”;唱到兴致盎然时,东家就会招呼宾客拿起帕子起身边歌边舞,而舞着舞着,大家就放开了,又会穿插一些“荤歌”,如,“姐儿生得像蔸菜,嫩嫩蕻蕻长起来。我找你三回你不肯,还过三天菜起苔,你再送上门我也不爱”,这时,尤其是男女搭配的组合就会跳得越发投入,不时通过眉眼传情,惹得场外观众兴趣盎然、跃跃欲试。
其实,当我们深入土家族人的生活,就会发现,“花鼓子”和“撒叶儿嗬”并不仅仅出现在喜仪和丧仪上,上了一定年纪的人,平日里兴之所至,独自在山林田间劳作的时候唱上几段“撒叶儿嗬”(“撒叶儿嗬”平日还是比较忌讳在屋场内唱),或者在屋中做家务时哼上几支“花鼓子”也是常有的事,既能解闷,又能解乏,甚至于野外作业还有壮胆的作用。即是说,“花鼓子”和“撒叶儿嗬”是鄂西土家族生活化了的民间文艺,其所哼唱的歌词和腔调,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乡音,而且较之平时说话更加有民族辨识度,这种由乡音带来的特有的味道和归属感,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也是最真实质朴的。
三、乡 情
乡容、乡音只是表面的物质性或技巧性的东西,真正深沉动人的,是乡情。乡容和乡音之所以令人感怀,也是因为承载着乡情的缘故。在鄂西,土家族人遇到喜事或丧事,亲戚朋友、邻里乡亲会自发地为东家跳“花鼓子”或“撒叶儿嗬”——这既有完成仪式的因素,也有娱人娱己的成分,更有帮东家“热闹”造势的一份人情在,正所谓“打不起豆腐送不起情,跳一夜丧鼓送人情”。特别亲的人或是关系特别好的人,倘若不为东家卖力地跳“花鼓子”或“撒叶儿嗬”,似乎首先对不起的是他自己;而东家对特别卖力之人的感激,不亚于人情簿上随份子钱多的人。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1]7“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1]8跳“花鼓子”或“撒叶儿嗬”成为“送人情”的事实,恰恰是这种生活环境和乡土信用的明证,种种因素归结到一起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努力让东家的活动办得热闹。表面上看这是出于“人情”,本质上则是为了维护他们共有的生活环境和乡土信用。
这种与生俱来的生活环境和不假思索的行为矩度,还生动地体现为“花鼓子”和“撒叶儿嗬”的种种细节——它无意于独立地放大这些细节,而是悄无声息地将诸多瞬间的感觉内化为我们朴素的乡情——或者说,正是因为乡情的缘故,这些细碎的情节方才变得意义非凡。笔者在鄂西作田野调查时,常常被这样的情形所打动:
“花鼓子”场景:堂屋里香桌上摆满了糕点,从山顶上接下来的“家家”(土家人将生小孩后办喜事叫作“接家家”)和山脚下作为东家的“婆婆”(土家人称奶奶为“婆婆”)各自带着一班人马(大多是跳“花鼓子”的女性高手)围桌而坐,整个堂屋四周八围全是看热闹的乡亲。“家家”的人和“婆婆”的人虽有宾主之分,其实大家往往是一个村的人,山上坎下熟得很。东家齐呼:“山上的,来一个……”,“家家”那边便站起一人唱了一支“花鼓子”歌,众人轻和;接下来,客人又说:“坎下的,来一个……”,“婆婆”这边便站起一人再唱一支“花鼓子”歌,众人轻和……一支歌接一支歌,看哪边唱得多、唱得好。多次循环下来,斗歌大致见出胜负,就在知客司的安排下起身相邀,于“大香桌”前两两组合边唱边跳了起来——只见“家家”与东家请来的一位男性“花鼓子”高手很快在众人的簇拥下手持新毛巾踏起“之”字拐进入四对阵容的舞蹈队伍。伴随着“两步半”的步伐,歌舞者含胸撅臀、扭动腰肢,手臂也随之在身体两侧如风拂柳枝般前后摆动;到最后半步,短暂的靠步停歇,歌舞者口中正好唱出姐郎的相思情怀,而借这一个停歇,他们均用左手牵住右手的毛巾,抬至胸前,让右手腾出活动的空间而将食指指向对方,他们的眼睛也顺着食指所指的方向含情脉脉地投向对方。这时朝四周望去,此前吃饭时帮忙端菜的、盛饭的、收桌子的乡亲,居然也系着围裙混在人群中津津津有味地看着,时不时笑得人仰马翻。
“撒叶儿嗬”场景:灵堂前人头攒动,丧鼓咚咚,歌师高唱,场上有一对汉子含胸屈膝、肩靠着肩正跳得起劲儿,围观的人群当中,一男子挽着袖子冲着旁边的熟人说:“来,我们两个砸一盘儿(即“跳一盘”的意思)?”非常短暂的眼神交流,对方把外套一脱,爽快地回应:“搞得,砸一盘儿!”两人嘴里便和着掌鼓人的歌声捉对上场,与场上的那对一起跳起来。只见舞者们于颤动中晃悠摇摆着身体,脚下踩着“升子底”,手上挽着“链子扣”,一会儿靠身退进步,一会儿“车身望月”,一会儿蹲步绕手,一会儿靠脚击掌……舞得酣畅淋漓。过了一会儿,有观众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眼看着场上哪位年纪大些或是跳出汗来了,便瞅准机会,待那人转到自己面前时以舞蹈动作顺手将其拨出场外,不露痕迹地替换上场,瞬间融入表演的队伍,而被换下的人也不恼怒,极其自然地与场下的熟人打着招呼,接过递来的香烟,慢慢往边上的条凳一坐,又开始聊上了……
由上,不难体会,这鄂西土家族的喜丧仪式,不只是东家自己的活动,更是全村人联络感情绝好的平台;而仪式上的“花鼓子”和“撒叶儿嗬”更是承载着浓浓的乡情,这一歌一舞的味道满是乡土的眷恋,成为维系土家族群的坚实纽带。
四、乡 韵
鄂西土家族人跳“花鼓子”和“撒叶儿嗬”,不仅要唱得地道,还要跳得地道,任何一个环节,从来都不曾刻意去关照,而又绝少出任何差池,因为不论是“花鼓子”的歌与舞,还是“撒叶儿嗬”的鼓、歌、舞,都是一个自足的有机的整体,轻松适意,神完气足。当乡间喜丧仪式活动的帷幕拉开,我们看到了乡容、听到了乡音、感受到了乡情,最后徜徉于迷人的乡韵之间。然而,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韵”呢?恐怕我们真的无法找到某些具体的东西来描述它,但它就是那么真真切切地存在着,朴实、自在、有呼吸、有韵律。它应该是土家族人的生命之韵,源自土家族人自然豁达的生命观,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其中,生活在鄂西山区、清江之畔的土家人一直处于闭塞险峻的自然环境之中,主观的心理和客观的条件造就了他们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生存的渴望,他们总是积极乐观,甚至有些戏谑地对待生、老、病、死:喜仪中的“花鼓子”男女对舞,戏谑调情自不必说,就连丧仪中的“撒叶儿嗬”也是在亦悲亦喜的情感戏谑与转换中叫歌起舞。当鄂西土家族的村落里有老人去世了,他们会认为这是走顺头路,高高兴兴地当作“白喜事”来操办;同时,他们借助丧葬仪式活动,将对亡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寄寓化为流动的韵律,在充满阳刚之气和乐观精神的歌舞鼓槌中流转。在这个信念下,老人的离世不再是一件悲痛而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人们在灵堂前也不再悲惨戚戚,而会唱着“人到九十要分手,人死只怕病来磨,断气好比大睡着”,一边洒脱地欢娱歌舞。也正是土家人这种乐观豁达的生命观,使得“撒叶儿嗬”的歌舞表演在真情与戏谑中得以自由转化。比如,灵柩前的稻场上,两位小伙刚刚表演完“燕儿含泥”:一人敲打铜锣,另一人应和锣声作燕子飞翔状,只见舞蹈的小伙子双臂背在身后模拟燕子的双翅震动,双腿横叉向下慢慢最大限度地贴近但不接触地面,俯身,用嘴叼起地面上东家放置的香烟与钱币,然后借助脚撑地面的反作用力收起双腿站立起来。“燕儿含泥”因为横叉俯身自由上下的动作技巧,以及用嘴一次同时叼起多盒香烟与多张(枚)钱币的特殊技艺而获得观众的喝彩。接着,随着鼓声转调,场上两个小伙瞬间用手掩面颤抖着嗓音开始“哭丧”,只见他们一边蜷身悲歌,一边作痛哭相互安慰状,更有东家拿着毛巾走上来帮忙擦拭眼泪,使观者也禁不住开始抹泪哀伤起来……正当大家悲痛不已时,场上鼓声又突然转调至“四大步”,歌师叫起欢快高亢的歌,两个小伙马上踏着鼓点和起歌来,与另一对入场的舞者一起欢快地扭动身姿,交替穿插地成对舞起来……
另外,如前所述,“撒叶儿嗬”和“花鼓子”的歌词,含有大量赤裸裸的“荤”故事色彩,有比较直露的,如“撒叶儿嗬”唱词中有“郎害相思要吃药,姐说吃药是白说,酒醉还要酒来解,相思还要姐来医。药罐儿还在姐怀里”;也有相对含蓄的,如“花鼓子”唱词中有“一树樱桃花,开在岩脚下,蜜蜂不来采,空开一树花”。如此种种,这些指向性爱的唱词,无论是成人间的戏谑相娱还是对青少年的口传教育,最终全都指向人的自身生产,亦即关系到个体生命与族群维系。当然,土家族的先民们不可能在久远年代就有如此深邃的理性思考,但他们从社会实践中积淀下来的生命经验与意识,却依托人生喜丧仪式以“花鼓子”和“撒叶儿嗬”等歌舞活动为载体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所以,当这种生命意识逐渐成为该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时候,当然不需要多说什么,一歌一词、一举手一投足,总关乎乡情,而乡情的背后隐匿的就是我们无可名状的乡韵,它滋养于土家族人祖祖辈辈耕耘、劳作的那片沃土之中,只有当传达生命更替、繁衍讯息的歌舞仪式活动进行之时,我们才能够自然而又清晰地感受到流淌其间的独特气息与味道。
结 语
由上述乡容、乡音、乡情、乡韵交融而成的乡土味,是鄂西土家族喜丧仪式歌舞——“撒叶儿嗬”和“花鼓子”的独特魅力所在,也是其经历岁月陶染后依旧质朴动人、焕发生命力的根本。而由这种“乡土味”孕育出的“美”,并不是我们对美的普遍的、一般的理解,它甚至在局外人特别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人群看来,或许无“美”可言,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这种美是尚且生活在乡间的人在更多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里倔强地彰显自我存在、民族存在的一种标签。其乡土之美,乃是乡土之自在,它“包含着故乡、故土、大地的精神实体,成为人的恋土和回归家园的冲动 本源。”[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