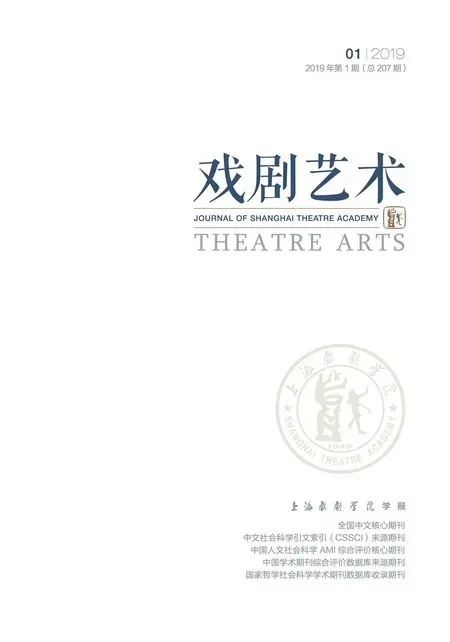跨文化戏剧:概念所指与中国脉络
跨文化戏剧不是分类学体系下的戏剧类型,而是方法论层面上的实践途径。其出现与表述,是对既有的戏剧实践方式的补充或颠覆。就当代中国或其他非西方世界而言,“跨文化戏剧”是译介的产物,因此,这一术语在“跨文化”的脉络中,其实是西欧“经典”(canon)戏剧理论与实践,面对复杂的全球化情境,对自身可能暗隐的文明普世性意识形态假定的一种强烈省察与质疑。和其他任何术语一样,跨文化戏剧的意义取决于言说它的具体历史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跨文化戏剧的概念所指无可追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其历史化:既避免简单粗暴地拒绝其理论锋芒与阐释效力,也要警惕将其供奉为超越具体问题脉络的理论“神学”。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把跨文化戏剧与中国问题脉络叠合,寻求并落实其诠释的合法性。
显而易见,跨文化戏剧这一偏正式短语中,是跨文化限定了戏剧,而不是相反。所以,跨文化戏剧就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跨文化加戏剧,而是一种整体、有机的跨文化观念与方法在戏剧诸领域的操作。换句话说,跨文化戏剧这一术语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不是“哪一类戏剧是或不是跨文化的”,而是“如何用跨文化的方法立场处理戏剧”。那么,我们首先要思考的就是什么是“跨文化”。
一、跨文化
事实上,“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这一术语诞生于文化、政治意义上的“非西方”古巴。古巴人类学家费尔南多·奥尔提斯(Fernando Ortiz)在1940年出版的西班牙语专著中,首次构建了“跨文化”的概念。1947年,奥尔提斯的专著的英译本《古巴的对照物:烟草与食糖》(CubanCounterpoint:TobaccoandSugar)出版,“跨文化”开始进入英语学术研究的视野。
在《古巴的对照物:烟草与食糖》中,奥尔提斯描述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背景中,作为古巴农作物的烟草与食糖在跨国经济行为中,如何以象征的方式展示了社会与民族文化的转型,而烟草与食糖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扮演的诸种角色正是“跨文化”的后果。奥尔提斯在强调“跨文化”术语的重要性时,对其含义进行了如此提炼:
在我看来,跨文化相当适切地描述了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转化的不同阶段。英文中的“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可以用来确切地表达这种文化转化过程,因为这个过程不仅包含获得一种新文化,还包括既有文化无可避免地丧失,此即“文化萎化”(deculturation)。除此之外,这个文化转化的过程还传递出了新文化现象应运而生的意味,亦即“文化更新” (neoculturation)……[注]Ortiz, Fernando. Cuban Counterpoint:Tobacco and Sugar, trans. by Harriet de Oni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02.
奥尔提斯的简要描述提供了一个理解“跨文化”的图式,即异质文化的互动场域,其中共时地包含着“文化适应”“文化萎化”与“文化更新”的阶段和过程。
奥尔提斯的“跨文化”概念界说具有明显的反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他借助此术语否定了单向的异质文化互动图式,揭示了其中双向协商的复杂情形。半个世纪后,奥尔提斯的观念启发了美国学者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在其《帝国的眼睛:旅行书写与跨文化》(ImperialEyes:TravelWritingandTransculturation)里面,跨文化作为整部著作的关键概念出现,并被作者提升到分析框架的层面。普拉特在有关跨文化这一术语的学术史注释中,明确提到了奥尔提斯及其著作。[注]Pratt, Mary Louise.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244-245.在论及跨文化出现的理由时,普拉特论证道:“虽然被征服者不能自如地控制统治者文化所施予他们的东西,但他们确实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如何应用,他们赋予这些东西以什么样的意义。跨文化是接触地带中的一种现象。”[注]Ibid., pp.7-8.值得注意的是,普拉特在界定跨文化时,发展出了另一个贯穿整部著作的术语“接触地带”(contact zone)。它指代“帝国遭遇的空间,在此空间里,因地理、历史原因被分割的人们,彼此互相接触,并建立起持续的关系,常常包括高压政治、极度不平等以及棘手的冲突等状况。…… ‘接触’的视角强调了主体间的关系。它处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或旅行者与‘旅行地人’之间的关系,它依据的不是分割,而是共在、互动、互联的理解与实践,彼此常常处在一种极度不均衡的权力关系中”。[注]Ibid., p.8.“接触地带”虽然强调主体间的共在共联,但始终清醒地在霸权的前提下讨论文化迁移与互动,并没有乐观地把被殖民者的能动性夸大到可以抵消权力关系的地步。在此前提下,普拉特拒绝了把文化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本质主义地安排在诸如殖民与被殖民、主宰与臣服等一系列简单、僵硬的二分范畴之内。这种思路既在哲学前提上彻底承认了殖民者的文化宰制能力,也忽略了更为复杂的历史情境。其实,被殖民者能够主动挪用宗主国文化材料、创制新文化的群体,这一意义面向不应被简化的二元对立屏蔽在研究视野之外。
即使没有注释,我们也能够在普拉特在其《帝国的眼睛》中使用的两个关键术语——跨文化和接触地带——中清晰看出她与奥尔提斯的一脉相承之处,即对欧洲中心的知识生产模式和文化互动图式的挑战。奥尔提斯首创性的《古巴的对照物》与普拉特典范性的《帝国的眼睛》都建议,跨文化研究须在共时的条件下,从外在于欧洲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心/边缘”的两极化对立叙事。在这个意义上,transculturation/跨文化这一术语可以理解为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运作过程中的文化杂糅。跨文化对异质文化之间杂糅性的强调,常常呼应着后殖民批评代表人物之一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关键概念“杂糅”(hybridity):“杂糅是殖民的权力、力量转变和固定性的生产力的符号;它也是通过否认,进而对支配进程的策略性翻转的别名(即那种对获取‘纯粹’和起源性的权威身份的歧视性认同的生产)。”[注]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eledge, 1994, p.159.巴巴晦涩的术语建构与论证提示了一种跨文化/文化杂糅的哲学效力。当异质文化相遇时,二者蕴含的既有身份边界开始遭到干扰,“‘纯粹’和起源性的权威身份”在跨文化的空间里面开始变得可疑,成为缺席的在场;原本被支配的文化在跨文化空间里面,可以对支配性文化投以“回望凝视”。除了杂糅,巴巴还有一系列互相支撑的术语,比如“居间”(in-between)、“模拟”(mimicry)、“协商”(negotiation)、“非家”(unhomeliness)、“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等。这些术语背后共享了同一种诉求,即一种流动的、动态的、非本质主义的跨文化互动观念,它们可以与普拉特的跨文化、接触地带等概念互相参照。
跨文化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研究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英国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她的《比较文学批评导论》(ComparativeLiterature:ACriticalIntroduction)一书中如此描述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截然不同。……后殖民主义虽然也挑战殖民文化的霸权,但它与反殖民主义不同,它会承认殖民与被殖民之间的多元接触。”[注]Bassnett, Sus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Oxford: Blackwell, 1993, p.78.在普拉特的跨文化研究观念与巴斯奈特界说的后殖民主义之间作一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完全一致,而普拉特的《帝国的眼睛》如今也已是后殖民研究的典范之作。事实上,在巴斯奈特与普拉特的之前的著作《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中,作者就明确指出:“用‘后殖民’这个术语来指称近年兴起的‘跨文化批评’及其建构的话语,是最贴切的。”[注]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任一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该著英文原版出版于1989年。如此看来,跨文化研究与后殖民研究与在英语学界(特别在是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至少在方法层面上似乎是同一回事。
二、跨文化戏剧的概念所指
当跨文化被用于限定戏剧时,一切与戏剧相关的创作、理论与学术都将微妙地沾染上复杂而矛盾的意味。比如,国别戏剧的纯粹假设可能无法立足,人文主义的观演立场将饱受质疑,形式主义的审美解读将不再有效……总之,在跨文化的视野中,文化杂糅与权力关系成为戏剧实践的核心关注。
这样的跨文化观念对戏剧创作或研究而言,最大的启发就在于避免运用戏剧材料去构建一套空洞、抽象的身份政治和起源想象。这一诱惑对跨文化空间里面遭遇的两种文化都颇有吸引力。就殖民者的强势文化而言,为被殖民文化涂抹一层浪漫多彩或邪恶可怖的异域外衣(比如“东方主义”)至关重要。如此,彼此间的差异可以被绝对化,被殖民文化就成为殖民者自我的表述和投射,以知识客体的性质服务于殖民宗主国的内外治理。殖民者这一“文化帝国主义”实践常常借助其海外拓殖的历史,在殖民地世界的心智层面深深地植入了其优越性的意识形态,并为后者留下了沉重的文化包袱。
作为殖民主义的一种后果,(后)殖民地知识分子在其包含戏剧创作在内的文化书写中,又会以充满挑战的姿态,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以地方性知识为基点,反向评估、甚至质疑二元格局中的强势的殖民文化的普遍性,进而论述地方性文化的独特意义与价值。这种反应往往源自否定的激情,它试图对殖民文化对抗和拒绝。但是,在激情的背后,它仍然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分享了同一个理论前提,即边缘和中心的二元区隔。在对抗式的文化实践里面,地方性虽然得到了承认和展示,但被忽略的问题则是:地方性文化需要谁的承认?为什么需要其承认?答案一目了然,即作为地方性文化对立面的殖民文化。在这一文化“比较”方案中,地方性文化落入了相对主义的陷阱,它假设自身是超越历史的、静态的、完成的既定传统文化模式。这一假设事实上支持了殖民文化的普遍性地位,因为地方性文化(不)自觉地把自身设置为其对立面,并未对它们所共处的话语结构构成任何挑战,从而使地方性文化成为“普遍——特殊”模式中“特殊”的一极。在这一过程中,二元格局事实上更加稳固了。而这也正是殖民统治所喜闻乐见的知识后果,正如法农所言:“倒是殖民者成为当地风格的保护者了。”[注]弗朗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70页。这种矛盾的情形,在戏剧领域亦很常见。就曾经属于半殖民地的中国而言,比如1925年5月,余上沅、闻一多和赵太侔等人在北京发起的为时短暂的“国剧运动”,[注]可参见拙文《中西戏剧交流的误区与困境:“国剧运动”及其文化民族主义悖论》(见朱恒夫、聂圣哲编《中华艺术论丛》第11辑,“中外戏剧互动研究”专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对该问题的讨论。梅兰芳1929至1930年在美国演出时,西方先锋文艺界对其在美学/意识形态层面的跨文化置换以及本土的回应[注]可参见拙文《东方文艺复兴思潮中的梅兰芳访美演出》(《戏剧艺术》,2013年第3期)对该问题的讨论。等,都暗示了19世纪末期以来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对“东方”美学思想资源的挪用。而这种跨文化挪用最终又诡异地反哺“东方”,在本土知识分子中掀起回归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
也正是这个原因,巴巴倡导“非家”:“它是一座桥梁,在此‘在场’才得以发生,因为这座桥承载了疏远那种为家和世界重新定位的意义——非家——这就是超越地域和跨文化开始的情境。”[注]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eledge, 1994, p13.甚至可以想象,在跨文化的历史脉络中论证地方性文化特殊性,其实也是自我否定的,因为它深刻地复制了原本属于强势的殖民文化的运作机制,它本身就是否定边缘的。在其心智层面,同样存在着成为“中心”的渴念。这种对抗的文化操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比诸如“东方主义”式的涂抹更加隐蔽,因为它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和合法的表象,可以掩盖其伪善和危险的一面。
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开始的情境”始于“非家”。旅美华裔学者陈小眉对中国戏剧的跨文化研究就彰显了这一观念与方法。其《西方主义:后毛时期的反话语理论》(Occidentalism:ATheoryofCounter-DiscourseinPost-MaoChina)尽管不是一部专论戏剧的著作,但其中对相关戏剧个案的处理方式,提供了一种跨文化戏剧研究的范例。该著鲜明清晰的问题意识远远超越了戏剧学科的畛域,而是参与到当下全球人文研究领域的公共性议题之中。事实上,这也是跨文化视野突破既有的戏剧研究范式后的必然特质——戏剧研究走出本体论的框架约束,迈向了文化批评。陈小眉的《西方主义》意在探讨半殖民地化的中国,在自身的语境中,把殖民地他者的话语挪用到自己的政治议程中去的策略与过程。[注]Chen,Xiaomei. 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 New York: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2, p.13.在此问题意识的统摄下,论者拒绝了“以本质主义的方式支持东方主义的反对者”。[注]Ibid., p.8.这种“本质主义的方式”具体表现在:“……在全球支配的脉络中,任何本土对他者的文化挪用,必定有负面的后果,如果是‘高级’文化挪用‘低级’文化,就是帝国主义式的殖民行为,反之,就是‘低级’文化的自我殖民。”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观点,陈小眉举出了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跨文化解读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TheMahabharata)遭到西方部分学者批评的例子。有学者认为,布鲁克的解读基于普遍性的预设抽空了《摩诃婆罗多》的内核。对此,陈小眉批评道:“在此,我们看到,相对于跨文化交流后被接受的文化中含有的异己特质,原初文本和文化中‘来自本土视角’理解的‘内核’首先获得了特权。”[注]Chen,Xiaomei. 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 New York: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2, p.7.所以,“忽略本土对西方话语以及为其发声提供焦点的各种境况的利用,将使跨文化研究寸步难行。”[注]Ibid., p.12.那种对强势的西方话语的跨文化挪用,她称之为“西方主义”。陈小眉对追寻原初文本“内核”的强烈质询,构成了她的跨文化戏剧研究实践的起点。
在《西方主义》中,陈小眉以五四时期话剧中的性别、“新时期”中国话剧舞台对莎士比亚、易卜生、布莱希特、桑顿·怀尔德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戏剧观念的搬演和跨文化挪用为研究对象,既运用跨文化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讨论了这些戏剧现象,又同时检验了跨文化的方法在戏剧研究中的有效性。比如,在关于中央戏剧学院1980年演出的《麦克白》的解读中,陈小眉没有去大费周章地比较中国的《麦克白》与近代早期英国的《麦克白》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论者摒弃了一种本质主义的视角,避开了在“原初文本”与“跨文化文本”之间辨析遵从或背叛的问题陷阱,而是去关注1980年的中国挪用既有文本《麦克白》的动机、策略,以重新搬演的新文本在新的文化语境和问题脉络中的意识形态功能。陈小眉认为,就《麦克白》在跨文化旅行中的意义错位而言,“在接受者的具体环境中,谁还在乎北京上演的《麦克白》的‘本真’含义呢?谁又能解释清楚《麦克白》‘本真’而‘正确’的含义呢?……在此,西方主义的戏剧在帮助中国人从刚刚过去不久的文化悲剧中走出,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注]Ibid., p.46.在陈小眉确立的跨文化戏剧研究框架中,我们看到,跨文化戏剧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被跨文化挪用的他者文化元素如何并为何成为自我文化语境中的戏剧思想资源,以及其中的文化权力、话语关系是何种构型(discourse formation)。
无独有偶,在克莱尔·斯彭斯勒(Claire Sponsler)为论文集《西方的东方:跨文化表演与差异的展示》(EastofWest:Cross-CulturalPerformanceandtheStagingofDifference)撰写的导言中,表达了与《西方主义》一致的跨文化戏剧研究观念。斯彭斯勒指出:“《西方的东方》把跨文化表演问题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仔细考察了那些跨越国族疆界的表演,探讨了表演和表演者从‘本土’移植到新的地方,特别是跨越了彼此曾经分割六百多年的东西方时,会发生什么。这本文集……同时也考量了本土传统如何努力地适应并赋予成效地转化移植进来的的文化。……表演被以各种方式被重新创制,以满足新的意识形态、社会和政治诉求,这种机敏的适应和文化的弹性在此过程中一目了然。”[注]Sponsler, Claire. “Introduction”, in Sponsler, Claire and Chen ,Xiaomei ed. East of West: Cross-Cultural Performance and the Staging of Differe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2000,pp.2-3.正如前文指出的,跨文化研究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之间有诸多呼应之处,甚至有学者认为二者间的差异仅在于名称。这意味着跨文化戏剧实践,是一种从广义的“比较”视野引申出来的观念与方法在戏剧领域的文化政治操作,而不是一种以显性的学科边界或戏剧题材构成为出发点的戏剧类型划分。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部分学者对“跨文化戏剧”仍存在着一定误解。比如,有些学者认为,像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胡适的《终身大事》、奥尼尔的《马克百万》、梅兰芳访日访美、布莱希特的《灰阑记》等戏剧家跨国交流合作或某位导演对异国戏剧的重新编排,这种具备显在、可见的涉及不同戏剧传统的创作才是“跨文化戏剧”。其实不尽然。姑且不论15世纪以降的大航海带来的全球化和今天数码科技导致的“时空压缩”,人类可能从来就无法拥有某种纯粹的文化。当我们谈及文化,就已经是一种相对的、权宜的表述。借用詹姆逊的观点:“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氛围,它是那个群体陌生奇异之处的外化。”[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20-421页。那么,“跨文化”与文化“杂糅”就是人类的常态,问题的关键在于,戏剧实践是否是在此视野中展开。所以,上述戏剧现象属于但不等于“跨文化戏剧”,“跨文化戏剧”的要点在于方法视野。“跨文化戏剧”可以理解为一个动词短语,即用跨文化方法展开的(包括创作、理论和研究等在内的)戏剧实践。简言之,不存在一种叫做“跨文化戏剧”的戏剧类型,跨文化在此是开启(相对于欧洲经典范式的)“全新”的戏剧实践的途径。
从思想资源的角度看,跨文化戏剧其实与其他当代其他人文领域,特别是比较文学共享了同一种知识结构。1970年代,“法国理论”(French theory)介入人文研究领域后,在巴特、德里达、福柯、克里斯蒂娃、拉康、德勒兹等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的启发下,人文研究领域开始实现大规模的科际整合或跨越。比较文学是最先回应并践行该学术动向的学科之一。[注]比如,美国比较文学学会(The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在冷战结束后,基于1965、1975年的报告和1993年的“伯恩海默报告”(The Bernheimer Report)及其回应与批评编撰而成的第一本关于学科发展状况的“报告”《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就对该现象作出了较为深入的研讨。See Bernheimer, Charles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诸如性别研究、大众文化批判、新媒体技术批评、翻译研究、后殖民研究、少数文学研究、“全球—南方国家”文学研究等,成为备受当代比较文学学者关注的新兴领域或方法。但与此同时,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同时也开始变得模糊,其研究方法也逐渐为其他人文研究领域借重。这种跨学科“要求的是学科间的相互借鉴与挑战,互相的对话甚至协作”,并借此质疑、打破既有的学科疆界带来的权力关系,厘清被传统学科疆界中存在的盲点所掩盖的内容。[注]钟雪萍:《前言:在妇女学与社会性别研究的思想交流中寻找共识》,钟雪萍、劳拉·罗斯克主编:《越界的挑战:跨学科女性主义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4页。跨文化研究或后殖民研究本身的跨学科性质,其中的方法视野与戏剧创作或研究相遇并互渗,是必然的。而且,戏剧实践采用了跨文化的方法视角之后,其本身也呈现出一种跨学科性,这种实践在处理戏剧元素或解析戏剧文本的跨文化流动的同时,还关注帝国与本土在知识生产中的碰撞和交叉,以及此中呈现的身份表征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9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名为“剑桥现代戏剧研究”(Cambridge Studies in Modern Theatre)的系列丛书,其中有一本《后殖民戏剧导论》(AnIntroductiontoPost-colonialTheatre)。《后殖民戏剧导论》的主体内容是评论全世界有着被殖民历史的国家的重要戏剧家,那么,理解“后殖民戏剧”的关键就在于观察该著遴选研究对象的学术尺度。
在 “前言”里面,《后殖民戏剧导论》的作者明言:“事实上,所有这些论及的戏剧家们共享的状况就是文化上的臣属或劣势。……在这些戏剧家的生活经验和艺术工作的核心位置,存在着这样一种认知:他们的人民和文化不被允许以一种‘自然的’历史图式发展,而是被他族扰乱或统治。”[注]Crow, Brian. “Preface”, in Crow, Brian and Banfield, Chris. An Introduction to Post-colonial Theat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VIII.该著论及的戏剧家有七位,虽然彼此的戏剧实践面临的具体历史脉络各不相同,但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共性就是对本土文化中的神话元素的倚重。这种戏剧“寻根”的实践意在恢复被西方民族主义及其惯常的历史假定中断了的文化认同与自信:“在其神话形式里面,时间不是‘按顺序变迁的’,而是‘不变的当下的永久资源’,其中的所有时代,过去和未来,都被含蕴其中。”[注]Crow, Brian. “Preface”, in Crow, Brian and Banfield, Chris. An Introduction to Post-colonial Theat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62.不同的时间观对应的是不同的历史观。用作者的话说就是,“神话的意义可能联结着变动中的政治议程”。[注]Ibid., p.164.《后殖民戏剧导论》中论及的戏剧家之间共享的特征构成了该著遴选研究对象的基本尺度:依据被殖民的历史经验,通过戏剧的形式进行自我文化的再生产,对西方帝国的普世性观念提出质疑。所以,后殖民戏剧中的神话与寻根其实是在挑战启蒙主义的线性史观和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进而解放出被压抑的本土历史与叙事。根据《后殖民戏剧导论》一书提供的线索,可以说,如果存在着“后殖民戏剧”,那么,其所指完全对应了作为方法的“跨文化”戏剧的实践诉求。
三、跨文化戏剧与当代中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跨国学术交流的日益密切,中国学者开始译介并思考跨文化戏剧的相关讨论和问题。跨文化戏剧在中国引起关注的历史和知识性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因应全球化进程的再次全面启动而激发出的非西方世界身份意识的自觉,而跨文化戏剧实践的问题意识本来就源自戏剧美学在意识形态层面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反弹,与此相应,中国戏剧界也带着自身的文化诉求,开始跨文化戏剧的相关实践;二是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思潮在这个时期被译介到中国,并在人文研究领域,尤其是比较文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界引起深刻而广泛的讨论,也为跨文化戏剧实践提供了基本的路径。这两个重要条件,暗示了跨文化戏剧本身的“跨文化”特性。
脉络生成意义。从欧美译介的观念方法,经过跨文化旅行至当代中国的问题脉络,在一定程度上势必发生萨义德所谓的“被其新的用法及其新的时空中的位置转变”的情形。[注]Said, Edward W. 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p.227.根据前文所论,跨文化戏剧作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特征的术语,其公共性体现于对西方文明普世性话语的质疑。因此,它必须以既有的西欧戏剧“经典”作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经典”戏剧的衍生物。这种关系类似于德里达论证的本源与“替/补”(supplement)逻辑[注]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456-459页。:跨文化戏剧虽然是“经典”戏剧的延伸或补充,但它反向动摇了“经典”戏剧的本源性、普适性;而更为复杂的悖论在于,跨文化戏剧自身也无法外在于“替/补”的逻辑。“替/补”逻辑对移植后的跨文化戏剧观念的自足性的干扰与消解,我们正好可以从它旅行至中国的历史条件与知识条件的关系中一窥究竟。
如果说倚重于后结构主义哲学,并诞生于欧美的跨文化思想视角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理论,在西方“起源”处意味着一种对启蒙现代性的内部反思,但在“终点”/本土却意味着对西方的外向批判和自我文化身份的重建。也就是说,作为“知识”的跨文化戏剧实践与国族身份政治的“权力”互相协调,跨文化戏剧在本土的知识条件与历史条件达成了一致,而不是互为制衡。这种状况与其最初在西方脉络中的自我批判的精神内核背道而驰,那么,跨文化戏剧在本土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甚或沦为民族主义和保守意识形态的附庸。该情形正是前文论及的本土对原本属于强势的西方文化的运作机制的悄然复制。跨文化戏剧作为西方“经典”戏剧的“替/补”,其背后的逻辑效力在解构西方“经典”的同时,此时却面临着自我消解的困境。
我们不妨以当代中国就跨文化戏剧的相关讨论作为文本,对上述困境展开进一步的说明。就笔者所见,目前国内对跨文化戏剧最集中的探讨表现在《全球化与跨文化戏剧》这部论文集中。除了个案研究,这部文集的第五章包含四篇谈话,分别是中国学者对德国学者艾利卡·费舍尔-李希特、美国学者理查·谢克纳的访谈以及中国学者之间的对谈,它们较为鲜明地折射了当代中国戏剧学界对跨文化戏剧相关理论建设的思考和构想。在中国学者对欧美戏剧家的访谈里,可以清晰地看到特属于本土的“概念焦虑”,即中国学者对“什么是跨文化戏剧”的追问甚为迫切。[注]何成洲主编:《全球化与跨文化戏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3、146、152、160页。这个被屡屡问及的问题本身,暗示了本土对“起源”的执念。该问题背后的假设是:存在着一个概念明了、意义确定的来自“西方”的“跨文化戏剧”。但事实上,概念越清晰,欺骗性就越大。跨文化戏剧并没有一个超越具体问题脉络的本质化界定,仅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戏剧实践的理念与方法,而且言人人殊。
有着比较文学学术背景的费舍尔-李希特认为,跨文化戏剧生成的过程中,“他者的传统根据接收者的具体情况在不同程度上被修改。……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对他者戏剧传统加以借鉴和挪用的出发点是解决各自文化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注]同上,第143页。费舍尔-李希特的比较文学知识结构使其“跨文化戏剧”观与前述玛丽·路易斯·普拉特、苏珊·巴斯奈特、陈小眉以及克莱尔·斯彭斯勒等学者共享了同一种分析框架,其中最明晰可见的部分就是:承认异质文化传统相遇之后,彼此可以挪用并涵化对方,进而创制本土全新的话语实践的可能。其中的关键追问已经不是“他者戏剧传统”如何,而是为何如此接受并挪用“他者戏剧传统”的问题。有趣的是,费舍尔-李希特目前已经放弃了跨文化戏剧这一术语,原因是她认为“跨文化”假定了存在着若干种边界清晰的文化类型(这也印证了那种依据显在、可见的“跨文化”现象定义跨文化戏剧类型的无效),而这在后殖民和全球化语境中,已经是不可能,当代的实际情况类似霍米·巴巴所说的“第三空间”或“杂糅”状态,所以她采用“表演文化交叉”代替跨文化戏剧来指代各种类型的文化接触。[注]何成洲主编:《全球化与跨文化戏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3-144页。“表演文化交叉”这一表述,至少在知识愿景层面,借用一个新的名词短语回避了“跨文化”概念所依赖的(不可靠的)异质文化边界假设。在后殖民“杂糅”与权宜的“文化”概念的知识系统中,艾利卡·费舍尔-李希特大费周章的术语转换其实大可不必。跨文化戏剧中的“跨文化”根本上是作为方法,而不是属性对戏剧实践加以修饰或限定的。不管费舍尔-李希特使用何种术语,我们都可以在她的跨文化戏剧观中,看到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理论范式,其观点与本文前述的跨文化戏剧的概念所指相当一致。
理查·谢克纳则表达了与艾利卡·费舍尔-李希特不同的跨文化戏剧观点。谢克纳也在承认不存在纯粹文化的前提下,[注]理查·谢克纳:《人类表演学系列:谢克纳专辑》,孙惠柱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216页。把跨文化理解为文化间的传播与交流,虽然他承认文化之间的交流“难以避免全球化和文化间的不平等”,但他“不去用殖民主义或是后殖民主义的话语视角来观看它们”。[注]同上,第212页。对权力问题的无奈和对“话语视角”的回避,使谢克纳倾向诉诸一种“乌托邦式的想法”:“我尽可能试着去接纳别人所呈现的。但我并不背叛自己的价值观。我并不反对冲突,却讨厌用暴力去解决冲突,我相信艺术的表现形式和仪式的制定也无须用暴力解决。”[注]同上,第215页。
显而易见,不同的言说条件下有着不同跨文化戏剧界说,并不存在一个实体性、起源性或本真性的“跨文化戏剧”。这一知识状况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迪在于,中国戏剧学者若要构建中国的跨文化戏剧理论,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当知识被冠以人为的标签时,随之而来的代价就是心灵的封闭。前文所论及的“替/补”逻辑的运作,将使“起源”(或中心)与“终点”(或边缘)均无法自洽,这已经昭示了“终点”也可以轻易地被转化为其所(不)欲的“起源”。这一潜在的倒置,很有可能把非西方的跨文化戏剧实践导向某种观念的误区。因为,简单地以本土的身份政治话语解构、批判西方“经典”的文化霸权,事实上是颠倒地复制了西方“经典”的霸权思维方式,并在深层次上悄然支持了西方“经典”话语所倚重的哲学前提。既然是对抗与反制,那么,这种本土的跨文化戏剧实践其实已经承认了西方戏剧“经典”的“起源”或宰制性质,而非西方戏剧传统则是其衍生物。这种思维大大简化了异质戏剧传统在不同问题脉络中流动的复杂性,假定了血脉纯正的西方“跨文化戏剧”观念可以单向地、无阻力地、透明地向非西方世界传播并为后者接受,而非西方世界的自我戏剧传统与“能动性”(agency)则被遮蔽在这一“起源性”的假定之外。
问题决定方法。如果存在着真理,那它一定永远都在路上,而且永远都是不确定且流动不居的。任何理论术语都面临着无法一语洞穿“真理”的窘境,所以,无需以牺牲思想观念的复杂性为代价,而去纠缠于某个概念能指的精准表述。使用何种术语并不重要,把原本充满思想活力的观念披上某种大纛亦无必要。跨文化戏剧实践的知识潜能主要体现为对非历史的、神学式的本体戏剧实践的拒绝与否弃。我们不妨把跨文化戏剧视为一种富于洞察力的视角和策略,开放传统的戏剧学科边界,在其无力回应的公共议题中,重构戏剧介入当代中国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