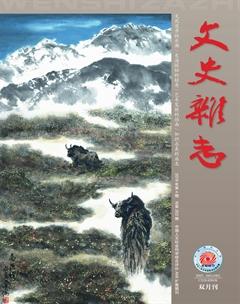谈“武丁中兴”
胥润东

商代青铜器(藏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在商代的历史中,曾发生过数次的兴衰更替,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便是“武丁中兴”。武丁中兴,就是商代晚期商王武丁所在部族由衰转盛的过程。据《史记·殷本纪》载,武丁前有“比九世乱”“帝小辛立,殷复衰”,而后来的“帝甲乱之,七世而殒”,庚、甲、文丁时代频繁的自然灾害(如《古本竹书》云“太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绝”)。帝乙、帝辛时期的战祸又终结了武丁中兴造就的繁荣。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武丁前的盘庚迁殷以其在许多方面为武丁中兴做的铺垫一直被认作是武丁中兴极重要的前提。那么我们要谈武丁中兴,就不得不先谈谈盘庚迁殷。下面我们先简单看一下盘庚迁殷的具体史实和原因。
《史记·殷本纪》说:“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迁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帝王世纪》说:“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
那么盘庚为什么要迁殷呢?要知道商代早、中期商先公先王所在部族的势力其实是很不弱的,这点由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中出土遗物之丰富可以证明。关于盘庚迁殷的原因,学者们有多种说法,但可以知道的是,商王所在部族由于生产、贸易不利一类事由,致使国力遭到削弱。例如有学者指出盘庚以前国力的衰落同以前商人过度倚重于商贸以促进发展的模式很有关系。[1]因为外患一旦来侵扰,商先公先王所在部族所受到的影响将远大于其他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部族,在盘庚之前商先公先王所在部族很大程度上就是因此衰落了——这就成了盘庚大力发展农业的直接原因。不过,我们需要明白:盘庚迁殷虽然尚未使商王所在部族立时振兴起来,却为武丁时期社会安定、农业、手工业蓬勃发展提供了先期条件;武丁中兴也正是武丁在盘庚迁殷的基础上在社会各个方面进行的改革的成绩。
那么武丁中兴是何以实现的呢?下面从五个方面来谈一谈。
一、经济
首先来看一看农业。据文献记载,商代农业是自盘庚时期开始大力发展的(参见《书·盘庚》),在这一点上武丁算是承继了盘庚的遗绪。据统计,现如今著录出版的武丁卜辞约有二万五六千片,其中与农业有关的有974片,占该期卜辞约4%,较后期四期中农业占卜辞总数的2%显然要大得多。(参见刘学顺、古月《武丁复兴与农业生产》一文)后来四期的农业生产应该是比武丁时期发达的,但我們在此文中所突出的,是武丁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视和推动作用。(农业成为商人的主要生产部门最早也应是盘庚迁殷之后,其高速发展当在武丁时期。到了商末,“文王不敢盘于游田”则是武丁之后农业不断发展并最终占取绝对优势的明证。)卜辞中“观黍”(《前》4·39·4)、“观耤”(《后》6.28)、“求年”“求风”“求雨”之辞更是不胜枚举,都可见武丁对于农业生产十分关心。他不仅常常向先祖上帝祈求合适农业生产的天气,更是常亲身省视农业生产,也无怪乎武丁时期农业发展之迅速了。
至于武丁时期农业生产的其他要素,比如说农业生产模式、种植作物类型及耕作技术等,就现有资料来看,在铁制农具普及之前基本就再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革新。那么武丁时期农业的较快发展,我们或许就可以归因于盘庚到武丁这一段时间内发生过农具的大幅度改良。因此,关于吴泽先生以为殷代农具已是青铜器的说法,[2]我是十分赞成的。(不过其大规模的应用似应被限定在晚商时期,武丁前后。)其说据甲文“农”“?”“耤”“物”“方”等字之字形说明殷带农具倘为石制,不当作此形状,且青铜农具亦有出土;青铜农具可重铸再造,故而出土数量不多(至于殷墟地穴中出土的石制农具,当是“当作废物垃圾丢弃的”)等数点以证明其说。此外,由于耒耜和是当时(殷商时代)的主要耕具,且原始社会晚期即已出现石,但商周时代石却销声匿迹,亦说明了青铜在此时代替了石。(参见杨锡章、商炜《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一书)倘若没有农具的革命性革新,没有农业的发展,武丁中兴是无从谈起的。(农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武丁中兴在其他方面的诸多进步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详下。)武丁时期农业对于晚商乃至于西周农业生产的奠基作用,一直到春秋时代普遍出现铁制农具方止。关于商代农具的究竟,学界讨论十分热烈,但武丁时期前后农业发生了一次极显著的生产变革,使得生产力大为增强,则无疑义。
此外,武丁时期的畜牧业还十分地发达。卜辞云“丁巳卜,争贞,降冊千牛,不其降冊千牛千人”(《合集》1027正),一次祭祀即用1000头牛,光靠田猎是绝对不够的,这足以证明武丁时期畜牧业之发达。至于当时畜牧业所畜养的动物如马、牛、羊、猪、犬、鸡、鸭、鹅等,也已同后世相近。可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当时渔猎活动的效用,因为当时的渔猎活动还能提供如虎、鹿、兕、廌之类的难以畜养的动物;再说自盘庚以后(尤其是武丁时期),商王朝农业不断发展,相关地区野生动物锐减,渔猎业规模因此不断缩小,并在地域上逐渐边缘化,畜牧业由此便相对壮大起来了。
据《今本竹书》“十五年营殷邑”,我们或可推知此前在殷地的城邑规模以及人类活动的规模(对自然影响)较小,而武丁田猎时所获的大量猎物恰好证明了此说法并且表明了彼时殷地一带动物分布的数量和种类之丰富。由于盘庚迁殷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发展农业的考虑,那么就注定了发展农业的地区不得有大量野生动物(尤其是一些危害农业生产的动物)的存在。因此,武丁的田猎,其实很可能包含着对野生动物进行捕猎以保护农业发展的意图。(参见孟世凯《殷商时代田猎活动的性质与作用》一文)这从侧面反映出武丁对农业发展的重视。
除农业、畜牧业之外,武丁时期的手工业亦十分发达。武丁时期乃至于整个商代晚期的手工业大致可分为青铜铸造业、制陶业、玉石器制造业、制车业和其他手工业等。现以前二种为例谈谈。
青铜铸造业在商代的社会生产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至晚商时期其青铜器铸造水平则达到“商代青铜器发展的顶峰”。晚商青铜器一般分为四期(妇好墓处于第二期),第一期的某些青铜礼器“在形态上仍较多地保留了二里冈期的特征”;而到了第二期,“柱足鼎则占据了绝对的优势”[3],呈现出殷墟青铜器的独特风格,对西周青铜器的器型仍有重要影响,足见武丁时期铜器铸造风格影响之深远。除此,武丁时期关于青铜铸造业的另一大贡献在于传播其铸造工艺,即便山东益都、湖南宁乡等地都能铸出工艺水平极高的青铜器如亚丑方彝、四羊方尊等。何况我们今日所见到的青铜器,晚商第一期的不多,基本在武丁时期才大规模出现,其出土范围较以前也扩大了许多。这两点表明了武丁时期青铜铸造技术有巨大发展与广泛传播。

至于陶器,至商中期“创制了我国最早的原始青釉瓷器”[4];但最终到了商代晚期,陶器瓷器在技术上其实并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需要指出的是,商代原始瓷器的烧制与使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实相当少,该技术的应用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南方地区),[5]那么殷墟发现的原始瓷器与南方地区的密切联系则都说明原始瓷器的成品和技术应当是自南向北输出的。武丁时期大量的征伐及其所带来的贸易有力地推动了制陶技术的传播。
而贸易则是商人社会生活的一个稳定的传统,这光从“商人”之名就可以看通透——不少学者研究指出这与商人从事商业贸易有着密切联系。(参见徐中舒《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一文及郭沫若《十批判书》一书)关于商人贸易的情形,本节以陶器、骨器具为例。
商代陶器生产同青铜冶铸业一样,已经开始了专门化、行业化的生产。早商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成规模的陶窑,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曲商城三处,正与商人早期靠贸易起家的记载相符;而到了晚商,其技术较于中早商并无多大进步(如前述),如安阳小屯南地发现的“升焰窑”(于早中商时期即已流行),所异者只是窑的体积增大了些而已,可知其贸易规模保持相对地稳定。
骨器中的骨笄,在郑州、安阳殷墟等地的骨器作坊(殷墟所发现的两处骨器作坊即大司空村和北辛庄骨作坊,参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年》一书)内所发掘出的大量骨料、成品、半成品,都很清楚地说明骨笄被制造出来,明显是用于贸易的。
殷商時期的货币之一为贝,妇好墓中出土有6880余枚货贝和1枚阿拉伯绶贝[6],数量巨大,这便说明武丁时期贸易的兴旺繁荣以及官方对于贸易的积极参与。
其实贸易在武丁时期以至于整个商代都是十分活跃的。据研究,殷墟中发现的许多非中原产的物品(如可能来自云南、湖南的青铜原料中的锡和铅、来自新疆和田的玉料以及沿海地区所产的贝等)“主要是通过交换的方式获得的”[7]。或许我们可以将朝贡看作诸侯与商王朝进行的贸易(只不过可能商王朝的贞人未将己方的支出记录下来),也可以认为诸侯在朝贡的同时携带了一些本国特产与官方或民间的商人进行交易,互通有无。而商王朝的贞人,则也是“参与贸易、管理、记账等”许多方面的事务官(如“某入屯”)。[8]武丁时期贞人势力的强大确保了贸易能在商王朝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我们可以说,武丁时期经济的大发展,一是靠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二是靠商贸活动的频繁。此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武丁时期(广义说自盘庚时期开始)核心的经济方针就是“重农”,不过“抑商”是没有的,这是商人的贸易传统使然。《管子·地数》云:“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余。天非为汤而雨粟,而地非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同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费时也。”这表明商人早期是靠贸易强盛起来的,《酒诰》“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则说明商人贸易传统一直延续到周初。《洪范》八政的前三政言:“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汉书·食货志》云:“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谓分财利通有无者也。”《洪范》是商旧臣箕子在回答周武王咨询时,对商王朝施政纲领作出的全面介绍。何崝先生以为人们通常所举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实为“一种错觉”,“食”“货”比祀与戎更加重要。[9]我们的确应当认清《洪范》的说法并给予商代的贸易以足够的重视。
总之,武丁时期经济重心虽已移向了农业,但先前的贸易经济基础和经商习俗使得武丁时期乃至于整个晚商时期的贸易依旧处于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况且农为商本,武丁大力发展农业,对于其贸易的发展来讲也是根本性的保证。这些应算是武丁经济思想的体现吧。
二、政治
政治上,武丁中兴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政治变革。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王权的加强,而加强王权重要推动力便是武丁对傅说的启用。据《书·说命》及徐义华对此的探讨,其政治变革有三大重点:1.强调君臣秩序;2.改革用人制度;3.改革祭祀制度。(参见徐义华《武丁治国与傅说其人》一文)这三点也确使武丁时期的王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此前太甲朝有“伊尹放之桐宫”,太戊有“言弗臣”、盘庚有“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到了武丁时期(尤其中后期,据研究,武丁前期有大量非王卜辞,这是武丁前期其权力并不足够坚强的证据),对傅说这“胥靡”的起用则昭示武丁利用培植与旧贵族势力毫无瓜葛的新力量以强化王权的政治目的。张光直认为,“商王就是巫师,还是群巫的首领”,强调了商王掌握神权的职能,商王朝是政教合一的。其时频繁的占卜活动最终也是“专门为商王的仪式和政治目的服务”的。[10]总而言之,武丁时期王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武丁因而对于整个政局的把控更显稳定,这便为中兴打下了深厚的政治基础。
三、外交
据朱歧祥的统计,武丁时期殷西北方方国有15个,西方方国有10个,西南方方国有13个,南方方国有2个,东南方方国有2个,共42个。[11]而这42个方国便是武丁时期的外交对象。武丁时期的外交,重心在西北、西、西南的那几个方向上;至于东部,那是殷人的发祥地,己方势力很稳固,无所谓“外交”。而所谓“史”“史人”(史或作吏,二字同源),则为商王朝派往或派驻外方的“带有视察、监督、协助地方事务、传递各国间的信息给商王等”(王宇信、徐义华:《商代史·商代国家与社会》)职能的官员。这些官员甚至还掌有兵权(“贞,我史其方”,见《合》6771正),可知“使”是具有政治军事双重职能的。
武丁时期的外交,主要是以战争形式进行的,少数时候也通过联姻及其他手段开展策略性外交。联姻外交直接体现在武丁的妻子数量上。据胡厚宣考证,武丁妻子数量达到64位之多,且其中包括许多来自外方异族的女子。(参见胡厚宣《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一文)武丁此举,无非就是政治联姻,用以加强各诸侯、方国与商王朝之间的联系,以维护商王朝的统治基础。
至于武丁时期的外交策略,大致又可归纳为三种:
第一种,“同化策略”。朱岐祥对此解释道:“殷武丁降服方国的手法,是先将战败的方国归并为附庸,助殷守边,继而转化为殷边田狩地区,其族众往往在殷人武力与文化的熏陶笼罩下,为殷民族所同化”[12]。可以推测的是,商王国所派出的史官很可能就是这个所谓“同化策略”的中坚执行者,殷人同化的成败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史官。而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个策略的实践基本是成功的;不过其效果当然不会十全十美,或服或叛的諸侯实际大有人在,如沚聝、望乘等。
第二种,“羁縻策略”,说通俗了,就是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如当武丁征服沚后,朝廷多次对之进行“毖”“告”,“毖”是“诫告劳抚”(参见裘锡圭《释“柲”》一文)之义;而“告”则如《多方》“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其“告”便是所谓羁縻策略了。(参见王坤鹏《商代沚方考》一文)
第三种,“用人策略”。这是将用人制度与开拓疆土的重点方向相结合的手段。如商前期的战略重心在东方,商王朝便提拔一系列出身东方的贤者,像伊尹、巫贤等。而到了武丁时期,战略重心调到了西方,像傅说一样的西方贤者得到提拔。这种手段实为商王朝开疆拓土取得了许多便利。
此外商王朝同诸侯相互间还有义务。诸侯对商王朝,需要诸侯本人到殷任职一段时间(如武丁时期卜辞中的“犬侯”),为王朝作出贡献(所贡献者可分为人员、谷物、牲畜、特产四大类,如卜辞云:“古来马”,见《合》945,“车不其致十朋”,见《合》11442正),为王朝提供军事协作如戍边(卜辞云:“贞,王令帚好比侯告伐尸”,见《合》6480)等。商王朝对诸侯则负有军事保护的义务(如卜辞云:“登人呼伐,贞邛弗敦沚”,见《合》6180),表明武丁对沚是否被邛方攻击的关注。王与沚“比伐某方”当是商王朝履行义务之一例。
从上述四方面及所引卜辞(大部分为武丁时期卜辞)可知,商王朝的外交无论是形式、对象、策略还是义务,都在武丁时期基本定型,后世商王鲜有改易;加之下节所述武丁时期的战争外交的成功,武丁时期的外交,确可以算是殷代外交的典范。
四、军事
关于武丁时期的军事行为,我们或许可以从武丁时期的主要战争和军事人物两方面获得一个粗略的认识。
传世文献中有关武丁时期战争的,只有《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和《易·未济》“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两条,而在甲骨卜辞中,记录则丰富得多了。据陈梦家先生统计,与商发生战争的方国近四十个。[13]武丁时期的战争,主要有三场,分别是针对邛方、土方和方方的战争。下面就以邛方为例谈谈武丁时期的战争问题。
邛方的地望,大致在今太行山西北方向(或以为“在晋西南及邻的陕西一些地区”,参见罗琨《商代史·商代战争与军制》一书),然大致方向总是相近的,距殷地不远,故而和商常常都在互相征伐(据统计,与邛方有关的甲骨大约有500余片)。常见辞例是“邛方我”(其次有邛方侵商诸侯:“邛方戉”,或目标不明的:“邛方出”),商于是“伐邛”“邛方”“正邛方”;而这些征邛方的卜辞,主要是典宾类,也就是武丁晚期的卜辞,说明对邛方战争的时间处在武丁晚期。或以为征伐在前,武丁末年商王朝在河东地区的霸权已是相当坚固。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看出武丁时期的征伐建立并巩固了商王朝的军事霸权。

至于征伐的规模,由这场战争所调动起的军事主体的数量可以看得出:1.王及其直属军队,如《合》6098“王往伐邛方”;2.诸侯及其军队,如“六日戊辰允来祸,沚聝乎伐邛方”(PJ295);3.族兵,卜辞云“丙午卜,?贞,勿人三千乎伐邛方,受有?”(《合》6174,《合》6167称五千人)。其时大量征召族兵,可知其伤亡甚重以及战争规模颇大。[14]
上述三类即商代三大军队系统,通通出动以伐邛方,征用人员规模巨大,耗用时间漫长。董作宾先生在《殷历谱》中排谱言商征邛方,时间持续有三年半;而据李发的研究,战争亦持续了至少三年;[15]再加上卜辞有“丁酉卜,亘贞,邛叶王事”“贞王曰邛来”(《贞》5445正反)诸句,或可知商王朝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只是不知上述卜辞是否属武丁晚期,不能明确作出结论。)
此外就是军事人物的事迹了。武丁时期主要的军事人物,据李发的统计,达到33人,且基本都是武丁晚期的人物。[16]这就是说, 武丁时期的战争基本上都是在其执政晚期进行的。下面我举沚聝为例谈谈。
沚聝,一般认为沚是方国名,聝是私名,沚国地望可能大致在今太行山西麓浊漳水和清漳水流域附近,即是说沚国正挡在土方、邛方向东南方向行进的咽喉处。其位置的重要战略意义不言自明。商王朝亦希望通过控制沚国而达到加强西部边防的作用。沚国曾是一个方国,卜辞“……未……沚方”(《屯南》4090,《历二》)可证。沚方除武丁晚期与商王朝保持较稳定的关系外,大多数时间与商王朝和逆无常。商王朝时有征伐沚国,甚至捉沚伯来做人牲,卜辞“……方,沚白执……其以用”(《东大》B.0945黄组)句可为证。在武丁晚期,沚与商王朝合作十分密切,主要体现在军事上。
沚国与商王朝的合作,大概是履行替商监视敌方和提供斥候的职能(参见王坤鹏《商代沚方考》一文),如卜辞云:“取目于聝,乎望邛”(《合》6188)。而在国家层面以外,商王朝与沚聝个人的合作则更多,如征土方、邛方、龙方、尸方、巴方等,沚聝都尽心尽力“为王前驱”,有卜辞可证:“辛卯卜,宾贞,沚聝启巴,王惟之从。”(《合》6461正)至于沚聝具体与各方战争的记载,《甲骨文中的沚》一文记载颇详备,可参看。
据李发统计,卜辞中关于沚聝者有573条(张乃夫的统计数字有200余条,且还有聝单见者百余条)。无论如何,这数量都不算少。再从武丁关于沚聝卜问的事类,从后者是否来殷,到途中有无祸患,再到给他的赏赐等等(参见韩江苏《甲骨文中的沚》一文),都体现出武丁对其的重视程度。我们亦可推断出这两人应当有较好的私人关系;加上沚聝拥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战功,使之成为武丁时期重要的大将。
武丁时期商王朝的对外战争,奠定了整个商周時期对外战争的基本线,即所谓“对北取守势,对南取攻势”[17]——这是郭沫若先生从《诗·大雅》中归纳出来的,殊不知武丁倒是其肇始者。至于其原因,郭沫若先生一语道破“北地苦寒,不适于农业,南土膏沃,特别是便于农业的发展”[18]。当然原因或不止这一个,但这确实是最主要的。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农业的进步及贸易的需求奠定了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基本路线,而武丁适应了这一路线,向北(西北)征伐游牧民族,保护本国农业,并趁机掠夺了大量财物和奴隶,大大促进了商王朝生产力的发展;[19]又向南拓土,发展耕地,掠夺铜资源,从而为商王朝的农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至于由战争附带来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传播(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青铜冶炼技术的向北传播及其带来的“北方系青铜器”制作风格的形成和制作技艺的提高),都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五、文化
武丁时期的文化基本上奠定了整个晚商文化的灿烂辉煌,无论是在武丁时期走向体系化的文字、适应农业发展的历法、科技,还是繁缛精美的艺术,都是可圈可点的。
文字上,我们如今所见到的殷商文字,主要是甲骨文,其次有金文、陶文等。
殷墟甲骨,一般认为是武丁时期才开始大量出现的(殷墟青铜器也是从殷墟铜器第二期开始普遍铸有铭文),而这曾使人怀疑甲骨文字体系是在武丁一朝突然出现的。对此,何崝先生作出了解释。他以为其原因有三:第一,武丁时期贸易规模迅速扩大(文字记录需求的扩大),这是最根本的。第二,商代在其早、中期积累了具有高度能产性的符号。第三,武丁时期卜人数量较多,具有管理贸易和创造字形两重职能。[20]笔者从此说。不过其第一点还可以再延伸,即武丁时期的农业发展为其贸易规模的扩大奠定了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甲骨文字体系就是在武丁时期基本形成的,武丁对此居功甚伟。武丁时期甲骨刻辞的字体风格十分独特,吴泽先生评价道:“反映在文字笔法的作风上,也是雄健宏伟,笔画虽细,却甚精劲,且字画多填朱砂或墨,绚彩美观!”[21]可见武丁时期的国势直接投影在其文字风格上。武丁以后诸王的国势,亦可从当时甲文风格中窥探一二。
在科技上,武丁时期农业获得的大发展同该时期的历法是分不开的。对于商人历法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富;然而学界达成共识的,似乎只有一点——即商代所用历法是阴阳合历,其余纪日法、日始、历月长度等等,众说纷纭。总之,商人历法已达到相当进步的水准。这无论从商人对于天象的细致观察(如“七日己巳,夕,?新大晶并火”,见《合》11503反)来看,还是从武丁时农业的大发展来看,都是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的。
另外,据彭邦炯先生研究,商代在数学、医学等方面也都曾取得辉煌的成就,数学如十进制、算筹的应用、数学教育等,医学如疾病的认识、治疗的手段等都有极显明的例证(参见彭邦炯《商史探微》第十一章)。彭先生在论述这些方面时所引用的甲骨原片,有不少都是武丁时代的。这也就说明了武丁时期数学、医学的发展确是不错。

而反映武丁时期艺术水平的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妇好墓中所出文物,例如所出铜器。妇好墓中出土铜器共468件,有礼器、乐器、工具、生活用具、武器、马器、艺术品及杂器八类;[22]但以礼器为主:其器型是晚商青铜器器型趋于成熟的重要过渡,而其纹饰的艺术水准和风格则大体确立了晚商时代以至于西周(早期)的典型纹饰特色。武丁时期的纹饰除了晚商常见的饕餮纹、夔龙纹和云雷纹等外,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蟠龙、凤、鸟、虎、蛇、鸮、人头纹以及蕉叶纹等纹饰。在殷墟青铜礼器第二期中段(妇好墓属此阶段)还出现了铸有三层花纹(“复层花”)的青铜器(云雷纹为地纹,主纹凸起,主纹上再铸阴线纹),体现出一种繁复之美。其与此前铜器(包括此期大多数普通铜器)主纹地纹都在同一平面上的表现方式相比,特别显出审美风格上的革新。除此之外,武丁时期还新出现大量器类,第一期不常见的器类(如卣、方彝、罍等,大量是酒器)在这一期得到了普及。不同礼器的组合形式也在这一时期变得愈加复杂。
妇好墓中更贴近生活的随葬器物依《殷墟妇好墓》分,还有玉器、石器、宝石器、骨器、象牙器、陶器、蚌器和海螺与海贝八类;而据该书再细分,除象牙器、陶器外均有被用作饰品、艺术品的例子。不过象牙器中的一件夔鋬象牙杯,“通体雕刻繁缛精细的花纹”,“因料造型,巧具匠心”[23];倘无细致的分工和高超的手工业技艺,断难达到此水准。由此器我们亦可看出武丁时期崇尚繁复的审美特点。
此外武丁时期的思想状况在晚商时期也很具有代表性。《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结合卜辞来看,这确是事实。殷人对于鬼神有着相当的信仰,据统计,现今所存甲骨,约有十万片。[24]它们除极少数记事刻辞外,其余均为卜甲卜骨,内容属清一色的卜问。还有祭名,据统计,有商一代竟达到211种之多。(参见常玉芝《商代史·商代宗教祭祀》一书)这表明商王室十分依赖卜筮和贞人。不过据晁福林先生的研究(参见《试论殷代的王权与神权》一文),殷代的神权,是在不断衰落着的,而相应的则是王权的勃兴。虽然“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但是武丁利用神权提拔傅说以加强王权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而更有趣的是,武丁时期的不少卜辞不记占辞和验辞,或者说在验辞上含糊其辞,纯粹就是在维护武丁作为人王的权威。(参见吉德炜《中国正史之渊源:商王占卜是否一贯正确?》一文)在思想上,武丁最大的特点就是维持了王权与神权之间的平衡,并通过巧妙地利用神权自身以缓慢地加强王权。这与他的政治举措是相辅相成的。
六、余论
在武丁执政时期,商王朝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诸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进步,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当时农业的快速发展、武丁对于农业发展的莫大重视与支持,以及商贸的推动作用。此外盘庚迁殷给武丁中兴奠定的基础、武丁长达五十九年的在位时间所促成的政治稳定,都有力地促成了武丁时期商王朝的繁荣,使“中国的社会从早期奴隶制社会加速向东方的发达奴隶制社会过渡”[25]。至于商王朝四处征伐,开疆拓土,则为各民族及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商王朝的国力也由此达到巅峰状态。商王朝借此又延续了二百余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故而文献上对武丁颇多溢美之词,甚至就连周公也评论武丁(以“诫成王”)道:“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怒,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足见武丁时期殷邦之盛。然而凡事总是盛极必衰的,武丁留下的庞大基业,终至“帝甲乱之,七世而殒”。
注释:
[1][7][9]何崝:《论商代贸易问题》,《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
[2][21]吴泽:《殷代奴隶制社会史》,棠棣出版社1951年版。
[3][6][22][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4][5]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8][20]何崝:《中国文字起源研究》,巴蜀书社2011年版。
[10]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郭净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1][12]朱歧祥:《殷武丁时期方国研究—鬼方考》,《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13][24]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
[14][15][16]李发:《商代武丁时期甲骨军事刻辞的整理与研究》,西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18]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
[19][25]彭邦炯:《试论商王武丁》,《中州学刊》1987年第3期。
作者单位: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