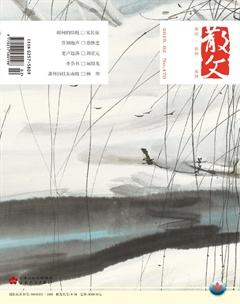时间的结绳(外一篇)
宋长征
你站在时间的旷野,节气的落花纷飞。一条隐约的时间之路通向远方,这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也是从生到死的距离。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二十四个节气,就像一个叉一个小小的驿站,停靠在时间的路口,鸡声茅店,人迹板桥。你需要暂时停下来休整身心,以免在通向来来的路上迷失方向。
转眼已是中年,相对于季节,中年就像进入了人生的秋天,是收获,也是渐渐枯萎的季节。这没什么可怕。不过是遵循大地的秩序,时间的律法。就像一株草面对秋天,惶惑电好,失落也罢。至少手中握紧了可以延承种族的籽宴。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二十四节气是独属于东方的历法,再贴近一些。节气是乡土大地最为陆情的告白,何时播种,何时耕耘,何时收获,都翔实记录在节气的册页。
我小时不懂,父亲坐在灶膛口,火光映红父亲的脸庞,也映红了灶神的脸庞,请来的灶神贴在锅灶旁,好像日子就有了着落。灶神像上端是两行油印的小字,写着农历日期和二十四节气,父亲称之为“绿福头”,现在想来应该是“历法头”叫讹之后的谐音——腊月二十三祭灶、送灶神,灶神爷爷和灶神奶奶去了天庭,只剩下窄窄的一条乡间日历。老河滩上的节气基本上遵循着“历法头”的指引。耕耘稼穑,祭祀或节日。
节气是在先民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依据太阳在黄道(即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位置变化,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代表在一个回归年中的天文、季节、气候、物候、农事活动等方面的变化规律和特征为依托,犹如结绳记事。在无形的时间之中找到了可以准确记录的方法。我似乎能看见那条若隐若现的线索,在时间的旷野中飘荡,却始终不曾偏离自己的轨迹。
节气是微物里的小神,相对于浩渺的星空,大地上的所有事物是如此渺小,如此馓不足道;但相对于我们,节气就成了时间的灵魂。再具体一些。就有了生动的容颜,善于在沉默中表达。
一首叫《苔》的小诗在节气中醒来,拂击旧时的尘埃。作别冬日的冷寒,苏醒在我们家的土墙上:“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若非细心,你断然看不见一株青苔的模样,它的根须比植株还长,它的隐秘就像时间暗生的情愫,不经意间染绿那时的光阴。我在月光下朗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谁知道节气的意义呢,谁能想到人的一生只需穿过一个又一个节气的隘口。便完成了生命的历程。此间。悲喜哀乐,甘苦自知。
时间在老河滩上醒来,春天到来,有时节气像一条无形的鞭子,在光影中鞭策村庄前行。躬耕的老牛,在沉重的枷锁下行走,犁开肥沃或瘠薄的土地。没有人倦怠,只有按时在大地上播种方可收获圆润、丰盈的备物。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节气这时是初洗的婴孩,在天父地母的襁褓中睁开一双清澈的眼睛,露珠在叶子上滚动,男人和女人在一滴晶莹的露珠里奔跑,麦子拔节,油菜花开,迁徙的鸟儿归来,用一声声清脆的啼鸣拨亮春色。
节气也是生灵的精魂,蛰醒的小虫在夏日的光影中飞舞,所有的生命临水而居。一条涌动着大地血脉的河流从远处,从历史的纵深浩荡而来。有关节气的发祥地有很多种说法,有说起源于古都洛阳,有说起源于邯郸磁山,有说起源于安徽淮南,有说起源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如同乡愁的诞生,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原乡,每一个故乡都是乡愁诞生之地。节气从未表明在某个具体的地方留下烙印,只是在行走的过程中叫醒花朵,唤醒沉睡的草木,喊醒一只刚刚从母腹中诞生的羔羊,一声轻柔的颤音,夏日到来。
夏日到来的老河滩上,羊群在安静地吃草,它们才更像时间的圣子,一旦降生在这片宁静的家园,就再也不曾离去。老河滩是我意象中的田园,在多年之前的某个季节,河水泛滥,一度冲击而成,土是素朴的黄壤厚土,偶尔可以发现贝壳与螺壳的遗存,它们在时间的上游,被冲刷,被掩埋,或者石他于黑暗的土层,轻放于耳边,抑或可以听见远古的风声,听见曾经的铁马冰河,听见先民的欢歌。无论如何。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节气起源于广阔的黄河中下游流域,井以此为基点,辐射到江河南北更为广阔的地区。
我有時也会惶然,自己是否也是一粒种子,由一双无形的命运之手播种,落地生根,而后在老河滩上奔跑。我喜欢那些藏蕤的草术,阳光透过枝叶在大地上斑驳闪烁,那闪烁中一定有一道叫作命运的方程,在我出生之时就注定了结局。我不知道如何求解,只是在与草木对视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条隐秘的小径。我要书写,穿过节气的光阴或者节气穿过我的胸膛,捕捉每一个闪光或沉默的物种。我在它们的眼神中发现了自己的属性,它们在我的笔下留下摇曳的身姿——这是写作的魔法,或者叫作彼此成全,一起完成在大地上简朴的一生。
秋天的到来有些仓促,尚未品尝够乡野的鲜嫩,又一次迎来饱满的谷物。物候是节气的重要特征,既然其本身其有缥缈不定的特性,那么就用具体的物象来表达对时间的认知。这个穿梭在时间里的小神,近乎魔幻般将植物的出生、生长与成熟一次性完成,行云流水,让你看不到任何破绽或瑕疵。节气太远,有时像是在寻找一个即将消逝的符码,只能通过大脑与往日对接,方可看见曾经的轮廓。“鹰祭鸟”“獭祭鱼”“豺乃祭兽”“鱼陟负冰”,在别人看来也许是神话或笑话,而在我的意象中却是古人浪漫的表达,相生相克中,出于对生命的尊重让节气有了仪式感。一种物候对应一个节气,一种物象像是一次无声的告白:秋天来了,冬天的脚步正在到来。
与其说我在书写节气,不如说是在时间的轮回中又一次完成回望,大概从去年的清明开始,我选择在每天日落时分快走。触目所及,皆是熟悉的事物,柳树柔软的枝条在风中飘摇,鹧鸪的叫声悠远而苍凉。也许,在这个匆忙的时代很少有人顾及身边的风景,节假日的出行,一次看似豪情的远足,却忽略了身边的花开花谢;而真正低下头来,一株萌发的野草,一只奔忙的虫蚁,无不在以自己的方式诉说艰辛或从容。
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对时间的自我启蒙中,明晰了节气的来源、发展与形成。从中国古代利用土圭实测日譬,将每年日影最长定为日长至,日影最短为日短至,到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制订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明确为历法,其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由商朝的四个节气,发展到周朝时期的八个,到了秦汉年间的确立,不知经过多少次计算与考量。而我,只是在此基础上的偷天换日——我也尝试一次次在田野上行走,我也在故纸堆中寻觅往日的线索;但最重要的是,我要记下属于老河滩的节气,属于自己的节气,我要在节气每一次穿胸而过的过程中打开记忆的门扇,让村庄里的草木苏醒,让村庄里的生灵生动,让村庄里的人们穿上节日的盛装,朝拜时间所带来的欢乐与丰盈。
“天地有大美丽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的智慧是,身处时间的旷野之中,所有的沉默都是最为清澈的表达。而我所要做的,只是记下故乡的节气之美,以及节气所带来的简朴食味。
民以食为天,乡间食味是难以绕过的记忆。节气在物中穿行,人在大地上奔忙,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养、助、益、充,都是提供能量的方式。
春有韭,夏有果,秋有五谷。才不至于脚步太过慌张。我在庄稼的密林中行走,叶子在耳旁唰唰作响,我恍惚做了一个住进一粒粮食的清梦,在梦中邂逅一个叫节气的精灵,通体如玉,攀上村庄最高的枝头,和我对视。她说:“你是我养育的孩子,你的血肉里流淌着我的血液,你的眼神中流露出我的神情,你走路的方式甚至也和我一样,脚步轻盈,不肯惊醒万物之梦。”这时的我该如何应承,村庄坐落在粮食里,老屋坐落在粮食里,就连草术与生灵也一起带了进来。谷物,这时等同于生命的方舟。
虫子在空中飞舞,鱼儿在水中游,乃至忙碌的蚁族,有时也會作为一种高贵的食物为人类所食用。有时,你不能带着批判的面孔去看待,人处在食物链的上层,好像就决定了这些弱小者的命运——尽管会有些不公,也不可能改变现实。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北户录》云:广人以山间掘取大蚁卵为酱,名蚁子酱。”我们村里的人也喜欢在夏夜中游走。捕捉匆匆破土而出的蝉,其间美味,只有品尝过的人方可言说。
还是有些残忍,在把三牲请上祭祀的桌案之前,家畜的命运就显而易见。到底是迎来了冬天,每一个节气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供品或吃食。猪牛羊,这些生是陪伴在乡村侧旁,共同见证了乡村的发展与成长,同时也成为村庄的图腾,在祭拜的进程中享受了祖先或神灵的札遇。或许,它们才是村庄真正的守护神,在与节气的守望中拥有了一种超然的力量。
大雪纷纷飘落,节气却从未停下奔跑的脚步。这是属于时间的结绳记事,我在记忆中按图索骥,也在隐约的时间纹理中搜寻到节气的味道,敬献于永恒的时光之神。
炊烟的根脉
更早更早的从前,人生话在荒野与丛林,兽的脚步在夜色中逡巡,可听见惊悚的低吼。守护家园的人不敢沉睡,即使假寐的瞬间,也能看见梦中的村庄与城邑,只是不知道未来的路有多远,只是不知道如此担惊受怕的日子还有多长。智者的诞生,从来不是用天才就可界定,这需要时间的熬煮,需要在一次次痛定思痛之后陷入深深的反思:若要躲避无边的惊悚与荒寒,就要在大地上修建属于自己的家园。
烧荒垦种,是一个关联词语,燔野之火,烧出一条艰难的生存之路—一野蛮归野蛮,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我的眼前经常会出现选样一种意象,炊烟升起,在有风的暮色之下渐渐飘荡、凝集。此时的天空近乎一张沉默的宣纸,白色炊烟犹如被一只无形的时间之笔着墨、点染、勾勒,在烟青色的背景上描画出一幅印象派水墨,流畅的线条,独特的晕染效果,如果仔细分辨,尚能分辨出哪一缕是我家升起的炊烟,因为日子单薄,笔画显得虚幻、空灵了许多。
人类定居下来,锅碗瓢盆就成了日常所需,再早一些时期的石碗、石釜太过笨重,尚不适宜逐水而居。就从附近的池塘或湖泊采来青碧的荷叶,衬托在用泥巴持成的盆状物底部,钻燧取火,引燃,烹煮采集而来的原始谷物,或者狩猎得来的野物。这是继茹毛饮血之后的巨大变革,以炊烟作为引子开启了人类早期的群居生活。
这荷叶衬托的盆状物即是陶的雏形。泥土是大地上的泥土,被棹打,被抟转,被切割,被做成一十个器皿的形状。火光燃起,泥土在火焰中所练,一次次煅烧筋骨,就有了源远流长的土陶艺术。陶的早期,即是作为生活的陪伴诞生在村庄侧旁,朴拙,沉默,在憨厚的表情之下潜藏着一颗悲悯之心。逮时的炊烟尚未葱茏,只是一缕缕从流水的河畔扶摇上升。洞见了先民简单的日常。陶制的鼎、甑、鬲、釜、罐,是为了盛放简洁的光阴:泥土的地灶、砖灶、石灶,是为了将谷物与野物炊熟。以面对日月沧桑;粗劣的钵、碗、盘、盆作为食具,足以让人体会到岁月的艰辛。
即便如此,生括也要继续。传说中彭祖为尧帝烧制的“雉簧”,大概就是在土陶的炊具中烹饪而成。尧帝病,彭祖捉来一只野鸡烹制羹汤,不多时飘溢出鲜美的味道,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尧,帝尧美而飨食之也。”病愈之后的尧帝太悦,喊来彭祖接受封赏,到徐州一带建国称王,便是彭城的来历。
我家也使用过土陶的器皿,即便是现在,当我端起一只廉价的青花瓷碗,依然能看见乡间炊具一路走来的仆仆风尘。炊具嚣皿革新,细致精巧的青铜食具登上历史舞台,不仅由于导热较快提高了烹饪效率,而且彰显出了贵胄之家的奢华与礼仪——这也是后来青铜器进化成礼器的原因之一,贵族们在举行祭祀、宴飨、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以此来表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和权力。到了春秋时代,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铁制炊具逐渐出现,相较于青铜炊具的身价更为亲民。
每当过年,我家的门楣就会贴上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对联,是希望在新一年里风调雨顺、风风火火。此时的炊烟有祝福的意味,谷神在天,灶神在地,一缕炊烟就是衔接天地的缥缈经幡,祈求家园康乐平安。
一只羊在老河滩上奔跑,它不知道自己的米路,也不知道归逾,只是在青草萌芽的季节骨子里的情愫开始萌动。还需要什么呢?自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开始,羊就开始了陪伴先民的旅程。水草丰美,就是羊最幸福与满足的时光,在清水中洞见自己温和的容颜,在睡梦中听见农人亲切的呼喊,山一程水一程。有了羊的村庄就多了几许祥和之气,在临近春节的时候,它们将被作为乡土的牺牲供上桌案。
牺牲应该是一个褒义词,无论作为刻画英雄,还是牺牲的本义。猪牛羊三牲,作为丰盛的祭品摆放在祖先与神灵面前,就足以表明了我们对天地的虔诚。原牛是一种颇具传奇色彩的野生牛类,在有记载以前分布在东至中国西至法国的广褒地带。或许在驯化的过程中原牟也有过挣扎与抗争,一次次将愤怒的眼神投向高举的鞭子,一次次却又在离去时踏着疲惫的脚步归返——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让它不得不思忖个体的安危与家族的未来。那么好吧,一头牛的陪伴可谓绵长,从大约七千年以前开始沉重的耕耘,一路风霜雪雨,进化成农人最为忠诚可靠的近邻。
这是物种起源的简单剖解,在面对被屠宰的命运时仍然让人觉得唏嘘,无人能阻挡食物的诱惑,正如这世界本身到处隐藏着悖论。但至少,站在食物链顶端的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悲悯之心,毕竟是它们献出血肉与力量供养丁生活在大地上的我们。
又是一年麦黄天,布谷在夜色中游走,毫厘不爽地敲响节气的鼓点。谷物春华秋实,原产于黄河流域的粟是最早的粮食,所以夏与商属于粟文化时代。粟与狗尾草同宗同源,广泛分布黄河两岸,当时的温度比现在要高出二到三度,降水不多但集中在夏季,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狗尾草的一个分支逐渐进化成了粟,也就是现在的谷子。
粟又叫稷,后稷的稷。后稷为谷神,传说从童年时期就开始研究种麻与菽,成人之后,有相地之宜,哪片土地可种谷子,哪片土地可种小麦,哪片土地适宜播种麻和豆子,后稷一眼看去,抓起一把土就能看出,于是做了掌管农业的官,教民耕种,这也是后稷被称为谷神的原因。
与此同时,在铁制锅釜代替土陶与青铜器之后,动物性油脂和调味品开始问世,为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油烹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菜品也开始出现了南北风味的分野,地方菜系开始崭露头角。其中北菜以现代的豫、泰、晋、鲁一带为中心,辐射整个黄河中下游,以猪犬牛羊为主料,注熏烧烤煮烩,崇尚鲜咸,汤汁酵浓。南菜以现今的鄂、湘、吴、越一带为中心,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淡水鱼鲜辅以野昧,鲜蔬拼配佳果,注重蒸、酿、煨、炖,酸辣调和以滑甘,且偏爱冷食。这一分野到漢魏六朝时继续演进,由二变四,逐步显示出四大菜系的雏形。
火候之法相当于艺术领域的灵感一词,其缥缈与不可捉摸性全在庖厨者的经验,是说在烹煮的过程中根据原料的老嫩硬软,厚薄大小,和菜品的制作要求,所采用的火力大小与时间长短。父亲坐在灶膛前,喷吐的火苗就是足以掌控的灵感,母亲司厨,在多年的乡村生活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碗热粥的温暖,虽说家境拮据,也会偶尔发挥一下多年积累的厨艺经验,做出一桌尚算丰盛的饭食。没有人抱怨,生在乡间的我们深刻体悟到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没有人轻言放弃,在与生灵和谷物的陪伴中或沉重或欢歌负重前行。
乡间炊事的发展就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缩影,在过漫长的光阴中,你能看见富者的奢华也能看见贫者的无奈与坚忍。几乎每一件现代器皿都刻印着日渐消逝的旧时风物的光影,几乎每一步前行都是蹄着先民的足迹,几乎每一时菜蔬、每一粒谷物都保持着生动的客颜,几乎每一种图腾都暗藏神迹,在冥冥之中佑护着村庄与大地。
炊烟是有根的事物,当暮色降落田野,一缕缕炊烟从村庄的上空升起。如果仔细倾听,你一定能听见远方传来麦子拔节的声音,流水轻斡的回声,耕牛悠长的啤鸣,甚至听见母亲唤归的声音,沿着长长的田垄,沿蓿炊炳升起的方向,回家。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