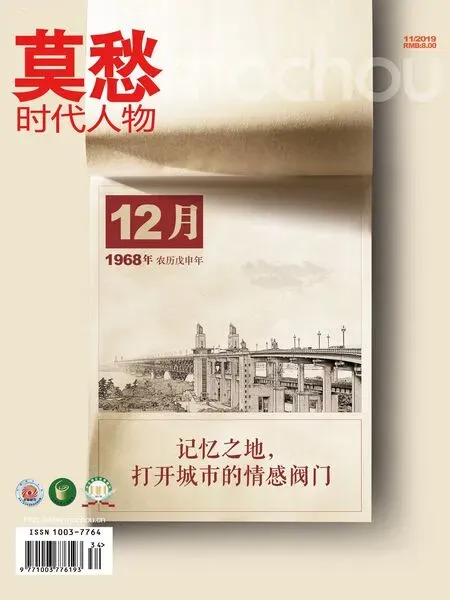常怀百岁忧
文/周云龙
一顿海鲜大餐之后,胃肠道功能紊乱。请教身边“赛百科”同事,他望闻问切一番:吃大凉的了吧?喝点粥,暖暖胃。我本疑心胆囊问题,怕是酒多所致。同事嘲笑:你蛮怕死的嘛!
一降生到这个世界,我就听到那句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想想,在特定的情境里,人是可以视死如归的。而在和平年代,阳光灿烂,生活舒适,人哪会不留恋世间的幸福,怎能不牵挂亲人的温暖?
小的时候,特别怕死,假如某天听了关于鬼怪的故事,晚上起夜也会浮想联翩,生怕被鬼怪逮去,恐怖至极。人到中年,压力巨大,不再那么恐惧死亡了,或许也没有时间恐惧。到了风烛残年,今天睡下去,明天不一定起得来,身边熟悉的兄弟姐妹、亲戚邻居、同事朋友,接二连三地走了,这时候,人的内心也是一个“咯噔”接着一个“咯噔”。
妈妈已经跃入“米寿”行列了。一个透支了体力、心力的农村妇女,能活到这么大岁数,该知足了。可是,妈妈态度很坚决: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想多过几天。
妹妹嫁在本村,每天坚持回去看望妈妈两次。前几天,妈妈跟她拉家常,你儿子都24岁了,再过两年要结婚,结婚就有孩子,你们肯定要去照应,那我怎么办呢?妹妹当场笑着说放心,转头跟我发语音:妈妈好笑呢,不晓得她今年多大了,好像真的要过120岁。
妈妈一边在做长寿“5年规划”,一边很担心规划成为空话。一次,打电话回去,妈妈故意试探我:不晓得怎么办,现在一个人在家,老想看到你们,是不是人到了……
妈妈是文盲,但是知道有些字词不吉利,不能说。妹妹的婆婆,在与病魔抗争三年之后,走了。妈妈前去悼念,一天三哭:你比我年轻,怎么先走了呢?!以前老往你家跑,以后再也望不到你,没有人可以说话了……转过身去,她和妹妹聊天,口气明显有些不淡定:你婆婆小我10岁……不晓得哪天,也轮到我啦。妹妹安慰她,你能吃能走,就是腿疼,有得过呢!妈妈并不踏实:这东西说不定啊。一口报出几个死者的名字,那些都曾经是她的好友。邻居一位九旬老奶奶,她们两人,都衣食无忧,都不识一个字,但是碰到一起,就会有一搭没一搭地探讨死亡的话题:这条路狠啊,躲都躲不掉;要死,就一口气上不来最好,不能拖,累人;不能夏天走,料理后事,后人吃不消;最怕倒在家里几天都没人知道,孩子们要天天打个电话,问问……
在我们大家族里,妈妈吃的苦最多,受的累最长,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七老八十了还不肯闲着。可是,劳碌归劳碌,她一不小心活成了“长寿冠军”。大舅、二舅、大舅妈、二舅妈、姑妈都是60岁开外走的,大姨身体最硬朗了,也就活到86岁……面对家里的“长寿冠军”,我们当然希望她刷新纪录,冲刺100岁。不过,因为她的焦虑我也开始有些隐忧,不得不换个角度安慰她:不错了,我将来要是活个70来岁,就满足了。
嘴上这么说,心里都悬着,人到中年,做子女的最怕半夜听到电话响。孔子当年好像也曾纠结过:“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他的意思是说:父母的年纪不能不时时记在心里,一方面因其高寿而喜欢,另一方面又因其高寿而有所恐惧。
我的爸爸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物。说“人物”有点大了,他就半个农民,农业户口,但很少干农活,因为早年缺钱、缺药落下肺病。而在妈妈悉心照料下,他居然活到75岁,在村里的男性长辈中,算是高寿。父亲嘴上十分坚强,一般得理不饶人,其实也是怕死的。
乡下的风俗,年长者到了一定年龄要订做寿材,并且宴请亲朋,燃鞭庆贺。父亲70岁生日那年,父母同时做了寿材。妈妈小他两岁,不想着急做,主要看着棺材就怕,而父亲坚持要给她也做一口:你要是在前面走了,那不是就要用我的那口棺材?我还得再做!寿材制作完工后,父亲将它们安置在厨房角落。而父亲当时留了一个心眼,把未来属于自己的那口寿材,特意放在靠墙的里面,外面放的是妈妈的,他不想让自己的那口先用。一直争强好胜的父亲,在这件事上,他变得谦逊了。

不过,他最终还是失算了。人生自古谁无死?人生自古谁不怕死?我们终其一生,学习,锻炼,或许就是为了坦然地、乐观地面对死亡。而父母一辈,文盲、半文盲,他们又有什么办法排解或慰籍呢?
古人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好多人其实没那么忧国忧民,只是替自己担心,只是“百岁忧”。不过,恐惧或是谦逊,可能是死亡的最大意义,是死亡对人生的最大赋能。假如死亡并不让人觉得恐惧,倒是一件恐惧的事情。
——我见过的最好的明天,是昨天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