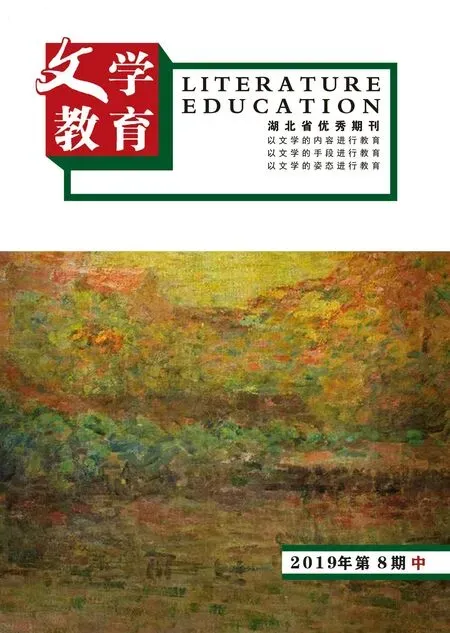赛珍珠《大地》:作为汉学全球化的初期形态考察
蒋画意
传统意义上的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异质文化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1]。19世纪初,汉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在欧洲各国相继建立起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美国的中国学为代表的现代汉学逐渐兴起,二战后,美国取代法国成为汉学研究的中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影响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不同国家、民族的优秀作家、学者用自己的作品开启了汉学全球化的新时代。
当下我们所说的汉学,是一门由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的学科。在众多汉学家中,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是极为重要和特殊的存在。1938年她凭借中国题材作品《大地》(The Good Earth)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美国引起轰动,《大地》成为西方世界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大地》是赛珍珠根据自己在中国将近40年的生活经历与深入观察而创作的、以中国农村生活为主题的小说,首次向西方世界展现了真实鲜活的中国社会与中国形象。赛珍珠美国生、中国长的跨文化身份使她成为当时汉学领域独特的存在,而她的作品的影响与价值也远远超过了文学意义的范畴,体现出汉学全球化初期、美国现代汉学辐射下的一部分形态。就基于《大地》这一文学作品而言,汉学的形态具体表现为以现实为中心,与历史时代密切结合,侧重于观念文化的研究,并流露出基督教文明影响下的对实用性的重视。
一.以现实为中心,与历史时代紧密结合
汉学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传统汉学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门高深而困难的学科。它要求研究者在掌握多种原始资料的同时掌握多种语言,包括古代汉语、蒙文、满文、藏文、西夏文、鲜卑文等[2]。在交通条件有限的十六至十八世纪之前,汉学的研究原料主要来源于具有文献性质的游记或各类古典典籍。而传统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很少到中国,他们大多在图书馆或档案馆做研究,一般不能用中文交谈[2]。这种“经院式”的汉学研究,大多通过阅读对于物质文化描述性的文字而形成一种感性的认知,长期以来汉学家们都远离现实,中国以其精美繁华的物质文明吸引了西方,在西方人心中留下美好而神秘的印象。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热情高涨的美国汉学则以强烈的政治使命和非历史主义对中国社会、中国形象进行了贬低,涌现出大量歪曲描写。或溢美或妖魔化的中国形象严重偏离了现实。而赛珍珠《大地》的创作则力求表现当时中国农村(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和中国农民(中国形象)的真实状况。赛珍珠童年在中国杭州、镇江等地的生活、学习经历;婚后与丈夫在安徽、南京等地农村的走访调查也为她的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使《大地》客观上展现出了中国社会的原貌。
1.《大地》中的中国形象
十八世纪末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大多是负面的、刻板的,例如马克·吐温笔下的阿鑫与萨克斯·罗默笔下的傅满洲,前者“愚蠢而可怜”,后者则狡诈邪恶,成为“妖魔化”华人形象的典型。赛珍珠以现实为中心的创作塑造了许多充满人性,性格饱满的形象。
《大地》中的主人公王龙是中国农民形象的典型,作者不仅赋予了他勤劳坚定的美好品质,也写了他厌弃发妻、纵欲堕落的封建痼疾。书中写到王龙一家第一次经历大饥荒,王龙不肯卖地宁愿举家到南方逃荒,即使逃荒的日子无比艰苦但王龙始终诚实而辛勤地劳动,当他发现两个儿子通过偷窃获得肉吃,他坚决不吃,还把当小偷的二儿子当街狠狠打了起来。他对自己的傻女儿十分温柔怜爱,“常常抱着她”,“把她塞进不太暖和的衣服里贴着他的肌肉”,但也曾动过卖掉她的念头。他用自己的劳动付出换来了富足的生活,但也一度无所事事、迷失于情欲,他开始嫌弃妻子阿兰“没有一点美丽和光彩”,转而留恋于妓女荷花,对阿兰冷漠。王龙对阿兰也有温情与愧疚,他为阿兰举行隆重的葬礼,悲伤中留下沧桑的泪水。王龙作为农民有着朴素的天命观,但又常常埋怨神明与之抗争。同样,书中的女性角色也个性突出,阿兰的喜怒哀乐、痛苦与勇气展现了中国女性在封建浸染下独特的抗争与生存智慧;荷花的纤细苗条、秀气精致“像是一棵榅桲树上的鲜花”;梨花、杜鹃、王龙婶婶等多个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向西方展现了中国女性当时社会环境下真实的性格面貌。
2.《大地》中的乡土中国与历史背景
《大地》忠实地表现了当时乡土中国的实况。三十年代出的中国农村诚如《大地》所描写的以皖北农村为例,贫穷、愚昧、流离、自私、混乱始终困扰着普通的中国农民,他们终年在大地上劳作形成了朴素的天命观,但又始终与天灾人祸抗争,在生命的挣扎中创造了一种稳定和谐的生存环境。
与历史时代紧密结合既体现在对中国国内社会背景的把握,又体现在对西方世界共性问题的探索。首先,《大地》这一部小说虽然主要是描绘第一代王氏家庭成员在田地上的挣扎史,但已经涉及到三十年代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例如王龙在南方逃难,发现“这个城市到处都有青年演讲……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必须进行自我教育”,一心想当军官参加革命的小儿子、从南方来在各家各户住下的“灰衣”军队,这些都透露着当时历史风云变幻的信息。而1935年出版的系列作品《儿子们》和《分家》分别反映了军阀割据时期的旧中国和现代中国新青年的活动。而大地三部曲与历史时代的紧密结合也得到了完整地展现。
另外,《大地》发表时恰逢美国经济危机爆发期间,它的土地主题契合了大萧条时期美国的时代精神。中国农民在土地上艰难挣扎的故事引起了大萧条时期美国人的广泛共鸣。[3]某种程度上《大地》中的乡土中国也寄托着赛珍珠与美国社会的理想与期待。赛珍珠以现实为中心的创作原则与真实细腻地观察描写也让《大地》具有了史诗般的价值,清晰地将现实中国展现在西方读者面前。
二.侧重于观念文化的研究
传统汉学主要涉及的是中国的物质文明,描述、介绍中国的山川、城池、气候,以及中国人的生活起居、饮食、服饰、音乐、舞蹈等等,还没有真正深入到中国的观念文化之中[1]。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汉学出于较为强烈的政治目的,汉学家们不再关心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文献典籍,对于汉学内容的研究更多集中在现代社会科学,企图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等各个层面,走进中国人的思想疆界,达到掌握中国社会核心问题并把握国际间发展的动态与走向的目的。赛珍珠《大地》的创作则敏锐地捕捉到了“土地”这一深邃而富有“世界性”的主题,将农民看作中国社会的真正代表,并在“土地”主题上发掘出一种情结、一种信仰、一种生存观。
1.土地情结、土地信仰与生存观
土地,是《大地》小说的主题也是小说的灵魂。《大地》中描绘最为直观的是主人公王龙的“恋土情结”。小说从王龙结婚的日子讲起,但他却“想不出这天和往日有什么不同。”直到他感受到“一阵柔和的微风从东方徐徐吹来,湿漉漉的。这是个好兆头……下雨可是件好事……大地就要结果实了。”[4]土地的收成是王龙喜悦、振奋的主要来源。在动荡饥饿的日子里,王龙对土地是极端不舍和依赖的。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决不会卖我的地的”“我的地永远不卖”。当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开始耕作时,“甚至连回家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搭了进去”,“如果白天活干得实在太累了,他就躺下来睡在垄沟里,他的肉贴着自己的土地,感到暖洋洋的”[4]。王龙用意外之财买了地,请了老秦合伙,雇了帮手,与粮食店签了合同聚积了可观的家产财富,直到他觉得“他做完了该做的一切”便开始迷失于情欲,打扮得像个少爷,逐渐远离了土地。情欲最终留给他的是“一块心病”,但“这时,一个声音在他的心里呼唤着,一个比爱情更深沉的声音在他心中为土地发出了呼唤”,他又亲自到地里耕作,土地治愈了他的创伤,“他笑着,因为他自由了”。岁月流逝,时光消磨,“有一样东西还留在他身上——这就是他对土地的热爱……他的根扎在他的土地上”。《大地》的末尾,他老泪纵横地告诫儿子:“如果你们守得住土地,你们就能活下去……谁也不能把你们的土地抢走……”可以说王龙的一生几乎与土地合二为一。大地系列的第二部小说《儿子》中,王龙去世,土地归了他的儿子们,但赛珍珠却这样写到:“王龙的血肉之躯溶化并流入大地深处。他的儿子在大地上随心所欲,他却躺在大地的深处,他仍然有自己的那份份额,这是谁也夺不走的。”
王龙是中国农民典型代表,土地对于农民这一庞大群体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价值,千百年来的农耕文明不断强化着中国人的土地意识,土地既是生存所需物质资料的来源,也是人的“根”、人的来源、人的归宿,这便形成了农民自己的“土地信仰”。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土地信仰在个体潜意识中凝固为“土地情结”[5]。土地信仰在《大地》中突出体现为王龙围绕土地庙、土塑神像,即“土地神”进行的一系列具有宗教性质的活动。例如,每当遇到结婚、生子、过年、丰收的日子,王龙都要去土地庙祭拜,还会买些红纸给神像剪贴新衣。像王龙这样的农民都有一种“靠天吃饭”的依赖心理,自然条件直接影响到一家人的生存状况,王龙长时间不耕作反而莫名的不安和空虚。这其实是一种生存观念的体现,尽管这种观念多是原始的、非理性的,但不可不说隐含着深邃的生存智慧,人与土地,与自然的统一既演绎着某种生命盛衰的规律,又激发出农民们诚实朴实、勤劳热情的传统品质。但这种神明崇拜也不是绝对的。旱灾来临,饿坏了的王龙曾向老天喊话:“你太坏了,老天爷!”他还向土地庙的神像啐了一口唾沫。从南方回来,更是嘲笑土地庙里的土地神破烂的不成样子,说:“这就是神对人行恶的报应!”显然,在对生命的热爱和尊崇面前,神灵也会成为诅咒和反抗的对象。
2.家庭伦理观
前文说到土地是王龙喜悦与悲伤的一个重要情感来源,除此之外,在《大地》中喜不是因为阿兰生了儿子,就是因为他有了孙子当上了爷爷;而悲多是因为妻子、父亲、老秦去世、对阿兰的内疚,还有对傻女儿的心疼。不仅是王龙,阿兰对待王龙的态度,对于人妻的定位以及荷花进门后她的悲欢与执念,都体现了《大地》对另一个重要观念的探索和阐发,即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伦理观。
首先,王龙对父亲是极为孝顺的。娶阿兰之前他尽力服侍老迈的父亲,在父亲的安排下娶了阿兰。对于父亲的决定,王龙几乎是不违抗的,尽量满足。饥荒时,王龙说:“我首先要照顾我的老爹,即使我不管孩子。”王龙父亲行动不便,也无法去谋生什么生计,只能吃饭和睡觉,即使是这样王龙也没有抛弃父亲,去南方也一直照顾着父亲,丝毫没有抱怨。父亲去世后,王龙为其买了质地精良的棺材,葬在了最首的位置,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孝敬父母这点上王龙是无可争辩的,这也是传统中国社会一直以来的美德,也可以说是一种父权的传承、一种和谐的秩序原则。而王龙对于自己的儿子虽然有制约和安排,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家庭的和谐,不去多干涉。王龙几乎独自承担了帮助孩子们组建家庭的责任,半生都在为家族的发展奔忙,出钱又出力。王龙“多子多孙”的子嗣意识是根深蒂固的,但他对女孩也没有明显的偏见,对自己的女儿还流露出甚至比对阿兰还多的柔情与关心。王龙首次对荷花翻脸的原因也是因为荷花骂她的女儿是“肮脏的”“讨厌的白痴”。王龙一直牵挂着这个傻姑娘,给她买糖、安慰她给她找漂亮丈夫,即便很大可能是处于可怜和愧疚的心理,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一直在为傻女儿的命运而担心,直至在弥留之际把她托付给梨花。王龙的身上有明显的“家和万事兴”“家大业大”的家庭观念。
另外,王龙依然处于封建男权社会下,对婚姻、妻妾的伦理观念依然是比较落后的,女性的地位并不高,即使是丰衣足食的荷花,也是他一段时期情欲发泄的对象而已。而阿兰虽是发妻,却一力承担了生育、抚养、伺候男主人等的许多家庭工作,多数情况下是忍让与顺从的,是封建规训下克己的女性。《大地》中引发读者关心与讨论的王龙的内疚和阿兰的反抗,虽然增添了复杂人性的多面性,但不改封建伦理关系影响下两性权利差距大的底色。
3.《大地》中物质文化的投射
《大地》所体现的侧重观念文化的这一形态特征也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汉学的突出形态特征,但这不代表《大地》创作中忽略了对物质文化的研究与描述。事实上,赛珍珠从小便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对中国的物质文化、人文习俗亦有亲密接触与细致观察,甚至相比起传统汉学在典籍游记中认识的物质文化更为细致、运用在创作中也更游刃有余。
曾在学界引发众多讨论域关心的“赛江之争”便是有关《大地》中茶文化的争论。1933年中国海外学者江亢虎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责赛珍珠《大地》的细节创作失实。比如中国人泡茶,不是把几片茶叶放在开水上,而是先放茶叶,然后倒水来泡[6]。诸如此类的指责,实际上是对赛珍珠创作真实性的质疑。此后赛珍珠做出了回应,解释这种“泡茶”的民俗是她亲眼看到上百次的。乡下百姓由于贫穷,是不会浪费茶叶的,这与高高在上、不考虑农民立场的江亢虎不同。事实上,赛珍珠对《大地》中的茶俗描写不但是真实可信的,而且准确地反映了主人公王龙的社会地位、心态,表现了饮茶在经营、娱乐、交际中的作用,对中国茶文化的习俗作了深层次的剖析,具有一定的民俗价值和艺术价值[7]。
丧葬习俗在《大地》中也有丰富的展现,具体包括寿木(棺材)的品级区分、丧服的规格、墓地的选址与送终、哭丧、守孝等流程,都有涉及。一定程度上也是属于中国民俗文化的范畴,能够展现我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
可见,传统汉学与现代汉学的形态特征也并非是互斥的,赛珍珠《大地》的创作中也兼有两种形态汉学的某些特征,且侧重明显。但将传统汉学与现代汉学合二为一的新形态在汉学全球化的当下已经崭露头角,相信在日后更多元的未来世界中将更具魅力[1]。
三.流露出基督教文明影响下的对实用性的重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赛珍珠《大地》遭受到国内众多学者的激烈批评,赛珍珠基督教传教士的身份成为了研究赛珍珠作品中思想情感难以回避的问题。赛珍珠虽然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从小就由中国人教授她中国传统文化,但考虑其家庭因素,父亲作为传教士同时也对她进行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教育。我们无法说这在这样“双重文化”的教育环境中,赛珍珠完全认同并沉迷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摒弃基督教文化,那么在赛珍珠的创作中也无法避免流露出基督教文化的印记。
首先,基督教的思维有其合理性。其目的在于探寻宇宙的终极真理,构成了西方价值观中“平等”“博爱”“同情”的思维原则。“博爱”“同情”体现在《大地》的创作中,几乎贯穿了人物塑造、主题探索、情感流露的方方面面,赛珍珠以仁爱宽容之心去接触和描写中国人,她发现了中国农民身上固有的弱点,他们封闭、愚昧、自私、有时胆小到以为忍让的地步[8],但她只认为这是人性的一部分,不仅没有忽视中国农民的优良特征,甚至呈现出更加积极正面的想象,这也得益于她对中国的善意与信任。“平等”的思维更多影响到她对于女性命运的关照和对中西文化“共性”的探索。《大地》中阿兰的人物形象倾注了赛珍珠强烈、感人至深的同情,这种同情甚至也迁移到了王龙的心理活动中。王龙为向荷花献殷勤而向阿兰索取珍珠时,应该是他最为沉溺、欲火难忍的时候,这是他生活富足也有了少爷做派,当时当地对于阿兰又怎会有“连正视阿兰目光的勇气都没有”如此强烈的惭愧呢?在展现王龙复杂心理的同时,或许也有赛珍珠对于阿兰被残忍对待的命运的同情,继而上升为赛珍珠对中国传统女性群体的同情和关怀,一时间也激发了美国、欧洲读者的广泛同情。20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东方主义发展,美国将中国想象成进步文明的美国“拯救”的对象、受美国保护的弱者、更需要美国政治上的解救。尽管赛珍珠的描绘大多是真实客观的,与当时丑化贬低中国的文学创作不同,但一定程度上也使得西方世界的优越感日益膨胀,以各种各样的目的想要深入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疆界最终达到服务于美国的、功利的、实用的目的。《大地》中虽然没有明确展现赛珍珠对于中西世界文化“共性”的讨论,但是其塑造的正常的中国形象,与美国时代背景紧密结合的土地主题,包括王龙在南方逃荒时遇到的时尚的、出手阔绰的外国坐车的人——尽管王龙认为给他银元的美国女人是因为无知、不懂行情,但在读者看来,美国女人多给钱并用结巴的中文让他“用不着拼命跑”是出于体贴和同情了。那么这也传达出了赛珍珠致力于让中西方世界放下成见、消除隔阂,从而相互关爱、亲近、沟通的愿望和目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初,有关《大地》的创作与美国东方主义的理论的联系与研究十分热烈,美国东方主义以“冲击—回应”“停滞与进步”这样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中国的变革归因为先进西方世界的影响,实际上强化一直以来的“西方文化中心论”,这不仅使得汉学研究偏离现实,更使得中西方文化无法平等交流。赛珍珠《大地》中确实出现了许多冷漠对待甚至否定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与对现代性追求的内容。例如:王龙向南方演讲的青年提问,遭到青年的嘲讽;打着消灭富人家旗号实则是抢夺财产的暴动行径;灰衣军强行住进农民家中坐享其成、不尊重妇女财物、农民敢怒不敢言的乱象;以及执意出走当兵不尊重父亲的、违背传统道德的王龙的小儿子。这些都流露出赛珍珠对当时中国现代化转变表现的不满。但她也明确表示,她对于中国人盲目照搬西方现代化举措的不支持。事实上,赛珍珠的社会、文化变革的观念与美国东方主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赛珍珠认为中西文化间存在普遍的共性而非直接的影响,一如“孔夫子”与“天堂里的上帝”是一样的。“我尤爱大慈大悲的观音,……她还有一个妹妹,即圣母玛利亚。”但由于赛珍珠本人对传统文化的迷恋与喜爱,她更倾向于构建一个古典而优美的传统中国,对于传统中国封建专、科举制等制度上的弊端还没有深入的了解,以至于更多体现的是“文化保守主义”的特征。若将其看做美国东方主义的践行者,利用中国题材的创作来假意逢迎,那就有对赛珍珠不太友好了。
总而言之,赛珍珠是一位身份特殊、生平传奇的汉学家,《大地》是她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基于《大地》这一文本,能够考察出在赛珍珠创作《大地》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汉学体现出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汉学的部分形态特征。这些形态既统一于现代汉学形态,又因为赛珍珠个性化的创作而有了独特的表现,也影响了往后的汉学发展。赛珍珠研究如今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了,而她毕生传递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沟通的愿望在汉学全球化的当今也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