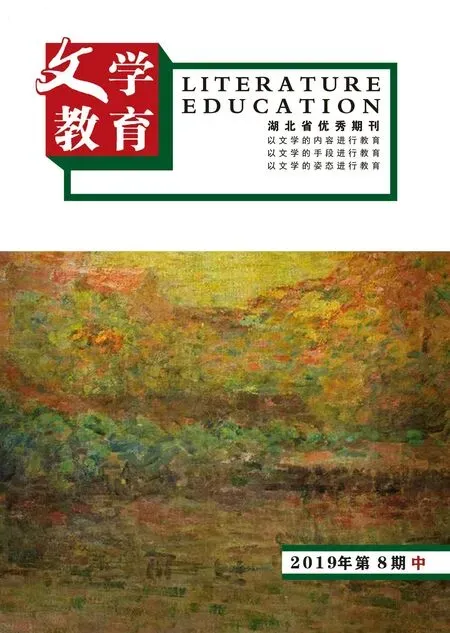《斯通纳》:他历尽失败却不虚此生
梁卫星
1.整体的人类没有尊严,人可以活出个体的尊严
《斯通纳》有点像约翰·威廉斯的自传。
威廉斯一生,创作过两本诗集,四部小说,在大学教了三十多年的书,是诗人、作家、学者。斯通纳没写过诗与小说,其内心饱满汹涌的激情在刻意疏离冷峻的生存选择下依旧散发着倔强的光芒,可谓疏于写作的本质诗人,他的人生遵循着诗歌的法则。斯通纳出过一本学术专著,没有什么影响,另一部也胎死腹中。起初,斯通纳对自己的学术也没什么信心,后随着自我认知加深,他意识到了自身学术的意义,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深刻最丰富的一部分,他的学术即他的人生。这是真正的学者,他的学术源于生命深处喷涌的呐喊,最终汇入课堂与图书馆,曾经召唤过敏感的心灵,也终将有后来者为之共鸣。斯通纳的一生囿于方寸之地,直到最后死去,从没离开过他求学与工作的密苏里大学,仿佛他来到这所大学求学,就是为了最终在此教书,直到耗尽自己的一生。
一个人在大学呆了一辈子,若没有出几本书,有个诗人作家学者的头衔,简直没法想象。按照世俗的理解,混也该混成一个诗人作家学者了,真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但威廉斯偏偏告诉我们,斯通纳就在大学教了一辈子书,既不是诗人作家,也非学者,即使作为一个老师,其身份也不算稳固,以致于其退休告别辞竟然是“感谢你们让我能够教书”。威廉斯绝决地扒掉了大学老师斯通纳身上所有的外在标签,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安之若素地以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触,极为克制、非常坦诚、按部就班地书写了斯通纳平凡到极致的一生。这是只有深味寂寞的人才能写出的寂寞人生,这寂寞的人生如同威廉斯老式的笔法远离时代,只在人们虚无的历史长河岸边背向而立,孤独地生,孤独地死。所谓本质意义上的诗人,真正的学者,不就是自家事只有自家知的寂寞,不就是无人领会没人在意的自我认知吗?威廉斯就是这样,他一生仅仅写了两本诗集四部小说,无不印数寥寥,在其有生之年也乏人问津。
斯通纳的人生,的确很大程度上是威廉斯的心灵痛史;然而,威廉斯绝非仅仅是借斯通纳来宣泄无法明言的一己人生悲苦。斯通纳的存在意义远远超越了威廉斯的个体人生,人类一代又一代重复着生老病死重复着哭笑悲喜,无数代人仿佛只有一代人,无量众生仿佛只有一个人,如此卑微,如此固执……斯通纳既是这卑微而固执地生死着的无量众生,亦是这卑微而固执地悲喜着的一个人,他是全部人类的镜像,他是一切生存的缩影。
再没有比人类更奇怪的物种了,一代人去,一代人又来,绵绵无绝地过着相同的生活,重复着相同的结局,但他偏偏有思想,甚至还能意识到自我——他的自我根本没有办法把自己从无量众生的生活中区别出来,无能把自己从死亡中间隔出来。仿佛他的自我洞悉这一切仅仅只是为了增加他的痛苦,他永远不能说自己和他人有根本的区别。他究竟为什么还是乐此不疲地哭笑走死?无论有多么不甘,无论如何争夺、强梁、横霸、算计……最终仍将归于虚无,他为什么还要精疲力尽地生活、繁衍、工作……直到被死亡收割,被遗忘归零?为什么?而人的尊严又究竟在哪里?
人类的自我意识使其沦为双重虚无的物种,从根本上说,人类是没有尊严的。第一重虚无是本质虚无,死亡的黑洞永远敞开着否定的巨嘴。第二重虚无是历史虚无,人类的历史来自其生理同一性,繁衍的本能开启了代际重复,也开启了代际不甘;然而,历史不过是遗忘的嘲弄,人能记下的历史,从来就既不是所有人的历史,也不是人的所有历史——何况所有的历史记载本身就自相矛盾,它本质上只是来自强梁的虚构,而虚构,不就是遗忘的表象,虚无的变脸吗?人的无能在历史记录过程中充分展现出来:人既无法记录自身的全部,也无法如实地记录。是以,人从历史中获得的不过是尊严的幻象,超越的意淫。
2.在荒芜的星空里,斯通纳认真地漂泊
荒谬,这就是人类及其全部生活的本质。万物皆实有,它们没有意识,所以他们无死也无生,他们只是存在。唯有人类,因为他有意识,所以他有生有死,最终却归于虚无。至于渴望尊严与超越,只是本质荒谬的衍生而已。这就是人,人的全部问题只是一个荒谬的问题:人如何在无尊严的规定性中活出尊严。这就是威廉斯书写斯通纳一生最想探讨的问题。斯通纳并非哲学家,也并不耽于沉思,他只是认真得近乎偏执地活着,他的生活方式给出了答案。斯通纳的答案甚至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斯通纳认为人类整体是活不出尊严的,人类没有尊严可言,人只有既不求助于整体亦不求助于历史时,才能活出尊严——人的尊严只能存在于个体的孤独与脆弱之中。斯通纳的生活方式是奇怪的,以人类眼光来看,他一生都似乎在顺应着什么又抵抗着什么,他认真得近乎偏执的活法,使他在人类眼光中时刻保持着这种刻意的姿态。但斯通纳其实并非刻意,如果人们认为他在顺应或抵抗着什么,那是因为人们抵抗着在他们眼中斯通纳顺应的东西,顺应着在他们眼中斯通纳抵抗的东西。这当然是荒谬的,斯通纳能活出尊严,并非与他们刚好相反或与他们恰好相容,而是与他们绝不相同,即使看似同样地活着,斯通纳如此活着的理由也与他们迥异。人们眼中,斯通纳似乎顺应着生活的传统,在奔赴死亡的河流中随波逐流;斯通纳也似乎抵抗着历史的洪流,与时代的热潮格格不入。但斯通纳既非人们眼中的勇士亦非他们眼中的懦夫,这样的评价于他而言,本身就是荒谬的。
对于人生的荒谬,斯通纳是如何面对的呢?斯通纳接受人生的荒谬性,首先,他坦然面对死亡,他并不认为死亡给予人生价值,这种人类主流观念的可耻在于他的自欺欺人,他不自欺更不欺人,死亡于他而言与他活着这件事一样,是一个事实,无法回避不能拒绝。生命不过是死亡的一袭袍子,每时每刻都在陈腐朽烂,直到最后彻底消失;如果人们能正常面对一件自身的衣服在时间的流里陈旧破败,为什么不能正常面对自己作为一件衣服的命运呢?斯通纳坦然到了呆若木鸡的程度,他很少顾影自怜,也很少忆苦思甜,他从不留恋往昔,更不恐惧衰老与疾病。他接受,并非顺应,除开他并不认为死亡给予生命价值,也因为他并不恐惧这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他的态度奇怪而鲜明:承认这个事实,但仅此而已,这个事实不能打破他活着的节奏,他严格依照生命的自然律令,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投入且认真,没有丝毫的虚张声势,没有刻意的紧迫慌张。他承认他活不出什么价值,但却可以活出尊严,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到的尊严。
斯通纳对历史亦无动于衷。无论是人类自古及今的宏大历史叙事,还是在人们看来,穿越而过他当下人生的历史洪波,他都视如无物。历史的虚无并不体现在他没有力量,恰恰相反,他的力量实有且强横。这是由人类整体生活的荒谬性决定的,人类把虚无的历史当成实有,以为历史乃存在之家超越之维,把参与乃至创造历史作为人类的价值体现。而以斯通纳的活法观之,人类陷入历史越深,人类的虚妄与可笑就越发深重。斯通纳对历史完全无感,他并不抵抗历史,任何对历史的抵抗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斯通纳不会以抵抗确证历史的存在,他不是历史洪波里一块坚韧的石头,他不是。斯通纳也不顺应历史,没有人可以在奔腾的河流里无动于衷,要么随波逐流以顺应,要么承受冲击撞刷以抵抗,别无第三种选择。而斯通纳既不曾顺应也不曾抵抗历史,因为他根本就不在历史之流里。他洞悉了人生与历史的虚无本质,他怎么可能在历史之流里。
那么,斯通纳在哪里?是的,他在荒芜的星空里,他偶尔与星空中零零散散漂泊的个人相遇,有时同行一段时间,有时相遇即永远分离,他始终是孤身一个,星空中的一介游魂——孤独、脆弱且无所事事。斯通纳就此活出了人的真实境遇,他认认真真地漂泊,认认真真地与他人相遇而后分离,不论这相遇是欣喜还是沮丧,不论这分离是痛苦还是愉悦,他无不全力以赴。他就此活出了他自身的尊严,他怀着悲伤的心情享受,尽管他深知这尊严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意义从来都产生于虚无的整体。斯通纳在死亡强横的论断与历史霸道的垄断下还原荒谬的人生本相,耗尽心力完成自身的荒谬存在,拒绝死亡与历史为其加冕,因为死亡不会给人加冕,而历史的冠冕从来都是炫目而喧嚣的虚妄。他无所求于天地之间,他的尊严他自己创造,尽管这尊严如此寂寞与寥落。
3.虚妄无法书写他,他也不在乎虚妄的无视,他的平凡与众不同
其实,如此玄思并不适合斯通纳。斯通纳只是一个平凡人,并非思想家。尽管他有着知识分子的身份,但他并不热烈追求知识以图挟知识自重,他对知识的态度勿宁说是够用就行,尽管他对知识极为严肃。他终生耽于美,响应莎士比亚的召唤,奉行美的原则生活。美本质上是脆弱与孤独的,一切所谓整体美集合美都是有意无意的欺骗,是死亡的号角与历史的法西斯谛。斯通纳并非缺乏对知识及知识分子的反思,而是他的活法本身就是对一切身份藩篱的抹除,他认真地活着,活成一个人的样子,身份对他没有任何意义与障碍。
平凡的斯通纳在整体人类的历史评价体系与死亡赋予价值的主流论断里是彻底的失败者。他出生农民,他的父母如同终生劳作生死于其上的贫瘠大地一样木讷哑言,他们的存在被历史书写彻底无视,他们的生如同他们的死一样没有价值。他们的一生既不知何谓随波逐流亦不知何谓抵抗,他们只是辛苦地活着然后死去,他们从泥土中长出来又回归泥土。斯通纳传承了他们的纯朴执着,如果不是他有幸遭遇天启,于星空中邂逅斯隆与莎士比亚,他也将完全重合他父母的命运。他和父母一样既不顺应也不抵抗,但他却以知道人类既有顺应亦有抵抗的虚妄与父母区别开来。因此,虚妄无法书写他,他也不在乎虚妄的无视,他的平凡与众不同。
斯通纳在需要爱情的时候追求爱情,他完全没有考虑双方身份地位的差别,他追求,只因为喜欢。结婚一个月后,他就明白了婚姻的失败,他也没有后悔懊恼。他接受失败的婚姻如同接受死亡,事实就是如此,他只能努力在失败的婚姻中给予彼此以与虚伪无关的体面。对于孩子,他的爱殚精竭虑却毫无力量,他罕见地痛苦,他无法拯救孩子于妻子歇斯底里的软暴力下悲苦地长大,他无奈地看着孩子以怀孕退学结婚的极端方式逃离冰冷的父母之家,他对孩子成年后在酗酒中精神痛楚地度日无能为力。除了尊重与理解,他不能给孩子任何帮助与扶持。
他在四十岁后遭遇了真正的爱情,他完全没有在意世人的非议与指责,他既不刻意隐瞒也不成心张扬,他遭遇了爱情,他就承受爱情并且尽情享受与奉献。这样的爱情注定遭受妻子的嘲笑与同事的毁灭,最终,他与爱人痛苦分离且再无见面。无论是对孩子的爱还是对爱人的爱,他都全力以赴竭尽身心,然而他既不能拯救孩子也无法挽留爱情,他的感情生活一败涂地。
他的工作卓有成效,他热爱教学始终对课堂充满热情,但他的学术著作一则影响寥寥,另一则胎死腹中。他坚持原则决不给系主任的门生开后门,却无力阻止对方以其他途径暗渡陈仓;他一生教学成效卓著,却为系主任构陷终生不过一助理教授。甚至几十年如一日,他的课程表都被人为地针对,让他疲于奔命。
这就是他的工作与生活、他的家庭与爱情,在人世的价值体系里,他没有一席之地,可谓彻头彻尾的失败。而且,以人世的标准来看,他对自身的冷漠与随意是不能理解的。比如说如果他不须对婚姻的失败负责,他为什么不取消这段婚姻?这样不仅可以把他从失败的家庭中挣扎出来,或许还能给孩子以有能力的爱。再比如说既然他不舍自己的爱人,为什么他不离婚与爱人在一起?既然他的工作环境全然异己,他又为什么不离开他就?是不是他害怕变动?是不是他没有能力应付变动后的生活?显然,他既非害怕变动,亦非对自己没有信心,问题其实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变动与不变动,于他而言,没有任何区别。
斯通纳在四十岁后遭遇爱情时,无论妻子的嘲笑还是世人的议论指点,他无不坦然自若心无芥蒂,全然没有婚外情乃不伦之情的觉悟,世俗的道德标准与人伦价值,他丝毫没有放在心上,他最终与爱人分离并非迫于世俗的压力,而是他非常清楚,爱情与婚姻本来就不同,当爱情遭遇世俗的压力时,无论是依旧我行我素一如从前,还是离婚而后与爱人在一起,都是让爱情不再纯粹,分离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唯有分离,爱情才永不褪色。至于他从没考虑离婚,也并非因为时代的清教徒道德氛围,否则就没有后来的婚外情了。根本原因在于,斯通纳认为,离婚也好,变动工作环境也好,其实是对婚姻与大学环境的变相肯定,这是违背他的终极体验的:人生无往不在虚无的陷阱之中,一切变动重来都是对陷阱的赞美歌颂。他绝不变动,陷阱中他人无处不在,他疏离地活着,活在家庭里,他是一个人;活在大学里,他仍然是一个人。他的状态奇怪地在而不在,不在而在,他活出了旷世的孤独与寂寥,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尊严。
孤独的斯通纳并不冷漠,恰恰相反,终其一生,他活得热烈而多情,他一生都在追求爱情与友谊,在爱情和友谊来临时,他积极主动全力以赴,他以自己的方式在内心深处守卫护持着爱与友谊。他热爱自己的工作,他并不把教学当成职业敬忠职守,而是把教学与学术当成生命一样守护经营,绝不容许有丝毫的懈怠与疏忽,更不容忍哪怕是一点点亵渎与假借。只是他如此活着太努力也太执着,反而显出了世俗的尴尬与混沌。在一片汪洋的尴尬与混沌之中,他并非刻意特立独行的认真执着令世人不安与拒斥,他成为众人口中的怪物与混蛋,他也不以为意浑然无住于心,他活成了无量人群中鲜明的一个人,这并没有什么意义,但还能有比这更具尊严的活法吗?再也没有了。
这就是斯通纳的一生,他活过爱过追求过,他孤独地生孤独地死,他历尽失败却不虚此生。在威廉斯看来,人类不可能像斯通纳这样活,但每个具体的人都应像斯通纳这样活。这就是我们应然的人生,纵然竭尽全力,我们也活不出什么价值,但尊严自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