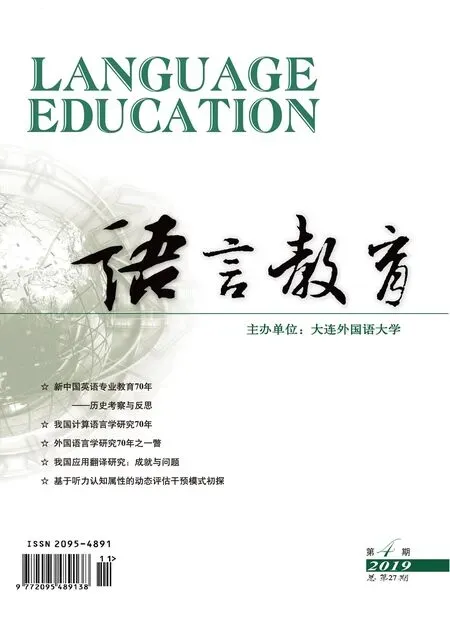“B是A的译文”意味着什么?
——基于唐诗《清明》及其五个英译文语篇认识世界分析的解答
王晓农 赵红梅
(1. 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烟台;2. 烟台职业学院基础教学部,山东烟台)
“翻译”是什么?这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在中外翻译史上,传统译论主要关注“怎么译”的问题。在现当代翻译学领域,这个问题逐渐进入了人们的焦点视域。不同的翻译理论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个问题进行观照,也就给出了存在不同侧重的尝试性界定,其中描写翻译研究学派的翻译定义最为宽泛,即“翻译”是由目的语文化发起的,在目的语文化中表现为或被认为是翻译的任何目的语表达形式(Toury,1985:19)。尽管同时存在界定过宽和过窄的问题,描写翻译研究学派建立的旨在研究翻译行为的普遍性、或然性规律的“发现程序”对于翻译定义性研究还是有启发性的。美国学者Tymoczko(2005:1083)在展望未来几十年翻译研究发展前景时指出了七种发展趋势,第一种就是对翻译的定义性研究,并认为翻译定义性研究在今后几十年仍将是翻译研究的中心领域。何谓“B是A的译文”的问题是“翻译是什么”问题的一个指涉文本关系的从属问题。本文拟应用认知语言学关于语篇认知世界的理论观点,以唐诗“清明”及五个英译本为研究对象,采用归纳性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探讨并描述译文和原文之间在认知世界上的关系,由此尝试部分地回答“B是A的译文”这个判断在文本认知世界意义上的含义。本研究属于文学翻译的定义性研究范畴。
1. 认知语言学的语篇认知世界概念
“认知世界”(Cognitive World)是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 简称CL)的一个概念。CL认为,语言世界和现实世界并不是直接对应的,二者的中介是认知世界。Jackendoff (1985:28)指出,人们所经历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智组织程序,他区分了“真实世界”(the real world)和“映射世界”(the projected world)。这里的映射世界即相当于“认知世界”,亦称为“经验世界”“现象世界”“心智世界”和“心理世界”等。沈家煊(2008)也指出,语言事实以及心理实验都证明存在三个并行的世界:物理世世界和语言世界。这里的心理世界亦相当于认知主体的认知世界。若把CL的根本观点“现实-认知-语言”表述为“现实世界-认知世界-语言世界”也是成立的。
与认知世界概念紧密相关的另一个CL概念是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简称ICM)。Lakoff于1982年针对客观主义语义理论提出了他的ICM理论并在1987年的著作中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以说明人类的范畴化、语义和概念结构等问题。ICM指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说话人对某领域中的经验和知识所作的抽象的、统一的、理想化的理解,是一种建立在许多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 简称CM)之上的一种复杂的、整合的完形结构,具有格式塔性质(Lakoff,1987:68)。语言符号在心智中激活的语义可以用ICM来解释。一个语言符号在认知主体心智中会激活相关的ICM,若其语义由直接理解的ICM加以确定,一般是该符号的字面意义或基本意义,而若需要通过隐喻或转喻模型来确定,则是其引申义或称为隐喻意义。ICM指涉认知主体组织知识的方式,更强调其主观能动性,对语言分析比“框架”、“图式”、“脚本”等概念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而对语篇连贯性的解释力更强。ICM作为分析工具多用于词语、句法、语义等领域的研究(Cienki,2007:180)。ICM理论考虑到了认知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差异,认知主体的ICM系统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对应关系,从对应到很不对应,从精确到很不精确。
CL认为,认知主体的认知世界的内容构成按照普遍性、代表性和理想化程度可分为ICM和背景知识,即认知世界 = ICM + 背景知识(王寅,2007:360)。背景知识不一定具有ICM的上述性质,它主要指细则性的具体知识,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是交际双方早已共知的,也可能是在当下交际中刚获知的,在具体语言交际中处于动态中,通过同化或顺应机制不断充实、加强、调整乃至改变会话双方的现有背景知识和当下交际情况。在共时维度上,一个语言社团及其成员的ICM是分层的,但和背景知识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开的界限。在历时维度上,ICM和背景知识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因此,认知主体的认知世界具有动态的实时在线性质。即使对同一个具体文本的语言符号世界而言,不同读者作为认知主体的微观认知世界也是动态的,只能是大致相似而不可能完全相同的。
2. 认知世界语篇分析方法和本文的语篇翻译分析框架
CL认为,心智连贯是语篇生成和理解的前提,必须从认知角度才能较合理地分析语篇。文本是实现了的语言现象,但一个文本却不一定成为认知意义上的语篇。①本文分别用“文本”和“语篇”两个术语,以区别作为一个语言符号集的“文本”与认知主体对该集的连贯理解结果的“语篇”,因此,“文本”是客观的,而“语篇”因不同的读者存在多多少少的差异。决定一个文本的一组语句成为语篇的必要条件是,语句的语义内容能在认知主体心智上实现认知上的连贯。文本语言符号的意义主要是指它经读者理解在其心智中建构语篇意义的潜势。文本的语句是一个有意义潜势的整体,只有当它在读者心智中激活的信息具有关联性和链接性,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语篇认知世界,它才具有语篇连贯性,才能意味着对语篇的真正理解。
2.1 认知世界语篇分析方法
文本理解具有体验性和多重互动性,涉及多重认知世界。语言可使作者运用最少的语法结构构建出适合某一语境的具有丰富意义潜势的文本语言世界,而文本可提供很少但却足够使读者能找到在某一语境下用于意义建构的线索(Fauconnier,2008:40)。对于作为认知主体的读者,语篇的生成从根本上讲都是以其体验认知为基础,在客观世界、他的认知世界和文本的语言世界的多重互动中实现的。随着语篇认知过程的启动,在文本语言符号引导下,大多数的认知建构在幕后进行,不断出现新的认知域,建立跨域连接,抽象的认知映现开始运作,内部结构开始改变、扩展,视角和焦点不断转换等等(Fauconnier,2008:40)。对可激活的信息而言,显性信息可能仅是冰山一角。读者会根据自己的认知世界知识,结合语境,在文本语言表达上增加许多内容,尤其要补充缺省信息,通过关联和激活机制在上下文概念成分之间努力发现照应关系,寻求命题的发展线索,获得语用推理上的顺应性。读者若能够在心智上建立一个连贯统一的语篇认知世界,就说明他理解了语篇。
CL的语篇认知世界分析强调语篇理解所依赖的认知基础。对于单语文本,王寅(2007:359-366)提出了一个认知世界分析方法,主要基于充分的背景知识从ICM入手分析语篇认知世界知识的激活和缺省信息填补问题。它主要从ICM和背景知识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要点是,只要一个分句中的任何词语所激活的认知概念域能与其后分句中任何词语所激活的概念域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存在命题上的索引性,就可以认为这两个语句是连贯的。当然,不同的人因认识世界和心智中框架结构的差异,在不同语境下可能会突显不同的信息,同时,由于为了某种交际目的(如打趣或不配合),交际者也可能调用其认知世界中权重较小的信息充当交际话语的中心。因此,在交际实践中,交际者需要视交际的具体情况来调整谈话内容。这是需要在分析中加以考虑的。
2.2 翻译的认知世界分析和藉此建立的语篇翻译分析框架
语际翻译也具有体验性和多重互动性,涉及多重认知世界。如果把上文语言内的分析应用于翻译过程分析,那么语篇翻译中理解原文和生成译文的过程都是以译者的体验认知为基础,在涉及双方的客观世界、认知世界和语言世界的多重互动中实现的。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实际上是还原其承载的交际事件图式结构的过程。译者在理解和翻译语篇时,其语篇认知世界主要指对当下文本进行心智加工而建立的复杂心智空间网络和语篇连贯表征(王晓农,2014)。可以认为,译者的语篇翻译目标是使目标读者能够在译文文本语言符号世界引导下建构译者所期待的、与目标读者的认知世界统一的译文语篇微观认知世界。这应该是译文文本构建的认知前提,而译文表达是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对翻译目的、目标读者和译语语言文化等因素理解整合后形成的,这种整合是译者经验思维的实时运作。
人们在阅读文本时,一般会假设文本具有语篇性即心智上的连贯性。这样看来,阅读文本就是一个验证语篇假设的过程。笔者在这里用CW表示一定历史语言文化语境中的读者的认知世界,用cw表示读者理解该语言文本A所生成的语篇认知世界,相对于CW而言,cw是微观的。本文对读者理解文本的假设是,读者经A的语言符号线索与其CW知识和相关的逻辑、推理等能力互动,通过体验性概念化过程,①关于“体验性概念化”的含义,参见王寅 2008(3):211-217。最终建构起与其CW相统一的cw。相对现实世界而言,CW指认知主体在体验基础上经认知加工形成的各种知识,内储于人们的心智之中,能够反映出个人兴趣、需要、知识、文艺修养、欣赏习惯、个人信仰等因素,构成了读者理解文本的一种主观性自我的必然存在;cw是相对一个文本内的语言符号微观世界及其反映的相对现实世界而言的微观认知世界。就翻译而言,在理解和翻译文本时,cw主要指对当下的文本语言符号进行心智加工而建立的复杂心智空间网络和形成的语篇连贯表征,可做如下假设,译者经A的语言符号线索与其CW知识和相关的逻辑推理等能力互动,通过体验性概念化心智运作,建构起与其CW相统一的cw,然后将该cw结合对翻译目的、目标读者等因素的认知再目标语言符号化为B。②这里沿用将翻译过程简化为“理解”和“表达”两步的传统做法。本文关于目的语文化中的译文读者对译文本B的理解假设,其表述与前文假设类似,不同主要体现在因文化缺省而造成语篇认知世界建构存在一定的困难。由此引出何谓“B是A的译文”的问题。
笔者以上述语篇认知世界分析方法为基础,借鉴描写翻译研究以译本为先的研究程序,从可观测的文本翻译事实出发,针对本文的研究问题提出以下不涉及对译文的价值判断的、描写性的语际翻译(本文限于汉、英语)语篇认知世界分析框架:对于声称具有翻译关系的两个文本B和A,首先对译本B从英语读者角度进行认知世界分析,然后从假设具备充分背景知识的汉语读者角度对原本A进行分析,再对两个文本的认知世界分析结果进行比较,将B和A的翻译关系描述具体化,以说明两个文本间在认知世界上的大致关系,由此提出界定翻译的认知世界关系参照点。这个分析程序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进一步细化。
文学是人类日常生活经验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特殊体现方式(Gavins & Steen, 2003: 1)。文学家的认知世界也是基于人类赋予世界以意义的一般认知能力之上,因此对文学作品的赏读就离不开人类普遍的语言和认知机制。一首诗是一个文学文本,其中包含一个中心主题,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具有完整的组织结构以及与其相适应的语言表达形式。基于人类语言所具有的可通约性及文化信息的可复制性和可解释性,也由于文化原型的再生性和文本的互文性作用,文学文本一般具有基本的可读性和可译性(王宏印,2011: 375)。关于诗歌翻译,历来有关于诗可译与否的争论。有观点认为,诗不可译。假若这个命题为真,还需要看它在什么层面上是成立或不成立的。从现象上说,这无需论证,因为存在大量的诗歌翻译现象。从翻译本体上说,若承认“非有失本而不成翻译”(王宏印,2017:17)的命题为真,那么在翻译中发生不同程度的“失本”就是一种翻译的根本属性,因此可译性是一个连续体,诗也必然是可译的。关于从CL来关照汉诗英译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不少成就。例如,国外方面,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一书的6.5节就简要分析了一些应用CL理论研究翻译的成果(参见Cienki,2007:1191-2),国内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呈上升趋势,但尚无专门从认知世界入手探讨译文和原文翻译关系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属于中国古典诗词及其英译范畴,具体的研究对象是唐杜牧《清明》及其五个英译本。①五个英译文(按本文顺序译者依次是蔡廷干、万昌盛和王僴中、吴钧陶、许渊冲、杨宪益和戴乃迭)转引自黄国文(2006:191-3)。该书对这些译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进行了分析。
3. 对唐诗《清明》译文和原文的分析
读者对一首诗的理解需要调动其认知世界知识中的语言文化百科知识,特别是诗学知识和审美经验。读者在阅读译文前对译作显现方式的定向性期待主要有两大形态:一是在既往对文学类型、形式、主题、风格和语言的审美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较为狭窄的文学期待视野,二是在既往对社会人生的生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更为广阔的生活期待视野(姚斯 霍拉勃,1987:200)。原文或译文读者对一首诗的读解可视为朝向杜威(Dewey)所说的一次审美经验的努力。杜威所谓“一个经验”是一个整体经验,它是完整、圆满、和谐的经验,有格式塔心理学所说的“完形”(姚文放,2008)。 一旦人们的日常经验改变了那种零散、混乱和分裂的状态而达到包容大度而又臻于完满的结局,那么就成为“一个经验”,具有了审美的性质,转化为审美经验(姚文放,2008)。读者阅读诗作以获得一次文学审美经验的努力和获得与自己的认知世界相统一的语篇认知世界的努力是一致的。理想情况下,若读者意识到所读的是诗,则会基于自身的文学知识和审美经验激活认知世界中关于诗的ICM,由此解读诗的语言符号及文本结构、比喻、声音等方面。当然,诗中的情感、审美等因素是非概念化的,是难以言说的。一个语言文化内关于“诗”的ICM在不同时代有所不同,对同一时代不同的人群而言也不是完全一致,但可认为一般的共识是,诗是一种文学体裁,形式上有韵律节奏、分行书写的特征,其理解需要依靠基于体验认知的想象力和审美力。对汉语读者来说,在诗的ICM中还涉及“意境”的知识和审美经验。与英诗相比,中国古典诗词创作和赏读又以精神意境的营构为着力点。基于诗的一般的ICM,具体的一首诗的语言符号使认知细化,再概念化而生成连贯的微观认知世界而理解该诗。据以上前提,本文案例分析主要限定在诗的词句、结构和比喻层面。
3.1 英语文本分析
(1)All Souls’ Day
The rain falls thick and fast on All Souls’festive day,
The men and women sadly move along the way.
They ask where wineshops can be found or where to rest —
And there the herdboy’s fingers Almond-Town suggest.
题目“All Souls’ Day”会激活读者关于西方天主教11月2日“万灵节”的ICM(例如,有各种活动,宗教意味浓,如纪念死者,为亡灵祈祷,愿其从炼狱升入天堂)。第一行The rain falls thick and fast 意为“雨大而急地下”;The是定指,All Souls’ festive day用零冠词,似乎指这样的节日总是下大而密、间歇时间短的雨。这和西方11月份的All Souls’Day的ICM不符。第二行The men and women和the way都是定指;move一词未说明是步行还是乘交通工具;在All Souls’ Day的街上或路上会有行人,因此本句和上句有一定连贯性。第三行They指上句的行人,他们问的问题(间接疑问)是哪里可找到酒馆或可落脚歇息,可能是劳累饥饿之故,这也可和上文sadly联系起来;ask一词激活的ICM中包括问自和问他,但句中描写的场景似和常识不符,因为不太可能所有人都问。第四行herdboy指照料畜群的或做牧人帮手的孩子;there the herdboy’s fingers suggest令人感到费解,似乎那个herdboy用手掌比划而不是用食指指。对于Almond-Town一语,读者能基于语言的ICM识别它是个地名,可能和almond有关。全文从第三人称视角描述了一个场景,雨、行人和儿童都是定指;整个译文总体上语篇连贯性较弱。若读者了解这个文本译自汉语古诗,可能有助于改善对文本的认知解读,但笔者认为,这个译文仍较难和读者的认知世界统一起来。
(2)The Tomb-visiting Day
The ceaseless drizzle drips all the dismal day,So broken-hearted fares the traveler on the way.
So broken-hearted fares the traveler on the way.
When asked where could be found a tavern bower,
A cowboy points to yonder village of the apricot flower.
标题意谓“上坟的日子”,虽有定冠词,但难以判断是否是个节日。第一行名词drizzle指毛毛雨、细雨,动词drip指雨滴落,二者在ICM上似存在冲突,但若是较大的细雨和较小的雨滴,二者也能构成一个自然场景。该句似认为读者知道the dismal day是哪一天。形容词dismal和标题存在关联,也和下行broken-hearted存在联系。第三、四行构成一个句子,间接疑问的问话人应是前文的行人,他寻找的是a tavern bower,即酒馆凉亭、树荫之类,似乎要在亭子里或树荫下吃喝歇息。第四行的cowboy的ICM多与西方文化中的“牛仔”“粗犷、莽撞之人”有关;cowboy指的村子位于开着杏花的地方。全文从第三人称视角叙述,文本内部有整体连贯性,总体上和读者认知世界也具有一定连贯性。全文描写的主题较清楚,由于“行人”只有一个,更像是一个个人经历的描写。
(3)The Pure Brightness Day
It drizzles thick on the Pure Brightness Day;
I travel with my heart lost in dismay.
“Is there a public house somewhere, cowboy?”
He points at Apricot Bloom Village faraway.
标题会使读者意识到文本与其他文化的节日有关,Pure Brightness可能是该节日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难以进行具体化的概念性认知。全文描述视角是第一人称。第一行更可能指具体的一个这样的节日天在下雨,而非在这样的节日天总是下雨。第一句与时间有关,因为“我”出行必然发生在某个时间,而通过这个时间关系可将两句联系起来。第三行是个直接引语,显然是I在问。问话中public house在ICM上指带“酒吧”的公共空间,有的提供便餐;如前所述,cowboy的ICM多与西方文化中的“牛仔”和“粗犷、莽撞之人”有关。第四行Apricot Bloom Village是个专名。全文内部有整体的连贯性,与读者认知世界有较强的连贯性关系,但译文的文化主题似乎较模糊。从题目和全文关系看,更像是对那个节日里一个个人经历的描写。
(4)The Mourning Day
A drizzling rain falls like tears on the Mourning Day;
The mourner’s heart is going to break on his way.
Where can a wineshop be found to drown his sad hours?
A cowherd points to a cot’ mid apricot flowers.
标题使读者意识到面对的文本与其他文化的节日有关,悼念活动可能是这个节日的特征,由此能激活较多的背景知识,联想起英语世界相关的一些场景,为全文定下了调子。第一行,drizzling rain和drizzle在ICM上类似,like tears在句法上似修饰fall,实为rain之补语,但drizzling rain不太像tears,用明喻tears指涉下雨样态似也不太贴切,但可理解为渲染气氛的修辞手段。英语fall突显了“落下”,限制了drizzling可激活的概念域。第一句更可能指具体的一个节日天在下雨,而非这样的节日天总是下雨。前文mourning和第二句mourner联系起来,也使该定冠词的使用较为自然。全文是旁观者第三人称描述,第三句是一个自由间接引语,更像是旁观者在问话。句中hours指数个小时,可能不只是吃喝,还要住宿。第四行cowherd的ICM指被雇来照料牛群的人,一般不是孩子;由cot’的写法和语境可知是cottage之略,牧人指向的是掩映在杏花中的一个村舍。全文内部有点连贯性阻断,第三行的问话人是谁不清楚,为了建立连贯关系,较可能的情况是把问话理解作When asked“where can a wineshop be found to drown my sad honors?”,但又似乎不是向一个陌生人的问话,且to drown my sad honors意指喝完酒就不再“欲断魂”了。全文更像是描写一个人的节日经历,文化主题似乎比较模糊,和读者的认知世界连贯性似不太强。
(5)In the Rainy Season of Spring
It drizzles endlessly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in spring,
Travelers along the road look gloomy and miserable.
When I ask a shepherd boy where can I find a tavern,
He points at a distant hamlet nestling amidst apricot blossoms.
标题明确说“春天的雨季”,由此可使读者激活较多的背景知识。第一句新信息不多,主要说春天雨季下的是毛毛雨;与on不同,during强调期间,句中the rainy season in spring似指常态。第一、二句主要通过时间概念联系起来,行人不止一个,但不清楚行人为何愁苦,从语境看可能与下雨有关。第三句使全文描述的第一人称明朗化。第一句的雨季包括了具体的每一天,而后文ask可能是发生在某天的某时刻,因此也可联系起来。I显然是前文所说行人中的一个,这里又使第一句似乎常态的描述具体化了;句中shepherd boy指牧羊男童。尾句hamlet多指比一般村子小的、由几户人家形成的小村落;句中描写的村子掩映在杏花中。全文内部有整体连贯性,和读者的认知世界连贯性也较强,但译文的文化主题不够清晰。
3.2 汉语文本分析:
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本诗是唐人杜牧所作名篇。题目较清楚地指向“清明(时)节”,中国人“清明节”的ICM一般与祭祖踏青有关。第一句中“清明时节”指二十四节气中的清明,其概念域包括了这段时间及其具体的每个雨天。“雨纷纷”,从自然现象上讲,这段时间南方多细雨,北方未必有雨下。诗中写雨主要为了营造气氛。第一、二句首先通过时间概念联系起来,“雨”和行人心绪也有概念联系。“路”和“行人”作单数或复数理解皆可,但单数更能体现一个离家而孤单的人在雨中行走所产生的凄苦愁绪、劳累疲乏的“欲断魂”心态。第三句“借问”的发问者应是前文所说行人,如理解为多个行人的话可能是其中的某个。问话是间接疑问句(有的版本句末用问号,表明是直接疑问。原诗古代版本没有标点)。尾句“牧童”所激活的ICM主要有:男童;牧的对象是一头或几头牛;人和牛悠然闲适。在中国绘画和文学作品中“牧童骑牛”“孺子牛”是一个经典形象。“遥指”一般是用食指指远处某个地方。“杏花村”不应是一个专名,因为牧童没有说话,问者对当地也并不熟悉,不太可能知晓村子的名字。因此,较为可能的情况是,“掩映在杏花中的村子”。全文的叙述角度可能是第一也可能是第三人称,文本内部整体连贯,文化主题清晰,和读者的认知世界具有统一性。
3.3 比较分析
各英语译文文本都具备诗体特征,都表现出情绪压抑的基调,都具有“雨”“人”“愁苦心情”和“问答”等基本元素,能够使读者建立起基本的认知框架。汉、英文本都具有自身的语篇连贯性,基本都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语篇认知世界,尽管程度有别。从前文分析可看出,译文不追求与原文在语篇认知世界上的最大相似性。有的译文内部存在一定的连贯性阻碍,如(4)。在与译文读者宏观认知世界的连贯性上,各译文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统一性。由此可见,作为认知主体,原作者和英译者在体验认知上存在一定的共同性,因此具有对文本大致相似的创作和理解的认知基础,译者也都是基于自己的体验对原诗进行翻译的。
汉、英文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与原诗相比,有的译文在语言符号的组织上有变化,例如诗行方面;因为语言符号激活的ICM和背景知识有差异,译文的语篇认知世界与原文必然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差异,有的差异较大,例如译本(1)。汉语语篇与读者宏观认知世界具有统一性,但英语文本和英语读者的认知世界的统一性则呈现多多少少的不连贯,例如译本(5)和(3)较强,而译本(1)较弱,但总是存在一定的统一性。①从文学审美来看,英语译文与英语读者的认知世界间的统一性未必越大越好,而译者追求的目标在理论上可表述为“英语译文与英语读者的认知世界的最佳统一性”。当然,何为所谓的“最佳”会受到其他诸多因素比如读者的英语诗学ICM的制约。汉语原诗语言的高度凝练使读者的认知解读空间很大,英语译文是对原文语言符号概念化的再语言符号化,诸译文的不同反映出不同译者对原诗概念化和认知方式的差异。
4. 对“B是A的译文”指涉文本翻译关系的描写性分析
基于以上对汉诗英译语料的分析,我们可尝试从译文本B和原文本A的语篇认知世界关系对“B是A的译文”这个判断的含义进行初步描述。我们说“B是A的译文”的时候,在它们的语篇认知世界关系上,意味着B和A在语篇认知世界上存在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可描述为:以A为参照点,B保持A的基本认知世界元素和基本认知框架不变,而不追求与A在语篇认知世界上的最大的相似性;B在语言符号的组织形式上可能有所变化;B在语篇微观认知世界上相对于A有或大或小的变化,涉及语言符号激活的ICM和背景知识差异,但B自身有基本的语篇连贯性,有时会出现一定的语篇内部不连贯现象;B在与读者宏观认知世界连贯性关系上有变化,或强或弱,但连贯性总是存在的;作为译文,B总会表现出某些与译入语ICM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不一致可能涉及语篇内部关系或与读者的认知世界关系。此外,A和B是一和多的关系,B的不同表现形式之间对读者而言总存在语篇认知世界的差异。相对于A的认知世界,B的不同文本间未必能形成完全的互补关系。
人们在理解一个词语的意义时要根据该词语在心智中被激活的相关经验和概念内容,同时还取决于加于其上的认知方式,这体现为操一种语言的人的ICM大致相似,而操不同的语言的人之间的ICM存在或多或少差异,因此导致对文本的理解必然同中有异。对同一原文的不同译文在选词和译法上的差异说明了语言表达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但不足以说明译者的自由性和放纵性(王寅,2008)。以上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文学翻译具有客观性和一定的主观性。关于认知世界内部的不连贯问题,从语篇认知机制来说,译文读者在遇到文本中新信息与原有认知结构产生冲突时,一般会基于现有认知世界知识,通过同化和顺应机制解决认知冲突,要么达到更高状态的认知,要么维持原认知结构的不变。
5. 结语
本文依据认知语言学的认知世界概念和语篇认知世界分析方法,设立了语际翻译的语篇认知世界分析框架,并以一首唐诗及其五种英译文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原文和译文在认知世界上的异同,尝试从认知世界关系的角度初步说明了“B是A的译文”这个判断的含义。在一个文化内部,其语言社团对语际翻译的结果即译文的ICM只能就其最为基本的特征达成共识,而不同的人群则有自己相对的ICM。因此,对于从各角度对翻译的定义性研究得出的结果,必然存在各种限制条件,也就不太可能同样地适用于整个文化语言社团的ICM认知。所以,本研究存在着将读者的语篇认知过程过于简单化的问题。另外,本研究未进行针对原文和译文读者的实证调查,因此必然存在研究者的认知分析代替了两类读者的认知解读的问题,并将两类读者理想化,即汉语读者具备充分的汉语语言文化和诗学背景知识,而英语读者也具有充分的英语语言文化和诗学知识。这是本研究的一些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