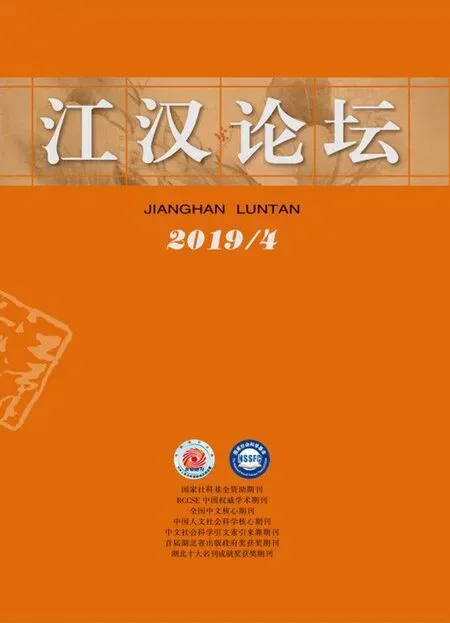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看近代汉商的公益文化精神
——以1930年代裕大华纺织集团的社会参与活动为中心
罗 萍 沈晓岑
近些年,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热潮的兴起,有关近代民族企业责任的研究逐渐增多。但总的来看,已有研究对近代不同地域民族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多样性表现,仍探讨不足,至于近代武汉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及其中蕴蓄的汉商文化精神,相关研究更甚少论及。①与此同时,近几年由武汉学兴起而引发的学界对汉商文化的热议②,却又明显缺乏实证的分析。这种情况与汉商企业在近代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相比,显得十分不相称。
近代中国民族企业诞生于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其时,从国家、社会到企业,从社会精英到普罗大众,对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尚处于初始阶段。不过,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多难兴邦的时代旋律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压力等,共同推动我国民族企业不同程度参与到了社会责任建设中,及至上世纪30年代形成了我国企业发展史上社会责任建设的第一次浪潮。裕大华纺织集团就是投身这一浪潮的民族企业中的一员。
裕大华纺织集团的核心企业是三个有着“姊妹”与“母子”关系的纺织公司,它们分别是1919年筹建、1922年投产的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和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及1935年由裕华和大兴联合投资创立并于1936年投产的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这三个企业的总公司同设于汉口而纱厂分别设于武昌、石家庄和西安。这三个企业的主要创始人和经营者是来自武汉商场的三位工业资本家湖北武昌人徐荣廷、四川巴县人苏汰馀和湖北汉阳人张松樵。其中徐荣廷和苏汰馀分别是裕大华集团第一、第二代掌门人,张松樵则长期担任裕华公司驻厂经理,是近代裕大华集团各个发展时期领导启动和支持各项管理革新的核心人物。1930年代,在裕华、大兴和大华以跨区域扩张的态势走向崛起,继而成为规模仅次于申新纺织公司、永安纺织公司的民族棉纺织大企业的过程中,“裕大华”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逐步增强,其企业领导人的社会声望不断提升。在此期间,裕大华一方面在企业内部着手加强劳工福利建设,另一方面则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活动,发展了“企业外部”社会责任建设。
一、担任社会职务,维护业界利益
1930年代裕大华集团的掌门人是担任裕华公司董事长、大兴公司总经理、大华公司董事长的苏汰馀。苏汰馀出身于四川巴县清寒儒士之家,青年时期曾任职成都报界,因撰文宣传反清革命思想而遭清政府通缉,被迫从成都逃到汉口,从此踏入商界,并结缘一批志同道合的汉商,共同开创了裕大华事业。当他接替裕大华第一代领导人徐荣廷而成为企业新的领导核心时,艰难走出1920年代纱业危机困境的民族棉纺织企业,又遭遇了更加严峻的民国第二次纱业危机的挑战,南京国民政府所谓税制改革与日本棉纺织业倾销狂潮等各种险滩恶浪交织迭现。裕大华企业正是这个时期乘风破浪,跻身国内民族棉纺织企业三强之列。以此为背景,苏汰馀也成为湖北工商界的领袖人物之一。
其一,出任多个社会职务。
1920年代中期,苏汰馀作为裕华、大兴两公司常任董事时,即已出任华商纱厂联合会湖北省分会主席。大革命时期,他一度担任武汉地区劳资仲裁委员会主席。1929年经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倡议,以民办为主、官方协助为原则,华商纱厂联合会湖北分会、武汉大学、进出口棉业公会及湖北省建设厅等单位,共同组建了湖北棉业改进委员会,苏汰馀出任主任委员。1930年代初,苏汰馀又出任了湖北省商会联合会主席。
1933年9月,全国生产会议行将召开,湖北省建设厅遵照实业部8月6日训令,着手推选“有成绩之企业工程师五人至十五人为会议召集人”,苏汰馀成为该厅推荐人选之一。苏汰馀对于参加全国生产会议热情很高,在接到湖北省建设厅邀约函第二天就复函建设厅厅长李范一表示应约,并附送了个人履历。③
1936年国民政府筹备召开第一次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日期。当时在武汉商场上,黄文植、陈经畬、贺衡夫、苏汰馀声名最著,人称“四大金刚”。武汉地区国民代表选举结果,陈经畬、贺衡夫、苏汰馀三人当选。此次国民大会因抗战在即未能举行。1947年国民政府重开“国民大会”,苏汰馀再次当选“国大”代表,并出席了“国民大会”。
其二,积极维护业界利益。
在出任多个社会职务,包括一定程度“参政”、“议政”的活动中,苏汰馀参与和领导了大量推动湖北工商业发展的社会活动。这其中最艰难的是为减轻工商企业税负与政府展开抗争的努力。期间,苏汰馀展现了面对强权,不卑不亢,勇于斗争,富有正义感的汉商形象。这种表现,与其前辈和前任徐荣廷担任武昌总商会会长时,为抗议当局向武昌地区工商业者无度摊派军饷,而与湖北督军王占元面对面展开辩驳的勇气④,一脉相承。
1933年在日纱倾销狂潮的直接打击下,华商纱厂遭遇纱业危机的形势极为严峻。该年年初,苏汰馀组织华商纱厂联合会湖北分会,向南京政府中央党部、行政院、财政部、实业部等分别递交陈情书,提出了要求政府增加日本进口纱布税二至三倍,对华商纱厂退还原棉进口税、实施“低利贷款”等救济措施。⑤同时他又以个人名义致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监察委员曾庆锡,再次恳切陈明上述要求,乞其转呈中央。⑥然而,南京政府却于1934年7月对关税进一步“作了有利于日货”的调整。苏汰馀随即响应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的倡议,于10月间带领湖北华商纱厂请愿团赴南京请愿抗争,并在列席国民党中常委的会议上,与财政部长孔祥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⑦华商纱厂联合会湖北分会的这些艰苦努力和奔走呼吁虽未达其直接目的,不过仍推动政府采取了一些避重就轻的救济措施,如促使南京政府军政部将被服国货订购制从上海推及到了武汉,一定程度缓解了湖北棉纺织企业在纱业危机中的压力。
1935年因不堪法属越南政府压迫虐待,30余万越南华侨“迭电”南京政府请求援助。南京政府与法国政府进行交涉的结果,法国政府以中国政府减低越南煤、米进口税,作为改善越南华侨待遇的条件;南京政府则“屈从其请”,拟议将越南进口煤减税2元。面对这一直接威胁湖北相关工商业利益的危情,4月26日苏汰馀以湖北省商会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分别致函国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实业部等,一面抨击政府拟议,犹如“开门揖盗”,“我政府纵不为商人计,其如整个国家经济何?”一面期望政府取消此成议,他说:“属会为民办团体,痛切剥肤,……伏望审慎将事,对于此类非法要求,悉力拒绝,以全民命,而维国脉”。⑧这封信最终并未能触动政府改变成议。
苏汰馀组织湖北工商界迭次与政府严重损害工商业者利益的政策举措展开抗争,虽难以取得成功,但其为维护湖北工商业界共同利益勇于担当的作为,无疑产生了积极社会影响。
二、珍视企业声誉,维护民族尊严
裕大华企业领导人有强烈的建立企业“永久”基业的愿望,因此从创业之初不但十分注重保护本企业产品的“商誉”,也极为珍视本企业其他各种社会行为的信誉。这种珍视,既出于维护企业形象的理性考虑,亦源自企业领导人一以贯之急公好义的内在精神风骨。
裕大华集团第一代领导核心徐荣廷,是裕大华“领导集体”中的长者,更是一位胸有大义、见识敏锐之士。早在武昌首义和阳夏战争时期,他就作为商界支持革命的积极分子,努力奔走于工商界劝募和红十字会伤兵救护等各项工作中。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作为当时汉口永济消防会会长,在组织办运干粮供给军需、支持革命义军上表现了特有的责任担当。有记述写道:“二十八日,我军得胜,该会张旗提灯,整队欢迎。……忽而我军稍挫,该会员逐渐星散,惟徐荣廷等坚韧支持。于九月初一日,群相解囊,招募壮丁40名,昼夜梭巡,罔敢稍懈。”⑨在后来汉口商界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出卖国家主权的“二十一条”的斗争中,年届六旬须发尽白的徐荣廷亦当仁不让,扛着大旗走在游行抗议队伍的最前列。裕大华企业自开创以来,直至民族危机严峻的30年代,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表现出坚定的爱国立场和特别敏感的民族主义意识。
裕大华各企业在成立时都明确规定招股范围仅限国人,如1923年《大兴公司章程》即规定:“本公司股票以本国国籍人民为限”。⑩1937年大兴石家庄纱厂在日本纱厂和国营纱厂内外包围之势的压迫下,“展望前途,不寒而栗”⑪,不得已求售,但明确限定不出售于外商,董事会遂拟议将工厂卖给觊觎吞并大兴纱厂日久的营业对头——国有中国银行。⑫1937年5月大兴公司股东大会召开,董事会正式将卖厂议案提交到了股东大会讨论议决。期间有股东提问:“承买者是否为本国企业家?”董事长回答:“确系国内大企业家,本厂决不售与外人”。⑬大兴纱厂售卖议案最终获股东大会通过,只是未及售卖成交,日本侵华铁蹄已伸向石家庄。
石家庄沦陷后,大兴纱厂为日军占领控制。日方军部先是“累催”大兴方面复工,大兴纱厂留守人员遵总公司指示“婉辞拖延”。日方随即派钟渊纺绩株式会社人员进厂“管理一切”。大兴公司不愿日军侵占工厂,曾设法“挽救”,期以通过交涉使日军“发还”大兴纱厂,而又不能不顾虑如若大兴纱厂得侥幸发还,“他日国军收复石庄,则难免不无与日方合作之嫌”。在进退两难中公司最终决定:“停止一切进行”,着手分批裁撤留守职工。日方此后并不死心,仍想迫使大兴与之“合作”,曾召大兴留守人员向其通告:欲想发还产权,绝不可能;若同意与钟渊纺绩株式会社“合作”,“共同营业”,则可取消军管名义,且营业利润大兴和钟渊按2∶1分成。⑭面对日方“合作”利诱,大兴总公司坚定予以拒绝。后来大兴公司一小股东张格投靠日本侵略军,出任石家庄伪市长,并妄称代表大兴公司恢复大兴纱厂生产,继而信函联络大兴总公司等机构,声称欢迎大兴股东加入合作,分享利润。大兴总公司对此严词驳回,并呈报国民政府备案。⑮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其时捷足先登站稳西北市场的大华纱厂营业十分繁盛。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别有用心的攻击大华的流言在西安传播开来。这些流言“不曰含有日股,即谓份子复杂”,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大华公司感到“值此中日交战之际,更非切实证明不可”。⑯于是公司备具股东名册等文件,致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第二厅,请其就大华有无日股予以证实鉴核。⑰公司又通过华商纱厂联合会湖北省分会,分别致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陕西省政府、湖北省政府、实业部等机关,请其就大华有无日股“核明布告,以正观听”。⑱大兴公司董事长周星堂亦亲自致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铭三,请其将大华不含日股的证明,“准予布告周知”。⑲经过努力,加上大华公司又“捐出救国捐1万元”,至9月,流言“不攻自破”。⑳
1938年底至1939初位于武昌的裕华纱厂被迫西迁。途中,为避免机器物料遭日机轰炸,不得已遮盖轴心国之一意大利的国旗。但在采取此措施前,裕华公司均向国民政府申请备案,以免“通敌”物议。㉑
三、维持政商“和谐”,赞助地方市政
裕大华企业总部、工厂及经销市场,分布于国内诸多区域。无论是从事企业生产经营,还是从事各种社会参与,都绕不开与当权的政治势力打交道。期间裕大华领导人无法超越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立场上惯有的两面性,或周游于不同政治势力之间,或与当道者建立和保持合作关系。如大革命高潮时期,武汉革命力量一时势盛,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是徐荣廷的座上客,徐还慷慨解囊资助刘少奇活动经费15万元。㉒但当革命力量失势后,反动军阀夏斗寅邀苏汰馀游东湖,苏亦被迫应募捐款5000银元。待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随着政局趋于稳定,裕大华领导人则十分注意与相关地区当政者保持善意往来,及至建立比较亲近的私人感情。
根据裕大华企业档案等资料的不完全统计,30年代裕大华企业领导人过从较多的地方政要有:湖北省省主席张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鄂西“剿匪”司令徐源泉等;先后担任陕西省主席的杨虎城、邵力子等;四川省主席刘湘、四川财政厅厅长刘航琛、重庆市市长张必果等。对于一些地方中层官员,裕大华领导人同样注意联络感情。如武昌市政处处长李捷才刚刚上任,苏汰馀即致函“捷才仁兄处长”表示祝贺,称“闻报载欣悉荣膺新命,无任雀跃”,“用先肃函道贺,容再趋候台阶面倾积愫也”。㉓裕大华维持政商“和谐”关系,其重心在于求得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外部条件,这当中有一部分与当政者的直接合作活动,则涉及社会公益。配合支持和赞助地方市政建设,就是其中的一项。
裕华纱厂曾多次以厂中每日所出炭渣支持市区道路修筑。1935年9月28日,武昌市政处处长李捷才致函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祥泰营造厂承包武昌三层楼地段炭灰路返修工程,需用大量炭渣,商请将裕华纱厂所存炭渣分拨于祥泰营造厂,以利市政工程。裕华公司回信表示:“敝厂所出炭渣……本身需要尚多,本难分拨,惟念贵处所需关系路政,自应设法酌拨,以利工程”,并请市政处派人“与敝厂卓董事荣煜接洽”。㉔在此前后,又有湖北省建设厅以修筑武汉地区近郊公路商请裕华纱厂分拨煤渣,裕华再次回信,表示支持赞助。㉕期间,湖北省会工程处欲修筑沿江防水堤路,因经费缺乏无力修筑正式马路,也曾商请裕华纱厂将日出炭渣留存以供其暂时铺设煤屑路,裕华欣然允诺。㉖
大华纺织公司成立后,先后在西安市内发起并赞助修筑数条马路。1936年春,经大华纱厂及“有关各家”之“共同发起”,西安市政府开始修筑西安市长安车站外“坎坷不便往来”的童家巷马路,筑路经费由沿路各商家分担,而由大华纱厂负责筑路费的解缴,其中大华纱厂分担筑路费5000元,其余商家一起共分担3000元。1937年7月初该条马路修筑完成,除大华纱厂已交款外,其余商家尚未缴纳。西安市政府建设委员会致函大华纱厂将其余3000元“迅速拨缴”。㉗随后大华果然催促各商家缴款,“以便汇转”。㉘1937年6月大华公司又发起修筑长安车站到大华纱厂之间的马路。大华公司总经理石凤翔以事关国货竞争力,分别呈请南京政府铁道部和陇海铁路管理局批准修筑马路,并在信中说:“修筑费用如悉由国库支付,敝厂固欣幸无已”,倘难筹拨,“敝厂为营业前途情愿忍痛分成担任”。㉙
裕大华领导人在社会参与中无法克服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但他们热心社会公益的态度是一贯的。裕大华与地方政府合作,支持地方市政建设的善举,有的相当于举手之劳,可谓不以善小而不为;有的情愿“忍痛”分担经费,则与自身企业发展利益直接相关,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虽不能与大生公司、民生公司等推动一方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伟业相比,但也值得肯定。
四、反哺地方民众,参与灾荒救助
裕大华第一、第二代领导核心徐荣廷、苏汰馀和张松樵,作为集团创业史上的三位元老和武汉地区开拓民营现代棉纺织工业的实业家,他们身上看不到近代上海工商资本家的攀比排场与斗富争雄之习㉚,也不见近代汉口社会“日趋侈靡任奢华”㉛的娱乐消费之风。自公司创立后,作为企业高管,一方面,徐荣廷等人将个人财产专注于支持公司核心事业发展,彼此约定:“不投机,不进交易所,不借债”㉜,个人多余资金全部存入公司,并在实践中自愿而严格地奉行始终;另一方面,徐等也将个人精力专注于公司事业,在个人生活上长期保持十分简朴低调的作风。徐荣廷无声色犬马之好,亦无赌博、吸食鸦片等陋习。苏汰馀喜爱碑帖,业余以练字为乐;生活上“严谨朴素,力戒奢侈”,与夫人生活相敬如宾。㉝张松樵长期以厂为家,住厂办公,他终身不穿呢绒绸缎,着布衫、布鞋,不涉足妓院、舞厅、赌场,不置办汽车,不坐人力车,并严禁亲属乘坐,“常挥泪讲述童年行乞往事”,以教育子女。㉞生活工作上克勤克俭的几位企业家,在公司和个人经济能力发达后,均投身到了回馈桑梓和地方民众的慈善公益活动中。
徐荣廷年少失学,曾以贩鱼为生。后来经济发达后,他捐资在家乡武昌青菱乡石咀村建造了占地2200平方米的徐氏宗祠。徐氏宗祠设有小学1所,免费提供给乡间子弟就读,直到1966年徐氏宗祠作为四旧拆除后该小学停办。每年岁末,徐荣廷还对族人和邻里贫困户实施救济,如发给现洋10至50元不等。他又出资在家乡兴修沿江堤坝,以消除水患。㉟张松樵有感自己早年失学之苦,在故乡汉阳柏泉、巨龙岗等地捐出房屋数十栋,创办松荫小学多所,承担办学经费,助学优异学生。张松樵又资助汉口德和医院每年派医疗队到家乡柏泉进行1个月左右的诊疗活动,为乡民种痘诊病,施舍药品,防治疾疫。㊱他还在家乡置办田产,无偿提供贫困宗亲耕种;在家乡永昌河上筑造木桥,方便行人来往。㊲
1931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洪灾,徐荣廷、张松樵等迅速设法赈济家乡百姓,如张松樵用裕华拖轮带木驳运送馍馍回柏泉,沿村发放,使乡民无一人饿死。与此同时,裕华公司则在武昌区多处设点救济市民,如在裕华桥头等地设点施粥,发放面粉、大米、压缩饼干等;捐款长春观,委托长春观道人向武昌市民施以救济,等等。㊳期间,“省当局集绅商举办赈务”㊴,武汉工商界名流接受政府委任,参加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湖北分会,苏汰馀被任为该会委员之一,直接协助省政府赈灾。与此同时,省政府与武汉工商界联合发起组织了湖北省水灾急赈会、湖北省水灾救济会和湖北省水灾善后会等救灾组织,苏汰馀与武汉工商界名人贺衡夫、陈经畲等共同担任急赈委员会常委,在7月29日急赈会开始办公之际,苏汰馀与贺衡夫分别以个人名义从湖北省商会联合会和汉口市商会先行借垫6万元充作办公经费,徐荣廷则于当天直接由个人向急赈会垫付2万元。㊵在善后委员会,时为大兴公司董事长的周星堂在该委员会担任三常委之一,苏汰馀担任该会执行委员和保管股主任㊶,至1932年2月该委员会结束。㊷在此期间,年逾七旬已从公司一线领导岗位退职的徐荣廷,也不顾年迈,出任了湖北省赈灾组织中的外勤主任,直接参加赈灾活动。㊸
继1931年大水灾之后,1934年湖北又发生了水旱交乘的严重灾害。湖北工商界在此之际发起成立了湖北救灾备荒委员会,苏汰馀在其中担任审核组副主任。苏为审核组“从速组织起见”,从裕华公司抽调了颇为精干的一批人到审核组担任干事,义务为救灾工作服务,其中有张沛霖(营业部负责人)、汪胜瓈(会计)、孙瑞麟(会计,抗战后担任裕大华三公司总管理处主任秘书)、李玉之(会计)、刘金城、戴石声等。㊹他们助力救灾备荒委员会做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救灾工作。与此同时,苏汰馀还积极协助政府领导的救灾工作。当时湖北省政府邀集各方人士召开赈灾会议,会中一致推举川人苏汰馀“向川办米运汉接济民食”,苏汰馀接受了这一委任,电函本公司驻重庆和万县等销售分庄负责人,要他们“调查米价及斤秤,如能品拢汉价即行着手试办”。他又致函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称“弟旅汉廿馀年,不啻第二故乡”,向川省办谷米救济鄂省“义不容辞”,请其提供运输方便与优惠“以玉成其事”。㊺
与裕大华领导团队勤俭克己、洁身自好而专注事业的个人修为相联系,裕大华反哺地方社会的慈善公益活动,浸透着其领导人浓浓的乡土亲情与家国情怀。
五、裕大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与汉商精神
1930年代裕大华纺织集团在以武汉地区为总部实现跨区域扩张的过程中,广泛参与到了维护同业公共利益、拒绝外资渗透、支持地方市政建设、回馈桑梓和办理地方慈善赈灾等一系列社会活动中,为发展社会公共利益做出了积极贡献,裕大华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与其领导人汉商归属意识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毋庸讳言,与近代大生纺织公司、民生实业公司等相比,裕大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成就“相形见小”,但与大生公司的过早衰落相比,裕大华很大程度实现了企业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双赢”。裕大华自创办至抗战爆发前,曾实现了二次相对平稳的跨越式发展。第一次是在1920年代纱业危机时期,裕华公司和大兴公司逆流而上,以企业内部治理和管理革新的及时启动与有效实施为基础,创造了在华商纱厂中堪称一枝独秀的营业兴盛的奇迹,进而实现了对整个内地棉纺织企业及至诸多沿海棉纺织公司的“弯道超越”。㊻第二次即在1930年代纱业大危机的惊涛骇浪中,裕华、大兴两公司不仅以民族棉纺织企业中少有的“不借债”㊼的经营方式“稳渡难关”㊽,而且捷足先登投资创办了西北第一家机器棉纺织企业——大华纺织公司,由此实现稳步的跨区域扩张。前文所述1937年石家庄大兴纱厂在公司赢利中求售出卖,事实上是裕大华集团面对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危险而欲以金蝉脱壳之计主动进一步向西部转移的战略决策。裕大华与大生、民生等企业社会责任建树上存在的差异,很难从道德层面简单地做高下之评判,而更多反映了地域文化不同和企业家个体经历不同背景下,近代民族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生态的多样性。
1930年代裕大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表现,既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诸多共有的精神风貌,又折射出一批汉商工业资本家与企业家富有个性的精神风骨。
其一,胸怀大义爱国利民的本质特性。裕大华从创业之初到1930年代,从第一代领导人到第二代领导人,从单个领导人到其经营管理团队,从武昌人徐荣廷、四川人苏汰馀到汉阳人张松樵,他们因共同事业发展走到一起,彼此秉性相投,见识相合,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上,有着一脉相承急公好义勇于担当的作为,有着发展事业支持公益的共识。他们身上固然携带着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克服的政治软弱性,以及与各路当权集团勉力联结的历史局限性,也有着通过社会参与建立和扩大话语权以更好地维护自身企业利益的现实考虑,但这些并不能遮盖他们献身实业爱国利民、胸怀大义勇于担当的本质特性。他们领导参与维护本地区工商业者利权,为此不惜与当政权贵面对面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在国家民族危难之秋,能够为维护社会公义做到舍身忘我,也能够舍弃企业眼前盈利保持高贵的民族气节;他们回馈桑梓,投身地方社会慈善公益建设,始终如一。
其二,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性格风貌。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是裕大华践行社会责任中比较突出的特征之一。这一特征,首先折射出学界普遍关注的汉商“与众不同”的一个突出特性,即在武汉商界兴起和发达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汇聚天南海北八方人士形成的汉商群体,在其经商活动中,较少背负“内圣外王”、“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儒家思想包袱,也因此较少个人理想主义色彩。其次,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也是裕大华领导人基于生活阅历与经营企业的直接经验而形成的一种行事作风。与近代诸多民族大企业选择急速扩张道路并由此常常造成发展步伐跌宕起伏,甚至难以为继的状况不同,裕大华事业开拓者徐荣廷、苏汰馀、张松樵等在企业经营上始终坚持控制风险、稳健经营的作风,其企业发展因此长期保持平稳发展的态势。这种经验无疑影响着他们对公益事业稳健“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再次,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还反映了裕大华企业家将践行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管理内在组成部分的具有现代经济理性主义色彩的考量。他们在经营企业与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之间,较好地促成了企业经营与社会责任建设的平衡推进。
其三,善结同道开放包容合作的处世风范。徐荣廷、苏汰馀和张松樵等几位裕大华管理团队核心成员,来自不同的地域,因缘际会于武汉商场,开创共同的事业,打破了家族抱团创业、乡帮抱团经营的局限。共同的志趣,而不是血缘、乡缘等,成为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纽带;发展事业当先,而不是发展家族利益当先,成为他们团结始终及至平稳顺利完成领导人换代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至1930年代苏汰馀成为裕大华掌门人,在他领导企业投身社会公益的活动中,徐荣廷、张松樵无不与他保持认识和行动上的一致。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裕大华周围逐渐集聚起一大批来自五湖四海的“武汉商人”,其中不乏活跃于武汉商场的名流贤达,如作为裕大华企业大股东并担任董事、常任董事等职务的就有毛树堂(湖北咸宁人)、周星堂(浙江绍兴人)、贺衡夫(湖北汉阳人)、陈经畬(江苏南京人)等,他们本身既是武汉商场上的大商人,又都是富有社会正义感和影响力的大慈善家。将他们与徐荣廷、苏汰馀等凝聚在一起的,无疑不仅仅是关系他们个人切身利益的裕大华事业,还有相近的处世原则与信念。这一切都显示了近代武汉商场实实在在的开放包容能量,也见证了汉商已实实在在成为一个彼此认同的商人群体。
其四,与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生态结构相似,汉商无疑是一个既包含着某种内在统一性又包含着一定矛盾性的群体,不同汉商在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表现上因而必然存在层次差异性与历时而变的生长性。1930年代裕大华在社会参与活动中践行社会责任的表现,无疑彰显了裕大华汉商企业家融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共性”中的具有更多正向力量的独特个性:在他们爱国利民的责任风骨中,透着务实稳健审慎理性的性格风貌;在他们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个人修为中,透着轻享乐重事业、洁身律己、朴素内敛的精神气质;在他们突破家族乡帮,以事为先、携手同道、共襄义举的行止气派中,透着开放包容合作的处世风范。由此折射出的汉商文化风格,某种程度上既区别于传统“徽商”、“晋商”文化,又有别于同时代的“沪商”文化。而胸怀大义、勇于担当、务实理性、包容合作,无疑是既浸润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爱国利民本质特性,又具有丰富个性内涵的裕大华公益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核。汉商“重商轻儒”的地域文化特性与基于个体经验形成的务实稳健的性格作风,并未将裕大华企业家淹没在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缺乏远大理想的市民化庸俗化气息中,也并不妨碍他们在捍卫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和扶弱济困上勇于担当,及至做出舍身忘我的行动选择。与张謇、卢作孚等不以赚钱为目、“只有兼善没有独善”样式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理想抱负相比,裕大华汉商企业家塑造的是凸显较多经济理性因素的胸怀大义、兼济天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样式。
注释:
①向明亮:《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的公用事业——以近代武汉电力企业为例》,《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该文是笔者目前所见的唯一一篇主要从经济社会史角度专门讨论近代武汉地区民族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文章。
② 朱英、魏文享:《话说汉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王斌:《试论“汉”商文化的基本精神》,《武汉学刊》2006年第2期等。
③ 《苏汰馀致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函》,1933年9月28日,武汉市档案馆藏,109—1—61。
④ 罗萍:《官商关系与清末民初湖北纱布丝麻四局承租权的流转》,《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⑤ 《华商纱厂联合会湖北分会函》,1933年1月,武汉市档案馆藏,109—1—73。
⑥ 《苏汰馀致曾庆锡乞转中央函》,1933年1月8日,武汉市档案馆藏,109—1—268。
⑦ 黄师让:《裕大华企业四十年》,政协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页。
⑧⑪⑫⑭㉑ “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编辑组:《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106、106、298—302、310—312 页。
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及武汉市委员会等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0—261页。
⑩ 杨俊科、梁勇:《大兴纱厂史稿》,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⑬ 《大兴公司第12次股东会议事录》,1937年5月30日,武汉市档案馆藏,111—1—62。
⑮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征编室编:《大兴纱厂工人斗争史(1921—1949)》,《石家庄党史资料》1989年第10辑。
⑯⑲ 《周星堂致蒋铭三函》,1937年,武汉市档案馆藏,109—1—61。
⑰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长安行营第二厅批示》,1937年,武汉市档案馆藏,109—1—61。
⑱ 《华商纱厂联合会湖北省分会函》,1937年8月27日,武汉市档案馆藏,109—1—61。
⑳ 《大华公司董事会议案》,1937年9月8日,武汉市档案馆藏, 110—1—253。
㉒㉝㉞㉟㊱ 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武汉市文史资料文库·历史人物卷》第8卷,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第 16—17、59—69、70—76、16—17、70—76 页。
㉓ 《苏汰馀致李捷才函》,(年份不详) 6月8日,武汉市档案馆藏,109—1—61。
㉔ 《裕华纱厂致武昌市政处函》,1935年,武汉市档案馆藏,109—1—49。
㉕ 《裕华纱厂致湖北省建设厅函》,1935年,武汉市档案馆藏,109—1—49。
㉖ 《湖北省会工程处致裕华纱厂函》,1935年10月3日,武汉市档案馆藏,109—1—61。
㉗ 《石凤翔致西安市政府建设委员会函》,1936年7月7日,武汉市档案馆藏,110—1—21。
㉘ 《石凤翔致农民银行周福华仁兄函》,1936年7月15日,武汉市档案馆藏,110—1—21。
㉙ 《石凤翔致陇海铁路管理局函》,1937年6年16日,武汉市档案馆藏,110—1—21。
㉚ 朱英:《近代中国商业发展与消费习俗变迁》,《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㉛ 丘良任、潘超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第5卷,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 546页。
㉜ 武汉市第四棉纺织厂厂志编纂办公室编:《武汉市第四棉纺织厂厂志》,1984年铅印本,第15页。
㊲㊳ 肖传伟:《毕生致力于纺织事业的裕华纱厂厂长肖厚生》,武汉裕大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藏,手写本。
㊴ 赵焕章:《序》,湖北水灾善后委员会工务股编:《湖北水灾善后委员会工赈专刊》,1934年元月,武汉市档案馆藏。
㊵ 《本会成立大会纪录》,《湖北水灾日刊》,1931年7月28日;《急赈会已办公》 (“中央”),《武汉日报》1931年7月30日。
㊶ 《湖北省水灾善后委员会会议录》,湖北水灾善后委员会工务股编:《湖北水灾善后委员会工赈专刊》,1934年元月,武汉市档案馆藏。
㊷ 《苏汰馀致湖北水灾善后委员会函》,1932年2月20日,武汉市档案馆藏,109—1—49。
㊸ 武汉市档案馆藏水灾期间徐荣廷任职“外勤主任”照片。
㊹ 《苏汰馀致湖北省救灾备荒委员会函》,1934年,武汉市档案馆藏,109—1—49。
㊺ 《苏汰馀致卢作孚函》,(年份不详) 8月17日,武汉市档案馆藏,109—1—49。
㊻ 罗萍、黎见春:《20世纪20年代的动荡政局与民营企业险中求生的经营策略——以裕华、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兰州学刊》2010年第6期。
㊼ 此谓“不借债”,是指裕华、大兴基本不依靠外部借债经营和扩张,包括既不向国有银行、华商银行和华资钱庄,也不向外资银行借债。“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编辑组:《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页。
㊽ 《裕华公司营业报告书》,1934年7月,武汉市档案馆藏,108—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