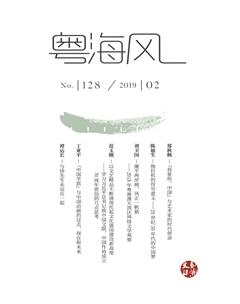一身“硬朗”,一生“风骨”
朱桦
2019年6月25日凌晨3点多接到徐中玉先生保姆的电话,告知徐先生走了,我再也无法入睡直到天亮,回忆着那些年在先生身边的日子,往事历历在目,感念不已。身在京城,一直惦念着我的恩师,每年去上海都会去看望先生。今年春暖花开时节去华东医院看望了先生,先生躺在病床上已不能表达,我摸着他的手用身体的感觉告诉他我来了,先生的手很温暖,虽然我们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在他的书房里聊天,但是依然感觉到慈父般的关爱。窗外的阳光照射在先生雕塑般的脸庞,依然是那么硬朗!目光、气息、心灵依然在感应和交流,通过温暖的手感受着先生的风骨与精神。
先生身子骨一直很硬朗,80多岁时走起路来健步如飞,精力充沛,我们几个弟子随他走路时是要追赶的,他始终在前面不知疲倦地在追赶着“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我研究生毕业后在校任教并担任徐先生的工作秘书近10年,有机会经常得到先生的教诲和指导,他常跟我聊起他在大学时代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各个时期的经历和往事,一生忧患,坎坷艰难,历经风雨,不屈不挠,在时代的激流中探索。先生儒雅率真,坚守良知,刚正不阿,处处“硬朗”!
忧患人生,在激流中探索
记得30多年前的一个晚上,当时我还在读先生的研究生,我来到先生家里,先生照常在读报,关注着当时的社会命运。我和先生一起坐到客厅的阳台上叙谈。那夜皓月当空,清风习习,先生抽着烟,坐在那张老藤椅上,月光雕刻着他那清瘦硬朗的脸庞,慈祥而坚毅的目光,在明月下更加闪亮有神。他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时而感慨地讲述着曾经的往事,时而鲜明地表达着对当下社会的看法。从先生忧患、思索的神情中,我感觉到了先生与民族、国家的脉搏一起跳动的内心,感受到了一位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深忧患与深沉思考。从先生对往事的回忆中我知道了什么是中国文人的良知与傲骨,从先生的议论思考中我明白了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精神。那时他早已年逾古稀,但仍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在人生的跑道上寻求新的起点,做着新的贡献。在他那饱经风霜的人生历程中没有过可以息足的终点。他珍惜生命,跟时间赛跑,抓紧分分秒秒,如果说生命在于运动,那么对他来说生命的意义则在“繁忙”之中。他忙得很有信心,很充实,也很有信念:“讲真话,办实事,尽其在我,别无他求。”[1]
曾几何时,“假、大、空”一度盛行,人们被一个荒唐而又罪恶的年代愚弄了,摧残了。他,一个灵魂不愿被扭曲而执意讲真话的人,自然是难以逃脱恶魔的纠缠。他出于良知,出于正义,讲了令那些人们不顺耳的真话,结果被批斗,被扣上了各种骇人听闻的帽子。然而,他并不屈服,他只相信真理,保持着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完整。他那坚贞不屈的样子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位当年的学生曾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回忆当时批斗会上的情景时说:“那是‘文革期间,你被造反派批斗,你‘不屈的态度惹怒了那些人,你被打了,打一下,你的头昂一下,越打头越昂。你不像其他有些被批斗的人那样害怕、认罪,而是高傲地抬起头。”在那黑白颠倒的岁月里,他凭着一副傲骨顽强地与不公正的命运抗争。尽管当时阴霾密布,但他还是深信阳光会重新照亮大地。最令他痛惜的是,写作的权利被剥夺了,大好时光被浪费了,他真不甘心!即使处于那种困境,他仍然坚持看书学习,在“牛棚”中尽可能地阅读大量的书籍。
他从没把文学看作是一种象牙塔中的“玩物”,而是十分注重文学与社会、时代的密切联系,把文学家的活动视为一种有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活动。这种责任感与使命感体现在文学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推进上。早在学生时期,他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为天津益世报主编《益世小品》周刊,为《东方杂志》《国闻周报》《光明》《七月》《自由中国》《文学导报》等报刊撰文。到重庆后,他便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唯一学生会员。在《抗战文艺》《抗到底》《全民抗战》《大公报》《国民公报》等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从中山大学研究院毕业后,曾北返母校山东大学任中文系副教授,后因参加进步活动并同情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而遭当局密令解聘。后在《文讯》《国文月刊》《观察》《时与文》《世纪谬论》《民主世界》《展望》等报刊撰文反对黑暗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与姚雪垠合编《报告》周刊,参加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大学教授联谊会”。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始终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他热忱地关注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社会变革,一方面,为改革所取得的成绩而欢悦,同时也为改革中所存在的问题而忧虑。他那为人的信条同样也是他做学问的信条。“求实,创新”是他治学的基本原则。在做学问上,他坚决反对那种一味追赶时髦,但求出语惊人而不顾实效的学风。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一直贯穿于他的治学生涯中。
做学问需要功夫,而且要有扎扎实实的硬功夫。1939年他从重庆中央大学毕业之后,又考进了当时迁在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研究院文学研究所,两年时间内专门攻读了宋代的诗歌理论著作。李笠、冯沅君、陆侃如等先生都担任过他的指导老师。在澄江城外荒山上斗母阁的油灯下,在粤北坪石祠堂式院舍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他孜孜不倦地抄下了上万张卡片,完成了30万字的一篇论文。他很重视搜集之功,也不辞抄撮之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治古文论,若没有丰富的资料,是难以进行深入研究的。40多年来,他摘抄的资料总共有两三千万字,若无运动干扰,还可以加倍。他也走过弯路,曾想从先秦古籍一路读下来,准备写一部文论发展史。费了很多精力,后来他感觉这样走不通。战线拉得太长,会有许多漏洞,反不如选定一些侧面,就某个时代、流派,甚至一家一书进行研究,这样可以周密、深入些。他认为,通史、总论一类大书,只有在大量专题研究成绩的基础上,利用集体创造的丰硕成果,才写得好。所以他把研究的目标逐渐缩小,集中在古代文艺家的创作经验上。
艰苦的学习,不倦的探索,使他在治学的道路上获取了累累硕果。在研究院學习时期,他专治宋代诗论,亦密切注视现实文学的发展,主张古今融会,中外贯通,先后于《中山大学学报》《新建设》《时代中国》《大公报》文艺版、《文坛》《收获》发表多篇论文;还分别于重庆和香港出版了专著《抗战中的文学》《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 《民族文学论文初集》《文艺学习论》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院系调整,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30多年来,历任中文系副主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尤其是他在备受不公正待遇的20多年间,仍孜孜治学,对国家民族抱有坚定信心。1978年重新担任教学领导工作以来,他全力以赴,在教学、行政、科研、社会活动等各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全国“大学语文”创始人之一,创办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主编《大学语文》教材近40年累计发行量达3000多万册。他被连续多年推选为国家教委全国高教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长、《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主编,连任两届上海市作协主席,获得第六届“上海市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探索创新,在融会中“求是”
高瞻远瞩的理论视野,古今贯通的治学方法,以及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使他在学术上又迈出了崭新而又坚实的步伐。
在他的治学道路上,始终竖着这样一个路标:“求是。”在他看来,积极、勤奋,甚至拼命一般的“求”的精神,将能保证一个学者总会做出一定的成绩。“是”的知识一旦被大家共同“求”了出来,普及开去,对民族、对全人类的进步发展,都有极大意义。“求是”并不容易,一辈子“求是”更不容易。他早已下定决心:“在专业研究的道路上,有生之年,还要继续‘求是下去。生命的意义,不正是可以不断地为一个有价值的目标而追求么?”[2]
对生活他有自己的信念,对艺术他有自己的感悟。他不仅思考艺术,更思考社会,思考时代,思考人类的命运。他总是紧随时代前进,他那敏锐的目光始终注视着现实社会的种种变革,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艺现象的种种变动。
比如,在有关创作与评论的各种探讨中,“当代意识”无疑是一个新鲜而又时髦的议题。评论家们更多的是从当代性上作笼统的肯定,对“当代意识”本身究竟为何物还缺少深入的探讨。针对探讨中存在的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和某些不科学的提法,他作了认真的思考和深入的探索,提出了自己的识见:“第一,并不是当代任何人的任何意识都可承认它就是‘当代意识。‘当代意识应该是指在当代科技发展、物质生产和人们生活方式迅速变革的背景下,人类相应产生的一种要求进一步革新、发展的思想意识;第二,在不同条件下生活的当代人,尽管人类发展的总趋势是基本一致的,但他们具有的‘当代意识的具体内容,在同一时期却并不总是一样的,而且即使有相同或很接近的东西,其表现形式也会有差异;第三,‘当代意识主要不应该是少数专家论证、思辨出来的,更不应该是个别人随心所欲想出来的,它主要随着科学、历史的发展,经过反复的实践,被证明确实有利于人类幸福的增进,文明的提高,既符合人们当前的利益,也符合人们未来的根本利益的意识。”[3]
当人们热衷于反思传统文化,甚至对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时,他却十分冷静而又清醒地指出;“现代意识不但并不总与文化传统对立,往往还是文化传统中合理部分的延伸和发展。现代意识并不只是一个限于现代时间的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有所发展、充实的观念。把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完全对立起来,把人为地割断与文化传统的联系当作一种有价值的现代意识来提倡,我认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徒劳的,有害无益的。”[4]
的确,他思索的领域是广阔的,凭着他那敏锐的思想触角,凭着他那几十年来严谨治学而形成的扎实的理论功底,他的见解是深邃的。他从不作脱离实际的“空论”和“玄谈”。即使谈论的是一些有关文艺发展宏观走向的问题,他也不作泛泛而论,而是紧密地结合着文艺现象的实际,很有针对性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无论是对人道主义问题,还是对主体性问题;无论是对新方法与旧方法问题,还是对文化“寻根”问题,等等,他都本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予以认真的思考和深入的探讨,力求做出符合实际的、科学性的回答。
他研究古代文论,但从未为治古而治古,而是力图把古代文艺思想同现实联系起来,做到“古为今用”。他多次指出目前研究文艺理论的同志还存在着各自据守小圈子,不大联系、不相融会的弱点。他说,搞文艺理论“知古不知今,知今不知古,知中不知外,知外不知中,没有必要的沟通,如何能逐步融会打成一片?如何能通过各种比较而易于认识、发现普遍的规律和各门艺术,以及民族的特点?如何能统一认识,扩大视野,加强联系,以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研究古代文论,老钻在古书堆里,尽管注释、考证、解说、争论都有其不可轻看的作用,若是忘记或疏忽了我们还应有更远大的建立新的自己的文艺理论的目的,得用这样的理论来协帮繁荣创作,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那恐怕不能说我们已尽到了应尽的职责”。[5]
既宽又严,在提携鼓励中育才
他,不仅是个学问家,而且也是个教育家。几十年的教坛生涯,使他更热爱阳光底下这崇高的职业。他爱才,惜才,对于每一位确有才学的人和有发展潜力的人,都予以充分的尊重和热忱的支持,特别是对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
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作家、批评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过他的指点和帮助。在培养学术人才上他从不论资排辈,而是唯贤是用。他常常破格选用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的富于创见而又扎实的理论批评文章在其主编的《文艺理论研究》上刊发或进行推荐,以鼓励学生“冒尖”成才,为他们的发展创造条件。每次他负责主持的文艺理论年会,总要让一些思想活跃的学生参加,让他们在会上畅所欲言,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习、锻炼,迅速成长。他常常是青年学者学术著作的第一读者,不仅为他们的书作序,而且在报刊上向更多的读者推荐和介绍青年学者的学术成果。他对青年学者的帮助是真诚的,充满着挚爱。这从他为当时一些青年评论家学术著作所做的“序”中就可以看到。他满怀热忱地赞扬与肯定了他们的探索精神,以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认真地指出了他们研究中的某些不足,并以平等的態度参与了他们的探讨。
他带研究生的方式是独特的。他是名教授,但从不以名教授的架势来“教”学生。在他的书房中气氛总是那样的平等、活跃、融洽,“教”与“学”之间一直是那样的宽松和谐。在课堂上唱主角的往往不是他,而是那些思想活跃的学生,他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时而为一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而他总那样认真倾听,有时像一个裁判,调整和维持一下争论的气氛和秩序,听到值得重视的地方,他就拿起笔记下来。他很尊重学生,对学生所提出的一些有新见解的观点,总是提醒和鼓励他们再作进一步的思考,以至形成文字。他也很宽容,一贯主张学术自由、百花齐放,尤其对自己的学生所持的不同学术观点,从不压制,而是让他们发表出来,在争鸣中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他主张给学生充分的自学与研究的时间,让学生在各种学术实践活动中得到锻炼。他在主编各类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专著时,总是留出些“空地”,让学生来耕耘。对于学生的劳作,他愿意花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并给予充分的指点和帮助。
他时时告诫学生不要死读书,要融会贯通,扩大理论视野,要博古通今,知中知外,将各方面的知识贯通起来。他要求“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尽量阅读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书籍,了解文化遗产的精华,为研究多提供一个理论参照,同样也要求“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学生尽可能地多读国外的和现当代的文艺理论著作,使对古代文论的学习和研究不局限于狭窄的圈子内。扎扎实实做学问,是徐中玉先生的一贯主张,尽管在具体的学习研究内容上他并没有太多地规范学生,然而,在治学作风上,他却对学生要求甚严。对于那些思考不深入且文风浮夸的文章,他总是予以中肯的批评。在治学上,他是深知“志当存高,入门须正”之理的。在引导学生上他更懂得“入门须正”的重要性。这种既“放”又“严”的教学方式无疑成为他培养人才的有效途径与教学特色。
践行信念,创造人生百年精彩
他老当益壮,在人生的运动场上跑出了更多的精彩,这可是一位跨世纪老人跑出的百岁精彩啊!真可谓“生命”在于“运动”。先生一生追赶时间,珍惜生命,坚持真理,刚正不阿,教书育人,务实创造,奉献社会,一身“硬朗”,一生“风骨”,他用精神与实践创造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精彩!
我每年从北京到上海都要去先生家里看望他,每次我们都会长聊,聊往事与当今。先生年迈却精力充沛,每天读书看报、剪报,写阅读评点,看国内外新闻和凤凰卫视节目,还与我谈论他的观感和思考,以及学校、学界等动态。先生忧国忧民,时刻关注国家大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在他的身上,從学生时代直到今天始终如一,对于时代的进步发展,他欢欣鼓舞,对于社会上的腐败不良,他直言批评,强调文学要与时俱进,增进文明,有新创造。最让我感动与敬佩的是,先生的坚守与坚持。他坚守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良知和独立人格,他坚持的是一生不变、全力实践的人生信念。爱国、忧患、责任、精进,是他人生的品格元素与体现。先生中正玉德,高风崚节,始终怀爱国之情,存忧患之心,尤其强调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并付诸实践。他对时代发展与社会命运的关切、对使命与责任的坚持、对教书育人的不断精进,无私奉献,充分体现出一位纯粹而高尚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他的“生命在于运动”实际是对思想的创造和精神的追求,是对“讲真话,办实事,尽其在我,别无他求”信念的不断实践。我曾担任他的工作秘书近10年,先生做事总是言行一致、以身作则、雷厉风行、求真务实,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大家风范。在百岁华诞之际,先生捐资100万元建立“徐中玉教育基金”,支持教育与学术发展,帮助贫困学生,大爱善举,功德无量。
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 仁、义、智、勇、洁,先生如玉!
(作者单位:自由撰稿人)
注释
[1] 华东师大学报88(5)封二,《徐中玉教授与文艺理论研究》。
[2] 《书林》82(3),《我怎么会搞起文艺理论研究来的》。
[3] 《当代文艺思潮》87(4),《关于“当代意识”的思考》。
[4] 《上海文论》87(2),《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
[5] 《文艺理论研究》8l(4),《略谈当前古代文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