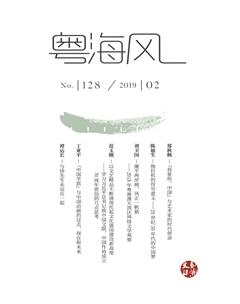当“第五代”遇上“后新时期”
刘晓希
重提夏钢,无疑是因为2017年3月份的中国电影市场中再次出现了他的身影,而如果说当年3月份的国产电影有哪些大事件发生,第五代导演夏钢携电影《夜色撩人》亮相全国肯定是其中之一。和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一样,夏钢是北京电影学院科班出身的中国第五代导演。诚如学者饶曙光所言,新时期电影思潮在“选择与接受”中与文学思潮交互演绎,带有民族忧患意识的第五代导演以《黄土地》《红高粱》《孩子王》等寻根电影切入民族根性和文化传统深处。而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第五代导演的创作主题发生了部分位移,但这一时期的第五代电影仍然大多脱胎于经典的小说文本。然而,与上述列举存在着明显不同,第五代导演夏钢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同样迷恋空前繁荣的文学成就并专注于人物内心尤其是女性复杂的内心世界,但是夏钢电影的时空语境则无一例外地与当下社会的城市生活相对接,与夏钢相类似的第五代电影人,还有孙周、叶大鹰等,他们更是将镜头对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州。
一
当夏钢、孙周、叶大鹰开始自己导演生涯的时候,正值世界格局已发生了战后最为巨大的结构性震荡与转换。“冷战”后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变使世界的未来尚未明晰,旧话语的溃解与新话语的建扬都尚在混蒙中呈现出它暧昧迷离的形象。而中国大陆则在走向市场化的进程中迎来了一个经历巨大文化转型的新时代。我们可以将这个新的时代表述为“后新时期”。后新时期的文学自文化寻根小说渐渐归于沉寂后,逐渐呈现出一种市民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取材的凡俗、叙事的平实、语言的生活化。总体来说,这些市民化的小说在艺术上体现了直面现实、反崇高、朴实叙事等美学风格。学者张颐武指出,后新时期“指的是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由大众传媒支配的,多元文化话语构成的,富于实用精神的新的文化时代。它既是一个时间上分期的概念,又是一个文化阐释的代码,它显然与国际性的后现代性潮流有对话性的关联。”[1] 正是从那时候起,一种绝对理想、纯粹的文学、艺术已悄然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则是被无情岁月无数打磨、蹉跎后的沧桑生命体验。这应该算作是文化历程中的一次前进与发展,是随着时光潜移默化成的新阶段。王朔文学便为此时期的代表。
夏钢、叶大鹰刚一出道便与王朔打上了交道,这是一场“第五代”和“后新时期”之间的相遇,迟来却惊艳(夏钢早期拍摄了王朔电影《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叶大鹰的处女作《大喘气》改编自王朔小说《橡皮人》)。1988年,王朔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被夏钢搬上了银幕。如果怀着对第五代的期待来期待这部电影,它显然是出乎意料的。无论是皮条客和英语专业女大学生的人物形象还是为爱而死和卖淫诈騙的故事情节,无论是炽热如火的情欲还是清冷似海的悔悟,都使摸爬滚打在黄土地和旧社会的第五代印象焕然一新。然而作为“王朔年”上映的四部王朔电影之一,《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则又明显不同于《顽主》《大喘气》和《轮回》的叙事风格。由于王朔小说鲜有抒情而颇具插科打诨式的对话,所以王朔电影便很难以电影独有的镜头语言来呈现小说里面戏谑却仍带辛酸的复杂美感,但是,在电影《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当中,一段段激情戏过后则会配上一段段安安静静的内心独白,以孤独、忧伤的文艺气质揭示出张明一样的“痞子”青年在面对腻味却无力自拔的生活时所流露出的羸弱和迷茫。而在《大喘气》一片里,摩托车、彩色电视机、歌舞厅、港台流行音乐等媒介符合的轮番登场,则极具诱惑力地为我们展示着改革开放之初南国景观的扑朔迷离,当然,晃动粗暴的镜头也折射出商业巨浪翻滚着的广州所意味着的生机勃勃,同时也是躁动不安。
夏钢与王朔的二度合作,是在1993年,那年,夏钢执导了电影《无人喝彩》,而《无人喝彩》对于王朔来说也是唯一一部先成型以剧本后又改写为小说的作品。电影以学生莫扎特的音乐开始,以师长海顿的音乐结束,暗示着对文化艺术传承的崇敬和尊重。同时,影片看似讲述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但实际上却表达了当时整个社会对艺术工作者的忽视,然而,“无人喝彩”不单指艺术家肖克平的不被看好,也指知识分子丈夫李缅宁的不被看好,更是指钱康一类商人的不被看好。在那样一个与消解一切的西方后现代遥相呼应的中国后新时期,夏钢正是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方式转述着现实社会对精英知识分子的态度,同时又深深质疑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大潮对既有文化样态的冲击。所以,如果说后新时期的文学或艺术是反崇高的、媚俗的或者亲大众的,那么,在夏钢的作品里则也同时映照出中国第五代导演所普遍具有的反思精神和忧患意识,当然,还有第五代导演对艺术表现形式的执念。和《无人喝彩》在主题上存在着相似性,孙周的《心香》在京京和姥爷(都是北京人)于广州生活的失落孤独感和传统文化京剧形式的式微之间形成互文式书写,而在孙周的另一部电影《给咖啡加点糖》中,空间背景仍为不乏时髦前卫的广州都市,但在不经意间,两部影片同时出现了大量京剧脸谱和唱词,当然,以京剧为象征的传统文化同时都遭遇了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冲击。
当第五代遇上后新时期,这种交手还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两部夏钢电影里。和夏钢联袂王朔相像,“冯小刚+郑晓龙”的编剧模式分别出现在《遭遇激情》和《大撒把》的创作当中,这样的结合,显然迥异于夏钢之外的第五代导演,尤其是如今当我们重提冯小刚和郑晓龙二人,前者无愧为商业电影成功的典范,后者则因为近年来的《甄嬛传》等电视剧的热播而名声大噪,当然,这种从出道开始便极具市场和观众意识的电影叙事策略无疑帮助他避免了那些年第五代导演频繁出现零拷贝的尴尬。在中国电影市场面临巨大转型的艰难时刻,《大撒把》的出现不仅在票房上胜过了众多合拍片,更因为摘夺当年的金鸡奖最佳导演奖而证明了其在艺术上的成功,而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日后被誉为中国最杰出的艺术电影导演之一——霍建起的加盟。正是霍建起一贯唯美含蓄的艺术质感才为夏钢的城市电影平添几分穿插在钢筋水泥之间的深情,从而令我们看到经济社会下冷冰冰的城市话语中所流露出的些许平缓和温馨。此外,导演了广州城市题材电影《大喘气》的叶大鹰也在几年后承担了冯小刚处女电影《永失我爱》的编剧。此后,不少学者都关注到冯小刚电影/贺岁片正是以“市民话语”完成了艺术和市场间的协调沟通,从而无限肯定了冯小刚之于中国电影的意义,然而,人们也许忽略了在冯小刚之前,夏钢、叶大鹰等第五代电影人为之所做的铺垫。事实上,当我们重提夏钢、叶大鹰的电影,我们则会非常轻易地看到夏钢电影(北京故事),以及叶大鹰电影(广州故事)的“深情喜剧”和以后的“冯氏幽默”之间的关联;我们也会想起《不见不散》《大撒把》《无人喝彩》《心香》,甚至包括胡柄榴那些以广州为背景的电影在主题上的呼应;而如果再对比夏钢、叶大鹰和冯小刚电影的创作队伍,便会发现更多相同的面孔。如果说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更多地将目光锁定在国外的各种奖项,那么夏钢、孙周、叶大鹰则在中国电影势必走向市场的改革时刻,显得比他的同代人清醒得多,毕竟,后新时期的中国电影发展对市场和奖杯拥有着相同的渴望。
二
如今,当我们翻开任何一份电影资料,其中鲜见对第五代导演夏钢、叶大鹰或者孙周的独立篇章,然而,无论是他们电影的后新时期特质,还是多年来他们对城市电影的情有独钟,都使得他们在第五代导演中独树一帜。对比我们所熟知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在新世纪执导了商业影片《英雄》 《十面埋伏》 ;陈凯歌也紧跟其后,凭借《无极》《赵氏孤儿》踏上了古装大片之路;田壮壮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的《蓝风筝》遭禁十年,此后便回母校以执教为主业……当第五代导演纷纷转型,连同时期的黄建新都以制片身份出现在当下电影圈,而冯小刚也禁不住诱惑拍摄了《夜宴》,但夏钢,以及孙周的电影却仍然聚焦城市人的生活,不改初衷,但又带有浓郁的艺术情结。然而,在夏钢多年的城市电影拍摄中,其风格面向则又是多变多元的。在他导演的电影里,既有对时下现象的关注,如《大撒把》,也有对城市文化终极的思考,如《无人喝彩》,还有对女性内心世界的关怀,如2017年上映的《夜色撩人》。
影片改编自须一瓜小说《淡绿色的月亮》,所谓“夜色撩人”,当然是指一次发生在深夜的抢劫事件在以后的日子里反复扰乱芥子的心意,但面对选择,女性总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她的需求不是对与错,而是本能的反应。早在1994年,夏钢就拍摄了类似主题的《与往事干杯》,此片在当年葡萄牙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国际电影联合会评委会特别荣誉奖。我们看到,《夜色撩人》中芥子的勇敢、正义使她眼睁睁地目送谢高的离开;《与往事干杯》中蒙蒙难忘昨日的情愫而永远地失去了恋人老巴。可以说,在这两部影片里面,都是女人的执念酿成了最后的悲剧,而夏钢所做的,无非是真实地呈现出女性这样一种细腻纠结的情绪,但同时又丢给我们一个难以言说的伦理困境:理想是否总是通往幸福。无论是《夜色撩人》还是《与往事干杯》,无论其讲述的方式是转喻还是独白,这种极具个人化的电影叙事本身终将难掩其中浓郁的艺术气息。当然,这样的艺术坚持也同样体现在了孙周和叶大鹰的几部城市电影创作当中。
导演孙周本人生活在当时已是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心香》之前,孙周在1987年就曾经拍摄《给咖啡加点糖》,这部影片当中,孙周个人一贯的观察者姿态就已经明显表现出来。1992年,孙周导演的电影《心香》上映。在影片中,著名话剧演员朱旭扮演的老年外公和著名女演员王玉梅扮演的莲姑形象,给观众留下难忘的印象。这也是新时期以来,传统文化的代表形象第一次以正面的样态出现在中国的电影银幕上。这部电影的问世,不啻预示着中国电影人乃至整个文化界开始将目光重新聚焦于传统文化的趋向,同时也与中国社会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日益迈向现代化的現实形成鲜明对照。透过电影《心香》现象,人们看到了中国电影走向的微妙变化,即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及在对待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问题上,电影界开始从20世纪80年代激烈批评传统文化的立场上退却,取而代之的是对传统文化流露出明显的回归趋势。尽管《心香》仅仅是一个开端,但是这种态势随后却不断蔓延,以至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系统成为此后中国诸多电影的叙事动力之源。因此,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心香》具有十分重要的史学价值。无论是该片所采用的风格化镜语,还是所表现的中国人之生存境遇,均体现着中国电影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观念的重新思考。
由叶大鹰导演的《橡皮人》,其背景是广州和汕头,男主角丁健是一名黑市买卖生意的老手,可是在跟香港客进行一宗电视机交易时,却碰到了真正的黑道人物老林对。丁健为了保命,宁愿向从街头驶过的警车自首。从警察局出来后,丁健去酒吧买醉,同样是做黑市生意的李白玲把他带回家,并对他表露爱意。但丁健发现她的皮肤就像画皮一样从肩头纹痕四散,最后竟变成了一个橡皮人,而自己的皮肤也跟着发生了变化。在黑市买卖风气初起的20世纪80年代,《橡皮人》的影像内容颇符合时代气息,而与内容相匹配的影像形式又极具艺术实验色彩:俯拍镜头下,冷凝光的折射与音乐的氤氲共同营造出商业大潮下城市的陌生与光怪陆离;固定镜头里,李白玲和丁健的情爱镜头除了浮华,更显缕缕缓慢温情。这种呈现,在那几年全国电影界尽现商业片的大环境下实属不易。
在2017年的新闻发布会上,据夏钢介绍,拍摄《夜色撩人》的想法其实已经酝酿很久,而影片选择在2017年上映,则是出于夏钢对当前中国电影市场的分析,“电影市场经历了大起大落式的发展,之前是不健康的,里面肯定有很多泡沫。现在我觉得电影市场在慢慢回归理性,观众都是有自己的艺术品位的,他们的审美要求电影不能只有‘大片,更重要的是还要有能打动人心的地方。”[2] 这样一个所谓电影的黄金时代,显然得益于观众素质的提高,而这样一个时代也必然会对电影市场有新的要求,在夏钢看来,随着市场的成熟,电影一定会由观众来主导选择,中国电影也一定将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些影片将有文艺片的情怀,也有类型化的选择。导演夏钢则将之定义为“新文艺电影”时代的到来。
这里,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当第五代遇上后新时期,夏钢、孙周,以及叶大鹰等导演因为准确地把握了艺术与商业的关系,从而令中国电影在特定时间段里得以摆脱零票房或者差口碑的尴尬处境,而由于“城市”本身的商业气质,北京、上海、广州等都市景观无疑成了他们聚焦的对象。虽然历史总是不可避免地经历着属于它自身的兴盛和衰落,电影历史,尤其是后新时期的城市电影形态,当然也包括以广州为背景的电影故事,也同样有过属于它的辉煌和冷清。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正视夏钢、孙周、叶大鹰,以及和他们同时代的电影人行走在商业和文艺之间的电影行为的意义,也应该看到“城市”之于电影叙事的存在意义,以及多种可能,更应该看到“广州”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电影转型时期所起到的城市媒介符号作用。
多年前,这些电影人在中国电影的艰难时刻让我们看到了市场的存在,让已经灰心了的电影人重新振奋精神;而如今,他们提出的“新文艺电影”无疑是对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再次诠释。如果说,“新文艺电影”的讨论应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电影人的行动自觉,而广州在那段特殊时期的媒介文化意义也理应得到承认,那么,以如今的广州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地位来重估其未来的发展,甚至以对广州的城市书写来思考电影商业属性与艺术特质的相关命题,无疑都将是一个很好的切入,事实上,以广东为空间叙事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和艺术电影《路过未来》《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已经给我们做出了相当层面的阐释。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注释
[1] 张颐武:《后新时期文化:挑战与机遇》,《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第112—114页。
[2] 《〈夜色撩人〉全国热映 夏钢回应口碑》,参见网址:https://cn.club.vmall.com/thread-12284110-1-1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