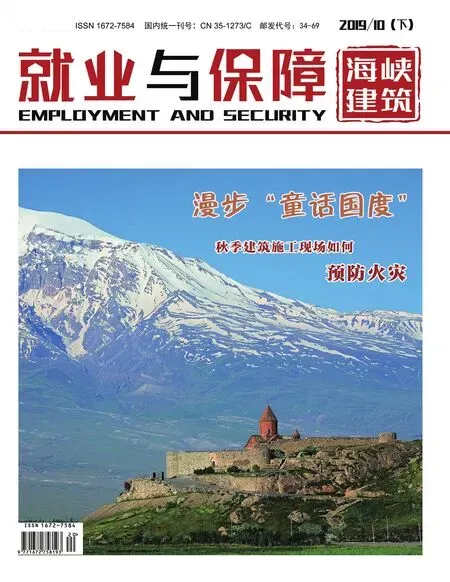花生的记忆
曾耀文
乡下的亲戚送我一袋熟花生,我迫不及待地随手剥开一颗扔进嘴里,年龄大了牙齿不大好,慢慢地咀嚼,磨成粉末咽下,一股熟悉的清香散发在唇齿之间,记忆的闸门顿时打开,仿佛回到童年在田间地头拔花生、摘花生的年代。
花生,闽南一带叫“土豆”,也正如它的俗名一样,果实外壳呈土黄色,粗糙凹凸不平,长在土地里。一说到“上开花下结果,大人小孩爱吃死” ,大家都知道是“土豆”了。家乡的土地贫瘠,只能栽种耐旱抗旱的地瓜、花生等农作物,栽种的农作物自产自销。地瓜是三餐的主食,花生当配菜、当零食都可以,百吃不厌,榨出的花生油也是一年四季炒菜的主角。当年物质匮乏,一年难得吃几回猪肉,还好自留地里种点花生,成熟后晒干到加工厂榨花生油,滋润一下缺营养正在长身体的我和弟妺们。一到花生收成季节,榨油厂排队榨花生油的人排成长龙,那个花生油的清香呀,飘荡在乡村的空中,沁人心脾,令人陶醉!
小时候,记得快过年了,母亲开始准备来年的花生种子。煤油灯下,母亲搬瓦缸,把花生倒在箩筐里,然后一人一筛子的花生,剥完才能睡觉。剥了一会儿我便开始打瞌睡了,手也酸痛。但母亲就是办法多,她在要当种子的花生中,掺杂少许的熟花生,从外表看不出来生的、熟的花生,我无意中剥开一颗熟花生时,甚是兴奋,瞌睡虫也跑了,赶忙放进嘴里。母亲就是用这种巧妙的办法来鼓励我们剥花生种子的积极性。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正是种花生的季节。湿润的一垄垄田地,农民们背着竹篓,一手拿着瓦刀,挖开三五厘米深的土,另一手放进二三颗花生仁种子,覆盖好土壤,就种好了。花生苗开花前,要做好除草,施一些草灰的肥料。
大概七月份的时候,地里的花生便可以采摘了,这是农民最辛苦的日子。火辣的太阳酷晒大地,炽热的阳光炙烤着花生园地。我们一家人全出动,大清早就来到地里拔花生。早晨凉快一些,又有露水,这样花生连着根一起拔起,不易断。
炎热的天气里,大人们聚在树阴底下来择花生。母亲动作敏捷,左手抓起花生藤的茎根部,右手一拧就掉下十颗八颗花生,三下五去二一株花生就摘完了。我的手掌小,拧一下只能择下三五颗。择好的花生,有的晒石埕上,有的晒屋顶上,有的洗干净放到大锅里,用盐水煮熟。到了这个时候,特别要留心天气的变化,稍有乌云,就要赶紧收起来,免得被大雨淋湿了,一年的辛苦就付之东流了。记得有一次,晒花生时下大雨了,我一边收花生,一边剥着熟花生吃,母亲看见了,大骂:“馋猫,大水淹上来了,还在吃?”
母亲煮的熟花生特别好吃,有的送国内亲朋好友,有的送海外亲戚,他们都称赞好吃,过后指定要母亲亲手煮的熟花生,说我们家的熟花生特别酥、脆、香,越吃越想吃,存放了一年多,质地依然不变,酥脆香兼备,和别人家的就是不一样。我曾经问母亲,她做熟花生有什么秘诀?母亲说,其实也没什么秘诀,就是花生煮熟了,要在太阳底下暴晒,而且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暴晒,要晒足晒够。再者,收藏也很讲究,要一层一层包扎,层层密封放进瓦缸贮藏。不能跑进去一点湿气。
啊!伴随我走过童年时光的花生,那香甜的味道深深地烙印在脑海深处,一想起,满满的记忆便如花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