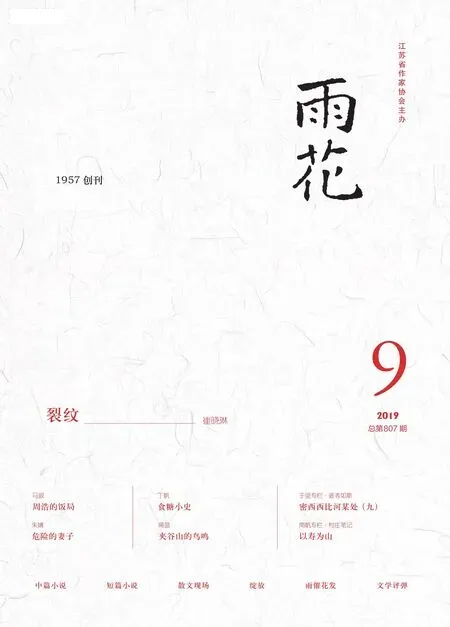密西西比河某处(九)
于 坚
四月底,温暖和光明就要回到明德堡,枯枝败叶正在山冈上缓缓地复活,乌鸦在灰色的云层上叫唤,啄木鸟开始干活,学生们穿着运动鞋,背着旅行包在校园里急匆匆地走着。与世隔绝的小镇,有几家商店(卖艺术品)和馆子,教堂雪亮,站在几条道路的核心处。一个青年坐在台阶上靠着睡袋朝我招手,要我给他钱,他刚醒。桥下有一条激动的河,忽然出现了断崖,地层像眼眶裂开,突然涌出瀑布,气势雄伟、舒朗。一位父亲牵着他的小孩在桥上走着,那孩子举着一截树枝。小镇就在瀑布旁,日夜轰响着。去哪条路留下第一行脚印?我决定走瀑布旁边那条街,经过了一些树,一些19世纪留下来的老房子。一家馆子的大厨在锅子上舞着铲子翻开煎土豆的另一面。一道泛油的微光。此地的人都在等待春天,还有两周或者三周它就要来了。老穆的办公楼前面有一棵垂地的老樱花树,花骨朵已经有拇指头大,花朵就要挺身而出,已经在黑暗里唱着歌了。弗蒙特州的冬天可真长,要持续半年。人们年复一年地盼着春天再次光临,其他都是灰蒙蒙的小事,只有春天激动人心、值得期待。大地越来越明亮,学生老师都注意到土地上那些非同寻常的迹象,他们走着走着就停下来,察看一簇新芽或者一树花骨朵,摸摸叶子,讨论它们会在第几日绽放。有些藏在屋子后面的冰还没有化掉,脏掉了。明德学院位于低缓的山坡和洼地之间,核心也是一座教堂,雪白耀眼。东亚系不过十几个学生,四五位老师,大多数是从中国来的。系里正为系领导的接班问题发愁,原定的接班人、一位从中国来的教授马上就要调到大城市去了。他们费尽心思引进,本来以为他会在这里呆下去,这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风景如画的山谷、海量的书、漫长的夜和冬天、无人打搅的白昼、营养丰富而烹调拙劣的食物——这种禁欲风格令人断绝了寻欢作乐的念头。“在黑暗时代的动乱期间,少数坚定地献身宗教的基督徒,离开社会到荒凉而让人生畏的文明边缘地带过着隐士生活。隐士的行为唤起更多陈腐的教士去发誓约守贫穷和奉献,重新聆听耶稣基督的教诲。这种教士组成一个新的同质信徒团体,称为修道院。”(百度)差不多就是这种东西。老穆说:“可以理解,人都是向往机会更多的地方”。他也快退休了,将来谁还教中国当代文学?这个世界都在玩手机,这种方块字写出来的文学还值得教吗?老穆让他的学生先读读我的诗,然后和我一起朗诵,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都愿意。开始的时候,穆老师先点名。我读汉语,学生们读英语。老穆让这些“贵族”排成一队站在我旁边,读过的人就走到我的另一侧。他们是非裔、华裔、印度人、意大利人、印第安人、玛雅人、白人……都是些小伙子和大姑娘。我写下的那些汉语现在变成了各种口音,就像从一座森林里发出。在拼音语言里,听是第一位的。汉字却是看的,许多字听不出来,一定要看。字形而不是声音决定字的区别。这种朗诵会就像是在一个村庄里游戏。世界的遥远之地、外省永远有一种村庄风格。麦克风出了点问题,这个家伙总是捣蛋,似乎讨厌这个世界的口臭。朗诵后讨论,我觉得学生们很害羞,放松了警惕,但他们忽然问出几个问题,令我措手不及。“你怎么看待诗和读者的关系?”“一首诗是怎么出现的?”
老穆的学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一位教授家里聚餐、聊天。聚餐的钱由学校提供。那位教授是希腊来的,因为我的来访,安排了一次聚餐。教授家就在学校里,从教室走过去几分钟,经过几棵树就是。他的家就像一个博物馆,排着队的书籍、躺在地毯上的画册、铜版画……餐厅里有两张长桌,自助餐,鸡腿、面包、奶油汤、沙拉……味道比学校食堂的好多了。大家边吃边讨论,仿佛是坐在苏格拉底的长廊上。时间过去一半,穆老师就要同学换换桌子,另一批围着我继续讨论。几千年过去了,讨论的话题在我听上去,不外还是这些:
苏格拉底:“对爱情的快乐呢?哲学家在意吗?”
西米:“决不在意。”
“好,还有其他种种为自己一身的享用,比如购买华丽的衣服呀,鞋呀,首饰呀等等,你认为一个哲学家会很在意吗?除了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他不但漫不在意,而且是瞧不起的。你说呢?”
西米回答说:“照我看,真正的哲学家瞧不起这些东西。”
“那么,你是不是认为哲学家不愿把自己贡献给肉体,而尽可能躲开肉体,只关心自己的灵魂。”
“是的。”
《苏格拉底对话录——关于灵魂与肉体》
西方文明从问为什么(why)开始,追求确定、是、THE。中国文明从“学而”开始。学而,意味着“确定”不是人的事,是道的事。道法自然,学就是了,没有为什么。仁者人也,仁就是亲近、相爱。爱并非非此即彼,而是“博爱之谓仁”(韩愈)。爱一切,就是一种不确定。“人是不确定的动物”“不断说谎的、艺术的、不透明的动物”“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曲折地接近自己的目标,一切笔直都是骗人的,所有真理都是弯曲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圆圈。”(尼采)道法自然,自然才是确定性,学就可以了。道法自然这种思路令汉语成为一种“不确定”的语言。曲径通幽才是抵达确定的小路。
强大的确定性,不仅意味着你不能搞错单数、复数、主格、宾格、时态、语态、情态、进行时态、被动语态……更意味着走路的时候你不能忽视任何一个路标,想当然地跟着感觉随便走。有时候我依照童年经验,走路看地形、风水、喜好,结果每次都走不通,而且危险。有些巨大的空地,看上去是荒原,刚刚往里面走了几步,狗就凶猛地吼起来,并且闪电般地向你发起冲锋。看菜谱也一样,“随便”很危险,必然点到你根本吃不下去的。很少有那种和稀泥、“差不多吧”的食物。你确定吗?要想清楚。印度菜、墨西哥菜比较亲切,基本的口感可以接受,虽然不知道在吃什么。西方的菜谱清清楚楚。鱼,什么鱼,哪儿的鱼,怎么做,没看清楚的话,往往误入歧途。是的,鱼,但只是鱼的肚子部分,根本不够吃。猪肉,是的,但端上来的是一只巨大的肘子,堆积如山。
一个学生开车带着我在学校里漫游,这个学校可谓无边无际,校友赠送了大量的土地。荒原、玉米地、麦田、山丘、森林、湖泊,落日、乌鸦、枫树、正在打洞的旱獭……与乡村的土地混在一起。美国人还在大地上玩着。19世纪砍伐的森林又长出来了。大地真是好心,“开发”被梭罗在瓦尔登湖棒喝之后,美国人重新尊重自然,有的地方尊重到做作,一切都原封不动。一路上经常见到死去的仓库、死去的汽车、死去的房子……许多死掉的事物都像根那样被留在原地,人们搬走了,上路了。谷仓、学校、社区、老屋就留在原地,任它生锈、腐烂、消失。
路过一家废弃的修车坊,不仅钻床、工作台被留下,窗子和门都没有关上。工具、家具、桌布、扳手、电筒、打火机、盘子、瓶瓶罐罐、硬成了石头的面包,某人读过的小书摊开在窗口……一切都留在原处,似乎忽然接到一个命令,即刻放下一切,走掉了。
一只野鹿躺在公路边,被汽车撞翻了,正在风干中。
有一家住在湖边,家长80岁的时候决定举家搬到加利福利亚去。在网上登出广告,剩下的东西于4月5日的上午8点到下午3点卖掉。路边停着一长溜车子,都是来买的。没有标价的统统一美元。旧铲子、旧水靴、旧毯子、灯座、勺子、磁带、锤子、马桶刷……都有人买。不在于好看,无关面子,只要还能用。
搬家是一个很容易的决定。
在路边发现一所“一间房学校”。一间插着美国国旗的白色房子。早年,交通不发达的时候,偏远地区的孩子就在这种学校就近读书。老师上完课就走,开着车去另一间房子。门没有锁,锁扣锈迹斑斑。房间大约二十平米,课桌原封未动,墙上的地图都是上个世纪的,钟、粉笔、擦头、铸铁的炉子都摆在原处,桌子上还有些老课本,似乎学生们只是下课出去玩了。学校孤零零地矗立在玉米地和公路之间。那些来自远方的、永恒的、在公路上一闪而过的汽车轮子不知道给过学生们什么样的教育?在这间教室里毕业的人都已经死了。谁还在上课?在那些月光明亮的良夜。
老穆家在弗洛伊德故居西边的另一处林子里。有一天晚上,一头熊靠近了老穆的房子,转一圈,又走了。老穆隔着玻璃窗拍了一张照片。那头熊相当原始,低头站在昏暗的灯光里。他家比弗罗斯特的住处豪华多了,明亮、洁净、典雅,挂着许多好画,排列着许多书。弗罗斯特并不穷,他的隐居处有三四个。老穆这所房子是他唯一的,他想在这里终老。周围是森林,他们两口子会坐在林边。他妻子芮贝卡是个画家,画室在另一栋房子里。她画得相当好,纽约的一家画廊正在举办她的画展。她属于美国画得最好的那些画家之列。她说她在画某种大海深处的东西,我以为她在画黑暗。每一笔都是细节,无数的细节混成了一种深邃的混沌。她的画曾经好卖,但是进入晚年,画得更深厚的时候,却越来越卖不出去了。美国喜欢时尚,人们只注意天才崛起的那一刻,“每个人都能成名一刻钟”(安迪·沃霍尔)。无所谓,她继续画着。那间画室像个车间,堆积着完成的作品,随便翻开一幅,很美。
房子前面是林中空地,摆着两把躺椅。他们有时坐在那里看着森林,落日,黑暗和星空,逗狗玩。林子里总是有什么在里面做着什么事。有时候住户会走出来,棕熊、野鹿,老鹰、乌鸦、苍鹭,几只蝴蝶……
铅灰色的天空,下面是玉米地。玉米地之间切出一条覆满灰尘的道路,踩上去,灰就吞没了鞋面。一群野火鸡慌慌张张地跑过去,吊着自己的肉飞起来。看上去,这条路修通后就一直摆在那里。天边开过来一辆卡车,冒着烟,驾驶舱里坐着一个胖子。
想起尤金·奥尼尔《天边外》,我读到他的剧本的时候,大约三十岁。“我知道你不相信別人说我‘悲观。’我是说,你可以透过我作品的表象,看到真实的情况。我绝对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在我看来,人生一片混乱,讽刺而绝伦、冷漠而美丽、苦痛而精彩,人生的悲剧赋予人伟大的意义。如果他没有与命运进行一场终将失败的斗争,他就仅仅是一只愚蠢的动物。我所说的终将失败的斗争只是象征意义上的,因为勇敢的人总是会赢的。命运永远无法征服他/她的精神。你看,我不是悲观主义者。相反,尽管我伤痕累照,我会与生活抗争到底!我不会出走,绝对不会错过人生这出戏!”
仁者人也,人就是他自己的悲剧。悲,非和心,意谓违背产生的心。人就是心,海德格尔所谓的“烦”。人违背、超越了动物性生命,立心,人必须自己负责了,自然不再自然,自然成为“道”。负责就是牺牲。自己将自己置于一种祭坛式的存在。扪心自问,“必有事”(王阳明),心就是爱。爱是关心、有心、担心、放心、心动,倾心、随心、安心、忧心、可心……违心、负心、痛心、无心——成为生命中最严重的事。历史运动无不在称心违心之间运转。爱就是“必有事”。无所用心也就无所事事。悲是一种生命的质量,悲剧性令生命获得一种精神质量。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在孔子这里,志士仁人并非只是少数英雄,而是普遍的“仁者人也”之人。人从赤裸生命(阿甘本)通过语言升华为仁者,心动、心烦,怜悯、爱,这就是悲剧。人意识到责任、牺牲,从无言的动物性生命升华为文化生命,“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这就是牺牲。人开始烦心。意识到这种宿命的悲剧性令人获得超越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李白)“万里悲秋常坐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苏轼)中国心灵其实是悲剧性的。内在的、不动声色、大智若愚、呆若木鸡式的悲剧。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生命的悲剧正在于对“正襟危坐”的担忧、烦、“愀然”。中国心情对悲剧的态度不是尤金·奥尼尔那样的抗争,而是“愀然”。这是一种道法自然的民族的“大地之悲”。这种悲剧性在全球化时代已达到自古以来最激烈的时期。乡愁,就是这种悲剧性带来的巨大焦虑。
弗罗斯特在明德堡的另一个住处是在山冈中,他租的。就在老穆家附近。老穆说,他拿到了房子的钥匙。我们就去看看。像他诗里写的,雪地上总是出现岔路,哪一条通向弗罗斯特?山冈中长着些山毛榉、白枫树、野樱桃……安静的树林,结着可怕的黑痂。这一代的森林从前由印第安人看守着,19世纪被白人砍光了。现在的树,是一百年前重新种下的。忏悔般的贫乏,很瘦。弗罗斯特住在这里的时候,新的森林还没有长起来,他或许喜欢视野开阔。从风水的角度,我看不出在这里隐居的道理,一个荒凉的操场。一只啄木鸟在某处干活,发出咄咄声。房东还在,依旧住在附近的那栋白色房子里,房子重新上过漆。弗洛斯特租过的房子已经空了,再也没有租出去过。如果不写诗的话,谁愿意住在这种地方?买到食物要开车十多分钟。一排原木搭成的简陋房子,屋后是树林,前面是开阔地,可以望得很远。地里长着杂木、蔓草、几颗野鹿留下的粪便。熊在后面的林中睡觉,说不上何时会醒。三间房,一间小客厅,一个小书房和一间卧室,一张大床上覆盖着塑料薄膜。最后面的一间堆着柴禾。书架上的书看上去他从未翻过,都是出版社寄来的。几乎没有厨房,转角处的石块砌的承重墙上挂着几只笨重的铁锅,那黑乎乎的铁炉子看上去不怎么喜欢火焰。他的日子相当简陋,大约就是做个三明治,煎块牛排。西伯利亚流放者的小屋或某个修道院的祈祷室,但是不封闭,三面都有窗子,可以望见外面的花、黑土。
这种情景有点像中国山水画里的隐居。在中国山水画里,你可以看见那些隐者在草屋里下棋、品茗或者对着一条瀑布发呆。齐物。“至人之非己,固物我而兼忘。”(沈约《郊居赋》)“与可(文同)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苏轼《书晁补之所藏文与可画竹》)弗罗斯特家外面的这类风景,山水画里少见。大地对于他是一个对象,他只是一个显微镜,他的诗反映出这一点。“当我看到那平整的草茬时,那使镰刀锋利的露珠已消散。”(《花丛》)“有两样东西,我们越经常,越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越使我们的心灵充满了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敬畏,那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弗罗斯特先生是否坐在那块石头上眺望过星空?或者“嗒然”?“我想着一些无根无底的问题”(弗罗斯特《花丛》)。
锁好门,我跟着老穆去还钥匙。这地方的乡公所是一栋建在公路边的呆板大楼,里面没有人。不是用来办公,而是作为夏令营、培训基地之类的场所。门关着,门口靠着一把宽铲,弗罗斯特的钥匙就藏在这把铲子后面。
柯盖特大学是两百年前创立的大学,在阿巴拉契亚高原的汉密尔顿镇的一处森林里。两百年前,12位牧师在森林中的一块石头边集合,决定创立这所大学。然后他们砍掉了那些上帝种的参天大树,盖了一群希腊风格的石头房子。出钱的是William Colgate 家族。这个家族的公司开始是做肥皂的,后来也制造牙膏,高露洁牙膏。所以科盖特大学也可以翻译成高露洁大学。留学生不喜欢这个译名,他们不想与那只在中国超市随处可见的俗气条状物有丝毫关系。这是一所贵族大学。
阿巴拉契亚高原。这个名字有一种荒凉感,像是月球上的地名。
最后的秋天。到处是枫树,从加拿大那边越境过来,很快就要熄灭了,之后将是荒凉和暴风雪。
树枝之间弥漫着一层烟似的东西。大地以红色和黄色为主,红色又有各种层次。所有的红都出现了,有时候,下一阵雨,把植物打上一层湿气,颜色愈发鲜活。黄金色的树,但有黄金中没有的红色、橘红色。低缓的丘陵,之间杂以各种湖泊。偶而,树林深处出现一辆废弃的汽车,汽车要死在何处,它还没有想好。有时候它死在桥墩下面,有时候翻倒在公路边上,死的很难看。
几栋房子,排列得就像积木。美国人不讲风水,那些地方怎么可以盖房子?自由只意味着房子想朝哪个方向盖就盖。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许多美国房子的朝向是危险的,安全依赖技术而不是大地。大部分的人都住在独立的房子里面。大同小异,大部分看上去都很新,仿佛南北战争才结束不久。
雪就像卡车运来的纯洁垃圾,大堆大堆地冻结在天空下。需要一台掘土机。
一个工人驾驶着轰隆巨响的除草机在墓地里开来开去,就像钢老鼠,牙齿撞在墓石上,好像不害怕惊动死者。
教师们在晚餐时间聚会,就像19世纪的俄国契诃夫笔下的人物。在灯火幽暗的餐厅里吃着野牛排,炸鱿鱼圈,喝冰水,谈论着布什或者克里。普通人的小政治,与纳税有关。
学生忙着参加各种运动和比赛。比起上课,他们更热衷这些。
一位学生在课堂上追问我如何“拒绝隐喻”,我回答不出来,他很失望。
房子的后面有一条小路,是废弃的铁路的路基。沿着这条布满落叶的小路可以走到镇上。镇上有七八家小店、两三家超级市场。有的房子的门前放着支持布什或者克里的牌子。一条街,几分钟就走完了。
偶尔有人跑过,没有人因为某事而跑,都是在锻炼身体,穿着跑鞋。绝不会有人穿着皮鞋或高跟鞋跑步,这一点令美国很单调。
一群学生在打橄榄球,所有的运动都在暗示人生必须你追我赶。
闲着就是死亡,这是美国的真理之一。“你做什么?”最日常的问候。“什么也不做。”啊哦,转身走开了,除非他对诗有兴趣。
拍录像的是一位黑人姑娘。抬着一个黑色的小箱子。黑色是一种隐忍,美丽动人。她储存着全部黑夜。仿佛一到时间,她就会把它们释放出来。
钓鱼的人用一种假漂钓鱼。漂子是塑料的,做了某种处理,鱼会来咬。相当残忍,人家就要当你的晚餐了,至少给点吃的吧。美国的吝啬。世界观在细节中。
寂寞荒凉的乡野,出现了一栋关着门的房子,推开门进去,货架上支着一长排玻璃鱼缸,中国金鱼和一些热带鱼在悠游。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里会出现这样的商店,就像是刚刚空投的集装箱。
黑夜里有一家别墅灯火通明。外面冷飕飕,一片漆黑,进到屋里,坐着一房间的绅士,杯觥交错,衣冠楚楚。晚餐味道不错,三道菜,餐前的小吃、正餐、餐后甜点、冰水、葡萄酒,这样一顿要花40 美元左右。美国文化并非麦当劳那么简单,但是麦当劳确实是个基本的食物,普遍的、便宜的。玄关处放着反对麦当劳的小传单,知识分子和教授的小游戏,有钱吃40 美元一顿的人们当然有资格反对麦当劳。共进晚餐的美国历史教授去过中国,当过富布赖特交换学者,他反对布什。历史教授问,法国是否与中国的关系更好。我回答不出。晚饭后,他邀请我们去参观他正在装修的房子,门廊撑着两根小号的希腊式石头圆柱。之后回家,看见路边站着一头野鹿。
东亚系的办公室里扔着些汉语诗集,有一个作者叫“黄风怪”,相当醒目的名字。一张海报上,一位流亡诗人站在讲台上痛哭流涕。
加拿大雁排成人字向着南方飞去,灰色的天空有些愀然。“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世说新语·言语》)
John Crespi 38岁进入科盖特大学东亚系,在这个大学教了30年的书。他妻子是云南宜良人,刚生了小孩。20年前的一天,John Crespi 东问西问终于问到我的工作单位,在昆明翠湖边的一间房子找到我,请我朗诵一首诗录下来,他上课要用,就认识了。他长得很精干,像是一截失去了枝叶的树干。话不多,总是在想什么的样子。谁也想不到,这截树干里藏着一位很棒的音乐家,他会玩多种乐器,每种都玩得极好。他送给我一枝印第安人削的箫。16年前,我去他的大学访问,就住在他家。他家在一条废弃的铁路支线的边上,孤零零的一栋房子,被雪地包围着。那时候刚下过雪。我觉得此人太牛了,在暴风雪中买了一栋房子。如今他是东亚系的主任,终身教授,孩子也长大了,一男一女,会说昆明话。
John Crespi 家的书架上有一本胡适之的《尝试后集》,下雪的时候读到这首诗,我抄了下来:
我们不崇拜自然
他是个刁钻古怪
我们要槌他煮他
要使他听我们的指派
我们叫电气推车
我们叫以太送信
把自然的秘密揭开
好叫他来服事我们人
我们唱天行有常
我们唱致知穷理
不怕他真理无穷
进一寸有一寸的喜欢
——《拟中国科学社的社歌》民国十八年一月作
1910年,20岁的胡适,从上海坐船去美国,九月进入康乃尔大学,选读了农科。胡适在纽约创办了华美协进社。华美协进社1926年由约翰·杜威、孟禄(Paul Monroe)、胡适、郭秉文等共同创建。在纽约时,我被邀请去这个社演讲,我都不知道这是胡适办的。曼哈顿东65 街125号Lexington 大道和Park 大道之间,诗人和翻译家裘小龙带着我去,我们差点迟到,奔跑了几条街,纽约的街道每一条都是等距的。一栋古老的独立房子,落在一群摩天大楼之间。二楼的一个大房间里坐着几个老太太和其他人,我念了几首在昆明写的诗,得到了200 美元。
中国思想的根基是“和”。“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自然就是各种材料之和,共适。在胡适一代人这里,自然已经成为资源,开发对象。“把自然的秘密揭开/好叫他来服事我们人。”20世纪,这种古老的世界观终于走到了末日:“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庄子》)
过了十年,再访科盖特大学。一切都是老样子。那堆雪不见了。镇上多了一家越南餐馆。卖卷粉、春卷,这种食物从广东一带传到越南,再沿着滇越铁路传到昆明。我很熟悉。老板娘很自信,决不迎合当地人的口味,地道的河内风格,深受科盖特大学的姑娘们欢迎,排队才能吃到。要了一份春卷、一碗卷粉,搅拌的时候,想起一个遥远的名字:吴庭艳。那是1963年,我正在读小学三年级。我记得报纸的照片上有一场大火,一个和尚坐在烈火中。永远难忘。40年后我去了越南,回来后我写了这两首诗。
湄公河印象
14
那一天大地正在生娃娃
B-52 轰炸机来啦!
炸弹从蓝天落下
湄公河亮着蓝眼睛
就像从前接待云彩和白鹭
以青山丛林和水田接着
以湖泊之瓢接着以渔船接着
以水井边的木桶接着
以少年的书包和母亲的怀接着
割草人以劳动之舞来迎接
一千只狗舔着阳光以忠诚的舌头接着
供果和雨来自土地也来自天空
僧人闭目捧砵黄色的袈裟随烟而散
15
稻米金黄越南在天堂以南
稻米金黄仙女们的旗袍在飘扬
稻米金黄湄公河洋洋汤汤
稻米金黄求婚的队伍浩浩荡荡
街上少掉了两家古董店,灰茫茫的玻璃窗子,里面陈列着空货柜,似乎有一股尸体的味道。另一条街上有一家热闹的餐馆,上次没发现。一家以摄影作品为主题的餐馆,墙上挂着些黑白风景。临街玻璃窗前的桌子上坐着一个留络腮胡子的肥胖男人,一个红色女子依偎着他。人们的话题离不开特朗普,他们谈论他,在加油站,在餐厅和客厅。这是美国的北方,少有人喜欢他,知识分子尤其反对他。他看上去像一个搬运工,如果让他扛上一只老式的钢制的氧气瓶,就像马新民。那位我工作过的工厂的搬运工,高大健壮黑亮。那时候去食堂打饭,每个人都用一只大号口缸,一缸足矣,他要吃两缸。我们常常给他饭票。科盖特大学的一位教授说,特朗普令人们失去了安全感,一切都不确定了。
这次我住镇上的唯一一家家庭旅馆。女主人告诫道,上楼的时候箱子不要碰到楼梯,门没有钥匙。客房门不锁,大门也不锁。她们夫妇就睡在我们隔壁。“5点钟我就起来了。”她的房子大部分是木质的,一个小康之家,美国家庭的标配,比必需品多些,俗气的工艺品、地毯,客厅、起居室里摆着冰箱、电炉和咖啡、面包、果酱、牛奶,一只巨大的垃圾桶。餐桌旁边的大玻璃窗外的草坪上有松鼠。再远,另一家的房子。再远,一片墓地。被盖是高质量的,绣着花,卫生间里摆着一打白毛巾。窗子外面可以看见大地和房子,看不见人。偶尔遇到一个,急匆匆地走着。
有时候村子会传来一阵勃拉姆斯。有钢琴的房子。外表可一点儿也看不出来。麦克维尔镇离汉密尔顿不远,磨坊,小河,旧车站。老房子、七八家古董店。镇外有一家作坊,卖橄榄油和蜂蜜。19世纪开工的饲料厂。两个身强力壮的青年在工作。这里有一个古董节,每年8月15日开幕。现在只有几家老店开着。买古董的人不多,美国人不像旧大陆那样热爱旧物。发现一个非洲木雕、一个蜡质的波斯风格的模板,上面刻着:1876。两样,老板要100 美元。相当深刻的东西。那件蜡板,后来我的一位亚美尼亚朋友说,有波斯的风格。古董店的老板不喜欢根究意义,厌烦阐释。绝不担心什么价值连城者被随便处理掉。旧物,他卖的是物,而不是旧,与超市的买卖一样。
纽约州崇拜希腊。许多地名都取希腊名字,比如罗马、特洛伊,比如UTICA,1798年在镇上的巴格斯酒馆(Bagg's Tavern)的一次集会中,“由提卡”一名与其余12 个备选名称一起放在一顶帽子里,之后则被抽中。
19世纪的火车站。一百年前此地浓烟滚滚,满地煤渣。煤渣还在,已经不那么黑了。铁轨不见了,地基成了一条小路。被火车运走的就运走了,包括火车自己,运不走的是这个地方的原物、令这个地方成为这个地方的那些。已经复原得差不多了。野草、树木、河流、山冈。铁丝网后面的乱野(原野本具的植被,其间混杂着各种废弃的工业品,废墟)上走着一群野鹿,在树林边迟疑不决,像是速度慢下来的黄昏风。John Crespi 决心在此地住一辈子。住在哪里无所谓,重要的是这个大学在这里,他爱这个大学。冬天太长了,将近半年都是白雪皑皑。哪里也不能去,呆在房间里,如果无数事事,那就是自我囚禁。John Crespi 不亦乐乎,一日又一日的上着课,一本接一本的写着书,研究的课题像屋后难以融化的雪那样冷僻,“中国抗战时期的漫画”。就是汉语,也是冷僻的学问,他教了二十年,也不过几十个学生。John Crespi、Thomas Moran 都是在百度上搜不到的汉学家,像魏晋人物那样不事张扬,“人不知而不愠”。你得有一种基督教精神,为上帝而忘我。不见得你要上教堂。这是人们与生活的基本关系。在世意味着对圣徒般的苦役习以为常,厌恶无所事事、一劳永逸。
科盖特大学正在举行两百年校庆,有许多活动,国际诗歌节、艺术展览、音乐会……校友从世界各地赶来。坐在我旁边的老夫妇来自德国,不停地吃着土豆片。校长是个秃顶的男子,相当健壮,像个伐木工人,他自己修理汽车。音乐会是几个老师组成的乐队,在一个圆顶的房子里,音乐家们穿着黑衣,刻意渲染一种萨满教的祭祀氛围。图书馆和博物馆混合在一起,书架之间摆着真正的古董。
那些热爱诗歌的学生关心这些问题:
中国当代社会对诗歌的态度怎么样?
你的“汉密尔顿组诗”把这个地方的很多小细节写得很准确,但是对汉密尔顿的感情上的反应不怎么清楚。一般来说,对汉密尔顿有负面的还是正面的感情?
汉密尔顿会不会让你联想到自己的童年?
开始写诗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文学的偶像?跟谁学习?
在你写过的诗歌当中,有没有最喜欢的一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首诗?
一般社会对诗歌的忽视甚至蔑視有没有让你怀疑自己?要是这样的话,是什么让你能坚持下去?
你平时一天都做些什么?
遇到写不出东西的情况,你怎么去找灵感?
你的诗能不能跟古典诗歌拿来做比较?
旅馆的后面的山上有一处墓园。墓地永远是一种自生自灭的样子,许多事物都自生自灭,最后也就不见了。人们活着的时候各行其是,死后却要埋在一处,死亡是一种团结,这种团结产生一种令人沉思的力量。死亡是什么?我要怎么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他的意思是通过生来认识死亡,只有在生中,人们才可以理解死亡,所谓“向死而生”。墓地东西表面上也是一个空间,墓碑,花台什么的。即使世界上没有一处墓地,墓地也在着。许多事物都成了废墟,只有墓地不会,墓地无法废弃,死亡无法废弃,死亡是一种永生。这一天是农历的四月五日,中国的清明节,墓地里一个人也没有,一只啄木鸟在树上干活,看不见它在哪里,只是传来那种咄咄之声。山坡上立着一棵被砍伐了一半的树。
在墓地里走了一阵,想着父亲。他埋在昆明的一座山上,他一生从未离开过祖国。我们从未谈论过美国。他有一个特权,60年代就可以看《参考消息》。这份报纸经常出现关于美国的零星消息。
那种老气横秋的火车站还在美国活着。含有大量木质的车站,里面有理发室和小卖部。候车室的柚木长椅被磨成了古董,等车的感觉就像下一趟火车会驶回十九世纪去。仿佛许多事物都在为自己的盲目维新而忏悔,人们怀念旧事物,怀念从前的原始森林、落日、旧家具、棉花地上的蓝调。怀念“垮掉的一代”。
坐火车的人很少,一对胖子在我旁边睡觉。车厢的椅子有脚踏,试了一下,是为个子更高的人群设计的。卫生间的镜子正对你,可以一边小便一边观察自己。
停车的时候看见一个胖子站在白色的汽车边,双手塞在裤袋里。仿佛他是站在一棵树下。
在火车上看见遛狗的人,跑步的人、骑自行车的人、打棒球的人、钓鱼的人、梳着长辫子的老姑娘、老鹰、死去的动物、至死不渝的夫妇彼此搀扶着在湖边走……旧风景,旧车站、旧工厂、旧木材、旧的篮球场、旧城、旧的电线杆子、旧掉的大地,废弃的汽车祭坛般地堆在荒野中间。新叶成群地朝天空嘟着小嘴,就要大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