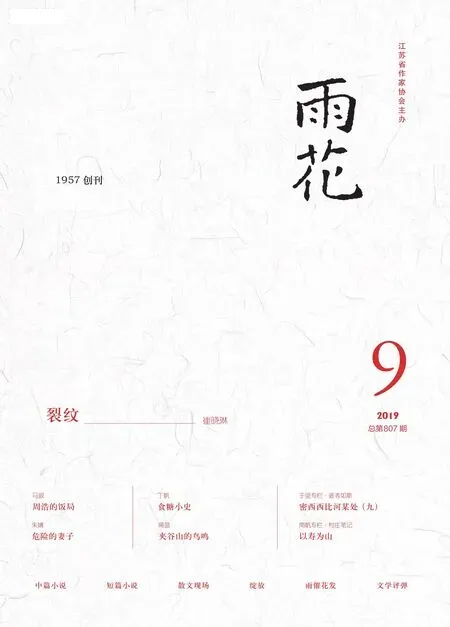创作自信是一种力量之源
——毕飞宇工作室第十六期小说沙龙实录
庞余亮:这两篇南师大学生的小说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小说文本。当然,它们还有许多有待商榷的地方。
易康:这是两篇有情怀的小说。毕飞宇先生说过,对于小说,没有一样东西比情怀更重要。就此看来,两篇小说是比较成功的。小说由情怀带动语言,情怀决定了小说的方向。两位作者有独到的语言追求。《通天》有两个主要人物:怀仁和泰和。他们其实是一个人物的两个面,背后隐藏着作者自己。但作者隐藏得不够深,小说空间没能够打开。小说表述单一,用同一种武器往一个点上猛攻,节奏控制不足,效果不佳。同时,这篇小说比较空,人性探究比较浅薄,核心意象挖掘不够。如果增加一个人物,从另一个角度来叙述,可以调整这篇小说的结构。《致哀日》风格类似摇滚,体现了作者的叛逆、反抗和力量,但比较繁琐、反复。看得出两篇小说都受到了翻译作品的影响,《致哀日》类似加缪的《局外人》、贝克特的三部曲,又有巴金早期小说的影子,作者在语言上有追求,但整体仍欲速则不达。
庞余亮:先谈《通天》。我说三点:第一,写作者要有自己的腔调。《通天》的第九部分:“清晨的时候,他和另外两个人把父亲的遗体抬到了河边……怀仁一哆嗦,他用袖口擦了擦脸,然后望着涟漪一点一点平静下去。”如果沿着这句话继续向内走,小说会非常棒。但整篇小说缺少体温。小说的构思不错,但只有一些意象的反复,写得很平。第二,棍棒。棍棒的打与被打之间的张力能不能出现,比如莫言的《檀香刑》,要把其中的打与被打模仿、借鉴过来,父子之间的那种张力就能全部出现。第三,力量。要以一个人的视角去挖掘得更深一点,不是让好多人的视角分散了力量。
《通天》表达准确,《致哀日》不够准确。但相比而言,我更喜欢《致哀日》。这里面有抑制不住的才华。《通天》的焦点不聚焦,《致哀日》焦点统一。《致哀日》的结尾出现了一句“你知道,嘉明当时很爱你”,接着又重复了一句“你知道,嘉明当时很爱你”,小说顿时有了力量。
庞羽:小说作者一般从偏向于自我的作品写起,但一个好作家,必须要关注身边、关注社会。《致哀日》是一种心理迂回小说,画面感强,类似于加缪的写法。《通天》的语言好,但这篇小说的动机不足,缺少核心事件与三角关系。
王锐:《通天》的视角不统一,节奏变化无规律,缺少推动叙事的力度,很难建立带入感,而《致哀日》能把你带入某种情绪当中。但《致哀日》不够准确,让读者产生了困惑。
何燕婷:《致哀日》作者有自己的想法,但它表述不够清楚,叙事很平。《通天》语言流畅,用环境描写烘托小说氛围,但它的结构有问题,人物形象由作者直接交代,而非塑造出来,缺乏真实性。
毕飞宇:大家好好读《喧哗与骚动》,就明白这篇小说怎么改了。
钱兴媛(学生):《致哀日》有画面感,令人感同身受。它让我想到李碧华的《胭脂扣》,嘉明和如花一样,是一个灵魂人物,因为他们的逝去,把大家聚集到了一起,发生了故事。
孙晨(学生):我更喜欢《通天》,但它的语言太直白了。作者应隐埋得深一些。
毕飞宇:在1987—1988年,这两篇小说足以让作者一夜成名。那时人们还不懂现代小说。西语有多种限制、重句,翻译过来,界定和重复过多。可现在是2019年,我们不仅要学习经典、读最好的书,还要提供新的小说语言。两篇小说都能体现作者的小说才华。《通天》有缺憾:第一,创作小说就如画油画,定个框子,反反复复地画,最后形成一幅丰富厚实的作品。油画是有画框的,不是一个生发的、开放的作品。第二,在叙述中呈现复杂的世界,以及世界的不可知性和不可预知性。《通天》类似于福克纳的小说,可以阅读他的《喧哗与骚动》。叙述的腔调要变,多方位多角度地塑造人物形象。
《致哀日》中,有一句台词:“我知道。”如果让我写,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写尽悬念,让小说处于未完成而完成的状态;其二是在“我知道”之后,继续往下写,设置情节、场景,再现爱情,或者曲终人散。《胭脂扣》就是很好的范本。这位作者的胆子太小了。
任一琼:《致哀日》中嘉明和“我”之间的感情比较平,最好再深入一点。《通天》语言优美流畅,但视角应有变化,故事冲突不够。
朱婧:《通天》语言集中、清洁和流畅,小说的结构、逻辑、支点全面,但作者对文本控制不足。可以看出,作者创作是出于本能,是个人的纯粹的快乐。
朱辉:这两篇小说中,《致哀日》更成熟,《通天》语言不错,描写准确。生活本身有逻辑,而小说也要建立一个叙事逻辑,这两个逻辑之间有巧妙的契合或适当的PK,这对小说质量至关重要。生活本身的逻辑与叙事策略匹配、同频或故意不同调都体现作者的创作能力。对于小说家的才能,除了语言要求,还应有情节要求,虚构情节的才华是创作能力的真正体现之一。短篇小说需要奇情,在有限的叙事空间里,给读者一个意外的、特别重要的发现,可以源于故事的情节、也可以源于细节,甚至是叙事策略和叙事方式。小说不是生活,小说是生活开出的花。
金理:《致哀日》最后作了心理学解释,会带来一定的阅读障碍。《通天》时代关系指向不明,它的表达方式和主题结构在创作之前就已存在,作者的视角集中在一个点上,反复攻击,少了一些旁逸斜出的东西。
朱辉:一个好的细节可以撑起一篇好的小说。毕飞宇《彩虹》里的细节就是一个好的例子。生动的细节描写显示出作家的趣味、力量、经验资源与想象的本领。《彩虹》成功的细节构成了小说的魂。比如四只石英钟,把时间分别拨到了北京、旧金山、温哥华和慕尼黑,依照地理次序挂在了墙上。看上去漫不经心,其实大有深意。小说结尾小男孩的一句话,他说你家的时间坏了。一下子,细节的精气神就出来了,通体明亮。小说在这个细节上反复流连,北京、旧金山、温哥华、慕尼黑,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一堆指向不一的时钟摆在一起,可不就是时间坏了么,然而,对这对夫妇来说,坏的仅仅是时间?他们劳碌一生,所得是什么?
缪一帆(学生):《致哀日》的开头是一个葬礼,但不明逝者是谁,这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作者把心理学逻辑套在生活逻辑上,想凸显构思独特,但并没有继续深入。加缪的《局外人》与此不同。《通天》小说开头符合生活逻辑。
马雅雯(学生):《通天》与曹禺的《原野》类似,都属于复仇者归来的故事。但《原野》里的复仇是必然的,《通天》里的矛盾不成立。
徐佳玮(学生):作者尝试隐去自己的性别,是值得鼓励的。《通天》恰似南美洲神秘主义小说,无论是对死亡还是对复仇的意识,是无意识的符号化。我们现在的创作还处于无意识状态中,与某种作家手法相似,也是一种偶然。
钱兴媛(学生):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有一位穷作家,他常穿一双带洞的袜子,实在活不下去了,就去铁路卧轨。最后他惨然一笑,接着镜头是带破洞的袜子,再然后,是露出的脚趾头。这些关于死亡的描写,包括毕飞宇老师的玉秀,还有司汤达的于连等,都让人读后有牙齿一酸的感觉。但《通天》并不具备这样的震撼。
易康:我更喜欢《通天》。杀父的缘由可以忽略。但小说的其他要素要让小说撑得起来。
庞余亮:《通天》以它的第十章作为开头,会是非常棒的小说。“怀仁已经在院门口等了泰和很久了”,这句话就能把小说确立起来。《致哀日》聚焦聚得很紧。短篇小说是环环相扣的。每个词、每个句子都有讲究。既然爱小说,就要爱小说的艺术。小说创作者应该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毕飞宇:《通天》最吸引我的,不是精神故事,也不是时代内容,而是一个故事颠三倒四描写了多次。一个作家,要么大量阅读,要么像马尔克斯当初学写作一样,去归类去尝试。创作者要线性,还是要非线性的,自己要很清楚。如果是非线性的,可以自由发挥;如果是线性的,就去学习,总结,寻求艺术规律。创作要胆大。小说的人称代词不要乱用,要清晰。比如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他的小说人称代词的使用,有一个身份和悬念的存在,而《通天》不存在。创作小说时,再漂亮的句子,只要它与小说没关系,那就得修去。
文雯(《致哀日》的作者):如果你对写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会写得更大胆、从容、自由一点。总体来说,我创作还不够自信,不懂取舍,文本显得累赘。
张步庭(《通天》的作者):我第一次尝试写这么长的小说。我沉浸在泰和的家庭悲剧中,没有考虑读者的反应,也欠缺了小说具体走向的思量。
李洱: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毕飞宇工作室小说沙龙,这也是我三十年来,第一次参加如此认真又如此仔细深入小说肌理的讨论。我想起了80年代,我的一次小说创作经历。我通过对小说的写作、修改、写作、再深入,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写作秘密。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这又是两篇关于死亡的小说。我认为很有道理,所谓向死而生。通过小说,我们一生能几次见证人世的险,几次接受生死的磨砺?从《诗经》以来,优秀的文学作品里都包含着死亡,人的死亡、自然的死亡、鸟的死亡……在死亡中,生命重新诞生,意义重新获得,这是文学的基本主题。在小说沙龙的讨论过程中,所有的意见、观点基本没有重复,这说明小说创作有基本的写作规律。小说分为两种,一种是契科夫式的,另一种是卡夫卡和博尔赫斯式的,前者是世俗生活中个人的孤独,个人和世界的关系;后者表现怪诞梦魇暧昧。这两篇小说大致属于后一类。这两篇小说有才华,也有许多问题,譬如说,要赋予小说具体意义,动机要足,要艺高胆大,视角要清楚,目光要聚焦,存在的内核要坚实,坚实才能让读者信赖。1949年之后的小说,我都看作是某种成长小说,小说创作的状态及精神世界要打开、要成长、要有所教益。小说要注意词与物的关系,赋予小说生命以强大支撑。
何平:非常感谢毕飞宇工作室小说沙龙请来的嘉宾、毕飞宇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和《雨花》杂志社的团队。南京师范大学是一个具有人文气息的大学,今天来了这么多学子,他们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这充分证明了这些。我期待毕飞宇小说沙龙再一次来我们南师大,给学子们丰富的文学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