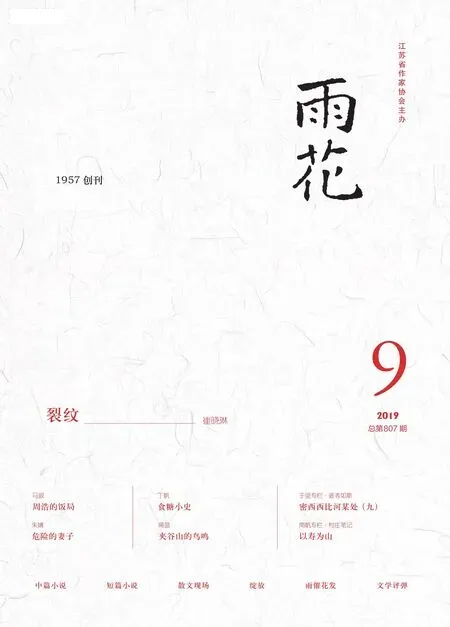致哀日
文 雯
热气几乎是从神经末梢直接灌入脑海,大脑中枢在作痛、作响。周围全是静止的风声。我把长发胡乱挽起来。
手机响,显示“妈妈”。我照常规跟她交代去处:“我去参加葬礼。”
“谁的啊?”
我觉得这时候我应该回答一个名字,但突然间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像是一次反复强记的背诵猛然断得一干二净,上下文所有语境骤然失去联系,我迟疑了一下,“一个高中同学。”
我去参加葬礼,在这个夏季尤为酷热的一天。
光把外面陈放的白边花圈染成淡淡的橙红色,白色的飘带们迎着炽风群然抖动,发出轰隆声。
前来悼念的人们——稀稀拉拉的人,坚持穿得严严实实、恭恭敬敬的人,还有几乎没有人迎接的客人,如我,没人引路,我就随性坐到最末一排的位置。我不用坐得太前,一是身份不符。我隐约只记得这是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可能毕业多年也未曾联系,实际上我跟任何一位高中同学都是这样的状态。遥远的人际丝线隐隐绰绰,那些片段的印象像是被删除一般。二则是,我也没多大兴趣,现在比起哀悼,我只想找个通风处。
头疼和眩晕感也许是这暑气使然,我的每个毛孔都在分泌汗水,像淋浴一样,我淋着汗水。
我收到讣告的不久前,天气就已经是这个样子。讣告很短,突如其来的家属简讯的通知。同一天还有一封小小的肃穆的黄皮信,送过来的时候四边轻微的卷皱。最初还有一种想知道死者生平的欲望,转眼又被我日常的倦怠压抑下来。
这个葬礼的主角在我心里只有个模模糊糊的图景,事实上,我几次起了一丝想要去了解死者的念头,但都莫名消散掉。
我远远地坐着,顺眼看过去,一幅巨大的遗照,大得逼近,大得吞噬了整体的面容,只让人看到那张已死去的脸上曾经生动的细节。譬如肌理,譬如发际,还有笑纹。那面容在我的视网膜成像,那就是一幅对比度极低的黑白轮廓,准确地说,是一团雾气。“真像画,”我看向那远远的一幅,小声嘀咕着,“是《伦敦国会大厦》里最暗的那一份。”
相框的边缘,银色,我注意到框边纹路处理得是那么精致到位,像是被粉红色的藤本月季满满地攀爬缠绕着。“生前也是生活得浪漫着呢。”我正想着,忽地,银边被渗漏到白帐里的太阳光照得反射,一阵目眩,我把脸和眼睛一同别到一边。死者是谁也许并不重要。
我开始环顾周围的人。最前方的一群着正装的中年男人大声地讲着无关的话,他们的样子在白帐荫蔽的烈日下显得焦虑不堪,我右边斜后方的女人用一张硬纸呼呼地给自己打扇,毫无吊唁的神情,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风把她前额的头发吹起来,才看得到里面藏着的蒸汽与水滴。我一面暗自好笑,一面也的确很想知道,为什么葬礼会在室外——在这八月流金砾石的天气。这样焦躁的气氛让人甚至怀疑,是否它已经击毁了本该有的哀伤并取而代之,因为悲恸的感觉几乎太难寻见了。
一个穿着黄衣服的小孩在我周围嬉笑着跑来跑去,这显然不是在肃穆的场合应有的。我想提醒他,我眼看着他飞跑,笑声像装着玻璃珠的瓶子快速摇晃时那样脆生生的利落,我的目光跟着他的脚步游移,最终顿住……“停下。”这不是我的声音。我要开口时忽然满嘴缄默。这时我感应到我的悲伤了,可惜不是对死者,是对我自己。
回头看,孩子的母亲,那个方才扇着扇子的女人,她一脸严肃的样子,好像从始至终都对死者抱有感怀与敬意一样。
在我看来,她与她的孩子也一样,我甚至觉得她百无聊赖用力扇扇子的模样倒比较义正言辞。
算了。我对自己说,算了,当然我也不高尚。我本来也不是诚心诚意来表达悼念,我的出席本来就是出于我自己的目的,那么我又何必要维护这个葬礼所谓的肃穆呢。
我把这场葬礼当作一次高中同学聚会。我要直面我的心思。
这样看来,我比起刚刚乱跑的黄衣小孩是更加不敬。本末倒置,于死者,这种寻找说辞和借口的出席是多么卑劣啊。
我是期待高中同学聚会的,我暗自期待很久了。倒不是我多怀念同道奋斗的友情,或是某一段被文艺作品浮夸再三搬来搬去的青葱岁月。我是很想见当初的一个人——但他想不想见我另当别论。所以我来参加葬礼了,我以一种不在意逝者的卑劣和恍惚到这里来。我坐在这里,感受汗水从我的表皮飞快渗透的细节。
我不见那个人也已经很多很多年。
想必他一定会来,他跟我不同,他是非常重情义的典型的世俗人。他那时候就有太多太多相处很好的朋友。他在意他的每一位朋友,甚至显得有些八面玲珑。记得有一次,他帮他那一帮人中的一个大高个子去高中后门拿外边从墙洞里塞进的米粉,热气腾腾,他护着走,被青苔送了一程,滑倒,最后身上泼满了粉汤,总之他什么都没说,自己回去换了身衣服,再买了一份米粉给大高个子,还连声道歉说自己送得迟。我不喜欢他那唯唯诺诺的样子。我记得当时或许还为此跟他吵了一架。
我们总是爱吵架,不是面红耳赤,不是大动干戈,我们就静静坐着,聊着聊着,聊的都是些尖刀剜人心肺的言辞,那些刀片铺天盖地下下来,他胸口一丛,我背上一片。我一个人哭得全身发抖,气息顺也顺不平,就一抽一抽,抽到很可怕的境地,他就开始担心,会说:“要不要叫医生?我给你妈妈打电话,快,我给你妈妈打电话。”
“你不要打——”伴随我轻声的气息吞吐,我哭泣就收敛一点。
他起初赏识我的脆弱,我也对他的怯懦表达谦卑和恭顺,天作之合。跟着这思路,我耻笑自己,耻笑一直持续到我看到三两熟悉的面孔。那些脸保有着某一雷同的内核,只是改变了质地,我对他们没有消散的五官落点和标志表情深感熟悉亲切,虽然我是个相当健忘、又被人形容为很漠然很单薄的人。我从一旁绕行走近,又换了换方向看,最终确认那是我的高中同学们。几分钟内,这个队伍微型扩张。而我仍在困惑要怎么过去自然顺承地插入他们的叙事抒情,首要考虑怎么去抬起这手,我消磨意志的时光居然快要难以支持我抬手。
高中同学,高中同学。
现在多来的几人,和原先的几人没什么不同,那一群人。我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一个都不,我反反复复确认,每一张脸在记忆里都能再现,就是所有的名字变成符号在那段岁月里原地蒸发,飞升到跟我现在的时空完全脱节的所属地去。那么,先跳过他们,他的名字是什么?我抄起手,右手捏着自己汗涔涔的左袖,冥思苦想。不过,那群人里没有他。
确实,真的没有他。事隔这么多年,模样再变化,我想我还是能认得出他的。我有一些失落,但并不为此感到失去希望,因为他总是迟到。上学时就是这样,踩着铃声踏进教室门,还要慢悠悠地携水杯到门口去接水喝,一边接水一边回身同门口一排他的“朋友”聊天,这不奇怪,谁都是他的朋友。
不过这种场合也迟到,堪比我的不敬。我是实质的不敬,形式还无可厚非……
“阿云!”对面叫我。
好生疏的一个称号。非要数,快十年没人这样叫过我,以至于我迟疑一秒才回过神反应过来。
“过来呀阿云。”
阿云,我的名字里没有云字。但我告诉过每一个我信赖的人,我的名字里的字本意是云彩的意思。然后他们一声一声那样喊我,其他人不明就里,也就随着这样叫了起来。第一个告诉的人也是他,想到这里,我又较方才添了一笔地想:还没来,他甚于我的不敬。
我迈步走过去,一边放下了心,一边又有一些不安又鼓动起来。我练习了无数遍的技巧,再来一遍,抬起手,摇摆手腕,掌心朝前,动作轻微但有幅度,象征友善和热情,说着“好久不见啊,天啊”之类的话,最后要笑——
对面的人看到我的笑露出了一丝转瞬即逝的又极其奇怪的表情,说不清是诧异还是鄙夷,但总之那神情很微妙,偏偏又一下子消散了,我没来得及将之捕捉分析。我有些难受,倒不是因为在这样示以哀伤的日子这样笑自责,至少我觉得我笑得很委婉。或者难道我不该笑吗,我想,那就是我不该笑,这是葬礼。
“好久没看到你了,要不是这次……”
“是啊,多少年了。”
我不喜欢应付这个,但我还做得不错。
对面有女人哭,男人拍着她的背。我们循声看过去,我就装模作样地侧身瞟了一眼,表示也以目光表达了关注,以及和他们的那份一起顺便交付的同情。高中同学们说,可惜,真让人难过,还这样年轻,无非是这些话。
这些词句中,我小声嘀咕了一句:“我热到头晕。”又迎来了方才我笑的时候他们那转瞬即逝的表情,我私以为那都是些古典的表情,像古希腊雕刻的人像,没有眼睛,他们不用眼睛传情,整个躯体就是诉说。就是那样从上到下都不自然的表情,不是某一个情感鲜明的眼神,或者表达喜恶的嘴角牵动,是全身地,看,他们的手都有些僵直,他们的喉咙动了动。我解读了一些。
我感到越来越闷,甚至开始动摇,他那样看重朋友,至少高中时候是这样,怎么还不来呢。只是这温度让我无法给自己一个类似于“只是早晚问题”的安慰。
我又陪他们坐了一会,仪式过了一半左右。我佯装听进去了回忆和叹息,他们嘴里流出来一长串的名字,都关于早就被冲淡了的那一段时间,像是强行把储存室角落里童年挚爱的泡泡机拿出来,塞到面前,不仅自己要吹出来,还要逼着我吹,这就使我觉得尴尬。总难免有几个时刻他们是看向我,这是人与人谈话必然的眼神交流,却是一种无声胁迫——你总要,也总该说些什么。
可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不关心逝者,也不关心绝大多数人,比方说他们,我想不起我面前这群人的名字,真是苦恼,这些叫不出的姓名混合着日头的温度变成一团粘稠的稀泥巴。我开始决定打量他们,每张脸都能让我明确肯定在那些犬马声色中出现过。先扫视,大约是七八个人,每个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我看看我身上,白色中袖薄衫,因为实在太热。我想传统出丧穿白,没什么不好,倒是西方牧师做祷告的墓前人们身着一片黑,我觉得很讽刺可笑,这个葬礼明明不伦不类,倒洋不土。而我没什么精力笑这个。我也不敢冒失,至少要表现出我来表达哀伤的主要目的,以及与他们共追忆逝者以及那段与逝者和他们共享的岁月的次要目的。我的目的不是这个,我自己知道就好。
焦躁让我审视我打量的一切。
这张脸,现在胖了不少,打着乱七八糟的领结。这是早年和他一起在球场的人,他们的球技真的很烂,我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要看。
这女人,白白净净的脸,我认出来,似乎是那时候他很铁的朋友了。就是她,我记得明明白白。他给她占座位。那时候我有种莽撞的义愤,觉得这是一种精神出轨的表征,年轻的时候蛛丝马迹都是世间大词。说这话好像有些老气横秋的成熟感,那倒不必这样抬举如今,我知道,好在这么多年,我除了磨掉脾气,也没修来比当年好得到哪去的秉性。这女人呢?她跟当年一样白净,也许其实已经暗沉了,借着过去失真的记忆加持,黑色又衬着肤色。
这个人是他后桌,是为数不多我认为的,他的“好”朋友,以前一股流气,衣服总穿大一码,还很皱,像摊开的一抓酸菜。最记得他走起路来鞋子在地上拖来拖去,好像不愿意离地似的。现在穿得仪表堂堂,皮鞋也干净得反光,这样子倒比较讨厌。
……
看到大概五个,不想再看了。
恰好刚刚的黄衣服小孩打碎了什么东西,很大个东西,我无心关注,只是没选择余地,被迫听到了伴随文明和感情结束的一声长长的呜咽,像是钟鸣。我热得失去耐心。
“喂,那个——”
我最后一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他们的目光齐刷刷看着我,像审判一个怪物,所有人微微张嘴,那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让我想跳上去撕开那些命定般的虚伪盘问。
“我是想说,我们等仪式结束后,同学间再聚聚吧?”
没人回答,只是奇奇怪怪地看着我。我知道自己又大不敬了,但我不想再装得多么肃穆,实际上我相信他们内心也不是,毕竟这么热的天,我知道他们早也和我一样整个头昏昏沉沉。但无人应答的会话就是会让周围变得很可怕。更可怕的是我又接着补充:“去吃吃饭,唱唱歌之类的。”恐怕他们觉得更怪诞,我加上了一句“像以前一样”。
“像以前一样”这种利用过往的自私盛情,我这种对过往几乎完全糊涂的人居然运用了起来。
葬礼我存疑,但如果是确认的同学聚会,他就一定会来。我面对我的心思。我对他的世俗太有把握。特别是唱歌,幽闭黑暗霓虹亮色的灯光旋转,以及可以作为朋友身份的一群人。大家都那么爱唱歌。那时候他就唱歌,还指导我唱歌。一间像歌厅一样黑的教室里,我抱着一杯水喝个不停,唱到后头就是寻常的吻。吻过来吻过去,人类恶心的暗室艺术,全民参演的戏剧表演。
一片荒谬的柔情登堂入室,自我陶醉。
我攥着袖子。
此刻,高中同学们面面相觑,好像在找什么话说。一个我没什么印象的人语气诧异地哼唧了什么,紧接着那个白净女人带着哭腔一样的低沉的愠怒,或是什么我也拿不准的情绪,开口:“嘉明死了,我们都很难受。”
我猜到会是大概这样一句。无非责备我不懂表达严肃的感伤或者是什么失敬的措辞。在这样的场合,我看起来不够感伤,措辞也很不当。但其实我也想说,他们也不感伤,他们只是有什么环境有什么遣词造句的本领。我倒不想为自己辩驳,只是想再争取些什么,很快地向她道:“不是这个意思,我……”
“你知道,嘉明当时很爱你。”
“我知道。”我想都没想就顺着这话应了下来。
——我知道?更该是这样,一句陈述句用尽了所有疑问的语气。我突然发现自己距离遗照的距离够远。那一幅巨大的遗照,大得逼近,消解了整体,只让人看到那面容曾生动的细节,还有那惯常的懦弱的笑纹。但现在已经够远。
她的声音像一件触感清凉的瓷器在滚烫的地上摔到碎片高高溅起,她低垂地,很轻地重复了一遍:“嘉明当时很爱你。”
我闪回我大脑空白的前一阵子。我听到自己也在轻轻说:“我知道。”
没有声音了,那小孩打破的东西偏偏撞钟一样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