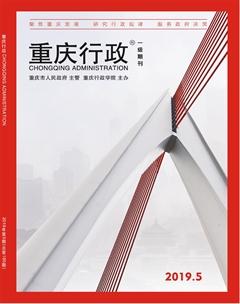环境保护社会共治中政府的角色定位
杨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本质上而言,构建该治理体系的目的在于实现环境保护社会共治。政府在环境保护社会共治中扮演着至为关键的角色,如何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直接关乎环境保护社会共治能否得到有序推进,亦关乎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否得到顺利实现。
一、正位:环境保护社会共治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
在环境保护社会共治中,政府基于其独特的政治、经济、信息、技术等比较优势而居于主导地位,既决定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政方针,又引导其他参与共治主体积极支持、配合环境保护立法与决策的“落地”。政府在环境保护社会共治中之所以要发挥主导“正位”作用,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环境风险的不确定及其治理的“复合性”,迫切需要政府在环境保护社会共治中发挥主导“正位”作用。风险社会理论的奠基者乌尔里希·贝克认为,传统社会的危机可以概括为“我饿”,而風险社会的危机则表达为“我害怕”。“我害怕”意味着风险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公众对风险的恐惧。此外,环境风险还具有“人因性”“复杂性”特征,这决定了单纯依靠企业、社会组织或公众因应环境风险往往力有未逮、效果不彰。换言之,环境风险的有效防治必须依赖于政府,充分发挥其在环境风险治理中的引导、激励和强制作用[1],如此方能更好地回应日趋复杂的现代环境风险。
第二,政府相较于其他参与者在环境治理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决定了政府在环境保护社会共治中应发挥“正位”作用。申言之,环境治理中的政府拥有决策、资金、信息流、技术、专业人才、组织等诸多优势,这些优势是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任何一方都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尤其是在环境治理市场尚不成熟、制度规范尚未健全、环保组织未成体系以及公众环保意识亟待提升的当下,由政府主导和推进环境保护社会共治无疑是一种最稳妥、最可靠、最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概言之,基于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与“复合性”以及政府环境治理的比较优势,使得环境保护社会共治中的政府应发挥主导“正位”作用。
二、缺位:环境保护社会共治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现实障碍
从应然层面看,环境保护社会共治中的政府在政策引导、信息公开、监督管理、法治保障等方面应发挥主导“正位”作用,但现实中政府在以上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缺位”,成为环境保护社会共治的现实障碍。
(一)部分政策引导职能缺位
2015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第9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环境保护宣传和普及工作,鼓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环境保护志愿者开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营造保护环境的良好风气。”据此可见,环境保护政策宣传与引导是政府的应尽职责,但在实然层面,各级政府对环境保护政策尤其是环境保护社会共治政策的宣传及引导并不到位。以危险废物治理为例,2016年新修订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规定了46大类别479种危险废物,但“针对名录中规定的废旧电池、坏节能灯、过期药品等家庭危险废弃物,大部分民众既不清楚其危害性,也不知如何回收处置”[2]。究其缘由,莫不与政府未积极履行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职责相关,即政府并未实质性地向公众宣传其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政策,也并未采取多种有效方式组织和引导公众学习危险废物回收、利用与无害化处置等知识,以至于政府作为环境保护工作“第一责任人”之定位并未得到体现。
(二)部分信息公开职能缺位
政府作为环境保护社会共治中信息披露与风险交流的主导者,理应拓宽环境保护社会共治信息发布与交互管道,“让社会公众都成为风险防控专家”[3]。但目前我国政府在环境信息公开与交互尚面临诸多困境:一是信息发布的单向性,环境信息往往从政府向社会单线条传递,严重忽视了企业、社区、媒体、专家、环保组织、行业协会在信息发布中的作用;二是信息发布的滞后性,政府难以事先对所有的潜在环境风险进行精准评估与机敏预警,在污染发生前后常常难以及时向公众传递有效的联防联控信息;三是信息发布后缺乏互动,由于环境信息交流平台与互动反馈机制尚未建立,政府在信息公开之后难以与公众展开有效互动。在环境信息公开与信息互动不足的情况下,政府也难以引导或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更难以获得以上参与者的真正信赖。
(三)部分监督管理职能缺位
环境保护社会共治本质上是“小政府、强政府、大社会”[4]治理格局,政府不再对环境治理“大包大揽”,而是“协调服务”,同时注重各主体的协作分工,以“分工出效率”[5]理念为指引,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然而,我国环境监管层面却存在监管方式单一和监管刚性不足的双重困境,阻碍了环境保护社会共治中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第一,监管方式单一,环保部门常选择“以罚代治”、“以罚代管”方式处置环境污染,在“罚字当头”的监管模式下,政府无法有效组织和引导社会组织、第三方治理企业和广大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第二,监管刚性不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由于受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尚未健全等因素的影响,环保部门在监管执法中对涉嫌环境犯罪的案件常选择“有案不移”或“以罚代刑”,严重弱化了环保部门监管的刚性与严肃性;另一方面,政府在环境保护重点区域(流域)尚未建立协同监管机制,致使各层级环保部门在监管中陷入“单打独斗”“孤军奋战”的局面,难以与其他监管部门做到信息共享与协同监管。
三、补位:环境保护社会共治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路径选择
为构建环境保护社会共治长效机制,应当对政府在环境保护社会共治中的主导作用进行“补位”,充分发挥政府在共治中的组织、领导、监督、协商、服务与保障作用。
(一)加强环境共治政策宣传与引导
充分发挥政府在环境保护社会共治中的主导“正位”作用,首要之义在于加强对环境共治政策的宣传与引导。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曾指出,“影响社会公众风险认知的因素包括:经验规则、显著性、伦理、对专家的信任、固执的判断与计算、风险公共教育”[6]。为确保企业、社会组织和广大公众能够广泛参与到环境治理之中,政府应当加强对环境保护社会共治政策的宣传、引导与公共教育:一是采取多元的环境宣传教育方式,譬如采取创建绿色学校和绿色社区,加强与媒体、企业、社区互动交流等方式,形成社会重视、企业支持、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二是创新环境宣传形式,立足于地方实际和地方特色,开展公众喜闻乐见的宣教活动,譬如为公众编写了图文并茂、浅显易懂的有害垃圾分类和倒放指导手册,以引导广大民众正确进行垃圾分类回收以及积极参与到环境治理之中。
(二)强化环境共治信息公开与交互
环境保护社会共治的顺利推行,须臾离不开政府对环境共治信息的公开与交互。具体而言,第一,加大环境风险信息公开力度,让公众成为环境风险的防控专家。除了通过发放小册子、发传单、印制广告、新闻宣传等传统方式外,政府部门还可通过自媒体(如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与网络等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环境风险的种类、来源与应对举措,确保公众对环境风险“心知肚明”与“从容应對”;第二,丰富环境信息的交互方式。信息交互可有效加速信息增量与信息流动,可有效减少社会公众对环境信息占有不对称和信息互动不足而带来的熵增效应。就美国经验看,较为可行的信息交互方式包括搭建网上信息交互平台、畅通电话咨询渠道、完善案件举报方式等。第三,举办全国性或区域性的环境保护学习活动,藉由此类学习活动帮助广大民众认识环境污染的类型、来源与应对措施,鼓励第三方治理企业积极参与环境污染治理,同时引导民众使用更加环保的替代产品,藉此有效防治环境风险。
(三)健全环境保护立法与执法机制
立足于环境保护社会共治法治保障的现存困境,当务之急应着力健全环境保护立法与执法机制。首先,通过修订相关立法,逐步构建一个结构严密、功能齐备、内在协调的环境保护社会共治法律体系。其次,建立健全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明确案件移送的条件与标准、廓清衔接中的证据转化规则以及“健全不移送案件的刑事追究机制”[7],以有效遏制环保部门“有案不移”、“以罚代刑”等问题。最后,加强环境执法队伍建设,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环境法治工作机制,加强市、县级、镇(乡)环境监管执法队伍建设,同时注重引入新技术(如大数据、自动监控、卫星遥感)开展环境执法,为环境保护社会共治保驾护航。如此一来,政府在环境保护社会共治中的主导“正位”作用才能得到真正体现。
参考文献:
[1]蒋云飞,罗实,李金惠.社会源危险废弃物治理中的政府责任:依据、问题与合理界定[J].生态经济,2017(11):196-200.
[2]陈磊.废旧电池等成“毒源”家庭危险废弃物该往哪儿丢[N].法制日报,2017-06-22(3).
[3]蒋云飞.危险废弃物风险的社会共治及其制度回应[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88-93.
[4]王名,蔡志鸿,王春婷.社会共治: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4(12):16-19.
[5]唐绍均,蒋云飞.论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的履行障碍与相对豁免[J].现代法学,2018(2):169-181.
[6]【美】史蒂芬·布雷耶.打破恶行循环—政府如何有效规制风险[M].宋华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45-52.
[7]蒋云飞.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检察监督之完善—以最高检挂牌督办4起腾格里沙漠污染环境案为例[J].环境保护,2016(7):54-56.
作 者: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刘小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