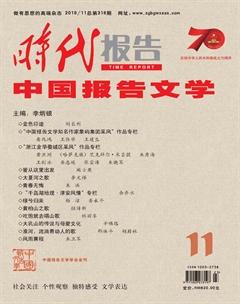不一样的枫树岭
余弃水
在淳安的最南部,有一片308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域,这里有淳安最高峰磨心尖,有四任省委书记的基层联系点下姜村,这里也有凤林港水电站,是千岛湖之外淳安最大的水库。从湖边湿地样的汪村、田畈村到坐凤林港溪而独具风味的滨河村源塘、下姜;从崇山峻岭,峡源深深的铜山到源头盆地的白马。其地理特色的多样性、多彩性,难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多姿多彩的样式,使枫树岭如同一块袼褙一样斑斓,没有奇異之处,但又不循规蹈矩。这里的流域,就像盆景中的树木,有着超人经验的不同,又无处描述其独特的存在。
白马与红马
白马进入我的记忆其实是与红色有关,那就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1934年几次从白马进入我县,在我县迂回,到过多地。长征之后,南方的地下党组织也是从赣东北来到白马发展党组织,一度还成立了衢遂寿中心县委,县委就立在白马的岭盘村。当我看到红军留在当地的标语文字时,内心其实是很不平静的。那一行行文字,写在墙上,觉得当年的那些年轻的生命立马栩栩如生起来,但与他们之间总有距离相隔,好像中间有一块银幕,他们在银幕上,我在银幕下观看。这种距离是很难填平的,不仅仅是年代的不同,更多的是意识的不同,他们是我们的英雄、先烈。白马因为有了他们和他们代表的历史,所以有诸多迥异之地,我自然会对这里充满着敬意,这种敬意放大了白马与自己经验中的不同,敬意总是要拉远心理距离。当我沉下心来,开始打量这块地域时,就发现了白马的地形地貌其实也有非凡之处,其地理元素也很了得。所以,心中对白马认知的不同多少来自红色的原因多少又是来自地理原因,真的说不清。
淳安高山众多,海拔千米以上的就有不少,但最高是属磨心尖,就坐落在枫树岭的白马与铜山之间。最高峰当然值得一说,当值得特书的不仅是因为这里的高,而是与这高相对应的缓所组成的“高与缓”的结合。磨心尖下的白马,恰恰是一个盆地,非常平缓,缓出了一大片土地,这平缓的边沿缓出了一拨村庄。到达这个盆地,却要经过弯曲狭窄的路程。因为有了这个盆地,当年也就有了一个乡。
遗憾的是我爬过不少山峰,就是未能登上淳安最高峰。最接近的一次是新世纪初,有一次在白马采访,准备登磨心尖。做好了充分准备,也叫了向导。准备登顶,了结个心愿。初夏的日子,其实很不错的登山时节。我们两人开始攀登,沿着山涧而行。据说磨心尖上是原始次生林,登顶还可远眺千岛湖。这些因素都成了诱惑,也变成了登山的动力。向导在前,我在后。在接近三分之一路程时,天气骤然变化,大雨马上来临。向导经验丰富,告诉我,停止攀登,往回撤退。撤退时还要往山岗方向移,虽然没有山涧好走,基本无路,但也得遵循向导的意思走。他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大雨天,一旦山洪暴发,我们会无路可撤。为了安全,我们放弃了这次攀爬。磨心尖,在梦里。后来就没找到机会,再后来机会都没了,膝盖已不能支撑长久的登山了。不能登高山可以在山麓转悠,走走白马,看看白马这不一样的地形。
我们的高中同学金幸福,在原白马中学的房子里办起了都市夏令营的场所。2015年下半年,我们一行十几个同学去看他。在白马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去走了几个村。其中有个村叫曲源头,就挨着磨心尖山脚。我们沿着爬磨心尖的方向走了好一段路,山涧水说有多清澈就有多清澈,几根管子连在溪里,是村里的自来水取水管。毛竹林、杉木林里面通透清新,这种感觉很不一般。村里不是新楼就是在建的新楼,在新楼上有挂上为攀登磨心尖做向导服务的。这高高的山和这山上的空气,本来是搁置山野无人问津的,谁想得到呢?贵与贱分界线在哪,什么叫此一时彼一时呀。
在白马我们还可以轻易发现除了这对“高与缓”之外,还有一对“新与古”,那便是新房与古树。在这里的每个村行走,你都会不期而遇地碰到几百年的古树。有银杏、香榧、枫杨等等,这些古树守护着的村庄,看起来不老,不起眼。但从古树身上轻易看到了,这里居住的久远。村庄其实也很古老,与古树同龄,只不过有的村可能换了一拨又一拨。古树忠诚地守卫着,经历着风吹雨打,留下不一样的沧桑密码。与常山交界的村叫凤凰庙村,跟那边村的房子基本是挨着了,这种边界的意味很有味道,但更有味道是村里的两根古树。两棵八百年的香榧伫立在村口的路两边,左右各一棵,如忠诚的卫士。满身的沧桑感,树枝与树梢如同被雷电撕扯过一样,像老人历经千年风霜,像年轻人的头发另类形状。横山庙村的枫杨树煞有风景,落尽叶子的枝条曲里拐弯,横竖无序,映衬在蓝天;下午的太阳从西南方向斜照过来,经过两边山的分切,光芒的形象额外清晰,有的经溪水的折射,加上微微的水气,如梦如幻的气息立马呈现,光影的迷幻样子俨如仙境,令人眩晕。
让人意外的是像乳洞山村这样的高山村,也有古老的苍天古香榧。这个村坐落在海拔650米的半山腰,整个村庄成簸箕状,朝正西。在村里看日落觉得别有风味,当日头接近西边的山头,夕阳横扫过来,整个白马盆地如同埋在夕阳之下阴影里,只有乳洞山仍在阳光照射中,这是白马最后一个送走太阳的村落。黄昏时分,我走进了吴约木家,他正在蒸蕃薯干,家里舍外弥漫着红薯的香味。家里的薯干没得成形就已定光,我也买了十来斤,也是因为上门了,近水楼台。这个村一年生产20万斤的薯干,成了重要的一块收入。2010年是白马薯干的转折之年,这年他们在加工上有了提升,摆脱了传统的粗糙制造,使白马与薯干之间的关系不可分离,白马薯干成了一个响亮的名词。是白马选择了蕃薯还是蕃薯选择了这块土地,这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白马人将贱变成贵的不断筛选。
红色白马出红薯,红薯干香飘万里。白马其实是红色的,本来也是红色的。曾经确实叫过红马,1958年人民公社的时候,叫大墅公社红马管理区,但到了1961年又恢复了白马,叫白马公社。白马的来历,传着一段很浪漫有趣的传说,红马尽管有当时政治意味,但如果一直叫红马我想也不会差到哪去。
真正的红马是一个人,在下姜,现任下姜村党总支书记杨红马。认识他大概在2002年前后,那是去下姜村采访,他还是个村委副主任,那时的村支书是姜银祥。杨红马年轻,看上去非常青涩,他养着好多蚕,是村里种桑养蚕的带头人。当时给我印像很深,因为他的名字很有趣,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很有趣,一瞬间就把其与白马联系起来,没有一点点道理。后来得知他当书记了,立马觉得:杨红马,不当书记行嗎?这名字好像天生是当书记的料。2015年,枫树岭采风活动,来自省内的作家诗人,三、四十人,其中很重要的一站就是在下姜。在会议室里,杨红马要向作家们介绍下姜的情况。我当时想,我得看看曾经青涩的红马书记如何开场。他开口了,我听着听着,觉得既没有拿腔做调,也没有支吾怯场,他表现得很好,让我刮目相看。
杨红马,与下姜的表现相一致。
下姜与上江
上江与下姜都是以姓氏取名的,但它们之间不是对应关系。下姜以姜为主要姓氏,下姜有一个对应的小村叫上姜;而上江在附近并没有对应的村叫下江。但我总觉得下姜与上江似乎是一对,叫起来特别的亲切,听着很让人以为是对应关系。可能它们之间确实有着一定的联系,两个都是枫树岭镇的精品村,而且这两个村在过去都有一个顺口溜,来嘲讽自我。听来很有意思,也从中可以感到这两村在从前岁月的潦倒。顺口溜在当地很是有名,有时成为一种毒咒一样,在民间生长,很叫人难受;有时又是一种鞭策,让村里人时时提醒自己,成为改变面貌的警句。
为何这两个村有顺口溜呢?一方面说明从前岁月的艰难,另一方面也表明这村在当地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村。毫无影响力的村也不太引起人的注意,能让人注目的村才能教人记得深刻。说下姜的顺口溜是这样的:烧木炭,住茅房,半年粮,有女莫嫁下姜郎。其实在从前又有几个村不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呢?单拿出这下姜村来说事,说明这个村还是有好些容易引人注目的地方。2000年之前,我们也经过下姜村,乘车从汾口来千岛湖沿淳杨线必经下姜,那时的下姜不太让人关注,没什么特别值得让人关注的东西。后来慢慢声名鹊起,与几任省委书记的基层联系点有关。这些都是下姜村变化的重要动因,大家都看到了。甚至还成为了一个榜样,成为一个教育培训基地。这个村过去纯粹做农业条件并不很好,但谁又能否认它的审美要素呢?
凤林港一路走来,到了下姜拐了几个弯,河道成了S形,看起来很有形象感。我们登到对面的山上,看下姜,那个在村里的弯,使下姜村三面环水。现在河南岸的房子渐渐多了,让溪在中间蜿蜒,美丽的新房以传统黑白调为主色彩,廊桥连着两岸。江南山村的村庄韵味,让人眼前一亮。溪流、岸坝、老村的缓坡,村后的毛竹,对面的绿林,所有的这一切都让这个山村呈现诗画的样态。把山村的特色推上“台面”,使村庄的美凝固成一种不可改变与复制的模式。使凤林港与村庄结合得更为紧密,成为村庄的重要部分。据说,为了让凤林港的水位恢复到从前的水平,枫树岭水电站正在改造,使其发电的水流入凤林港。这样的改变会让下姜村的那段溪流的溪水更为丰润,临溪而居的样子更为突出。
凤林港流过下姜在其村尾流入了一个密境,溪流似乎在这里消失或者断掉。它流进了五狼坞峡谷,这个峡谷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段,也是枫树岭与大墅的交界之地。峡谷两岸山势陡峭,高山巍峨,背后就是大墅的公山尖。峡谷内植被丰厚,绿色世界,满眼苍翠。溪中,各种型号的鹅卵石,星罗棋布,在这里看溪就如同走入比较原始的生态环境。如果说凤林港是一根长长的带子,那么五狼坞就是一个结。如果说凤林港是一株修长挺拔的松树,那么五狼坞就是一个(节),五狼坞让凤林港作为河流上升了一个档次,使下姜村变成不凡的一个基座。下姜因为有了它,而使其地理上十分突出,可以有所述说。
下姜还有葡萄,这葡萄有什么好说呢?因为它们有着不一样的来历,有着不一样的过程,承载着不一样的使命,所以也有不一样的甜度,传递着不一样的情怀。这几个农业基地,是杭州农业科技人员帮助发展起来的,其中100多亩的葡萄基地是其中之一。所以葡萄的甜蜜便有着不一样的滋味,这种甜,恰恰契合了一种情分。如今这葡萄承包给了麦冠公司,李总问我如何改变面貌,我说在最显眼的地方写上四个大字:葡萄传情。
与下姜相比,上江的顺口溜完全演变成民谣了,也更为损人:
你哪里的?
我上江。
你做什么?
我买糠。
你喝茶吗?
我早上吃粥汤。
你坐一下吧。
我屁股上生羊胡疮。
这个有情景,有细节的民谣可以说把上江损得体无完肤了。为什么编排出这样生动的段子,一定有不为人知的原因,估计从前是比较艰难的,百姓生活较苦。
其实上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地理要素非常了得。按淳安人的风水要求,是经典的簸箕形。村后的那座山,是一个半圆弧形,把整个村庄环进怀抱,三面都被其抱牢,这种规正的圆形山应该是很少见的,非常漂亮。以前乘车路过,看不到村庄,只见几株古树,要走上两里路才能到村。我在这个村住过一晚,走过这座山。这座小山其实类似于半岛,后面有另层更高大的山,这小山与大山之间的关系,就是像大山身上长出来的一个岔道。小山与大山之间构成一个小流域,有一山涧,其出口在村庄三里开处。
这种一层又一层的山势,造就了特别的地理,几百亩梯田在云雾处,有曾经香火旺盛、晚钟回荡的寺庙在山上,已湮没在荒草杂柴间。
上江村是一个很古老的村,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江氏人口与村庄同龄,这么长延续不断的村庄,在淳安也不是太多。这种古老又与新时代发生了反应,形成了新的形态,在新农村建设领跑在先。
山涧清泉欢腾跳跃,青山碧岭画圈伸展,清清溪流粼波荡漾,幢幢新楼描绘风情,民风似金的秀美山村,构成了一幅上江图。
铜山与铜山口
铜山的古老其实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个地名的来历一目了然,是一个矿石丰富的地方。最早在唐朝就开始开矿了,那时可能主要是挖掘铜矿。在淳安锡铁矿废弃的矿区,庞大的生产设施与生活设施,可以彰显曾经的兴旺。在一个岩壁上,留有唐朝天宝年间的刻字,依稀可见。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矿区,从铜到铁到锡,断断续续一直未断,直到前几年,因矿石枯竭而废弃,留下空旷、败落与怅然。在铜山矿区,历史上还出现过多次矿工起义的事件。当年的矿工,是在如何条件下劳作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将铜山的矿石运出去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与此地的地理因素有关,没到过你想象不出当年的出口是怎样走的。
地处凤林港上游的铜山,按正常逻辑是沿溪,顺流而下,往流域的出口走出去。交往也是这样,顺流而下自然而然。但铜山不是这样,它像一个被封死的胡同,基本独成一体。铜山里面几个村,都是嵌在大山的皱褶里。里面山高林密,溪流曲里拐弯,不断的迂回。在这样大山深处,那么一瞬间觉得置身异域。尤其是开化有个叫茂新的村插在其间,将枫香埂、大源、西坑三个村隔在更远的“深处、源头、天边”,这种异域的感觉更为突出。
冬日的大源,一派闲散的样子。人们晒着太阳,聊着天。也有老人在劈柴火,好多人門前都是整齐的柴柈子,煞是好看。那种乡村与农家的特别味道,伸手可掬,临近年关的感觉十分明显。往左前方望去,连着磨心尖的巨大山体,在太阳照耀下,闪闪发亮。我们模仿着村民的样子,看这里的一切,看四周的山。那种置身很遥远的感觉特别强烈,如同一个孩子被父母放置在很远很远的人家。但同时也觉得,被关在一个独立空间,也心生轻快。
铜山是这样一域空间,原乡政府所在地叫铜山村。但与之对应的铜山口村,却不在流域的外边。铜山口村是原夏峰乡政府所在地,处在丰家源流域。很早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村叫铜山口,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叫铜山口。当时似乎也感觉到与铜山有着丝丝屡屡的联系,但不知是什么联系,由于没有深究的习惯,也就放弃了。三十多年前,还是十几岁的时候就到过铜山口。我高中同学金幸福就住在铜山口,那时我每年正月都去他家。他父母都是外地来淳工作的人,不是本土人。他就住在夏峰初中边上的一幢房子里。丰家源溪从旁而过,溪水清得让人不忍洗手。后来那个房子卖掉,住到建德父母亲老家去了。我也没再去过铜山口,估计金幸福工作在沪,到出生地的机会也屈指可数。2015年他投资白马,也算是回馈了家乡。即便这样的关系,我也没深究为什么这里叫铜山口。
铜山与铜山口不处在一个流域,确实是个奇怪的现象。它们之间隔着一座山,需要一条道将它们联在一起。这条道叫盆家岭(也叫盆公岭),从铜山口翻越盆家岭的古道很有气质,在过去这已经相当于而今的国道了。石头砌得很有规律,一米五左右的路子走在上面你会觉得很闲适。大多地方因现在走的人少了,都被青苔包裹。路边废弃的亭子,整个被一种腾裹得密不透风,墙就像自然生长在哪里的石头一样,满身绿色。岭顶的几株红豆杉高大,古老,传递着古远的信息。树下的房子,只剩一堵墙,墙在风雨中的坚守,其实是在卖力地告诉你看不到的一切:这房子所经历过的岁月。岭不算高,十几里长度,按当地的说法叫上七下八,也就是说从铜山口爬上去七里,那边下去八里。但事实上最多十里,当地人走走就一小时,快点50分钟。这个说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铜山口为基点的。这个古道成了过去铜山人唯一的出口,这道也成了千年古道,所以把地处丰家源流域的这个村叫铜山口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为什么铜山不顺流而下走出通道,而是拐弯越岭把夏峰当其出口呢?铜山的余村以下近十里是没有村庄的,是峡谷地形,两边悬崖伫立,中间仅容一条溪穿过。过去连一条羊肠小道都没有,这样的地形也就注定了铜山人失去了与外面凤林港沿线村庄之间的交流。他们与夏峰交流就成了常态,虽然隔着山,但铜山与夏峰说着同样的话,走着同一个岭,亲戚血脉相联更紧密。直到六、七十年代后,由于开矿的需要,沿溪开了公路,铜山通公路了,这种顺流而下的交往才渐渐多起来。但在无车的时代,这两地的交往还是十分密切,不仅是地理要素相近,心理距离也亲近。
同样的方言,是因为从前是一个都,遂安九都。十分有特色的铜山、夏峰话,在民间也往往成为一种符号,识别哪里人的重要标志,有时也是学逗的重要材料。方言把这一域的一群人给框在一起了,这群人同音同腔,散发着其特有的情感。过去九都沿丰家源流域也只管到现已移民江西的程家村,所以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捡了铜山、鲁家田,丢了沿店、薛家源。鲁家田、铜山是铜山流域的两个村;沿店、薛家源是丰家源流域最外面的两个村,已不属于九都了。这话轻松如戏言,但也从另一个则面道出了铜山与夏峰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难以分离。把它们联在一起的就是这条古道——盆家岭。
盆家岭不说车水马龙,也可以说往来熙攘。古代的矿石也是通过这条岭往外运输,矿工的脚步一直在古道上回响。到了七十年代好多挑矿石的队伍也是在这条古道上来往,矿石挑到铜山口又挑到薛家源码头,然后运往姜家的淳安钢铁厂。这些队伍是由青春横溢的人组成的,他们也会制造许多爱情,与沿线的村庄发生着关系。这条线路是那一带很有名的线路,从铜山出发的货物都是沿着这条线走出去。在过去还有一个事,可以强化这条线的理所当然。
过去集体化时代,我们淳安山区都有供应粮提供。当时枫树岭、夏峰、铜山、白马四个乡,也就今天枫树岭范围,他们的粮站很有意思的是办在沿店村,而并不是办在枫树岭或者别的哪个乡府所在地。很明显,在这里考虑到了铜山一带的村民,沿盆家岭到铜山口到沿店这条线路的方便,当然枫树岭、白马到沿店也没远起来。还有一点就是也考虑到了薛家源码头起货运输的方便。
铜山与铜山口,不在一个流域的对应关系,它们挑起的不仅仅是两个地名的使命,而是两把钥匙,打开一些地域密码,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