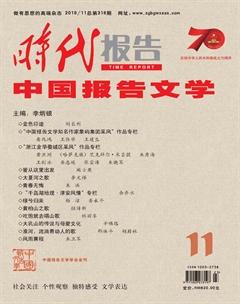和陈新华大师喝茶
陈大师的茶不佳,但陈大师用来招待我们饮茶的器物不得了。这是一个时阴时晴的上午,有时还下点小雨,天气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变幻不定。我们在陈大师的工作间里坐下来,羡慕地看着大师面前每一个茶盏都呈现出一种制式大致相似细节却大有不同的奇光异彩。这是婺州瓷的光彩,却不是所有婺州瓷的光彩。我们刚刚走过展览厅,看到了已有两千年历史的婺州瓷穿越时代风烟展现了它们不朽的风彩,更看到了陈大师和他的多位高足们在我们厕身其中的这个时代的新作。坦率地讲,我在偏重于食用瓷的古代婺州窑的作品中没有感受到过多的激动,倒是大师和他的门徒今天的作品让我有了一种不惜重金购买它的愿望——当然没有买,一大群人参观一位工艺美术大师的工作室,熙熙然,轰轰然,也不是我这个侃价好手施展拳脚的地方——想购买是因为它们横空出世般的精美,是他们那种如同千古文章般的光华射目,是眼眸之光和它一加碰触便知道遇到了绝代佳人式的激动和另一种要和它亲近并且长相厮守的强大欲望。
还是说喝茶的事情吧。我们这一行人,远道而来,像一群羊一样被领进了大师的领地,大师的王国,也是大师人生的樊篱、狱所、无垠与无尽藏。大师手上仍然粘染着釉彩,满面笑容地接待我们这些对婺州窑知之甚少甚至闻所未闻的不速之客,甚至地方都没有挪,就在他的一尊正在完成的作品前坐下喝茶。大师解释茶是徒弟家自产的土茶,可我们想知道的却是他面前这些一下就夺走了我们全部注意力和惊叹的茶具,我们姑且称它们为婺盏吧。大师边亲手为我们泡茶边为我们释疑解惑,说这些精美绝伦的婺盏之所以个个焕彩不同,是他近来恢复传统婺州瓷烧制技艺的一种尝试,两千年来婺州窑使用的都是龙窑,用的是木柴,现在几乎所有烧瓷工艺都改用天然气,因为受热均匀,烧出的瓷器千篇一律,再没有古时因为木柴火受热不均造成的千奇百怪的窑变。古时烧出的每一件婺州瓷都是天下唯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即便是鬼神也不可能控制窑火烧制出光彩完全相同的两只婺州瓷器,不久前他下决心改掉天然气,回头使用龙窑和木柴。这些婺盏就是他恢复古法造出来的,每一只都像古时的婺州瓷一样是天下无双。这些话让我这个此刻仍然心猿意马的门外汉擎着一只婺盏饮茶的手不觉紧张起来。也许一只婺盏并不珍贵,但天下唯一就珍贵了。一位说话直率的同行人脱口便问大师这只婺盏值多少钱。大师没有回答,脸上现出一种难以言说的表情,但回答我已经听到了,这是不需要问的,在他心里这每一只婺盏都是无价之位,还是因为那四个字:天下无双。
我们就随便地和大师聊起了他的经历,很快就惊奇地发现大师和我是同时代人,只小我一岁,1955年出生,生在我们那个时代,基本上不可能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从幼儿园小班一直读到大学甚至博士,但他们那個年代也自有那个年代的丰富性。我没有听清大师讲他是不是读完了初中,总之很早就失学进入了婺州窑工作,在不止一位大师身边做学徒。已经不是旧社会的学徒了,入门后先要络老师傅倒夜壶,那个年代众生平等,师父和徒弟先是同事,然后才是师徒,但这样一种情境既没有妨碍他向身边太多的大师苦心学艺,也没有影响大师们无私地将他们的绝活一点一滴悉心传授给这位徒弟。不仅如此,因为这位学徒的勤奋好学,还有他从那时就表现出对婺州瓷与众不同的热爱与创新精神,厂子里的领导开始重视他,不惜脱产让他进入浙江美术学院接受正规教育。大师说虽然只有两年时间,但在他的人生中却意义重大,这是正规的学院教育和传统婺州瓷制作工艺的激烈碰撞,更让大师得到了古今中外美术理论的系统学习,在那个年代殊为难得,于是也就成就了他高于没受过正规教育的同代人的视野和学术高度。重新回到婺州窑的大师已经不再是吴下阿蒙,而是一位在婺州瓷的继承与创新方面有着清醒和自觉意识的年轻艺术家和工艺师,看山仍然是山,但山外的山,天下所有的山也都在心胸之内了,一种一览众山小后回头再看山是山的意境,于是一位高级工艺美术师,一位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婺州窑传统烧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出现了,他的作品开始一骑绝尘,以连续12个国家级金奖的煊赫成就惊动了前辈和同代。到了今天,大师不但成了浙江省青瓷中青年十大名师之一,浙江省优秀文艺人才,金华市劳动模范、浙江省青瓷行业协会副会长、金华婺州窑陶瓷研究所所长、浙江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还在2018年登上了人生的最高境界——被评为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茶喝到这个份上,所谓幽赏未已,高谈转清,话题自然就转到了大师目前的生活和创作。无论得到多少荣誉,大师这些年的创造仍然一天也没有停止,每一件重要作品的问世都会引起天下人的喝采,并且马上具有了价值连城的身价。大师叼生命与创造之火仍在熊熊燃烧,更惊动人心的作品仍在不断问世,但是大师的表情显示他并没有因为这些志得意满,相反却显现出了某种发自内心深层不愿表现出的真实的苦恼与焦灼。是的,是焦灼。事实上大师这些年的心血已经更多地泼洒向了向新一代传递婺州窖制作工艺的薪火。在培养徒弟方面大师也被公认为是成功的,他告诉我们出师的徒弟已有三十多位,名震全国的就有八大高徒,其中三位甚至和他一样也进入了工艺美术大师的行列。他的苦恼和不时显出的焦灼在于他觉得这还远远不够,他对婺州瓷的历史和今天的研究,他对这样一种已经拥有两千年历史的中国古瓷制作技艺的热爱,让他觉得无论是他还是政府以及更多民间人士都应当投入更大的力量去发掘、培养、光大婺州瓷尤其是能够继承将这一脉断而复续不绝如缕的工艺的人才。他似乎不由自主地说出的一句话引起和这位一直心猿意马听他讲话的饮茶者的注意:他说还是要有文化。婺州瓷不上是一种技艺,我的徒弟中只要上过大学,有过正规教育经历,他的创造力就大不一样。没上过大学的徒弟也能把前代的作品复制得惟妙惟肖,但创造力不行。倾尽毕生的经历,他的感慨是一门技艺不管有多么久远的历史,真正的生命力仍然活在和时代同步的创新精神、能力和作品之中。一个时代需要一个时代的婺州瓷,不给婺州窑注入新时代的生命它就没有未来。一位熟悉情况的朋友这时就插话道当下政府部门正在准备帮助陈大师开办一个为期半年的学习班,以培养更多未来的婺州瓷工艺人才。大师没有说话,我这个对旧时代师徒关系及其人才成长意义略有研究的人却一时冲动脱口而出说学习班不行,还是过去的师徒关系,徒弟要进入师父的门,先学着给师父倒夜壶,啊他最好像大师本人一样,上过大学再来拜师,日近师父之身,耳濡目染,不但学技艺,更重要的是要观察学习师父生命的全部,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乃至于形容变化,喜怒好恶,理解他每时每刻都在想什么,为什么那么想,沉入到师父的生命深处去理解他,而且时间要长,最好要有十年,不知不觉他就变得像师父一样想事情和做事情,再后来他就会变成另一个师父。归根到底,我们不是需要更多的技工,而是需要更多具有时代创新精神和创造力的大师。大师一直没有说话,我以为他不会再说什么了,但我错了,他突然喃喃自语起来:愿意学的人不少,文化高的不多。文化高低决定创造力。真正愿意用一生的时间做婺州瓷的人更少。我们要造世界上最高级的瓷器,无人能及的瓷器。我们有这个能力的。大师这一瞬间目光辽远,越过窗户望向远方山野,似乎那目光里也有了一层雾,但很快就转化为一道犀利的光辉。我想到了,大师也许在想,只要有了人才,大师之后还会大师,更多的创新,更美的器物,婺州窖和婺州瓷连同它们所代表的中华技艺就不会再像历史上那样断而复续,就能和天地一样长久。
告别的时间到了。大师和我们一行人照相,挥手告别。像每一次旅行一样,我们是大师接待的又一批来访者,大师则是我们旅行中无数风景中的又一道风景。车子远远离去,我不觉回头望去,大师和他的工作坊只剩下了一座青山和一片白云。我已经开始忘记大师了,却信马由缰地想到了另一件事: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让婺州窖的产品走遍世界,让全世界每个国家每座城市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都以拥有一套价值连城的婺州瓷并以此为荣耀,这是大师之志,但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民族复兴吧,何况我们今天有了“一带一路”。成为一名大师其实是一种修行。大师的与众不同就在于比起师古,他更注重的是出新;比起技艺,他更看重的是创造;比起传承,他更注重的是发扬光大。民族复兴当然是精神的复兴,但也非常可能是器物的复兴,器物的复兴又要靠天、地、人,还要不排除与国内外同行进行激烈的创新层面的竞争。思绪这样流淌下来居然有点汹涌澎湃的意思了:器物是什么呢?它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与物化,也是它生生不息的传承,在历史文化的意义上,器物的创新和流传对于中华文化精神的永世长存可能比一时的言说甚至古物与书本更为重要。
车子走得更远,现在连遮没了大师工作坊的青山和白云也看不见了。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作者简介:
朱秀海,当代作家、编剧。河南鹿邑人。满族。中国作家协会第八、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笔会中心会员。曾任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主任。文学创作一级。作品曾获第二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四次)、“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全军长篇电视剧金星奖一等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两次)、中国电视剧金鹰奖优秀长篇电视剧奖(两次)、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长篇电视剧奖(三次)、首届首尔国际电视艺术节最佳长篇电视剧奖、第三届电视剧风云盛典最佳编剧奖、中国电视艺术五十周年全国优秀电视剧编剧奖、冯牧文学奖等。长篇小说《音乐会》2015年入选《百种抗战经典图书》。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入选“2017年度中国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