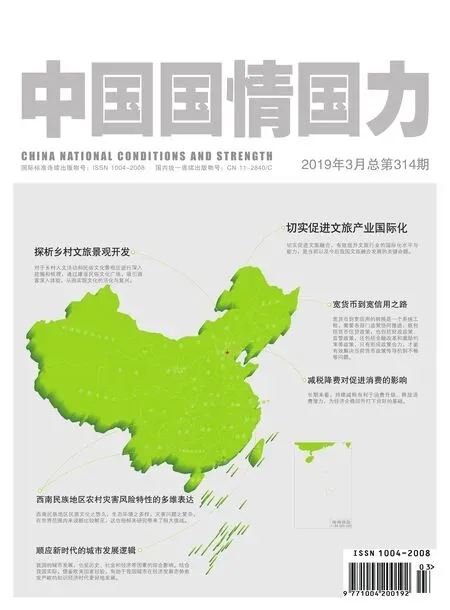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灾害风险特性的多维表达
◎商兆奎 邵侃
灾害学研究表明,自然灾害具有明显的区位特征,源于区域灾害系统中孕灾环境、致灾因子和承灾体的差异及其相互作用力的强弱不同[1],灾情的频次和程度在不同区域变化很大。特别是对于我国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而言,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的局限,自然灾害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更为严重。本文所关注的区域——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恰恰是“民族”“贫困”和“农村”三者高度叠加的场域,故而灾害问题相较于其他地区更为突出。
西南民族地区自然环境复杂,自然灾害种类多,发生频次高[2],其中旱灾、洪涝、冰雹、大风和冰雪冻害是排位前列的主要灾害类型,其发生频次呈现逐年加快的发展态势,并且近些年来灾区范围不断扩大,灾害强度不断增大[3]。特别是农业重大气象灾害多发、重发,抗灾能力偏弱,地域性、链网性、突发性和危害严重性是其主要特点[4]。进入新世纪,这一地区洪涝等级以重级为主,2010年以来连续多年出现特重级洪涝;干旱灾害风险格局模式具有明显的地带性和复杂性,近60年其范围、程度和频次均呈增加趋势[5];由于山地面积比例高,地质灾害尤为突出,主要灾害类型为崩塌、滑坡及泥石流;地震活动极为频繁,曾发生过多次强烈地震,云南和四川是地震灾害严重或较重的区域[6]。从灾害成因来看,往往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的敏感性和易灾人口的脆弱性则进一步放大了灾害的破坏力。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大量经济损失和人身伤亡,以及救灾减灾机制的不完善,使得这一地区低收入农户极易陷入贫困和返贫状态[7]。
致灾因子的复杂性和高风险性
致灾因子是指可能诱发各种灾害后果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集合,一般而言灾害后果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型。而就本文的主题而言,研究范畴仅限于自然灾害。对于自然灾害来说,其致灾因子是可能引起生命伤亡、财产损失和资源破坏的各种自然因素,为地理、气象和水文现象,是极端的自然现象或自然事件。结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分类,自然致灾因子主要包括水旱、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生物和林火等。通过资料搜集和整理发现,西南民族地区自然致灾因子包含上述所列所有类型,水旱致灾因子主要有洪涝和干旱;气象致灾因子以低温冷冻、冰雹、大风、雷击和大雾为主;地质致灾因子包括滑坡、泥石流、崩塌、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等;生物致灾因子主要有虫鼠、病源物和杂草;海洋致灾因子主要在广西自治区境内,以风暴潮、海啸、海浪、赤潮和海雾为主;此外还包括地震致灾因子和林火致灾因子。
西南民族地区自然致灾因子不仅存在类型的复杂多样性,更为严重的是,其所具有的高风险性甚至是不可控性的特点,往往会诱发频次高、强度大和影响大的自然灾害。如贵州省境内地形地势多以山地、丘陵和盆地为主,平均坡度17.8度,喀斯特地貌面积达全省总面积的61.9%,地质灾害点达3万多个,洪涝、干旱、滑坡、泥石流、崩塌、地裂、冰雹、雷电、大雾及病虫害等致灾因子广泛存在,而且致灾风险极高,导致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重发,是全国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据统计,贵州全省9个市(州)88个县(市、区)近年来每年都有重大灾害事件发生,各灾种平均每两周发生一次,年均超过100次,远远高于全国每年平均19次的水平[8]。而且极易导致灾害链,主要有“暴雨洪涝-泥石流”灾害链和“暴雨洪涝-滑坡”灾害链和“暴雨洪涝-泥石流-水土流失”等,灾害类型的多样性和灾害链的存在,往往造成灾害后果更加严重,损失更大。贵州省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一般年份在70亿元左右,重灾大灾年份超过200亿元。四川省同样也是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境内原生环境脆弱,地质地貌复杂,气候多变,水旱、气象、地质及地震等致灾因子多类多样,其中地质灾害隐患点多达3万余处,占全国15%左右,70%的区域处于较高地震烈度区,因而导致大灾频发多发,灾害损失异常严重。近10年来,四川省相继遭遇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2013年“4·20”芦山强烈地震、2014年“11·22”甘孜康定地震、2017年茂县“6·24”特大山体滑坡灾害及2017年“8·8”九寨沟7.0级地震等重特大自然灾害。据不完全统计,四川省近10年来发生的自然灾害已造成约2亿人次不同程度受灾,近9万人遇难和失踪,直接经济损失超万亿元[9]。再如云南省,自古以来就是“无灾不年、十年九灾”的省份,由于气候类型多变、地形地貌复杂和地质地理环境特殊,自然灾害高发频发,水旱、地震、泥石流、低温冷冻及冰雹等是最典型的灾害类型,并且灾害链特征及趋势日益突出。1991年以来,全省每年因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都在30亿元以上。2008-2013年,各种自然灾害累计造成1.5亿人次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292亿元,平均每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超过200亿元,相当于云南省每年经济总量的5%[10]。
区域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易损性
从20世纪80年代“脆弱性”概念提出之后,就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但是对于生态脆弱性的概念,学界众说纷纭。一般而言,相关研究往往将脆弱性描述为三个基本特征:特定的人、地方或体系暴露在威胁之下;这(些)人、地方或体系对这个(些)威胁的敏感性;这个(些)地方、人或体系抵御冲击、应对损失和(或)恢复功能的能力[11]。
生态脆弱性是指特定的区域生态系统暴露在威胁之下的敏感性和恢复力,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是基础,自然脆弱因子的存在不一定意味着所属生态环境一定脆弱,往往是遭受了外界因素特别是人为因素的干扰之后,造成生态环境的正常功能被打乱,超过了自我调节的弹性“阈值”,进而引发一系列生态功能退化、自然灾害衍生等问题。2008年印发的《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简称《规划纲要》)划定了全国八大生态脆弱区,西南民族地区就有其二:西南岩溶山地石漠化生态脆弱区和西南山地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前者生态环境脆弱性主要表现为:土层较薄,肥力瘠薄,人为活动强烈,土地严重过垦,土壤质量下降明显,生产力逐年降低,丘陵坡地林木资源砍伐严重,植被覆盖度低,暴雨频繁、强度大,地表水蚀严重;后者生态环境脆弱性主要表现为:全年降水量大,融水侵蚀严重,而且岩溶山地土层薄,成土过程缓慢,加之过度砍伐山体林木资源,植被覆盖度低,造成严重水土流失,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频繁发生。同时,《规划纲要》也指出,生态脆弱区的形成除生态本底脆弱外,人类活动的过度干扰是直接成因,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人地矛盾问题、检测与监管能力低下与生态保护意识薄弱等。西南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会导致抗外界干扰能力偏低,自身稳定性差,对于人类活动的介入尤为敏感,容易产生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区域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极易导致易损性,易损性通常指易于遭受自然灾害的破坏和损害。按照人类生态学的观点,人和聚落的易损状态是自然灾害形成的重要原因,因为自然灾害是自然现象与相关的社会易损状态相结合的结果[12]。西南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易损性特质,同样也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无论是房屋、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等财产的易损性,还是作为承灾体的人的易损性,都不难看到社会决策、社会行动等人类行为在其中打下的烙印。在自然灾害研究领域,易损性被定义为暴露程度、应对能力和压力后果的综合表现,而应对能力被认为是易损性的决定性因素[13]。
脆弱性和易损性,是“风险”这个复合概念体系下的两个核心内容,风险可以通过脆弱性和易损性作用于承灾体,如果恰恰承灾体如西南民族地区一般应对能力有着先天劣势和后天不足,就会诱发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因而,社会经济规划者以及灾后一线人员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脆弱性是减少风险的关键性因素,这种认识在国际减灾战略的大环境下也被广泛认可[14]。
承灾体的弱势性和弱质性
承灾体是指直接受到灾害影响和损害的人类社会主体,主要包括人类本身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如工业、农业、能源、建筑业、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各种减灾工程设施及生产、生活服务设施以及人们所积累起来的各类财富等[15]。对于承灾体的分类,学界划分标准不一,一般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人”和“物”两大部分,“人”就是自然灾害所危及的所有人,包括人的群体和个体;“物”主要就是财产和资源两种类型。灾害学研究表明,仅有致灾因子和承灾体两者其一,或者两者同时共存而没有发生相互作用,均不能形成灾害,只有致灾因子直接或间接作用于承灾体,并在这种异动反馈的综合运动中方能形成灾情。不能否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尚不能消灭致灾因子,所以承灾体的灾害韧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灾情的大小和强度。就西南民族地区而言,无论是作为承灾体的“人”还是作为承灾体的“物”,相较于我国其他地区,其弱势性和弱质性更为突出和明显。
人的个体和群体是灾害面前最活跃也是最脆弱的承灾体,面对灾害,所有人都处于弱势地位,而先天不足后天乏力的西南民族地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一,防灾减灾意识淡薄。广大农村地区是西南民族地区自然灾害的主要发生场域,而作为当事人的农村居民大都缺乏灾害风险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把灾害当做小概率事件或不可抗力事件,较少注意防灾减灾知识的学习和储备,也基本不会进行日常应急物资的储备,灾害来临时也就很难正确地选择有效的自救或逃生方式。防灾减灾意识的淡薄还体现在农村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过垦、过牧、过伐等对于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和利用,造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人为因素成为灾害发生的重要推手。可以说西南民族地区自然灾害愈来愈重,损失愈来愈大,与本区域农村居民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密不可分。其二,防灾减灾主体的弱质性。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山区、半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发展空间有限,因而青壮年群体大都远赴都市打工,留守人员大多为老弱妇孺。自古而今,青壮劳动力都是防灾减灾的主力军,是村寨安全和稳定的基石。但是当他们大量输出造成农村空心化这一普遍现象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老年人、妇女被迫走到防灾减灾抗灾救灾第一线,其效能势必大打折扣。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灾害预警和灾害信息传递往往通过现代互联网工具如智能手机、电脑等进行,而本就文化水平不高、经济条件又有限的村寨老人、妇女和儿童在信息化工具的使用上处于弱势地位。这样一种状况不仅使得他们无法高效地参与到防灾减灾体系中来,而且一旦灾害来临反而极有可能失去自我保护能力,成为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体。
“物”的“双弱性”集中体现在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农村防灾减灾公共设施建设的滞后性,是一个普遍问题,而西南民族地区尤为严重。该区域最主要的灾害类型是暴雨洪涝和干旱,而从目前来看,防汛抗旱水利基础设施仍非常薄弱,大江大河及重要支流防洪治理能力仍然较低,“五小水利”工程覆盖面不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灌溉“最后一公里”问题较为突出。另外,应急救灾物资库多设在中心市县,而民族村寨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严重制约其救灾减灾效用的发挥。除了公共设施之外,农村住房大多为村民自己设计并建造,多数没有考虑也没有达到防灾减灾标准。对比2008年我国汶川8.0级地震和2010年智利马乌莱大区8.8级地震发现,前者造成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而后者只造成1279人死亡或重伤。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差异,除了震源深度的因素外,根本原因在于汶川地区建筑物的脆弱性远远高于智利[16]。
结语
西南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之悠久,生态环境之多样,灾害问题之复杂,在世界范围内来说都比较鲜见,这也给相关研究带来了极大挑战。从人类历史时间尺度来看,自然灾害问题是自然运动和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对于这一地区灾害问题的研究,一条基本的主线就是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以及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依存和协同演变的作用机理,在反思与调试中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在此之前,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明晰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灾害风险的特性,对于自然灾害系统的结构性要素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和判断,方能为相关研究奠定基础。
近年来,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随着承灾体越来越复杂,各种不可控因素越来越多,灾害风险也在不断累积和加剧,而防灾减灾能力不足的问题将会日益突出,这是我们必须要认清的一个基本事实。因此,加强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灾害风险关注和研究的力度,有助于提高全社会对于该地区灾害风险治理重要性的认识,并且可以为农村防灾减灾体系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