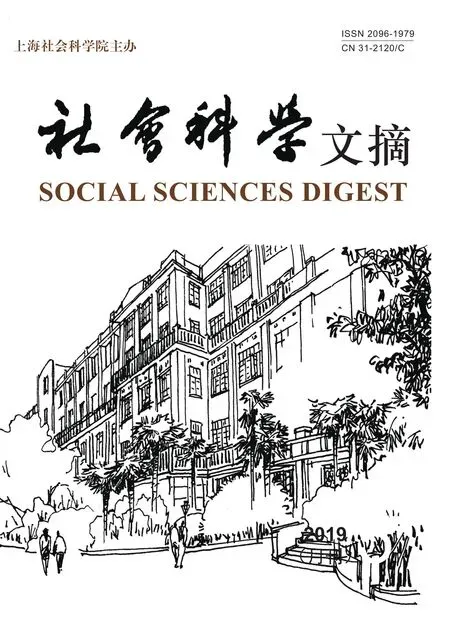中国经济学派别:观察与思考
——中国改革中“马和非马经济学”的视角
改革开放40年已经把中国引入一个多元社会,如今的中国经济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地位在理论上的合法性无可怀疑,但西方经济学正逐渐占据上风、成为事实上的主流。中国经济学界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性特点,出现了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经济学派别。本研究只从“马或非马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学界的不同派别作一观察和思考。
“马经话语群”和“西经话语群”
“话语群”是使用同一理论范式、话语体系和概念范畴的类学术共同体。在中国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两个理论范式就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套话语体系有两套概念范畴,分别在不同领域发挥主导作用,这种“普照的光”使几乎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都逃脱不了它的影响,留有它的印迹。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只有一个模式,作为其理论反映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只有一种声音、一个主义、一个“学派”,都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话语体系和概念范畴。大学课堂讲授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己培养的学生也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系统教育,所用的自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话语和概念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研究、讨论中国经济问题,讲述中国故事,形成庞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对国外资本技术、西方管理方法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引进,特别是大量向英美等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大批在西方大学经过严格的西方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硕士、博士回国,在把西方经济学知识带回国内的同时,也把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带了回来。他们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话语说话,用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思考,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交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的经济学教学发生了与原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科研日益强化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逐渐消弱和边缘化。这种明确的西方经济学价值导向的做法大大强化了人们的西方经济学存在感,对青年学生进行大课时、大力度西方经济学教育的结果是使年轻学者一经走上经济学学术之路就习惯地认为经济学就是西方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不过是一门“思想政治课”。这样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使以西方经济学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西方经济学话语群”茁壮成长,日益扩大。
“话语群”并不是个严格的“学派”“流派”概念而仅仅表明群内成员的话语体系相同、使用的概念范畴相同、在其成果中可以检索到共同的“关键词”,但这些词语的使用者对其的态度可以是肯定的,也可能是否定的,有着同样“关键词”的文献有的作者是赞同、支持,有的却是质疑、批评,情况并不相同;同属一个话语群并不意味着其基本立场、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的一致,相反,同一“话语群”的学者可以有着彼此相反的立场、观点和政策建议而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派别。
改革开放40年,两个“话语群”此消彼长。改革开放前“马经话语群”一群独大,现在的“西经话语群”已呈压倒性优势,而“马经话语群”随着其成员年龄的日益老化和新加入成员数量的边际递减而正加速弱化。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种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
几个影响比较大的经济学派别
(一)西经话语群的三个派别
1.市场化改革派:该派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研究员为代表,相当一批身处高位的政府高级官员置身其中,对中国高层决策有着直接而巨大的影响,在中国的经济学各派别中拥有最为豪华的阵容,很多成员都既是高级官员,又是知名学者。20世纪80年代改革大潮中吴敬琏流行全国的“吴市场”绰号也足以说明该派在改革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和在社会各界的影响。早在改革初期的1983—1984年吴敬琏就作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访问学者在美国耶鲁大学进修学习,深入接触了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该派推崇自由市场原理,倡导竞争性经济体制。抱怨中国模式是“强势政府驾驭市场、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以及所谓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国家决策最高智囊他们却不大热衷“主义”的争论,只提改革的具体主张,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对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善于在“体制改革”与“制度改变”的边缘地带发挥作用,虽时常被“新马派”经济学家指责为以西方经济自由主义误导改革、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有违国家宪法,却很难看到他们的声辩。
2.现代经济学派或西经中国化派:市场化改革派重在采取行动、推动市场化进程,而现代经济学派或西经中国化派则强调推广理念、营销市场化思想,二者形成鲜明对照。与市场化改革派的官方色彩不同,该派占据大学经济学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的重要领域,对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普及、传播,进一步对中国经济学的未来、中国青年经济学世界观的形成,影响深远,因而对中国下一代的成长和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培养,产生影响,这使该派比其他经济学派别有着更久远的考虑。该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和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洪永淼等几位教授,清一色海归博士,在国外著名大学接受过正规、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有着“现代经济学”在中国之代表的美誉,其对西方经济学运用娴熟,善于用正宗地道的西方经济学语言说话,具有学术的面貌,很有“科学形式”,在国内为众多青年经济学人所崇拜,在中国大学经济学教研、学科建设和管理者以及研究生中有相当影响力。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就像数学、物理学及其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那样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西方经济学是适用于任何制度条件下的经济学,主张用西方经济学话语讲述中国故事,用中国案例来验证、丰富西方经济学,把“外界承认”作为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目标。
3.西经背景国情派:与市场化改革派采取行动来推行市场化、西经中国化派推广理念以营销市场化思想不同,西经背景国情派是运用西经工具解释中国奇迹、力挺中国崛起、强化中国自信。现代理论、留洋背景和重视国情是该派的鲜明特色,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他们都是中国高层智囊,都有深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掌握先进的现代分析工具和方法,又都做着专职国情研究,比较了解中国实际,懂西经而不囿于西经,理论先进而不激进,能够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证、支持中国经济发展,解释中国奇迹,完成有份量的国情研究报告,发挥政策决策咨询作用,在国内和国际都有很大影响力。值得指出的是,该派虽系“西经话语群”却能对不顾国情盲目迷信西方经济学的倾向进行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情结,相反,他们用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释放善意”的方法也常遭到新马派经济学家的激烈批判 。
(二)马经话语群的派别
1.新马派经济学:主要代表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程恩富学部委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有重要影响力。主张以马学为本,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国情为据,世情为鉴,他们精于马经、兼通西经,还懂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研究机构都有着广泛联系,堪称中国最为国际化的经济学派别。和其他学术派别不同之处明显在于,它有着十分强烈的主体意识、责任担当和批判精神,是一个“战斗学派”。表现为学派顶层设计完善,组织机构健全,与世界各国左翼学者和政党组织保持频繁学术交往,主持多个国际性和全国性学术组织作为该派学术新人培养和学术交流平台,主办多家中外学术期刊作为新马派经济学学术阵地,承办多个国际国内学术论坛释放新马派经济学声音。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立场、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关注改革开放发展现实,具有很强的责任心、使命感和战斗性,对其认为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经常进行指名道姓和不留情面的批驳,甚至对一些被认为不利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新改革政策措施也敢于提出异议和修改建议。在工农阶层和学术界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在有着改革前后两种经历的部分知识人群中有很大影响力,是从另一个方向直接间接对高层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力量。但该派也被指有些成员的观点有过于理想化、超越阶段性、不具可行性之嫌。
2.阐释派经济学和个性派:阐释派经济学在解读中央政策、解释和阐发中央精神方面地位无可替代,聚集着马经话语群最多的经济学者,一大批知名经济学家身在其中。马经话语群里的个性派学者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他们确确实实做着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使用马克思经济学话语体系和概念原理开展研究,经常活跃于全国各种政治经济学学术活动,展示于人的是他们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功底,但他们总能研究出让人意外的成果,即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发研究得出的结论看上去往往不利于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派别与改革走向
不同的学术派别决不仅仅是学术观点的不同,更重要的还有学者基本立场、价值取向、代言人群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学术派别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发声,他们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一定的民意,这些民意都会通过种种渠道反映在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高层决策和具体实施方案中,不同的经济学声音和政策建议会化为一定的社会行动,这些行动是各领域、全方位的,有着无数的方向,先是在变化着的各个方向的边际上然后是整体上逐渐改变着各领域行为主体的利益格局,由此规制着整个社会演进的趋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统一和内在结合,不同学术派别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基本制度和经济体制有着不同的偏好和侧重。有着官方背景的市场化改革派强调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市场取向性,在国家决策咨询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占据高校经济学教育领域并对教育主管部门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现代经济学派或西经中国化派强调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的科学规范,在经济学教育和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领域有着举足轻重作用;而新马派经济学则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改革的指导作用和改革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之性质不能改变,主张政策的制定和改革的推动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地位显赫。
改革走向的确定和改革政策的制定其实并不单是最高决策者的个人意志,而是个公共选择问题。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这里,恩格斯强调的就是社会选择不是“一致同意”而是不同意志的综合与平衡,这可能是最早的“公共选择思想”。由于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存在,任何改革方案都有一个是否遭到抵制、反对或反抗的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不同的经济学派别实际上分别代言相应群体而参与其中。正如樊纲所言:“所谓政府政策,不过是执行这一公共选择结果的具体形式罢了。”因为“政府不过是在它们之间周旋的一种平衡机制”,“政府政策,不过是这种利益平衡的一个产物”。汪丁丁的表述更加直白:“政治是折衷各种利益,而不是只代表一种利益。在西方民主政体下,布坎南假定每个政治家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利益可以在类似市场均衡的政治均衡中得到‘折衷’。但这不适于‘一党执政’的情形。在后者,执政党的领袖要负责折衷各方面的利益。”
中国改革走向和改革政策也是如此。新马派经济学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的“社会主义”方向,不断提醒决策者、引领社会公众,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防止改革“走得太远”超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外。市场化改革派和西经中国化派则更加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经济”、市场化改革,提请决策者要加快、更深地市场化。中国实际的改革决策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总体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广泛听取包括不同经济学派别在内的社会各种不同声音,综合、统筹、权衡各方面的意见,使改革政策达到“和而不同”的和谐效果。在这个意义上,甚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改革目标的确定本身,就是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中决策者对各种不同意见和力量进行折衷、妥协、“和谐”的动态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新马派经济学“两线作战”:在实际改革进程中盯着市场化改革派,市场化改革步步进逼,经济自由越来越多,非公经济日益扩大;在经济学学术和学科建设上盯着现代经济学派或者西经中国化派,大学的经济学教育和学科建设日益西方经济学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被动地“你进我退”。在艰苦的“两线作战”中,新马派经济学步步退守,又不得不以攻为守,养成了“战斗学派”的风格。但实际改革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的标准对改革的约束,随着不断深化改革的现实进程,不断因“初级阶段”而被放松、软化,在各项改革的边际上不断触碰新马派经济学家的改革“底线”和“可容忍限度”,逼着他们对原来理解的“原则”和原来掌握的“标准”作出适应性调整,以体现时代精神与时俱进。与日常行为不同的是,在创新的边缘上“违宪”可能并不是很严重的事,中国改革开放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原有宪法和法律的突破,当宪法本身也成了需要改革和完善的对象时,它就不再是独立于改革进程之外的客观参照物或者标准,改革的过程就成了制宪、改革突破、“违宪”、修宪、合宪,再改革突破、再“违宪”、再修宪,使宪法更趋完善以更适应“初级阶段”要求的过程,40年改革开放我们正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一过程中,各经济学派别都想使中华振兴、让中国伟大,但理念各异、主张不同,正是这种经济学理论观点的百家争鸣、相互制约,为国家改革决策提供了多种选择和参考,保证了使出台的政策更加合乎民意、符合国情,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