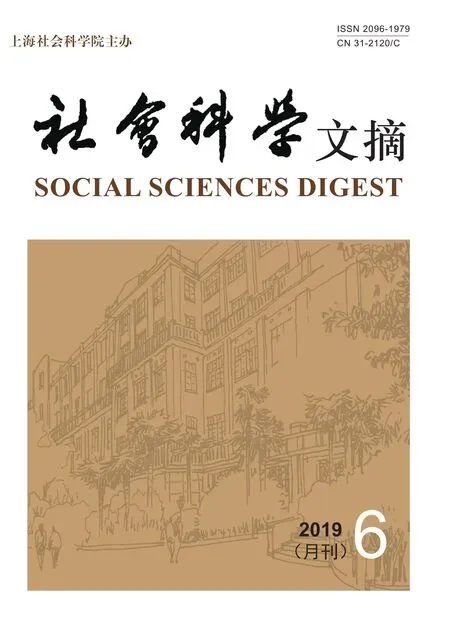全球治理制度变革的中国方案优势
推动现有全球治理制度体系朝着增进人类共同福祉的方向转型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对此,中国有责任在科学把脉当前全球治理制度存在的种种现实制度困境的基础上,从制度的合法性、融洽性以及有效性三个维度彰显中国制度方案的优势,从而推动现有全球治理制度体系朝着增进人类共同福祉的方向转型。
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制度困境
当前,国际社会的治理体系主要是由美国主导的各类国际制度所构成。这些制度在恢复全球秩序、实现整体和平、推动全球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成为维系战后秩序、推进全球治理的基石。但是,随着全球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全球权益格局出现新的变化,现有的全球治理制度并没有随之进行有效的调整,从而逐渐陷入种种制度困境之中。
第一,现有的全球治理制度面临着合法性不足的困境。这种困境主要集中在反映普遍意志以及回应现实需求两个主要方面。意志的反映需要制度性平台,而需求的回应则需要制度本身的正向作为。对于前者而言,其无法在现有的全球治理制度中得以全面反映。具体来说,作为全球治理制度现有主导者的发达国家,由于众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其在世界市场中的垄断优势不断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因此,在现有全球治理制度无法有效反映发达国家意志的状况下,新的制度构建或与原有制度的脱钩行为便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与此同时,一大批新兴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以来是现有全球治理制度的接受者,其地位、权益和话语权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和尊重,其意志追求与合法性诉求也无法在现有的全球治理制度安排中得到有效回应。可见,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本身的制度弹性开始逐渐减弱。随着这一趋势的蔓延,在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的现实需求时,现有的全球治理制度愈来愈无法发挥正向作为,而这同时作用于现有全球治理制度的主导者——发达国家和其接受者——发展中国家。
第二,现有的全球治理制度面临着融洽性不足的困境。之所以出现这种制度困境,关键的原因就是现有的全球治理制度在较大程度上是美国依据自身的发展诉求而在全球范围内所制定的。由于这种制度性安排的目标在于实现制度主导者而非国际社会整体的发展诉求,因此其必然是由不同且相互间缺乏有效互动的制度单元所组成的制度体系,这是造成现有全球治理制度融洽性不足的根本原因。而融洽性不足则主要表现在制度碎片化、制度重叠化和制度孤立化等方面。其一,制度的碎片化。其主要表现在国际组织数量的增加、成员身份的扩大以及议题关联的增加等方面。此外,行为主体权威以及权力的分散进一步使得制度碎片化这一现实困境变得更为突出。其二,制度的重叠化。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是最主要的制度性安排,其与新的制度性安排——二十国集团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从而导致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之间的非融洽。其三,制度的孤立化。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制度单元之间缺乏应有的协调与互动。具体是指在同一区域,针对不同议题所做出的不同制度性安排间缺乏应有的协调与互动。
第三,现有的全球治理制度面临着有效性不足的困境。有效性是衡量全球治理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塑造或影响国际行为的一种尺度,然而现有的全球治理制度并不符合这一标准。一方面,现有全球治理制度本身日益呈现出不同程度上的滞后性。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全球治理制度进行了部分的改革与完善,然而,由于国家利益至上、大国之间缺乏战略性互信以及全球发展极不均衡等原因,现有的全球治理制度无法取得实质性的变革。另一方面,现有全球治理制度在建立之初所面临的问题境遇已发生显著性的变化。比如,在全球治理的问题对象方面,现有的全球治理制度在建立之初主要是为了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以及推动全球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然而,随着国际社会不同区域生产力水平的普遍提升,威胁国际社会和平以及制约全球经济发展的因素均已发生重大变化。
彰显全球治理制度变革的合法性优势
合法性是任何一种全球治理制度能够得以生效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所在,而能够反映普遍意志以及回应现实需求则是制度合法性的关键要义。对此,在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进程中,中国倡导的制度主张与制度实践紧紧围绕这两个方面,为提高全球治理制度的合法性不断注入中国的制度理念和制度力量。
在反映普遍意志方面,中国倡导的制度主张与制度实践在兼顾发达国家利益诉求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提高中国制度方案的全球认同度。然而,作为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塑造者,美国在自身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要求新兴市场国家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承担较多的全球治理责任。但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其并不具备足够的实力来承担超越自身能力的全球治理责任。如果出现责任错位,那么其后果将使其无法有效表达自身的发展意志,甚至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金砖机制的建立是避免产生责任错位的有效制度实践,其为新兴市场国家表达自身的发展意志搭建了有效的制度性平台。除此之外,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并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推动中国自身发展、推进区域间合作以及加强全球性对话搭建了新的制度性平台。这一平台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其以亚欧大陆为重点并面向国际社会所有的主权国家,致力于相关成员的共同发展以及国际社会的整体稳定。
在回应现实需求方面,中国在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过程中大力倡导“共赢共享”的制度理念与制度实践,以回应来自国际社会的多样发展诉求。此外,中国始终倡导并践行“合作共赢”理念,反对任何形式的“零和博弈”思维。相比较而言,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治理制度从建立伊始直至现在,更多的是为资本增殖打造一个有利的全球制度环境。然而,这种治理制度必然会被资本所绑架,它的建立与发展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资本的增殖,由此便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在全球化不断发展、各地区交流不断增强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倡导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规则理念,为探索构建符合国际社会发展诉求的全球治理制度提供了根本的价值指向。而在制度实践方面,中国积极打造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一平台是中国为探索新的区域性发展动力以及全球性金融对话的制度实践,其不是推翻现有的全球金融治理制度,而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发挥作用,从而能够针对性地整合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并以此形成合力,以推动亚洲区域的发展,进而促进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
彰显全球治理制度变革的融洽性优势
融洽性是任何一种全球治理制度与其他制度之间的协调关系,这种关系的协调程度直接影响到全球治理制度融洽性的深度。中国在具体的制度理念和制度实践方面均注重全球治理制度之间的融洽性。除此之外,这一融洽性优势还体现在中国处理自身与原有制度间关系时所采取的渐进式的制度参与这一特殊的策略方面。
就新旧制度间的契合度这一层面而言,无论是中国倡导的制度主张还是付诸的制度实践均不是谋求“另起炉灶”,而是不断完善和补充现有的全球治理制度,从而稳步推进现有全球治理制度的变革。具体而言,在解决制度碎片化这一困境方面,中国通过制度参与者这一角色积极推动相关制度间的对话与合作,从而使得原本关联不够紧密的不同制度成为了相互推进的制度系统。而这突出表现在中国与中东欧“16+1”合作机制与欧盟机制间的关系上。通过跨界成员国,“16+1”合作机制在给相关国家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同时,也赋予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的内涵。在解决制度重叠化这一困境方面,中国通过整合区域内成员对某一领域的共同关注,倡导构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制度安排。这一点在亚太地区的贸易领域得到典型的体现。中国积极倡导亚太自贸区这一制度的构建,努力推动现有重叠制度的功能明晰化,从而为处理现有制度安排间的复杂关系注入正向制度动力。在解决制度孤立化这一困境方面,中国通过确立制度目标这一未来行进方向,积极破除相关制度间的孤立状态。例如在非洲地区,虽然非洲联盟这一政治性制度安排存续了很多年,但多数非洲国家并没有实现在政治整合基础上的经济发展。而中非合作论坛这一经济性制度安排要想切实推进非洲地区的整体发展,就需要在政治性制度安排方面拥有有效的制度保障。在此现实境遇下,加强这两类制度安排间的对话与合作,能够在破除制度间孤立状态的同时实现非洲地区的整体发展。
就中国自身与全球治理制度间关系这一层面而言,中国非常注重依据自身发展需要而采取渐进式的制度参与策略。在参与范围方面,中国从主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逐步扩大到众多新兴领域的治理。具体而言,中国之前参与全球治理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虽然在非经济领域也进行了一些国际合作,但其侧重点在于为经济发展谋求良好的外部环境,而非深入参与具体的治理实践。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对这些新兴的治理领域参与时间相对较短,在很多方面虽具有越来越强烈的治理意愿,但尚不具备很强的治理能力。因此,中国若想在更多治理领域推动更好的实质性变革,仍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参与过程。在参与方式方面,中国采取逐渐加入现有全球治理制度的渐进策略,从而保证自身能够在既定的“游戏规则”中谋求发展机遇与发展空间。在以较小阻力实现制度性融入后,中国的参与开始更多地体现在力促现有制度安排的变革,并依据自身实际、地区现实与国际现实需要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安排仍主要集中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这是符合中国实际和国际现实的。与此同时,中国也密切注重其他领域的治理参与,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这些领域具有巨大的利益关切,而且还因为处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本身需要中国在多个治理领域发出更多的“声音”,从而有效推动全球性共识的达成。可见,中国在过去的参与进程中,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性融入,是渐进式参与,这种渐进式的制度参与策略使得中国在付出较小融入成本的同时,能够进一步促进全球治理制度的变革和完善。
彰显全球治理制度变革的有效性优势
有效性是全球治理制度最终被认可的根本性因素,因此,其决定了制度本身的生命力及其生命周期。面对现有全球治理制度在有效性方面所存在的不足,中国紧紧围绕来自国际社会不同国家主体的权益诉求,在议题设置、规则构建等方面注重提升全球治理的制度理念与制度实践的有效性。
在议题设置方面,中国倡导的制度理念与制度实践紧扣国际社会的客观需求,并能够及时做出制度回应。具体而言,在全球安全议题方面,虽然自冷战结束以后没有再发生全球性的武装冲突,但局部性的武装冲突却在不断地发生。在主权国家间的竞争博弈中,冷战思维以及零和行为依然十分盛行,一些国家仍迷信武力制胜的信条,不断加强自身的军事实力以及扩大自身的军事同盟。随着地区冲突效应的不断外溢,全球安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中国适时提出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这一新安全观努力打破传统的冷战思维,努力为国际社会贡献全新的安全理念,进而为构建维护全球安全的新型治理制度提供价值指引。在全球发展议题方面,发展动力不足、发展机遇缺乏、发展平台萎缩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整个国际社会。对此,中国在积极倡导共同发展的同时,努力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构建包容性的制度性平台。这一平台虽然由于中国本身实力、治理经验等方面的原因更多地是针对域内国家,但其在构建之初便坚持制度的开放原则,积极包容域外国家的参与。而这种包容性的制度安排不仅为满足域内国家的发展需求提供了实质性的制度保障,也为满足域外国家的利益诉求提供了转型性的制度机遇。因此,这一在新的全球发展环境下所做出的制度探索符合国际社会的发展权益,能够对不同区域的国家提供切实的正向制度作为。
在规则构建方面,相较于现有的全球治理制度,中国倡导的制度方案更为注重制度本身的全面有效性。一方面,这种全面有效性体现为对象的全面性。对比亚洲开发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不难发现,虽然前者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有效为亚洲地区的发展注入动力,但由于其在运行规则等方面固守不合时宜的制度安排,导致亚洲开发银行难以在服务对象方面实现切实的全面性,从而导致这一制度性安排的有效性不断降低。而后者则在非常明确地针对亚洲地区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现实需求的同时,积极容纳来自全球不同区域主权国家的加入。中国在构建新型治理制度时便十分注重对象的全面性,从而能够充分发挥不同对象的各自优势,进而彰显出制度本身的现实有效性。另一方面,这种全面有效性体现为领域的全面性。当前,美国主导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应对恐怖主义这一全球性问题时,所采取的解决措施往往是简单的军事暴力。“以暴制暴”是西方国家典型的制衡思维。然而,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措施只能在极为短暂的时期内起到相当有限的作用,但对于战争期间普通民众的安全问题以及战后经济恢复问题均无法提供一个有效的制度解答。而由中国倡导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在应对这一问题时,所坚持的理念是用发展解决问题。这一制度性安排在维护地区整体稳定的同时,积极深化经贸、投资、金融、农业等领域合作,从而推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可见,这一制度性安排能够在不同领域内加强对话与合作,进而有效推进这一制度框架内所有成员的共同发展。
结语
在推动现有全球治理制度变革的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正在不断复苏的全球性大国,理应为这一进程做出自身的制度性贡献。同时,中国依托自身综合实力的增长,不断省思现有全球治理制度存在的缺陷,努力在制度理念与制度实践双重层面上彰显自身的制度优势,进而为推动现有全球治理制度朝着增进人类社会共同福祉的方向变革注入有效的制度动力。由此,中国应以更为主动、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到推进全球治理制度变革的进程之中。总体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构建新型国家关系的实践指明了中国推动现有全球治理制度变革的基本方略。当然,这一制度方略还应当采取一种集“最大公约数”的现实姿态,以努力与现有制度的参与者搭建各种对话渠道,从而减少他们对全球治理制度变革的误解误判。如此,中国才能够在面临较小阻力的情况下不断彰显自身的制度优势,进而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的制度性贡献,最终为推进全球治理制度变革贡献中国的制度智慧和制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