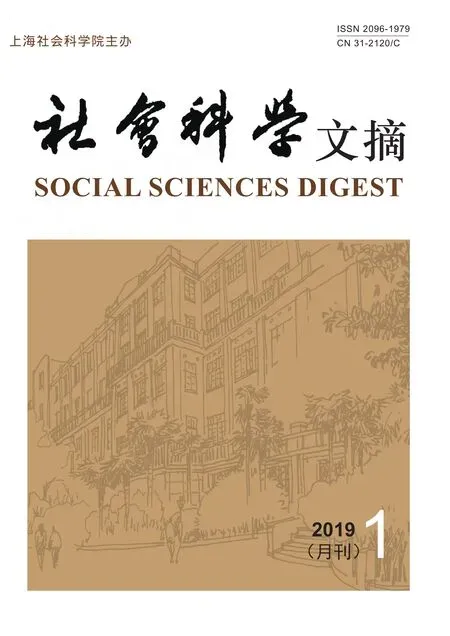国家转型:明代还是清代?
——有关明清国家性质的新理论与新研究
一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明清史研究范式,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隐含的但又“坚实”的假定之上的: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迅速崛起和以中国为代表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形成的巨大反差,成为研究明清历史的当然背景。这里既有19世纪以来的经典论述,比如“没有历史的国家”“停滞的帝国”“东方专制主义”等论断,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比如“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白银帝国”甚至“唐宋变革”等理论。这些研究都隐隐约约地依托或者反对着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历史观。很遗憾,这些假定大多是主观建构的,非历史的,更没有经过批判性思考的审视。
大多数资本主义与现代性制度只是在17世纪以后才开始逐渐在欧洲核心区域形成。在此之前的欧洲政治与社会经济,还是一个以封建领地、公国、自治城市、地方市镇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浪潮之前,大多数欧洲国家权力的行使形式都是由王室成员带来若干税务官员造访其领地的皮包式权力模式(里夫金著、杨治宜译《欧洲梦》,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154页)。确定的国家领土意识和统一制度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后的若干个条约中逐渐形成共识。仅仅在300多年前,资本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推广是不可想象的。而这300多年逐渐形成的东西,被18世纪以来的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想当然地当作东西方社会永久的鸿沟。由此催生的东方性、内亚性、亚细亚模式、资本主义萌芽、唐宋变革论等历史学范式,禁锢了几代学人的思维。
二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史研究的范式开始逐渐具有更多的本土特色,其表现为更注重中国视角,更深入挖掘全球收藏的中国文献,重新建立中国历史的解释模式。一些中国史家开始从中国历史演变的特征出发提出若干更为贴近本土意识的历史解释框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赵轶峰提出的“明清帝制农商社会”(《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科学出版社,2018年),万明提出的“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国家转型”(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楼劲提出的王朝国家与中国历史(《北魏开国史探》自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都从更深入的层面为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国家结构与社会性质提供了精彩的新视角与新范式。
倪玉平新近出版的《从国家财政与财政国家——清代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清代关税:1644—1911年》(均为科学出版社,2017年)为我们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待明清大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证研究案例。《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一书将有清一代的财政发展分为清前期至嘉道时期,咸同之际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同光以后的影响期。以清代国家财政的主要机构户部银库与关税等国家财赋数据作为基础,全面对比了清前后期国库财政的总量和构成比例,以及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后这种比例发生的重大变化,通过对比土地税与厘金、商业关税(包括国内市场的常关和海外市场的洋关)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来说明清代国家由农业型转化为工商型的历史过程。而《清代关税》一书则以基本保存完整的清代关税资料为主体,详细梳理了构成关税的各种材料的数据,揭示出关税在有清一代的变化趋势。在清中期以前,常关税保持稳定,但在太平天国以后,常关税下降幅度达到一半。而洋关税则大幅度增加。两种关税合计的总额从清前期的500万两到清末增加到每年3500万两。其位于港口的各洋关税则增长迅速,直接反映出沿海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势头。
这些数据通过与人口和物价指数的修正,作者得出了关税史的研究结论——清朝从传统农业财政向以商业为基础的新型财政的转变。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关税管理、财政机构改革、实业贸易机构的设立,我们才能据此做一综合性判断:从洋务运动以后,清朝逐渐开始了其面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这种转型从经济史的角度或者财政的角度来讲,作者称为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的转变。
当然,财政国家的形成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链条。其背后隐藏一系列重要的变迁。这种变迁需要配合制度史、观念史、文化史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才能看得更为清楚。从财政这一概念来讲,是近代以来引进的西方国家制度形式之一。明清时期以度支、国库、国帑等概念来指称国家财赋,以赋、税、租、钱粮、榷、关、徭役等概念来指称国家敛取财赋的形式。从光绪中后期开始,中央整顿形色不一的财税制度的呼声开始大量出现,在各种奏议中,将整顿财政作为一项主要内容。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之变全面失控,导致实际掌控中央权力的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西逃避难。在这个过程中,慈禧集团不得已再次回到改革的道路上来,下了一道谕旨:“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定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七十六,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这是清朝中央政令中首次使用财政这一词汇的开端。在此之前,马建忠在《适可斋记行》、李鸿章在上奏中都曾将财政作为变法的重要内容加以提出。由此可见,所谓财政国家的形成,最终形成于清朝晚期开始实行宪政改革的时期。
财政国家的概念,还伴随着现代西方财政、经济学在中国引入及其选择性吸收的过程。金观涛在《从“富强”、“经世”到“经济”——社会组织原则变化的思想史研究》(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一文中,对这些学科名词在中国的确立过程与社会运动的互动关系做了深刻的剖析和揭示:
现代经济学一词,来源于古希腊的家政之学。亚里士多德在《家政学》一书中明确指出,以家庭生计为主的家政学与城邦政治学完全不同。“财产是家庭的一个部分,获得财产的技术是家务管理技术的一个部分。”economy作为家庭财产管理技术是必须的、体面的。但超出家庭财产管理之外的商业活动因从他人之处获利而应受到指责。
但中国传统社会将国家看作家庭的放大,家国具有同构的特征。家庭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也是国家政治与经济活动的基本载体。梁启超就注意到,在众多学科中,生计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古代比西方更为发达。早在秦汉时期,众多思想家就税收、理财、盐铁专卖、货币等问题有经典论述。而古代士大夫的知识体系中,并不仅仅围绕着道德与人性的探寻,还包含着另外一套“经世济民”的学问。比如《朱子语类》中说:“陆宣公奏议末数卷论税事,极尽纤悉。是他都理会来,此便是经济之学。”所以,财税与度支等知识,在传统儒家道德秩序的国家中有其重要的地位,但要获得专门性学科的地位,还需要进行现代性转换。这个过程又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引入同步。
西方现代经济学从洋务运动开始传入中国。在一八八五年翻译刻印的傅兰雅《佐治刍言》一书中,指称西方现代经济学的Economy被翻译为“伊哥挪迷”。到了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名著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一书时,将意为“对国民财富的本质及原因的探寻”的书名翻译为《原富》,可谓简洁而准确的传达出了这部著作的核心思想。严复将Economy译为“计学”,并且指出日本将economy翻译为“经济”,从经济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义来讲,经邦济世范围涵盖一切围绕着儒家社会秩序所对应的行动与学问,并不能专指西方特定的经济学科。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将“中国史事、本朝政论”称为“中学经济”,将“西方各国政治、兵制、学校、财赋、商务”统称“西学经济”。可以看出,在经济之学日益成为一门专门之学的强劲势头之下,还有人试图将其纳入传统文化框架。正是在这种拒斥与接纳的多重变奏中,中国的国家治理形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是将实现某种道德秩序的社会组织形式转换为实现特定政权功能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经济或者财政不再直接以实现道德蓝图为目标,而是以形成“自我持续增长、能够通过借贷手段解决财政支出问题、并且能够通过税收保证偿还”的现代财政国家。
根据这一研究,我们从明清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观察到的中国社会所呈现的画面与近来学界提出的若干论断还有着较大的分歧与断裂。比如“明清帝制农商社会”概念的提出,将农商社会作为明清社会的主要特征(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这无疑为学界摆脱过去“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等论调对中国史研究的束缚有着重要作用。万明根据对《万历会计录》的研究提出明代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赋税国家转型的国家转型说,进一步推演出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型、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这样的结论。但这种农商社会的具体情形,中央到地方的实际运作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从《清代关税》一书来看,清代前中期财政收入的比例以土地税占绝对优势,从87%到70%左右缓慢递减,直到1841年土地税的比例依然占到了69%;而反映商业流通税的关税则从2.6%缓慢增长到10.2%。所以,倪玉平指出:1850年前的关税只占财政收入中很小的一个部分,低于总收入的15%,甚至比盐税还少,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土地税。数据清晰地表明1850年以前的清代社会仍是农业性质的,具有农业为基础的财政结构。关税和商业税收也只是在17、18世纪以来成为西方社会的主要财政工具。
《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一书通过详细分析占有第一手档案史料,从国家财政的角度首次梳理出一个从农业型社会向工商型社会转变的历史脉络。其中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各项财政收入、支出在国家财政中所占地位的变化。根据农业税负和工商业税负在清代前后期所占比重的详尽分析,清代国家在咸丰、同治年间由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与危机,新设立的厘金和关税才逐渐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这一重大变化既带来了国家财政收支格局的重大改变,也带来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权重发生重大变化。而这两大变化,正构成了近代以来国家转型的底层原因。如果从现代化叙事的路径来看,晚清以来国家与社会在疾风苦雨中所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财政研究无疑为学界提供了又一基本的研究框架。
那么,农商社会的性质该如何看待,商业在明清时期的地位如何体现,进一步说,国家转型的发生,到底发生在明代末期还是清代末期?17世纪是否存在一个中国式的现代转型?在我们摒弃了资本主义萌芽等研究范式后,以国家转型来取代资本主义萌芽是否是相同问题的再次提出?这都需要学界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三
利用统计方法与数字来进行历史研究,是一条充满陷阱的途径。一方面因为史料本身的性质,我们通常会将残存的数字当作历史的全部来处理,大量推断与修正性数字的使用会使得建立于其上的各项推论发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失误。另一方面,数字与统计极度简约化了复杂的历史过程,容易引发简单片面的历史结论。例如,明清对外贸易的重要形式,贡赐贸易的总量,可以根据明清两代藩属国的朝贡时间、规模以及贡赐物品的种类进行某种描述,这种实物贸易很难还原到当时的对外贸易总量中去,所以由洋关税额所揭示的中外贸易量还需要加一补充参数。
其一,清朝北方贸易情形相对复杂。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官方档案中,从顺治到乾隆期间至少有50件档案内容为与俄罗斯贸易的,其中贸易线路涉及到从东北的黑龙江、嫩江、北京、张家口、鄂尔多斯、伊犁、哈萨克整条草原丝绸之路的商道。这反映在明清时代,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进入了鼎盛时代。由于清朝分别在康熙与雍正年间与俄罗斯签订了划界和贸易条约,尼布楚、恰克图、库伦等地获得了合法的贸易地位,这条线路虽然被俄罗斯所垄断,传统进亚欧大陆的商道中间出现了代理商性质的梗阻,但北方丝绸之路并未衰落,甚至还更加兴盛。根据两件内阁和理藩院档案《题为遣员至蒙古会盟处传谕蒙古各众做贸易不得行骗等事》《函达俄商在中国境内所有妄为举动定加惩处请仍旧照约将俄商放行入境由》,可以看出,中俄贸易从顺治到康熙间已经呈现常态化,中央部院题奏中这类日常贸易纠纷的内容显示了贸易的广泛和深度。北方贸易路线上的主要商品为茶叶。据说最早进入俄国的茶叶是崇祯十三年(1640年)俄国使臣瓦西里·斯达尔科夫从中亚卡尔梅克汗廷带回茶叶二百袋,奉献给沙皇。这是中国茶叶进入俄国之始。即使在海运大开之后,通过陆路进入欧洲的茶叶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陆路运输茶叶的质量要远远高于海洋运输茶叶的质量。马克斯在《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指出,恰克图贸易中的中国茶叶“大部分是上等货,即在大陆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队茶,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货。俄国人自己独享内地陆路贸易,成了他们没有可能参加海上贸易的一种补偿”。但是这种贸易必须遵守清朝的规则,如《大清会典》规定:“俄罗斯国贸易,人不得过二百名,隔三年来京一次。在路自备马驼盘费。一应货物,不令纳税。犯禁之物,不准交易”(《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四十二《理藩院·俄罗斯互市》,乾隆三十二年)。这些未被纳入关税的对外贸易总量的,尚不止俄罗斯,其他几十个藩属国,都有类似规定。
其二,东南沿海大量存在的民间贸易、走私贸易的规模会牵涉到粤海关等洋关的数据,这些隐匿的经济活动对判断国家转型亦有重要参考价值。
其三,传统边疆贸易存在大量以实物作为等价物进行的交换,比如库伦、恰克图等地就长期以砖茶和其他零碎百货作为货币进行结算,这种现象在西北部许多地方都长期存在。这对于估计这些地区的商业活动有着重要影响。
历史学既是一门有关事实与真相的学问,更是一门有关历史理解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有关缺憾的学问。如果我们不能深刻地理解这种缺憾,野心勃勃地以为了解了详尽的历史真相,便极易陷入主观性论断的陷阱。在清代所有的经济数据中,关税数据保留的相对完整,才使得我们得以通过统计与分析得出若干历史结论。历史学家对历史最基本的敬畏即表现为对缺失的尊重。历史数据的缺乏导致用现代工具分析历史问题的空白,这种空白就必须留在那里。历史的空白也将彰显支离破碎的历史记录的可贵,那种试图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完全填补历史空白的做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更是有害的。充分注意到历史学本身的局限,正是史家的一项基本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