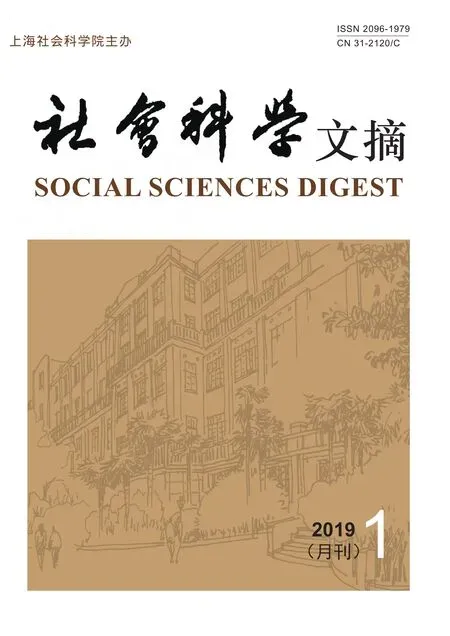从启蒙的角度看真理标准大讨论
从思想文化上来说,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建立在关于实践标准的大讨论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把它与西方历史上所曾经发生的启蒙运动加以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今天,从启蒙的背景上来思考这样一场伟大的变革是完全必要的。
实践标准中的两难
从真理标准讨论的一开始,人们就关注一个重要问题:真理的标准究竟是实践上的检验还是逻辑上的推论。当时,人们在争论中所得出的结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逻辑证明在检验真理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当然,这种重要作用表现在它对实践证明具有辅助作用。实际上在真理标准的争论中,关于实践标准和逻辑标准的关系的讨论涉及到一个问题,即有效性和逻辑上的正当性的关系问题。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讨论的真理和价值的关系问题。逻辑标准所侧重的是真理性,而实践标准所侧重的是有效性。
实践标准的讨论在当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它所产生的社会作用。其社会作用首先表现在它对于人的思想所具有的启蒙作用。实践标准的提出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是针对当时的“两个凡是”的。“两个凡是”中包含了对于权威人士的迷信和崇拜,而不对有关思想进行理性的分析和进一步的检验。从一定的和有限的意义上来说,这种迷信和崇拜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神学,它使信仰高于理性。从一定的和有限的意义上来说,正如当年的启蒙运动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一样,实践标准的讨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然而,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实践标准以及其后的理论讨论中出现了关于“真理与价值”的关系的讨论。这个讨论实际上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延伸,也是对于真理标准的一个有极其重要意义的理论反思。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实践就不应该包含情感和价值的因素。因为,情感和价值的因素干扰了人们对于真理的探索。这个观点却把我们引导到实践标准中真理和价值的关系。于是人们区分了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真理原则就是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它要求人们在认识中是价值中立的;而价值的原则却相反,它以人的需要和目的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学者们认识到,在人的实践中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是结合在一起的。理论上的这个成果实际上对于真理的实践标准提出了进一步的思考。按照真理和价值关系的基本理论,如果实践要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这种实践似乎应该是追求真理的实践,而不应该是实现价值目标的实践。然而,我们用来检验真理的实践实际上都是带有价值目标的实践。
实践标准中包含了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两个方面。如果人们只是从价值原则出发来看待真理标准,那么这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同样的标准可以验证两种相反的理论。在这里,人们忽视了实践标准中的真理原则。如果在实践标准中,人们只是从价值原则出发,而忽视了真理的原则,那么真理标准就会被庸俗化。而在有关讨论中,讨论双方所采用的标准都往往以成功为标志的实践标准,而成功的背后所隐藏着的是价值原则。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有用世界中的自我迷失
启蒙思想在批判神学的时候,强调理性。不过这种理性变成了一种工具理性。而实践标准在批判两个凡是的时候,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这就是按照成功与否来判定真理,判断社会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把实践标准庸俗化了。当实践标准庸俗化的时候,一种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就会盛行开来。
本来,从认识论意义上来说,在获得了某项研究成果、得出某种结论之后,人们需要通过一系列实验来检验这个成果或者结论。在这里,实践是检验理论的真理性的标准。但是,实践标准还可以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任何一种实践活动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检验标准。工人的劳动是检验工人劳动能力的标准,医生的医疗活动可以成为检验国家医疗改革政策有效性的标准,教师的研究活动可以成为检验教师科研能力的标准。于是,实践标准可以成为社会生活一切行为的基本准则。如果人们在生活中把实践标准当作一种基本准则,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实践标准已经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中,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基本精神品格。实践标准的大讨论为形成这种精神品格提供了动力。这是实践标准的普遍化。
这种普遍化当然有它的积极意义,任何一种教条主义观念、任何一种对于权威的信仰都无法在这样一种精神品格中立足。但是,在这种普遍化之中也潜在地包含了庸俗化的可能性。如果实践标准被庸俗化,那么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相对主义就会盛行开来。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正当性)的唯一标准,那么国家制定的权威政策为什么必须不折不扣地被执行呢?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就会出现。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法律和道德规范所应有的威严就会荡然无存。在这样一种庸俗化的实践标准面前,一切权威、信仰、绝对的东西都会被否定。这自然也会出现中国革命中的烈士们被恶搞的情况。
在这里,我们看到,如果人们用价值原则来冒充、取代、削弱真理原则,那么这个标准就变成了一个具有巨大的弹性的尺子,根本上失去了检验标准的作用。我们把这种用价值标准削弱、贬低乃至否定真理原则,并潜在地用价值原则取代真理原则的做法称为实践标准的庸俗化。在这里,价值原则失去了真理原则(权威、信仰和绝对是被检验过来的理论)的束缚。其具体的做法是,如果一种理论在实践中满足了实践者的期待,那么这个理论就是正确的。这实际上是用有效性来取代正确性,用价值原则取代真理原则。
有效性之所以能够被用来冒充或者取代正确性是因为,一种理论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某些正确的东西,至少包含了实现目标的手段的正确性。如果手段不正确(有效的),那么人们也无法达到所期待的目标。但是手段的正确性却不能被用来确证目标本身的正确性(正当性)。西方学者所批判的工具理性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这就是在实践中,人们只管实现目标的手段的有效性,而不管实践所达到的目标是否正确。韦伯揭示西方科层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也是指这种情况。在科层体系中工作的人员只顾有效地完成自己职位上的工作,而不顾这项工作的目的。在当代社会,这种情况往往是以隐秘的形式出现的。如果科学家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要实现个人利益,那么科学研究只是实现他的个人利益的手段。虽然手段是正当的,所追求的目标虽然不够高尚但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人们把科学研究变成手段的时候,科学研究的结果是否正确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数据造假等情况就会发生。在这里,真理性被有效性所取代。一种科学实践的成果究竟是否正确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对研究者所产生的实际利益如何。在科学实践中,一旦真理原则被价值原则所取代,那么大量的伪装的真理就会出现。
实践标准庸俗化的另一种情况是,在实践中,人们所确立的目标是正确的,但是用来达到这种目标的手段是不正确(正当的)。显然当我们用实践标准来进行评判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结果,而不看达到这种结果所采取的手段。在某些地方,少数领导干部为了实现本地区的经济增长采取了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如果我们只考核干部的政绩,而不考虑这种政绩得以产生的手段,那么这实际上就是把实践标准庸俗化。同样在考核一个学者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的时候,如果我们也按照庸俗化的实践标准,只看结果不看产生这种结果的手段,比如我们只是看文章的发表的数量以及发表的档次,那么这无疑在不断地鼓励伪装真理的不断出现。在当代社会,我们在评价各种社会政策,评价一个科技工作者,评价一个领导干部,甚至评价一个普通人等都是用实践所产生的结果来评价它(他)们,甚至是一种可量化、可计算的结果来评价它(他)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变成了实践的结果、特别是可以量化的结果是检验一切、评价一切的标准。我们之所以说只看结果的实践标准是一种庸俗化的实践标准,是因为这种实践的结果都潜在地把价值原则置于真理原则之上。少数地方用不正确的手段所取得的经济效果是以牺牲其他地区甚至整体的利益为代价的。对于少数人所产生的有效性破坏了总体上的正当性。
为了达到人们通常所期待的结果,人们采取了各种策略性的方法来达到这种结果。于是商人可以昧着良心赚钱,干部可以昧着良心出政绩,学者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出成果。如果这种情况成为一种社会的普遍现象,那么这就不仅仅是我们的社会各个领域中的评价体系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我们可以通过优化社会评价体系来解决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心理乃至人们精神层面上的普遍问题。人们对待一切社会实践只是看它们所产生的被期待的结果,而且是一种可以量化的结果。这种精神实际上就是一种实用主义,即有用就是真理的精神。这也是一种变味了的功利主义,即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精神。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实践标准就会变成为在一定程度上被灌注了这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标准。这也是实践标准庸俗化的社会原因。
在这里,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按照黑格尔的分析,在对于信仰的批判中,启蒙失去了信仰,陷入了精神上的迷茫。在实践标准中,本来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真理的维度,一个是价值的维度。但是,在庸俗化的实践标准中人们放弃了真理的维度,而只关注价值的维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失去了对于“绝对”和崇高的信仰。成功就是一切,至于所谓的理想、信念都是一些空话和大话,是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启蒙当时就是这样批判信仰的。当少数共产党员也用这种带有启蒙色彩的工具理性的态度对待信仰的时候,他们也把信仰当作是假大空的东西。即使他们也在口头上宣传信仰,实际上却是采取了一种启蒙的态度,即功利的态度。他们之所以信仰,是因为这种信仰对于他们有用。如果少数党员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共产主义的信仰,那么这些党员常常会越出底线,贪污腐败的现象也就由此出现了。
所有这些现象中都潜藏着这样一种实用主义原则。在功利的面前、在成功和失败面前,人们不是坚持原则,而是放弃了原则。人作为目的就是人要努力实现这种自觉自由的存在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就可以作为自由者摆脱各种物质的诱惑或者权力的诱惑而追求真理,讲真话。否则,人就会屈从于物质或者权力的力量,把自己当作实现物质或政治利益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拘泥于功利的目的,那么这个人必须把自己当作手段,而且仅仅被当作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不仅把自己作为手段,而且更乐于把自己变成别人实现目标的手段。有些人甚至会把自己成为别人的手段看作是一种荣誉。这就如同江湖上那些大哥与兄弟之间的关系一样。兄弟们乐于成为大哥的工具,甚至把自己变成大哥的工具看作是个人的荣誉。更可悲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所有人都会追求自己的工具地位。从功利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只有被利用了才有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实践标准,一个人只有被利用了,那么一个人就成功了。在社会中,如果所有的人都努力追逐自己的被利用,努力使自己成为工具,那么这个社会的人还有可能成为主体吗?这个社会中还有自我和人格吗?
走向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实践标准从提出的一开始就包含了庸俗化的可能性。这是启蒙辩证法所提示我们的。而置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经济的环境中,实践标准的庸俗化就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实践标准的庸俗化在社会不同的领域中已经蔓延开来,在某些地方甚至相当严重。今天在我们重提实践标准的时候,在我们强调实践标准所产生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实践标准被庸俗化的可能性。然而,我们强调实践标准被庸俗化的可能性并不是要否定实践标准。这就如同黑格尔分析启蒙辩证法不是要彻底否定启蒙,而是要把启蒙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说启蒙所倡导的理性是知性,是一种工具理性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在强调理性的时候,这种理性应是一种更加全面的理性。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讲实践标准,必须超越那种庸俗化、功利化、实用主义化的实践标准,而真正地把价值原则和真理原则统一在一起,真正做到真理和价值的统一。我们批判实践标准的庸俗化,就是要把实践标准提高到新的层次上。
实际上要实现真理和价值的统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哲学史上,人们对于两者统一关系的认识也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过程。不可否认,在实践标准中,真理的维度和价值的维度是存在着相互冲突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在这种冲突面前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而放弃另一个。这就是说,两者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真理就体现在这种统一性中。当然,这种真善美的统一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它是在人克服矛盾的实践中不断实现的。人在自己的实践中同时都包含这三个方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人不仅会按照外在的尺度,而且还会按照内在的尺度以及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世界的观点。这实际上就是指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辩证统一。而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就应该贯彻马克思的思想。
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批判工具理性的时候,他们进一步指出了工具理性的缺陷。他们追求的是那种“客观理性”。这种理性实际上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追求绝对的理性。如果说黑格尔对于启蒙辩证法的批判是从方法上(本体论)来进行的,那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更多地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来批判启蒙辩证法。他们同样强调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从实践标准的角度来说,我们就是要在实践中坚持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这就是一方面要坚持真理,用真理来引领价值;另一方面也要借助于真理来实现价值。如果失去了真理的引领,失去对于绝对和崇高的信仰,那么对于真理的探索就会变成工具理性的行为。反过来,如果实践中失去对于价值的关注,那么真理的追求就变成唱高调,而缺乏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只有把这两者统一在一起,实践的标准才能真正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