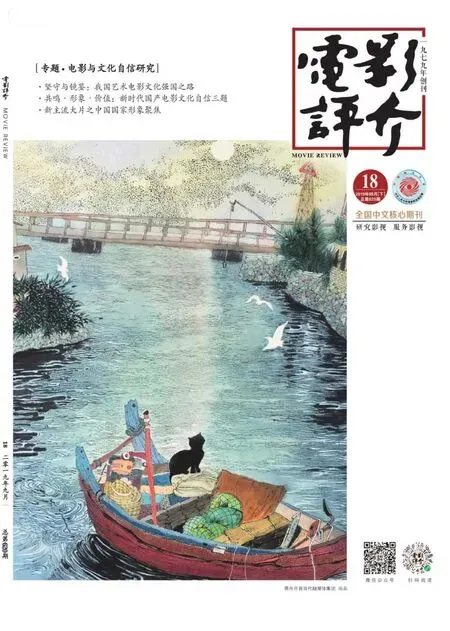危机·情景·游戏:网生代电影身体记忆探赜
国玉霞
电影是通过身体中介实现主体知觉与情感之间的连接,或者说电影本身也是“身体”。“身体是人的行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是我们的身体,使我们能够展开行事,介入并改变日常生活流……所谓行动的人,也就是行动的身体。”[1]所以说,一切电影其实都是关于“身体”的电影。而电影不仅可以通过影像对演员的日常身体进行形塑,还可以通过影像身体以及影院空间的感知与社会成员建构交往关系。电影中的身体记忆就是以“身体”为中介,通过身体影像或影像化的身体表达过去的记忆、现在的记忆和未来的记忆。从知觉层面上说,这种记忆是在知觉—身体—情感链条上的绵延,从潜在到显在不断循环;从文化层面上看,身体是记忆的“储存室”和“保温瓶”,可以通过身体与媒介的传导,将个人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连通,建构代际记忆并促进情感认同。
网生代是指在网络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批新导演。他们有的是在网络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纯网生代,也有从其他领域介入或跨界而成长起来的新导演,包括肖央、陈正道、郭帆、韩延、易振兴、卢正雨、董成鹏、姚婷婷、韩寒、郭敬明、李芳芳、苏伦、闫非、彭大魔、宋阳、张迟昱等。这批新导演生于1980年前后,其成长正值中国社会、文化、消费的转型期,教育文化的全面提升使他们具有很强的思维意识和个体主体性;独生子女的成长背景使他们对于个体情感具有强烈的敏感性和表达欲;媒介技术的进化,尤其是网络环境中的虚拟实践使他们具有较强的技术融合和艺术想象力。这些因素都潜在影响着他们的创作思维和美学观念,并且在影像与“世界”关系层面,他们更加认可影像的虚拟本性,对影像对现实的反映性、再现性持不那么坚守的态度。[2]因此,剖析网生代电影中与记忆关联的部分,可以透视网生代导演如何保存过去的观念,以及对待历史、文化、现实与自我的态度。
一、记忆危机化:身传与刻写
社会、文化转型不断形塑着社会内部结构和外部生活形态。在消费文化和现代技术的全面渗透中,时间的碎片化、瞬时性、即时性增强,人们更关注现实体验。如詹姆逊所说,时间在今天是一种速度功能,只有按照它的速度或速率本身才能感受到;时间又是空间性的,甚至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也变成空间性的了,这都造成时间的断裂感。记忆也是时间的记忆,时间的断裂容易使人对记忆的感知深度消解并产生虚无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忘却,甚至形成了记忆危机。因此,作为全面感知技术迭代与速度驱动的一代,网生代对于记忆危机的症候非常敏感,其电影往往通过外显的固化实践和内隐的身体实践聚焦记忆与现实生活脱节所产生的危机,并借助“体化和刻写”两种方式,在情感、文化怀旧中强化记忆存储、抵御记忆危机,使记忆得以巩固、结晶和延续。
“体化和刻写”[3]是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提出的两种传承社会记忆的身体实践方式。其中,“体化”主要是人以自己现在的身体举动来传达信息;“刻写”主要是通过储存和检索信息的现代手段来捕捉和保存信息的记录行为,如印刷、照片、录音带、计算机等。网生代电影的记忆书写体现了身体体传和影像刻写的相互嵌合。
网生代导演惯于通过细节化放大强化怀旧情感,以抵御记忆危机。《第一次》《同桌的你》《谁的青春不迷茫》《80’后》《李献计历险记》《绝世高手》《夏洛特烦恼》等影片重复运用80、90后观众所熟悉的影像动漫桥段、玩具用品、明星歌曲、零食小吃、动作姿势等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物件、动作或生活细节,将微小的记忆放大重现。这些已然消逝的微末细节是80后、90后在童年、少年生活所亲历的,具有经验相关性,因此也最亲切、生动,容易产生共鸣。所以,借助主人公的体传感知能够使情感记忆得以强化。同时,影像刻写融合了创作者当下对过去的理解,调动了观众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体感的全面感知,通过影像和影院空间的身体感受使得记忆得以传递和加固。网生代导演还惯于通过节日、纪念日、历史事件等具有纪念性或仪式化的活动“让回忆固着于它们的结晶点”。《80’后》《同桌的你》《谁的青春不迷茫》《夏洛特烦恼》等都包含仪式化纪念活动或历史事件,如“中国女排夺冠”“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北京申奥成功”“千禧年纪念”“9·11事件”“张国荣去世悼念”“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如李芳芳导演所说,大事件的展现是一个锐度的把握,并不是我要做一个多么宏大的主题,而是我们这代人经历的大事件特别多,我们的人生在自觉和不自觉中被改变了。[4]仪式化活动和历史事件通过新闻报道、情景再现等方式,不断在媒介刻写中进行记录和固化,使观众能够在历史定位中去重新寻找自我的记忆,从而引发怀旧体验。《老男孩之猛龙过江》《缝纫机乐队》《重返二十岁》《乘风破浪》《无问西东》《夏洛特烦恼》《流浪地球》等还采取场景化方式,将具有时代感的公共演出、娱乐选秀、校园学习生活、群众批斗、民间日常等予以呈现,利用大众媒介在新旧记忆冲突中讲述故事,促进观众通过影像“穿越”进行重温和审视,在文化怀旧中实现情感认同。所以说,网生代导演通过细节化、媒介化、场景化的体传和刻写实践“使记忆可以作为‘社会水泥’,作为一种粘合的力量,起到持续、团结的作用”[5],有助于促进记忆在集体中的固化和延续。
在记忆危机化的内化呈现上,网生代电影还通过主题内涵的反思性将记忆危机引入文化深层。这些影片在深层主题上具有一些共性,即在一个充斥物质与消费的现代社会,主人公因为身体疾病、心理压力或者社会压力,产生情感焦虑甚至记忆危机(错位),之后主人公通过艰难的身体实践终于解除危机或实现自我超越(回归)。大部分影片都以圆满方式结局,体现了这些新导演的理想化色彩。《第一次》中的宋诗乔用录音机录下对宫宁的情感记忆和对时间的真实感知,对抗记忆危机并实现了自我超越,用体传的实践方式将自己与他人的生命照亮;《李献计历险记》中患有“差时症”的李献计用差时记忆对抗残酷现实,在游戏幻境中实现对王倩的拯救;《同桌的你》中的林一在现代压力之中,个人记忆不断被想象改写呈现出不可靠性,但是面对“盒子记忆”却始终保留“那一分真”;《重返二十岁》中的沈梦君通过身体穿越感受错过的青春,在唤醒“没人打开的记忆”的体传实践中让亲人懂得爱和记忆的延续;《绝世高手》在记忆衰落的焦虑中找回了情感记忆的“本真之味”;《缝纫机乐队》借助“文化秀”,用身体姿态和追梦态度激活了热血的“摇滚记忆”;《记忆大师》中江丰夫妇经历记忆删除、错配危机后,通过身体反思拯救了情感危机;《超时空同居》中陆鸣在身体记忆的复写中对抗异化并重回自我。可见,在网生代电影中,这种“记忆危机化”的表征渗透在身体、情感、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并通过媒介的演绎性刻写一次次强化拯救行动。这种处理通过切身体验的记忆危机情境以及身体知觉的过程,使观众与主人公感同身受;又通过媒介的刻写、定型和仪式化使记忆结晶成为文化记忆。文化记忆通过保存知识的储存,能够使一个群体从这种知识储存中获得关于自己的整体性和独特性的仪式[6],这种文化记忆具有身份固化功能,能够通过记忆结构唤起“我们”的代际共识并实现情感上的认同;又有助于通过身体实践激发自我反思、对社会系统形象的反思,使得集体记忆不断得以巩固。但是,网生代导演在反思中往往不做过深层次的挖掘和批判,而是更多关切主人公在矛盾冲突中的抗争、适应甚至平衡,体现了网生代温和的价值观。
二、记忆情景化:唤醒与抵抗
在个人记忆的书写中,网生代导演惯于借助与事件密切关联的情景记忆,通过记忆情景化的方式呈现。“情景记忆是对某一特殊事件的记忆,而这些事件是个人在其早期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每个事件都有它自己的开始和结束,有它自己的界定和特性,甚至有时还有它自己的情绪和气味。”[7]情景记忆运用不仅仅在于呈现事件,还在于如何解释和利用这些事件。在情景记忆的选择上,网生代导演注重选择对个人具有特殊意义的情感记忆事件,或者具有公共性质的集体记忆事件来显现,形成了个人印记鲜明的情绪和气味。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中提出使个体记忆成为身体稳定剂的三种方式:强烈情感、象征和创伤。[8]网生代电影中情景记忆的书写也体现了这三种方式的有效运用,并且通过对事件的解释和利用形成了“唤起”和“抵抗”两个功能。
首先,网生代电影惯于借助强烈情感呈现个体记忆,而强烈情感往往是通过“情感链条”上让人铭记于心的事件来实现的。《同桌的你》中林一和周小栀奇幻的相遇、相恋、相离,《第一次》中宋诗乔和吕夏的“糖味道”初吻和“二次元式”告别,《李献计历险记》中的爱的差时体验和奇幻感重逢,《80’后》中明远和星辰集体舞中“旁若无人”的两情相悦和误会后的决绝分离,《谁的青春不迷茫》中氤氲水记忆和“Hey-Jude”的隔空传情,《无问西东》中陈鹏对王敏佳的“核”告白以及假坟前的抱头痛哭,《滚蛋吧!肿瘤君》中熊顿恋爱、失恋的奇幻景观以及熊顿离世的“在场”告别等,通过极度诗意化、奇幻化、小清新的情景化记忆,强烈图像效果的“能动意象”“唤醒”受众尘封已久的心底记忆,使其在自我体验中不断生成新的混合记忆,汇聚成“回忆场”。还有一些电影则采用颠覆、戏谑、荒诞的方式呈现主人公在集体“大事件”中的身体抵抗。《老男孩之猛龙过江》中筷子兄弟背离残酷现实而去美国追梦,《同桌的你》中的林一和周小栀在游行事件中“不严肃”的“牵手”和“非典”时期的“为爱营救”,《谁的青春不迷茫》中的“飞翔梦”“光头事件”“颁奖叛逃”,《夏洛特烦恼》中的夏洛在学校集会、班级中的“爱情幻梦”和“绝地反击”等,都将小人物的情景记忆放置集体记忆事件中予以呈现。这些情景记忆不仅具有时间定位器功能,还带着“集体记忆”印记,通过奇炫化的组织、加工、改写,构成了社会与个体、现实与梦幻、秩序与反叛的多层对立面,使影片体现出对身体规训的反叛意识,又在主流文化之外开辟“另一空间”,在奇遇、梦幻、穿越、虚拟中实现向另一空间的自由逃逸。在富有现实感的《记忆大师》《重返二十岁》《滚蛋吧!肿瘤君》中也体现了这种处理方式。“身体可以通过形成某种习惯使回忆变得稳固,并且通过强烈情感的力量使回忆得到加强”。[9]网生代导演借助这种切身的情景记忆实现了“唤起”和“抵抗”的功能,体现出一种既不向现实妥协,又不同主流彻底决裂,并保持自身相对自由状态的一种包容的价值观。
其次,网生代电影还惯于借助象征力量的回忆固化记忆。与强烈感情不同,这种回忆是在对自己的生活经历进行回顾性阐释时获得的。它体现了创作者通过当下的“我”对过去的“我”的一种叙述和回顾,体现了记忆过程中的“延宕”,并通过距离感产生了象征性的力量。《李献计历险记》《重返二十岁》《记忆大师》《同桌的你》《乘风破浪》《超时空同居》等都通过情景记忆事件回顾甚至是“陌生化”的叙述实现象征化的记忆。其主人公往往以身体“穿越”或声音“穿越”的方式亲历过去“现场”,让现在与过去并行甚至直接对话,在“唤醒”与“抵抗”中,补偿错过的美好、犯下的错误,揭开疑惑、抵御恐慌,使得回忆在一个诠释性甚至否定自我的阐释行为中得到固定。哈布瓦赫说:“每个个体记忆都是一个对集体记忆的‘远眺点’,这个远眺点随着我们在集体中的位置而变化,并根据我与其他环境的关系调整自身的位置。”[10]所以说,这种记忆的讲述使得主体能够不断在集体定位中重新审视和理解个体和集体记忆,使记忆具有了一种反思性力量。
此外,网生代电影还惯于通过童年创伤、情感创伤等来深化记忆。这些创伤记忆的发生往往是通过一些无法预知的突发性事件形成张力时刻,造成了主人公成长或人生的断裂。在影片中,这种事件的影响更多是以一种“记忆疤痕”的作用存在,它们具有潜在力量,通过“唤醒”和“抵抗”的功能影响着主人公的成长。如《超时空同居》《记忆大师》《谁的青春不迷茫》《第一次》《乘风破浪》《绝世高手》《李献计历险记》中的人物都经历了铭刻于心的童年或情感创伤,他们大多具有强烈的叛逆性,缺乏安全感,甚至具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这些“伤疤”往往成为唤醒痛体验、抵御再受伤、驱动自我创造的欲望和力量,使主人公的命运走向积极或消极方向。同时,部分电影在主体意识的体现上具有巴迪欧所说的,让主体在事件中获得真相(真理),让真正的主体性显现出来的创作意识。《80’后》中,明远和星辰的童年创伤激发了他们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在他们成年后得以显现,使得两人在创伤遭遇的磨难中理解了爱的意义;《记忆大师》中的江丰遭遇记忆的困境后才激发出主体意识并懂得情感的意义;《绝世高手》中的卢小鱼遭受创伤之后失去了知觉和痛感记忆,找到初心之时恢复了知觉并懂得了“情”的真谛;《谁的青春不迷茫》中的高翔在父亲入狱后懂得了“越是沉重,越要飞翔”的生存信念,并唤醒了林天娇的主体意识;《乘风破浪》中的阿浪在遭遇车祸“穿越”之中才懂得“父辈”的人生;《滚蛋吧!肿瘤君》和《第一次》的主人公都在遭遇情感和疾病危机中激发主体性并懂得了“快乐而生”的意义。“现在的一代人是通过把自己的现在与自己建构的过去对置起来而意识到自身的”[11],当下部分网生代导演在身体记忆的书写中已经逐渐显现出自觉的主体意识。
三、记忆游戏化:快感与修复
网生代导演是在网络文化浸润下成长的一代,日韩、欧美动漫和电子游戏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我们这代开始,谁也不能说没受过二次元的影响,《灌篮高手》《七龙珠》《火影忍者》你总看过,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二次元用户。什么类型都看,日本的,或者漫威的,好看的我都感兴趣,都会看。”[12]“因为我从小就看日美的漫画、动画片和好莱坞的影片,我觉得中国也应该有很活跃的、关怀个体的、属于年轻人的,甚至包含二次元美学感觉的东西。”[13]动漫和游戏思维、视像逻辑、沉浸快感等潜在影响着网生代的创作,使网生代的电影更加偏重趣味性、赏玩性与游戏感,对记忆的表达也呈现出游戏化。从游戏文化的角度看,“游戏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在特定的时空里进行,遵循自愿接受但绝对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游戏自有其目的,伴有紧张、欢乐的情感,游戏的人具有明确不同于‘平常生活’的自我意识”[14]。在电影中,网生代导演往往通过游戏情境、游戏规则、游戏体验等多种新奇手段来呈现、选择和重组记忆,将观众代人参与和体验。《李献计历险记》《重返二十岁》《记忆大师》《超时空同居》《绝世高手》《羞羞的铁拳》等都通过游戏化的情境形成一种假定性的参与和选择空间,并通过“游戏规则”的设定,例如“把游戏打穿就能回到过去”,“记忆删除只是将参与者变成旁观者,切断细节跟感受的情感联系”和“只要出血就会变苍老”,“两个时空中的自己不能碰面,否则会加速消失”,“在我梦里我还能让你把我欺负了”等,使影片具备好看性、好玩性和参与性。在游戏功能设定中,记忆总是作为一种具有“操纵性”的驱动力或者“随机性”的意外使得人物的命运跌宕起伏。《李献计历险记》《绝世高手》都通过记忆的“超能力”驱动,以身体穿越带领观众找回本真情感;《重返二十岁》《记忆大师》《超时空同居》《羞羞的铁拳》通过记忆穿越、记忆奇遇、记忆错位等引领观众感受时光倒流以及记忆错配带来的震惊。《乘风破浪》《老男孩之猛龙过江》《同桌的你》《滚蛋吧!肿瘤君》也通过想象性的记忆感受青春(过去)记忆与残酷现实之间的流动。通过这种游戏化的方式,这些电影实现了一种沉浸、卷入或者“心流”体验,尤其是在不同属性之间的综合与切换,使观众如“玩家”获得了引人入胜的快感体验。[15]
媒介技术和媒介文化的影响也使网生代导演对于虚拟身体的感知、想象力和创造力有所增强。网生代电影中的记忆游戏化表征常常借助身体化身、欲身、交换、变形等多种方式予以呈现。约翰·赫伊津哈说,游戏的“独特”和秘密最生动地体现在“化装”之中。乔装者或戴面具的人“扮演”另一个人的角色,成为另一个人。[16]这种多重身体的游戏化体验是网生代电影中的一种重要元素,能够带领观众在快感体验中进行记忆的重组与修复。《重返二十岁》《超时空同居》《老男孩之猛龙过江》《乘风破浪》通过主人公的身体化身激发观众的奇异体验,也实现对主人公完整(完美)记忆的补充和修复;《羞羞的铁拳》《记忆大师》《夏洛特烦恼》《第一次》通过身体交换、身体错位、身体扮演等形式,在身体救赎之中唤醒自我并实现了记忆的修复;《滚蛋吧!肿瘤君》《李献计历险记》通过二次元的数字身体使主人公在“梦游般”的想象中实现记忆情感的修复。麦克卢汉说,游戏是社会肌体的延伸,游戏是我们心灵生活的戏剧性模式,给各种紧张情绪提供发泄的机会。[17]网生代导演通过这种记忆游戏化的方式不仅实现了主体知觉的快感体验,也使迷失与焦虑的主体在游戏中得以自我平抚,使断裂的个体或集体记忆得以修复。
通过对网生代电影的梳理可见,网生代导演具有很强的身体感知、身体实践和身体反思意识,能够借助多种记忆表征形式呈现具有网生代特质的“身体记忆图景”。当前网生代导演的创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具有太多变化和拓展的可能。随着创作形态的不断丰富、创作观念的不断成熟,网生代影像中的身体记忆书写也将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元、富有想象力的样貌和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