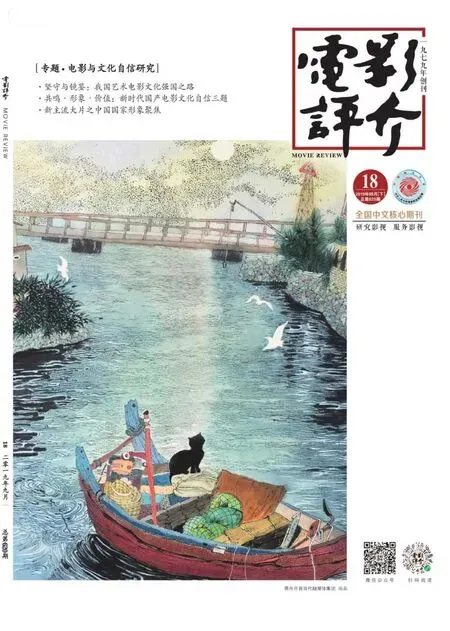后革命时代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的话语建构
——基于电视剧《伟大的转折》的叙事学考察
兰东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夕,央视综合频道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展播38集电视连续剧《伟大的转折》,讲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后的那段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历史。观看之后让人明白,这段历史并未尘封,它已融入中国共产党的血液。
一、叙事原则:当代背景下的历史书写
关于长征题材的影视已有很多,人们关于遵义会议的故事也不陌生,而要用影视作品将一个熟悉的话题再度创作,达到吸引观众的效果,需要解决很多问题。
首先,客观存在的历史不能改编,却要实现内容创新。
中国古代对历史小说创作有精辟的论述,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叙》中说:“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80多年前召开的遵义会议,其原因和结果,主流历史已记录得非常清晰。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参加会议的人物、会议作出的决议等,都有当事人的回忆和文献记载,任何文学艺术作品都不能随意编造。在这部电视剧中,对重大史实、重要人物、无争议的时间和地点、有定论的观点,创作者均未作改动,这既是对基本史实的尊重、对主流价值的尊重,也是对观众的尊重。
但是,从影视观众的心理而言,对自己熟悉的历史信息往往缺少继续观看的兴趣,对形成刻板印象的认知也不愿意接受简单的改动。就影视剧创作而言,不能仅仅停留于对历史简单的视觉呈现,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等的创新,几乎是其根本属性和本能的冲动。从叙事学理论而言,认为历史是对过去发生的客观事实的表述,表现为文本,客观事实本身不是历史。正如克罗齐所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叙事,不存在叙事的地方就没有历史。在他们看来,历史的真实看似是事件本身的真实,其实是表述者秉持客观的态度,恰当运用符号,对发生的事实所做的记录。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叙事的客观性是通过所有叙事者的关涉物的不在场来定义的。”[1]“不在场”,不是叙事者不在事件发生的现场,而是对所叙之事保持距离。该剧在文献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录之外,补充了历史人物的活动细节,增添了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的材料,展现红军基层官兵的精神状态。这不仅没有削弱该剧的客观性,没有妨碍其历史剧的性质,而且使过去扁平化的历史书写变得立体,使过去单线索叙述历史的手法变成多视角。
其次,不违背对历史的基本评判,却改变了叙事重点。
关于话语的意义,叙事学从来都不认为只停留于语义,有的人以说什么或怎么说来判断,有的人通过话语间性去分析,还有人从叙事的结构和节奏去观察。既然观众知道历史上召开过遵义会议,该剧就把重点放在引导观众去思考为什么召开遵义会议;既然观众知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那就通过详细叙事陈述为什么能成功召开遵义会议;既然观众知道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那就侧重于叙述遵义会议为什么能贯彻执行。遵义会议作出的结论则被一笔带过,语义就蕴藏于叙事的详略取舍之中。
其三,不改变影视剧的叙事传统,却巧妙运用画面语言。
该剧以湘江战役失败开篇,与其说节省了影视剧拍摄战争场面的经费,不如说是创作者不愿意把血淋淋的惨像呈献给观众。该剧的创作主旨不是为了表达革命曾付出巨大的流血牺牲,而是指向中国革命的初心、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第一集从中央红军转兵湖南通道开始叙事,接着叙述到贵州黎平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然后叙述到贵州瓮安猴场后再次召开会议,再叙述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确立,党和红军出现了历史转折,开启新的征程。
在以时间为线索的叙事中,观众直观地看到毛泽东的建议从被拒绝到被采纳,他从权力的边缘一步步进入领导核心。而转换一个视角又会发现:毛泽东的地位变化不只是因为长征中敌我形式的变化所致,关键是中共领导层对长期执行的路线在认识上发生转变,是集体的觉悟。
一方面,无论小说、戏曲,还是影视纪录片和故事片,都很忌讳创作者直抒观点。中国古代有一位笔名为“蛮”的评论家在《小说小话》中说:“最忌搀入作者论断,或如戏剧中一脚色出场,横加一段定场白,预言某某若何之善,某某若何之劣,而某人之实事,未必尽肖其言。”[2]该剧的创作者没有直接提供观点,观众通过细腻的叙事,隐约体会到遵义会议本身不是党和红军的历史转折,而从叙事情节中认识到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其实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是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抛却私心和坚守初心的结果。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党和红军的历史转折,是因为在革命的大熔炉中经受血与火的洗礼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另一方面,电影或电视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都离不开意义表达。在意义表达时,“表演不是主要的,意义是在上下镜头的联系中产生的,不同的画面可以组合在一起,并产生隐喻”[3]。该剧充分运用影视画面的组接来表达意义,画面中红军在遵义会议前后的精神面貌、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言行举止直接传达意义,画面的构图和组合间接表达意义。该剧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对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红军生存状态的叙述,对中共中央高层领导艰难抉择的铺叙,对四渡赤水酣畅淋漓的记录,“既是一种表达方式,也是对事实的解读”[4]。观众从这部电视剧中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错误的路线和决策会断送革命成果,英明的领袖会使领导集体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健康的组织是决策得到贯彻的保障。
二、叙事策略:国家叙事主导下兼顾民间叙事
正如特里·库克所言:“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生活在后现代社会里。”[5]后现代社会是价值观多元的社会,反对一切形式上的元叙事,关注“他者世界”和“他者声音”。也有人把现在所处的时代称之为市场时代或“后革命时代”,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和社会功能多层化,“文化越来越听从市场逻辑的支配,而不听从先验理论逻辑的支配,主流文化在失去对文化市场的掌握权的同时,也在失去对历史叙事的特殊解释权”[6]。文学艺术作品表现出多元叙事占据主导地位,叙事策略转向以市场为主导的消费性书写,影视剧不乏对红色文化以消费性视角来建构主题。甚至有人认为“后革命”时代的“后”,一方面是在革命历史及革命的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另一方面是对革命的历史及其意识形态的反思甚或批判,叙事中的反思抑或批判革命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7]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发生在80多年前,今天的人们了解那段没有留下影像的历史,只能借助于传说、口述、文献记录、珍贵的照片和实物。当年留下的会议决议和实物只是客观事实;传说、口述、回忆录和照片都是用符号对当时事件的意义建构,它尽管在时间上与这部电视剧建构意义有先后,但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创作者在今天制作这部电视剧,不可能只满足于对那段历史用光影重现,它表现出来的人物形象、叙述的长征故事其实在建构意义,是当代人与那段往事相遇时的表述。从理论上讲,“当人与某个未知的、危险的、以前非常遥远的东西狭路相逢的时候”“人、地方和经历总是可以通过书本而得到描述,以致书本(或文本)甚至比它所描述的现实更具权威性”[8]。但是,描述总是带着时代烙印的描述,即使最接近真相的历史描述也在建构描述者的主题。
该剧第一个原则就是坚持主流叙事,回应民间多元价值。创作者为何要再现这段往事?再现往事选取哪些片段?用什么线索把片段串起来?这就建构了意义,形成了自己的话语。
该剧在叙事中更多地观照了民间态度,屏幕上的博古(秦邦宪)等“左”倾路线推行者不再是曾经描述的那样冷血,他们对红军战士一批批倒下也心痛如绞,他们在革命巨大牺牲之后也在反思和纠正错误。从剧中看到毛泽东等伟大领袖积极努力促成遵义会议,还看到曾经的“左”倾路线推行者不断放弃教条主义,他们都有共产主义信仰,都有同样纯洁的初心。该剧叙述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指挥土城战斗失败,还原了真正的历史,无损毛泽东的形象。中央没有因为毛泽东指挥一次战斗失败而轻易撤销其职务,足以说明遵义会议作出的决议的严肃性,足以证明党中央严格遵守会议决定。创作者淡化遵义会议本身而对会议召开前后详细叙述,采用了既符合主流价值又符合平民认知的叙事策略,兼顾了消费传播的大众心理。
今天已进入后现代社会,对革命的认识置于后革命时代成为常态。中国进入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高度商品化,社会生活高度娱乐化,社会思想高度平面化,影视作品就不可无视当下的消费风潮。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革命历史无法改变被消费、想象、改写的命运,革命的资源与回忆以被改编的方式搬上屏幕不可回避,在消费主义笼罩下就会孕育出“后革命之花”。文化无法完全超脱市场逻辑的支配,不能完全受制于先验理论逻辑的支配,国家叙事在失去对文化接受者绝对掌控权的同时,就要俯身靠近民间叙事,改变对历史叙事的传统策略。近几年来,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国产大片和电视剧不断推出,展现出“后革命”时代的影视叙事特点,为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叙述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路径。该剧借鉴了很多后革命叙事的历史影视剧的经验,仍关注历史本体,一如既往地在主流意识形态下对历史文本重构,同时兼顾个人化和民间化的历史叙述,对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遵义会议的决议之所以能得到贯彻执行作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叙述,从而赋予了共产党人新的面孔和遵义会议新的意义。其叙事策略总体上仍沿袭国家主流话语叙事,对伟大的长征坚持严肃主题,伟人的气质、红军的精神、蒋介石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军队的形象基本上定格在传统的框架之中,观众没有看到颠覆性的形象。又巧妙地融入当下民间话语,改变曾经的“一元化”单一的革命叙事模式,兼顾对革命历史书写的社会价值的多元性。在刻画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时,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红军官兵的内心世界用平民视角观察,从平民的价值取向去体察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情怀,使观众在消费性收看中结合自身去感受革命道路探寻的艰辛。
该剧另一个原则就是采用显性的国家话语与隐性的民间话语的双重叙事,表现崇高的同时,满足文化消费时代影视娱乐性。在对遵义会议历史的处理和表述中与当下的政治建设耦合,真实人物与虚构情节相互交融。
作为历史正剧,在失去了戏剧化效果的可能之后,世俗化、平民化的叙事至关重要。在观众不必牵挂人物命运和红军前途的观看心理下,必须实现剧中人物和观众的情感认知双重同构效应。该剧突出中共领导人物与环境的冲突、领导层之间的冲突、影响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这些冲突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效果,这些冲突在纠缠中缓解和化解,促成了遵义会议召开,达成了遵义会议决议。这些充满“后革命”时代的叙事特色,完成了革命历史崇高品质的再现和“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历史世俗化的重构。一方面为观众重新揭开遵义会议历史的面纱,另一方面加大了我们探讨那个历史时期党和红军命运、共产党人初心、长征精神的政治想象空间。
在双重叙事的弥合下,通过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政治理想和个人情感、党的路线和现实处境叠加,深刻地演绎人情、人性和党性的关系。这种手法增强了历史的沉重感,拉近了历史与当下的距离。在剧中,观众看到了残酷的革命斗争和尖锐的党内路线斗争以及领导人物内心的思想斗争。该剧塑造的形象都胸怀大局,都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他们只是在探索革命道路时对国情和革命形势认识上的不同,他们都可敬可爱,都有温度。在宏大的叙事中不失微观叙事,在国家叙事不失民间叙事,在表现崇高时不失世俗观照。党和红军曾经发生的历史不容虚构,观众对结果已无悬念,但是在微观叙事上强化各种冲突的展开和化解,照顾到了媒介消费时代的审美趣味。
三、叙事技巧:外视角叙事中包含内视角叙事
选择以遵义会议为电视剧题材,一开始就使创作者面临四个难题:第一,观众对基本史实清楚,结果几乎失去悬念;第二,只能做成历史正剧,不可戏说,创作空间小,增加故事性和趣味性不容易;第三,以会议为核心要素,没有战争片宏大的场面和视觉冲击力;第四,将已有定论的历史以影视的方式呈现,需要突破却又存在风险。
为了克服这四个方面的困难,该剧在叙事视角上作了精心设计。视角被西方批评家认为是叙事的规定性特点,[9]因为处在故事与读者之间的是叙述者,他叙事的视角决定着讲什么和让人怎么看。
该剧的题目为“伟大的转折”,转折点是遵义会议。转折只有在前后比较中才能充分体现。所以创作者没有急于对遵义会议直接记录,而是从红军在湘江战役失败后开始叙事。以此作为叙事的起点,一是因为稍有历史知识的观众都知道最终结果却未必知道细节,通过增加细节以满足观众的心理期待;二是通过突出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和“左”倾路线推行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形成观众的情感和剧中残酷的生死存亡之间的对立。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有“百折千回法”,读者越是急于了解就越是故意延宕,令人心痒难熬。该剧在讲述中央红军遵义会议之前那段惨痛历史的时候,创作者以观众之外的视角叙事,刻意使用非常缓慢的节奏:红军湘江战役后从8万多人锐减至3万人、李德无视红军将士的牺牲仍固执己见、博古没有勇气冲破教条束缚而面对现实一筹莫展、毛泽东机警睿智却没有决策权、周恩来和朱德等红军将领明知不可为而只能为之、广大官兵慷慨赴死却做着无谓的牺牲。观众希望剧情快速推进,而镜头却几乎滞塞凝固。这种刻意制造出的剧情和观众的心理在观剧的过程中形成冲突,使观众既想跳出剧情却又深陷剧情之中。观看剧情的心里憋屈与中国革命这段憋屈的历史奇妙地达到高度统一,由此而使观众在昏沉的画面观看中深刻理解革命先辈在危急时刻的艰难抉择。当剧情推进到红军占领遵义城的时候,观众的心情如释重负,期待电视剧最核心的部分出现。当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创作者又叙述土城战斗失利,毛泽东再次陷入舆论漩涡,观众对结果又产生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是创作者站在观众之外特意设置的。
评判一部影视作品是否为历史正剧,主要根据两条标准:必须忠实于客观事实;对待历史必须用严肃的态度。严肃的态度本质上是叙事者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又是通过叙事来实现的,表现为剧中当事人看待事件的立场、处理人物关系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手段等。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持否定态度、彭德怀拒绝接受最高军事指挥官李德决定时怒骂、刘伯承提醒红军战士砍伐当地老百姓楠竹后记住留下银元、第三军团参谋长邓华牺牲后许多中央领导都眼含泪水……这是长期以来国家叙事的立场,具有外视角叙事特征。博古听到各军团上报湘江战役牺牲人数后痛哭、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不遗余力促成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也不能确定最后的结果……这是今天民间叙事假设身处其中的历史描述,具有内视角叙事的色彩。
该剧最核心的内容是遵义会议,采用外视角叙事便于调度观众情绪。在讲述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历史时,故意延宕情节以蓄积观看的期待心情,一方面消解观众对故事性的挑剔,另一方面也可增强观众对结果的探知欲望。观众寻求剧情答案的急迫心情和对革命前途焦虑的情感相互交织,模糊了影视剧与客观历史的界限,情绪随着剧中主人公的态度、人物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而起伏。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穿梭于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周恩来游走于博古和毛泽东之间,朱德纠结于最高军事长官李德和广大红军将士之间,博古徘徊于党员初心和当前处境之间,观众也漂游在电视创作者营造的艺术氛围与自己观看电视剧的现实环境之间。把对会议作出决定的叙述转变成对会议之前核心人物关系的叙述,会议的决定因此如水到渠成。观众的历史知识储备已经知道遵义会议的基本内容,通过该剧了解会议召开前的细节,获得填补信息短板的满足感。
在外视角叙事中,又总能看到内视角叙事的影子。每一个中共高层领导都在经受灵魂的拷问,都在坚守党的组织原则和直面残酷现实的矛盾中挣扎。中央政治局书记博古尊重集体意见,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建议在会上总结湘江战败的问题。因为张闻天与周恩来极力主张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博古服从党的组织原则,尊重多数人意见,同意更改议题。周恩来深刻剖析自己执行“左”路线的错误,彭德怀直言不讳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损失,张闻天和王稼祥客观回顾过去,朱德正视目前的严峻形势,刘少奇、陈云等同志都把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放在第一位,他们立体塑造了共产党员的群像。作为电视剧,不可能把这次会议转化成宏大场面;作为尊重历史的电视剧,不应该杜撰违背基本史实的人物冲突迎合观众的浅层次心理需求。创作者用当代眼观重新审视这段早已定性的中共党史,用内视角书写人们熟悉的这段中国革命史中人物的思想情感,开启了历史与现实、老一代革命家和当代人的对话。在对话中重温历史、审视历史,并从对历史的重温和审视中实现观剧的娱乐、信息获取、思想引领等传播效果耦合。创作者把观众带入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之中——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并取得具有转折意义的结果,充分说明当时党的政治生活依然健康,党的集体初心仍在。这种叙事技巧符合历史,又没局限于已有的历史叙述框架。
遵义会议之后的历史,今天很多人只知道党和红军有了毛泽东的领导,中国革命从此转危为安,但是并不清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立还经历了一个过程,更没有冷静思考遵义会议的决议能够得到贯彻的深层原因。该剧详细地讲述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确立,又经历了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阶段。毛泽东在遵义会议确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总司令朱德与政委周恩来才是真正的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定的负责人。毛泽东策划的四渡赤水摆脱蒋介石和军阀“围剿”,他的军事才能更加彰显,在周恩来提议下,博古欣然同意由毛泽东领导全局。这在表面上是外视角叙事,其实在引导观众以内视角去思考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实现转折的历程。
今天,我们能够从电视剧中看到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形成有一条清晰的政治逻辑。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失败,党和红军需要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领袖力挽狂澜,毛泽东经过革命洗礼成为党的核心是时代的选择。毛泽东指挥土城会战失败,中央没有因为一次战斗的损失而改变遵义会议决议,最终成就了毛泽东军事指挥四渡赤水的杰作,观众能够从中真切理解复杂的形势需要灵活应变,更能从中深刻理解党的决议的严肃性。在这部电视剧中,观众不仅看到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而且从该剧细微的铺陈中体会到这一结果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从未动摇的宗旨作思想保障,离不开党的组织原则作制度保障。“叙事的超真实”才是影像创作者追求的真正的“真实”。[10]
对每一位中共领导人细腻的叙述,观众仿佛感受到共产党人一直坚守初心的温度,从而认识到遵义会议成功召开是一个必然结果,间接地给出了遵义会议决议之所以得到贯彻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