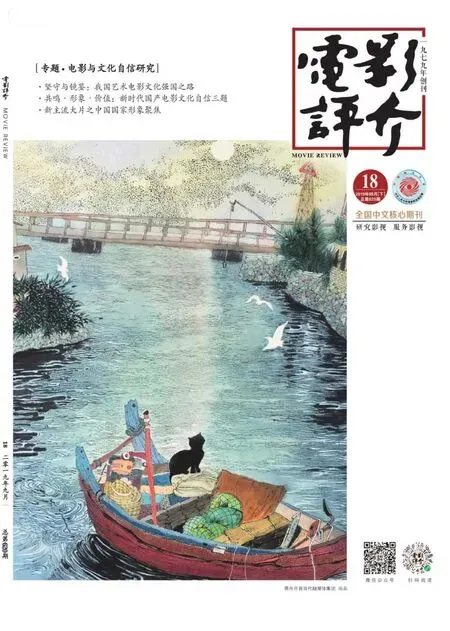《攀登者》宏微观情感叙事解码
宋 晖
2019年国庆节前夕,由李仁港执导的《攀登者》正式上映。作为一部主旋律影片,主要讲述了中国登山队1960年、1975年两次从珠峰北坡登顶的事迹,在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基础上有所改写,使得故事有了很强的戏剧性和可看性。主演吴京在剧中占据了最大戏份,影片具有吴京近年主演影片的典型特征,即情节紧凑、注重视觉效果、将宏大叙事与情感叙事结合起来,尤其是情感叙事,比《战狼2》更为突出和丰富。
一、宏大叙事中的家国情怀
作为一部国庆献礼片,《攀登者》讲述的是两次攀登珠峰的具体登山者,也隐喻为国“攀登”的各行各业奋斗者。影片以两次攀登为主线,一轻一重,重点讲述了1975年,在老队员方五洲和曲松林带领下,李国梁、杨光等年轻队员再次向珠峰发起登顶挑战的故事。影片洋溢着家国情怀,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中表现了登山运动员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作为主旋律影片,《攀登者》追求一种史诗般的宏大叙事效果,力求将影片拍成一部体现“现代强国梦”的国家史诗。一般认为,史诗的叙事特征主要有两种,一是要展示“广阔的文化时空范围”,二是在叙述中要体现“历史的某些必然的规律性”。黑格尔认为:“史诗以叙事为职责,就必须用一件动作(情节)的过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联系上,必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1]影片开始就是蓑羽鹤在天空自由飞翔的镜头,画外音介绍这是一种鸟,为了飞越山峰,牺牲生命在所不惜。画面隐喻了登山队员的使命,也使得故事有了一种抒情性和史诗的悲壮性。影片简单交代了1960年登山的背景:中国、印度面临领土纷争,珠峰登顶因此关系到国家大义,对于解决领土争端有直接意义。故事从一开始就放在了国家宏大叙事的框架下展开,在影片中,更是通过演员点出了登山的意义:“我们自己的山,要自己登上去。”珠穆朗玛峰成为一个符号象征,既是山在那儿要去征服的客观实在,也是实现家国情怀的一个最高象征物。由于1960年登山队为了救助队员,丢失了摄像机,导致没有拍摄下证明镜头,于是有了1975年的第二次登山:“要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登上自己的峰顶。”“要测量珠峰准确的高度,中国的高度。”
在影片中,这种家国情怀是通过反复强调表现出来的。于是我们看到,队员在第一次登顶之后,高呼祖国万岁;井柏然扮演的李国梁主动请缨要去担起登山大任时说:“你们这一代人总是在国家最因难时接过国家的重任,为什么我们不能?”第二次登顶成功,吴京扮演的方五洲向总部报告时说:“报告大本营,报告祖国,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这种爱国之情是登山队员之间的重要粘合剂,也是凝聚观众的向心力,国家叙事被成功放置在艺术修辞语境中。“叙事的目的就在于把一个社群中每个具体的个人故事组织起来,让每个具体的人和存在都具有这个社群的意义,在这个社群中,任何单个的事件,都事出有因,都是这个抽象的、理性的社群的感性体现(黑格尔),这个社群或‘国家’、或是民族、或是人类。”[2]伴随着电影进程,影片充分表现了第一代登山者的精神、第二代攀登者的情怀以及以徐缨为代表的气象工作者、后勤工作者对攀登者不遗余力的帮助和支持。这些形象与精神已经上升为每一位观众的共同情感。攀登者通过攀登这一行为,将奉献、团结、爱国主义等抽象的价值观与强烈的家国情怀联系起来。作为祖国象征的符号表征在影片的刻意安排下同样一再出现,如登顶时插上的国旗、测量珠峰高度的觇标、中国登山队在第二台阶处安装的中国梯。这些符号表征以艺术的方式展示着祖国的形象,与影片叙事语境融为一体,成为国家叙事的重要修辞手段。
二、微叙事中的儿女情长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说:“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3]如果说影片的国家叙事是通过史诗式的风格、宏大叙事和多种表征来实现的,那么剧中对于主要角色的性格和内心的表现则落实在微观叙事上,主要是通过感情故事进行展现。与宏大的叙事相辅相成,在微叙事中体现人物情感,以情动人成为该片的重要特点。
“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角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4]《攀登者》整个故事是以方五洲恋人、气象学家徐缨的视角展开的,从她的视角讲述登山队的故事。徐缨的讲述一开始就表明,两人的感情结局是不圆满的,给故事带来了悬念。故事讲述中,始终在全知全能的视角与徐缨的视角之间切换,给影片叙事带来了更多的悬念与趣味。
整个影片穿插了两段爱情故事,一段是方五洲和徐缨之间的感情故事,另一段是年轻队员、摄影师李国梁和黑牡丹的感情故事。两条感情线一强一弱,其中,李国梁与黑牡丹的感情故事略写,方五洲和徐缨的感情故事则浓墨重彩,两段感情故事在整个影片中占据很大分量,与登山故事融为一体。两段感情均是因为登山开始,李国梁与黑牡丹是在登山队认识,在训练中产生感情,又因李国梁在登山中牺牲而导致刚刚萌芽的情感戛然而止。方五洲和徐缨同样如此,由于1960年的登顶不被国际承认,方五洲因此有了心病,两人之间有了一座无形的山,感情也随之陷入危机和停顿。徐缨支持方五洲的登山事业,并冒着生命危险向登山队通报气象信息,导致肺气肿病逝于珠峰,在临终前向方五洲表白:“我们之间的山消失了。谢谢你让我真正谈了一次恋爱。”在这里,珠峰既是要翻越的物质的山,也是两人要克服的心理上的山。家国情怀和儿女情怀融为一体,宏大叙事与个体微叙事融为一体,个人的感情因此不仅是抽象地和国家信仰结合了,个人和国家也融为一体。
影片不仅表现了爱情,还表现了亲情和友情。队员杨光虽患有马凡综合征,但仍然坚持登山,而他登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过世的父亲能够在天上看到他登顶那一刻。方五洲为了救曲松林,舍弃了摄像机,导致第一次登顶没有留下影像证明,此后10余年得不到社会理解,曲松林也因此一直无法原谅方五洲。两人同时又有着深深的信任与默契,训练时,一个眼神就可以站出来力挺对方。李国梁为了不拖累队友,砍断绳索掉入深渊。剧中对于感情的表现与故事情节紧密结合,因此,这种感情不再是灌输性的,而是感染性的。
尽管故事的感情线设定有着独特的刻画人物性格和内心的作用,感情段落一般来说也符合观众的口味,然而,这两段感情还是有一定的不足之处。方五洲和徐缨的感情仅仅是由于登顶得不到承认就陷于停顿,10余年不联系,难以说服观众。李国梁和黑牡丹的感情戏也比较单薄,有些游离于故事主线。剧中表现浪漫情境的段落,由于受到西方电影情节的影响,与整个故事的氛围不合。如方五洲第一次登顶成功,在兴奋与喜悦中向徐缨表白,并在工厂建筑里展示攀登技巧,徐缨则在一边念着西方小说教堂攀登求爱的段落,感受着方五洲的爱意,更像是从西方爱情电影里移植的情节。此外,黑牡丹偷偷闯入李国梁房间,想要接近对方,也显得不合情理。
在个人情感叙事上,影片略显老套,对于当代观众的审美趣味和个人倾向不够敏感。当前观众认同的是“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主流叙事更多的是将个人幸福与祖国强大联系起来,而非对立。然而《攀登者》中两段感情无一圆满,隐隐将个人幸福与祖国建设对立起来,并且这种对立缺乏合理情境,难以得到当前观众的认可。
三、当代文化语境下的情感叙事矛盾
情感叙事既是当代电影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教化、影响观众的重要手段。对于影片而言,对于情感的处理是影响传播效果和票房的重要因素。如何处理情感,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作为一部商业片,《攀登者》必然要将票房作为重要的考量,同时,影片自身作为主旋律影片和国庆献礼片的定位,又必须要将弘扬主旋律作为主要任务,由此产生了该片在情感叙事方面的内在压力。
对于《攀登者》而言,情感不仅具有连缀事件、推动情节的功能,更是影片表现的目标。主导情感是“为国登顶、寸土不让”这样一种爱国情怀,对方五洲个体而言,则又有为爱攀登的含义。《攀登者》情感叙事的基调是崇高的,在弘大叙事层面,这种崇高体现为为国家牺牲小我情感;在微叙事层面,崇高体现为个体在国家面前放弃个人儿女情怀。在《攀登者》中,一再强调的是珠峰的难以攀登,如在攀登珠峰途中,一直用字幕表明气温和风速。个体的渺小和珠峰的冷漠,形成令人畏惧的对比。片中有一个细节,在第二次登山时,寺庙里的喇嘛们表示,珠峰登顶不会顺利,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神并不总是慈悲的。珠峰的难以攀登在影片中有了一种绝对性,一种让人敬畏的特质。这既是叙事的需要,也是激发观众崇高和悲壮情感的需要。珠峰让人畏惧,并成为影片中要克服的对象,不仅出于爱国情怀要克服,而且为了个人情感也需要加以克服,在这个层面,家国情怀和儿女情长统一起来了。
然而,遗憾的是,影片在处理情感矛盾时的摇摆不定,导致影片的情感叙事出现了矛盾。导演李仁港说,影片的主线不是集体荣誉而是证明自己。这就与历史上真实的登顶故事有了很大的不同,也与宏大叙事的主调产生了内在矛盾。影片的题材本身决定爱国情怀、宏大叙事必然是占据主导的,但由于商业片的内在逻辑,又使得影片导演去迎合市场、迎合观众、排斥宏大叙事,试图以儿女情长去获得观众认可。
强行扭转主题的结果之一,就是儿女情长作为人物个性、证明自我的手段之一得到了过多的讲述,“这种将爱情抽离出系统性来特别强调的现象,透露出强化文本消费性的意图”[5]。这种脱离故事主干的过多的儿女情长,损害了影片的崇高感、悲壮感,使得影片失去了本该带给观众的情感净化体验。
强行扭转主题的结果之二,就是情感设置不合理,强行将攀登与个人情感糅合在一起,而不是尊重情感发生发展的自身逻辑,导致人物感情不符合逻辑,完全成为登山的附庸。而这又恰恰不符合当代观众强调情感独立、自主的精神。
强行扭转主题的结果之三,就是商业情感叙事目标与故事题材情感基调的矛盾。商业片的一个重要功用就是使观众的情感和本能在观影中能够得到充分宣泄和释放,从中得到替代性满足。因此,大团圆的结局是观众最为喜爱的。影片固然遵循了商业片的逻辑,将主角方五洲打造为超级英雄性的角色,每次能够奇迹般脱险,然而对于《攀登者》而言,宏大叙事下的爱国情怀、为国奉献一切的精神和众志成城的集体荣誉感,是影片题材最为打动人心的部分。为了体现这一点,一个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让人物牺牲。牺牲生命、牺牲健康、牺牲爱情,于是有了李国梁的视死如归、第一次登山队长的牺牲,有了曲松林的残疾、杨光的截肢。作为个人情感的两段爱情,也是悲剧结尾,观众很难从中得到情感宣泄和替代性满足。
强行扭转主题的结果之四,就是对于情感的处理不合当时历史情境。影片的个人情感叙事是拍给当代观众看的,但是20世纪60至70年代的情感语境与当今大众文化语境有了很大区别,这就使得当今观众能够接受的情感叙事和当时历史语境下的情感不一样,大众文化语境下的世俗情感消费与历史语境下的崇高奉献产生了较大矛盾。对于《攀登者》而言,导致的结果就是当代观众无法理解方五洲和徐缨15年守望的感情故事,产生了排斥。仿佛是为了弥补前一段感情故事过于脱离当代语境的不足,影片又讲述了年轻一辈李国梁和黑牡丹的感情故事。李国梁偷拍黑牡丹,黑牡丹心疼对方、在训练中偷偷放水,黑牡丹热情奔放、主动展开追求等这些故事情节更多像是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展开的。其中,李国梁牺牲后,黑牡丹看着李国梁留下的偷拍照片泣不成声,更是可以看到对日本电影《情书》的明显借鉴(《情书》的男主角也是一位登山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然而,尽管这段故事符合了当代观众的审美趣味,但是这种情感表达模式,无疑是与当时的历史情境相悖离的,于是,尽管感情本身可以引起观众的共鸣,但是却由于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情境,同样让观众觉得虚假,难以产生代入感。
“商业性影片的情感叙事为大众提供了释放情绪和压力的渠道,但并未体现个体真正的自我意识和真实需求。”[6]这句话可以说是点出了商业片情感叙事的本质。《攀登者》情感叙事始终处于游移之中,导致的结果就是影片既未满足观众释放情感的消费性欲望,也未能唤起观众深层的情感共鸣。
结语
2019年,国庆期间,三部主旋律电影《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同时上映。三部影片中,原来最被市场看好的《攀登者》却在国庆档期中垫底,尽管票房也不错,但是相比另外两部明显落后。是什么使得这部影片在市场看好、档期优先的情况下没有成为档期票房第一呢?
考察同档期另外两部影片,我们可以看到,《我和我的祖国》启用了7名导演,吸纳了大量明星演员,充分运用了流量思维,将影片打造成一部类似于春晚、能够尽量照顾各方口味的影片,注意各方面的平衡——主题的平衡、明星的平衡、悲喜剧的平衡、现实与历史的平衡,尽可能多地将可能的观众吸引到影院来。尽管有表现历史的《前夜》《相遇》,但更多的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后,更容易得到观众的共鸣。《中国机长》更是直接改编自2018年川航的飞机事故。由于乘机出行已经成为中国民众的重要出行方式,故事题材因此具有了接近性,加之同类型电影较少,题材本身又有了新奇性。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两部影片的结果均是圆满的(《我和我的祖国》中仅《相遇》结局不够圆满),符合国人对大团圆结局的偏爱。这一点,在节庆档期尤为明显。
相比之下,《攀登者》的故事时代背景相对久远,与当前的文化和社会语境有所脱节,影响到了其票房。首先,在对个体情感的处理上,采用的是悲情叙事,不符合观众的观影期待。其次,则是情感叙事上的逻辑性不足,难以说服观众。此外,《攀登者》的情感叙事与认知叙事存在巨大的矛盾。作为一部商业类型影片,《攀登者》可以归类为行业片、灾难片,观众期待看到的是专业知识和写实的大场面,从而满足自己的认知需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机长》基本没有什么感情戏,却仍然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收益,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影片满足了观众的主要观影诉求。尽管《攀登者》在艺术成就、叙事技巧、制作精良度上,比《中国机长》强出很多,但是过于煽情的情感叙事,忽视了观众的认知需求,导致在票房上未能超越对方。
《攀登者》在票房方面的挫败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如何更准确地把握观众的观影心理,通过总结包括《攀登者》在内的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和运营经验,从中得到一些关于主旋律电影创作和策划、发行的共同规律。而这也需要电影界、学术界今后进一步加以研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