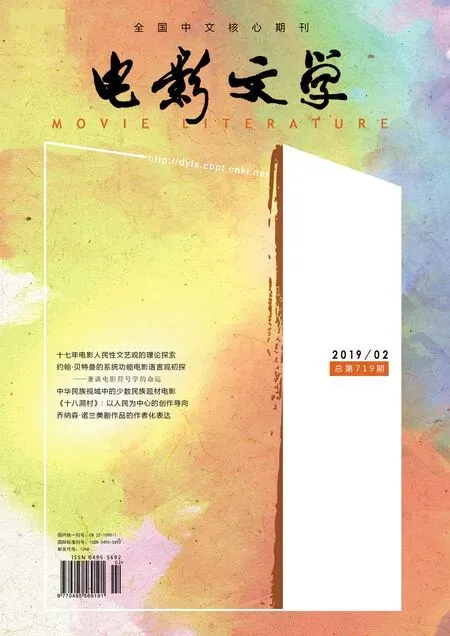規訓與體驗的四次交鋒
——对电影《东宫西宫》的文本读解
陈希洋 (福建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根据中国知网CNKI以“东宫西宫”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从2000年到2018年一共有43条检索结果,然而关于电影《东宫西宫》的学术研究却只有20篇左右。其中,又集中于两类:对导演张元的访谈录或个人研究和放置在其他学术理论或视域下的电影研究。
比如,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及表演版)在2000年第2期刊登的两篇Chris Berry的《导演张元采访录》以及崔子恩的《张元简历》。周旋《张元 我是一个职业导演》(《电影评介》2001年第12期),赵晓兰、张元《张元:宽容与自由的传道者》(《当代电影》2006年第5期),已经停刊的《当代艺术与投资》2010年第4期刊登了一篇《有种:与张元对话》等都是对于张元的采访与对话,而硕士研究生王苏的毕业论文《迁徙的灵魂——张元电影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6月)等则是对张元导演电影作品的集中读解。
此外,还有Adam Lam《“第六代”:后现代文化的符码“仿真”——张元、管虎创作比较研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以后现代文化及杰姆逊的符码理论分析了《东宫西宫》隐藏的“第三世界”话语文本。李正光的《中国第六代导演的影像话语》(《福建师范大学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和其博士毕业论文《“以丑为美”:第六代导演的审美观》(福建师范大学2006年4月)等在“第六代”导演的话语之下对张元导演研究有所涉及。其之后的《先锋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寓言——张元电影〈东宫,西宫〉解读》(《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7年第1期),从同性恋者的生存背景、创作者的表现策略、身份认同的寓言性表述等几个层面对电影《东宫西宫》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与读解。刘舒婷《边缘身份者的权力诉求——浅析〈东宫西宫〉中同性恋文化与权力控制关系》(《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9期,已停刊)从小史和阿兰“权力颠覆”角度解读同性恋身份者的权利诉求与表达。
在关于电影《东宫西宫》为数不多的研究当中,大多数又都是将其放置在“同性恋”“亚文化虐恋”“地下电影”状态、“张元导演”甚至是“第六代”导演等话语之下,而很少有针对电影《东宫西宫》的读解。或许是因为张元导演一贯的“叛逆”与“先锋”使得拍摄一部号称“中国大陆第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这一行为本身承载了太多复杂隐晦的所指和意识形态的表达,而导致对于电影作品本身的文本分析受到了有意无意的忽视。从“规训与体验”四次交锋的叙事角度对电影《东宫西宫》文本本身的读解,正好可以对这一研究领域做出有益的补充。
一、话题&题材:“男同性恋”“sadomasochism”“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电影《东宫西宫》所呈现出来的容易辨识的面貌大概就包括了“男同性恋”“sadomasochism”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等形而下的直接意指。
同性恋现象古而有之,但同性恋(homosexuality)这一概念是随着19世纪对人类个性发展与人类性行为研究的开展而被创造出来的。[1]导演坦言,自己是因为在报纸上看到的一篇关于艾滋病研究所对同性恋者调查的报告而引发的剧本故事写作,在这一事件中,导演将目光集中于警察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得出“权力”的答案。(1)参见Chris Berry:《导演张元采访录》,《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4年第2期。可见,《东宫西宫》的电影文本并非立意于“同性恋亚文化”而是“主体与权力”。
第六代导演在创作之初,求变心理极其强烈,以“真实”来反对“寓言”,喊出“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的口号。(2)参见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新的影像、新的人物使得第六代导演们的创作具有明显的“代群”特征。“同性恋者”作为新时代下被遮蔽的新发现,往往成为他们影片中的“新人物”。《东宫西宫》不仅选取了同性恋者作为影片的主角,而且这位男同性恋者,更是虐恋行为中受虐的一方。“虐恋”(sadomasochism)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艾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创造的,是他首次将施虐倾向(sadism)与受虐倾向(masochism)这两个概念引进学术界,使之成为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概念。我们采用的“虐恋”这一译法是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提出的。[2]身体的“献祭”是精神“献祭”的载体,但这种“献祭”是为了得到“控制”。它是权力关系的仪式化和戏剧化表现,虐恋中的权力不是真正的权力,却是权力的标志,以此来探讨人与人之间权力关系的主题。(3)参见李银河:《虐恋亚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影片中不断重复的“死囚爱刽子手,女贼爱衙役,我们爱你们,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实在是有斯德哥尔摩病症的嫌疑。京剧曲目《苏三起解》本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珍品,但在《东宫西宫》里的运用已经剥去了其现实主义的精神而幻化成为个体独立的“内在体验”(L’expérience intérieure)。(4)参见乔治·巴塔耶:《内在体验》,尉光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女贼和死囚并没有什么冤屈,也没有什么罪行,是一种“缺失的在场”,更多的只是一种身份,恰好与衙役和刽子手相对,就像影片中的“我们”与“你们”相对。在死囚被行刑的那一刻,她体验到刀锋的锐利和冰凉。在女贼被捕的那一刻,她体验到衙役手掌的粗大有力。以内在体验为基础的感性主义就此感受到对痛苦施加者的不胜感激。(5)参考吴迪(启之):《中西风马牛》,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当中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对张艺谋导演电影《活着》的分析。
电影《东宫西宫》作为第六代导演的重要代表作品,集中体现了第六代导演话语里复杂的能指和隐晦的所指。《东宫西宫》将男同性恋作为影片主角,故事的主要关系在两个男人的对话之间展开,通过讲述来告诉观众同性恋是如何形成的可能性。在当时的社会语境里,确实有向主流话语挑战并正视同性恋现象的现实意义。或更确切地说,影片的能指所包含的对同性恋者的关注,是一种深深的人道主义。
二、人物:个体存在的四次情感体验
当影片开场,人物进入之后,很快地便集中于小史对阿兰在派出所值班室里的拷问。正如麦茨所言,对于电影而言,任何叙述都是一种话语。在《东宫西宫》之中,虽然是作为警察的小史一直在对阿兰进行拷问,然而主导话语的走向很快便转为了阿兰主动言说的形式。在这一过程之中,阿兰的四次情感体验通过言说的方式得到话语权利的认可而逐步加强;小史的四次规训(discipline)却在不断地遭受质疑甚至到最后走向失败(有了生理反应)。在这四次交锋之中,创作者(导演张元和编剧王小波)的立场和表达便通过文本得到了展现。
体验就是在狂热和痛苦中追问(检验)一个人关于存在(être)之事实所知道的东西。体验,是唯一的权威、唯一的价值。它走向了人之可能性的尽头,正是体验,而非预设,产生了揭示。[3]阿兰对于自己同性恋成因和感情经历的自我主动讲述,正是在狂热和痛苦中不断地追问、检验关于自己存在之事实所确定能把握的东西。换言之,阿兰的体验走向了真实,走向了真情实感,确切的痛与乐。小史对于阿兰的规训(discipline)则是基于自己“警察”的身份生发的,这是他的工作和职责,是社会运行体制的要求而非小史的主动追问与检验。阿兰的言说,是一种“坦白”——一个人确认自己的行为或思想,坦白真相内在于权力塑造个体的程序之中。[4]在小史与阿兰的一晚上对话之中,伴随着小史规训(discipline)的失败,是小史(在阿兰的“启蒙”之中)不断走向面对自我的体验过程。至影片结尾,这一晚的经历,对于小史来说,也是一次独立个体的内在体验。
第一次交锋,是小史作为警察以强有力的执法者的姿态进入影片的。警察在公园里逮捕同性恋者,并让其自己打自己嘴巴,蹲在地上,大骂“社会渣子”。小史逮捕了阿兰,将其带往派出所,却不料在半路上被阿兰反亲一口跑掉了。在第一次交锋中,阿兰面对权威便是不卑不亢,因为体验是唯一的权威,人的权威将自身定义为质疑本身。(6)参见乔治·巴塔耶:《内在体验》,尉光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所以,小史作为警察的执法者对于阿兰而言,“算不得”权威,阿兰将小史视为个体,一切平等的个体。所以,当他爱上了他之后,便调皮地吻了他然后跑掉了。更为准确地规训(discipline)的开始是小史真正将阿兰带回派出所值班室,或者说,是阿兰愿意和小史去一趟值班室(阿兰并未像他的同伴那样仓皇逃窜)。
要想理解规训(discipline),必须先注意到成为社会历史核心现象的是:它们在整个社会身体的层面上,以一种无所不包的方式,表明权力关系和策略关系之间的密切绞合,同时也表明了它们之间的互动后果。小史作为规训(discipline)行为发出者的个体,是特定的权力技术和权力形式在日常生活中运作而生成的“主体”:凭借控制和依赖而屈从他人,通过良心和自我认知而束缚于他自身的认同。[5]当我们读解“小史”这一人物形象时,必须同时注意到他作为被权力创造的主体所包含的双重意义。小史把阿兰带回值班室,让其蹲着,然后绕走廊一周,猛地踢开正对着阿兰的房门。通过摄影机跟着小史绕一周,我们能看到派出所值班室明显属于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7)参见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24页。小史处于监视的地位,蹲着的阿兰是被监视的对象。
在值班室里,小史问阿兰:“你真的结婚了,和谁?”阿兰却开始言说他的第一个爱人,他的同班同学,并得出体验:“我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小史却暴跳如雷(规训):“你是不是忘了这是哪儿了,你丫就是贱。”阿兰平静地回答:“我从小就这样。”在这第二次交锋中,小史所代表的是当时社会占据主流的话语对于同性恋这一群体基本的典型态度和认知。阿兰的回答则是创作者在普及同性恋作为社会学现象的正视态度,一种“祛魅”。在这一次交锋中,话语的主导权明显在阿兰一方,但是仍旧是规训(discipline)的力量打压着个体体验的“活着的”。在第一个爱人之前,阿兰对同班女生“公交车”也有好感,但正是这第一次的体验,使得阿兰正式认识到自己,那是“活着的”。
在第三次交锋中,个体体验便开始与社会规训“分庭抗礼”,体验喊出了自己的大胆宣言:“你错了。”阿兰讲述自己的第二段情感经历对象是其母亲改嫁后新爹的一位朋友,得出“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痛苦”的体验。这次,不仅仅是“活着”了,更是当露水打湿布鞋,关节开始疼痛的时候,伴随真实的感官体验袭来,阿兰感受到“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痛苦的”。这和异性恋者情感遭到背叛的体验别无二致,同性恋者并非妖魔,虽然性别取向不同,但他们的情感体验和异性恋者相差无几,都是活生生的人。小史同情地给了阿兰一口烟抽,但很快就将其夺走,然后批评其“肉麻”。阿兰便大胆地站起身来发出宣言:“你错了,不是我肉麻,是我写的东西肉麻。”区别这一概念的行为本身或许比区别这一概念更有意义。
面对阿兰站起身来的宣言,小史却只能重复:“你是不是忘了这是哪儿?”小史规训力量(权力)的来源不是源自于它本身,而是他作为警察的身份所赋予他的,具体就表现在“你是不是忘了这是哪儿”,不停地重复一个理由只能说明反驳的无力。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必须注意到小史这一形象所包含的双重意义。通过阿兰的言说,不断检验阿兰关于存在所知道的事实,同时,也是在唤起小史作为个体权利的内在体验。在规训与体验的交锋中,是阿兰的体验(不断检验)在唤起小史作为个体权利的内在体验。在第三次交锋之后,话语权就已经完全由阿兰所主导了,当阿兰主动言说“每个人都有一个主题,都是相同的又是不同的”,以及之后敞开心扉讲述自己的内心情结(希望警察把他带走),其为个体正名的引申意指(connotation)不言而喻。小史则要给他“治病”,在意识形态的领域,这便隐喻着“思想上的病”,而“治病”则不是压抑,而是创造。权力创造主体。
规训与体验的交锋,在第四次达到顶峰状态,在阿兰讲述过他遇到的那个穿风衣戴墨镜的高个子帅男人之后。阿兰的这次情感体验,终于走到了为爱而陷入完全的疯狂——迷狂,你对我做什么都可以。彻底的屈从是为了得到权力。(8)参见李银河:《虐恋亚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施虐和受虐说到底,还是人与人在沟通,是一种意识上的交流,不管是施虐还是受虐,如果对象由人换成动物,则得不到同样的快感,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权力关系的发生标志。
在这一次的交锋之中,规训(discipline)甚至无法发生。小史面对阿兰的言辞“我没病,我是同性恋,我爱他,你不能说我的爱情贱”,尽管不屑一顾,甚至还有戏谑、侮辱的行为举止,但规训(discipline)已然无法发生——小史打开了阿兰的手铐,并且让他离开。在阿兰离开后,反倒是阿兰透过窗户在看值班室里的小史。面对阿兰的表白,小史经过一番十分费力的折腾(最后的挣扎),然而对于阿兰“彻底的屈从”,小史最终还是失败了,他对阿兰有了生理反应。或许我们不该忘记阿兰的那句:“你为什么不问问你自己呢?”——非常具有启蒙意义的话语。小史的个体体验终于被唤醒,规训(discipline)的力量,在文本的想象层面上得到了挫败。
三、意义:寻找所指
电影《东宫西宫》的人物关系非常简单,场景也涉及不多,在时长相对较短的电影文本中,影片集中于小史与阿兰在派出所值班室的讲述与冲突。一个晚上的两个人之间的事,重要吗?重要到要导演拍一部电影来表现吗?对于张元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或许,对于“第六代”电影运动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电影《东宫西宫》因为在国内无法上映,所以实际上对于男同性恋者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改观而产生的影响力是非常微小的,包括第六代导演的其他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创作,但毕竟,对于电影文本而言,发现了“被遮蔽的存在”并深入展现个体的内心世界。在具有象征意义的两个个体身份之间开展的交锋之中,导演对于权力关系的探讨得到文本想象层面的宣泄。
不同于“第五代”电影运动所采取的文化寓言方式对于国家、民族、传统文化等形而上的抽象批判,“第六代”电影运动处于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之际,由西方进来的“洪水猛兽”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现实,使得他们不得不将镜头直面当下,去关注“被遮蔽的现实”,并且以一种“低语”的方式。电影是导演的表达工具,第六代导演在社会转变和艺术创新两大压力之下,所找到的能指非常复杂而混乱,“血液里流淌的胶片”使得他们的影片立足于现实却又和现实中的观众所“脱节”,毕业后的艺术追求在现实生活的焦虑中,显得遥远而不可得,怪力乱神的能指带来随时而发的所指。在电影文本中,导演与观众在理解上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学文化意义产生断裂,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第六代”电影在所指清晰之前,首先找到的是可见的能指。
四、结语
在电影《东宫西宫》一个晚上的时间所进行的颠覆与置换之下,隐藏着的是作为内在体验(L’expérience intérieure)的个体与作为规训(discipline)力量的个体进行的四次交锋。在同性恋越来越得到正视和理解的今天,我们不该忘记这部号称“中国第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对于消费时代的我们,或许也更能理解个体的内在体验,以体验为唯一的权威、唯一的价值,将自身定义为质疑本身。使电影文本和人们的现实生活产生互文性的影响,使人文价值关注于生存的“成为”(to be)本身,应该是我们不断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