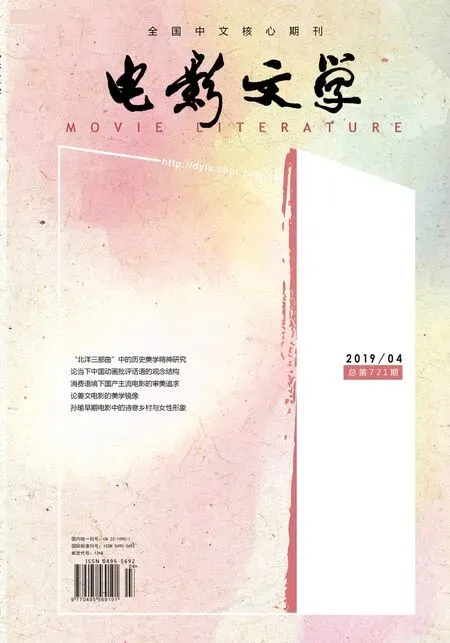韩国战争电影的叙事策略
田美燕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 外语教研室,吉林 长春 130022)
自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电影振兴运动开展以来,韩国本土电影的发展出现蓬勃之势。韩国民众高涨的民族凝聚力与爱国热情,被融入以电影为代表的各类韩国艺术形式之中,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韩国战争电影。与人们所熟知的另一张韩国电影的“名片”——悬疑犯罪电影一样,韩国战争电影也在日趋成熟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叙事策略。
一、战争:韩国电影的永恒主题
在电影审查制度取消,韩国电影获得了具有相当自由度的创作空间后,其类型化过程是全面推进的,但其中以战争为命题的电影,在韩国社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始终常拍常新,战争可被视为韩国电影的一个永恒主题。根据韩国对观影人次超过千万的电影的统计,在本土的十大高票房电影中,战争电影就占据三席,分别为金韩民执导的《鸣梁海战》(2014)、姜帝圭的《太极旗飘扬》(2004)和康佑硕的《实尾岛》(2003),而这三部电影也都以各自奖项证明了自己在业内受到的认可。
可以说,战争电影在韩国电影中,成为兼具强势市场地位与一定艺术成就的代名词。这是与一种已经深深嵌到韩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国族认知密不可分的。即一方面,朝鲜半岛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始终为民族内外战争所裹挟,这成为民众不可磨灭的记忆,也影响了民众的某些价值判断标准;另一方面,南北对峙的现状依然存在,朝鲜、韩国政权依然没有停止在包括媒体宣传、教育等方面上的互相攻讦与指责。“冷战在韩国社会作为具体的记忆和经历,通过文化再现的方式,长期以来层层积淀已过于厚重。而且,尽管苏联的解体与柏林墙的倒塌象征了冷战阵营的瓦解,却无法改变南北韩‘一触即发’的敌对性对峙态势。尤其是朝鲜为了维持其政治体制的存续,坚持着冷战思维与行动,甚至时不时强硬地以舞刀动杖相威胁。所以,冷战在韩国至今依然并不是虚空的口号,而是对历史、政治和社会颇有影响的真实的现实。”世界战争熔炉的锻造、朝韩的敌对与民族的割裂,使得韩国人不断用战争电影来保留历史的苦难经验,也通过纳入主流价值观表达和平愿景的方式,让其获得广大非韩国观众的认同。
二、韩国战争电影的基本叙事策略
在实践中,韩国战争电影形成了某些较为突出的叙事策略。
(一)以历史真实事件为叙事基础
依托真实战争,是战争电影的共有特色之一,而韩国战争电影也以此作为叙事策略,电影几乎无不取材于真实的、让广大韩国民众念念不忘的历史事件。在参照史实的基础上,又考虑到当代人的生活和审美倾向,既高度还原历史环境,又以艺术的处理创造出能为广大国内外观众接受的情节内容。一般来说,韩国战争电影可分为正面表现战争之作,以及与战争有关的间谍题材电影,如柳昇完的《柏林》(2013)、崔东勋的《暗杀》(2015)等。而前者又主要可分为三类,一类以中国明代时的李氏朝鲜为背景,主要有如《鸣梁海战》等。《鸣梁海战》对16世纪李舜臣指挥的著名的以少胜多,在鸣梁海峡重创日舰的历史事件进行了较好的演绎;一类以中国清代时的李氏朝鲜为背景,如黄东赫的,表现在中国于明清易代之际,朝鲜王国在对待满清是战是和之中举棋不定的《南汉山城》(2017),又如表现了“丙子胡乱”的《最终兵器:弓》(2011)等;第三类则是观众最为熟悉的、以朝鲜王国的统治结束以后的20世纪为背景的影片,这一类影片所牵涉的战争主要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乃至越南战争等。如李宰汉的《向着炮火》(2010)、吴篾的《芝瑟》(2013)和朴光铉的《欢迎来到东莫村》(2005)等,都属此类。除了《鸣梁海战》这样为数不多的以领袖为主人公外,绝大多数的电影都聚焦于小人物,以具有观众基础的历史背景和具有新意,能表达人物细致、真实情感的小人物共同制造影像魅力。
(二)主次矛盾的清晰设置
戏剧被认为“是一连串悬念和危机,或者是一系列正在迫近的和已经猛烈展开的冲突,在一系列前后有关联的、上升的、愈发展愈快的高潮中不断出现”。韩国战争电影普遍能够建立起主次矛盾,使得情节段落之间实现有因果、情感关系的摩擦碰撞,最终实现具有一定冲突密度的、跌宕起伏的效果,让观众的情感产生落差。其主要矛盾,一般都可以被清晰地把握为民族分裂之痛,韩国自身的腐坏,或是韩国在美国阴影下的挣扎。如在朴赞郁的《共同警备区》(2000)中,在游客连帽子飘落都无法跨界捡回的共同警备区,发生了朝鲜士兵被射杀的无头案,双方马上陷入高度紧张的对峙中。而次要矛盾则通常设置为历史窘境下人物的情感纠葛,如在《太极旗飘扬》中兄弟二人在精神、情感和身份上的错乱,又如在《共同警备区》中,韩国士兵李秀赫和朝鲜士兵吴敬必成为朋友,但是这份友情又注定在两国的矛盾中粉身碎骨。主要矛盾决定了次要矛盾,而牵动人心的次要矛盾又使得冰冷的史实得到了艺术提炼。
(三)修辞的频繁运用
韩国战争电影在叙事上,惯于使用比喻等各类修辞,以达到引人回味的表达效果。例如在张勋的《高地战》(2011)中,在最后阵地上出现了一场迷雾。通常情况下,迷雾代表了吞噬,是令人排斥的,而在电影中吞噬人生命最为无情的却是战争,迷雾的降临反而有了某种巧合、天意式的救赎意味,迷雾象征着在人类已经无法不为了利益而自相残杀,早已迷失了人性道路时,天降迷雾而让人不得不停止杀伐,在迷雾中传递歌声而非炮火,等待最后的停战协定。当迷雾散去时,银幕内外之人对生命的关切、对战争的控诉都已压倒了对L高地归属的关心。又如在表现朝鲜战争结束初期,韩国人的生活被美国阴影所笼罩的《收件人不详》(2001)中,一贯以“半抽象电影”著称的导演金基德也有意运用了修辞来表现自己对强权政治的不满。电影中的尚武是韩国母亲与美国黑人士兵生下的孩子,自幼被父亲抛弃,他本来就是美国强权干涉半岛政治下的产物。女孩恩洛在幼年时,一只眼睛被哥哥自己做的手枪打伤,而制作这把手枪的材料就是一块写有“美国”字样的木板,这块木板来自于美军的战斗机。长大以后的恩洛为了眼睛竟又和尚武的母亲一样委身于美国大兵,但还是遭到了欺骗与戏弄。美国对韩国、对朝韩兄弟/妹关系的伤害通过与手枪相关的事件被暗示出来,让观众看到了在战争结束之后留下的后遗症,包括社会畸形与变态、人性的卑劣等并未离去,人们依然无法获得平静美满的生活。类似的隐喻修辞在《收件人不详》中比比皆是,例如象征了人无法活得有自尊、自由的狗以及三个角色都失去的眼睛等,给观众留下了极大的解读空间。
三、日趋多元的韩国战争电影叙事
首先,韩国战争电影出现了从宏大叙事渐渐向着个体叙事转移的趋势。只要与早期韩国电影如《花郎道》《爱情山脉》和《浊流》等进行对比就不难发现,韩国战争电影体现了去政治化的特征,抛弃了那种有救亡和启蒙意识的宏大叙事话语,非脸谱化的小人物进入到银幕之中。例如在千成日的带有“无厘头”意味的《西部战线》(2015)中,主人公韩国下等兵南福的主观思想和意愿是被限制的,他的肉体也被约束于狭窄封闭的坦克空间中,这是与作为多年之后的旁观者的观众截然不同的。在认识了来自朝鲜的荣光后,两人一开始颇为敌对,荣光表示自己是来“解放”韩国人民的,而南福则愤怒地表示,我们怎么就需要你们来“解放”了?最终两人成为挚友,荣光被炸死,南福回到家,看到妻儿的笑容,“解放”的宏大话语再也与荣光和南福无关。在《高地战》中,官兵们在L高地严阵以待,继续着手足相煎,只知道自己要为最后的12小时而战,却不知道板门店谈判究竟推进到了哪一步,达成了怎样的协定,实际上也不知道这最后12小时的战斗是不是还有意义。电影有意以慢镜头表现停战协议上的麦克阿瑟、彭德怀与金日成的签名,以暗示注定“万骨枯”的小人物与他们之间的天渊关系。
李翰的《想念哥哥》(2016)中更是将这种属于个体的悲哀、迷惘或蒙昧表现得淋漓尽致。电影中人们原本安宁的生活因为如火如荼的战争的到来而改变,村民们并不了解政治,而只知道村里的年轻人因为上战场而牺牲,就将怒火发泄到了村里与人民军有些关系的东九兄妹的父亲身上。无辜的父亲因此而死亡,兄妹俩只好相依为命,如果不是少尉韩尚烈的照顾,他们很难拥有快乐的童年。这种仇恨的移植无疑是荒谬的,让观众不得不感慨村民的无知和无理,但这又却是在战争年代有可能发生的无数悲剧之一。一个个见识有限、对利益的考量都有着鲜明底层普通人特征的人物,主人公既在战争中受苦,也不乏歌唱、插科打诨乃至骑牛追坦克等让人啼笑皆非的经历,韩国战争电影的叙事从英雄回归凡人,从严肃的政治生活回归到充满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
其次,韩国战争电影出现了观念叙事与“零度叙事”的并存。所谓观念叙事,即电影的叙事在某种预设的观念下进行,电影人成为类似传声筒式的角色。而“零度叙事”则又被称为“白色叙事”,指叙事不受固有观念的引导和支配。金基玉曾经指出,韩国战争电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有着战争宣传机器的身份,这一身份在冷战期间,以及冷战结束之后都得到了凸显。这是与时至今日三八线两端的矛盾都没有被彻底解决,甚至也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缓和分不开的。因此,韩国战争电影不可避免地承载了韩国方面进行一种潜移默化式的自我宣传的话语。而也必须承认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战争电影也出现了对朝鲜一方较为客观的展现和“代言”,电影中的矛头主要对准的也是残酷无情的战争本身,而非具体的某一政权。例如在《高地战》中,朝鲜大尉放走了被俘的韩国士兵,因为在他看来,战争即将结束,而对方和自己一样都是同胞,应该回家休养生息,准备共同建设新的国家。然而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最终两军血染高地,大尉在宣读停战协议的广播中睁着眼睛死去。临死前,姜恩彪曾问大尉战争的意义是什么,得到的是“时间太久了,我已经忘记了”的回答。电影并不预设黑白善恶,以“忘记”表达了战争意义的虚无。
又如在《太极旗飘扬》中,老家在朝鲜的韩国士兵林泰修失去了自己的家人,还被身边的战友骂为走狗,让他愤怒不已地质问,“以前打日本是为了救国,现在是为了什么?”。处于尴尬位置的林泰修同样在质疑战争的意义,他参加战争的目的就是要让弟弟回归和平的生活环境。电影人更像是戴着现代文明的眼镜回到战争现场,窥视那个血肉横飞的世界,回到人存在本身,而不是钻入某种政宣观念的箩筐中。呼唤和平和正常人性,成为唯一统摄电影的既定观念。可以说,韩国电影人试图用一种“非零度”的方式来实现“零度叙事”。
战争电影对于韩国人而言,有着唤起民族记忆、表达美好憧憬、激发民族精神力量的意义。韩国战争电影通过确立与改进叙事策略,使自身逐渐具有品牌力量,在国际电影的竞争,在国家的文化建构上,扮演着越来越令人瞩目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