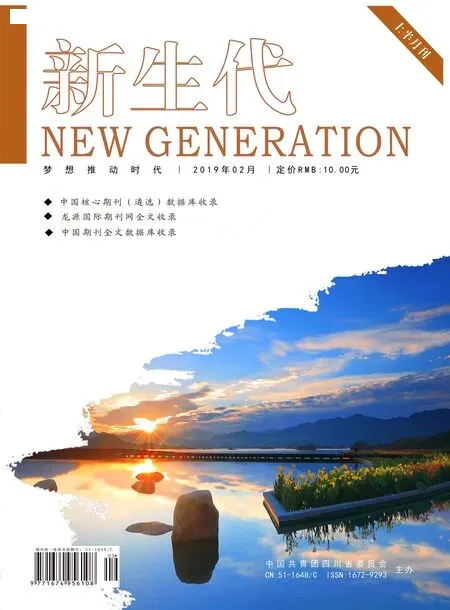阿来《尘埃落定》中几个文化意象的翻译处理方式
黄予 西南民族大学 陆保君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1
《尘埃落定》是作家阿来的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其英文版系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与夫人林丽君翻译。本文旨在探讨和分析译者的几个中国文化意象翻译处理方式,同时提出一些看法或认识。
1.“辖日”被译为Shari,属于音译的方式。该词在藏语中是“骄傲”的意思,代表一种种姓制度,“把人分出高下”;而这个词由藏语翻译成汉语其实是“骨头”的意思,译者没有直接翻译成“骨头”,正好说明“骨头”在汉语中偏于中性,没有太多的感情色彩,而音译为Shari显然也让读者一头雾水,不能直接从这种译法中得知其深刻的文化内涵,而只能通过注释或者具体的文本语境加以理解。不过音译的方式显然比直接译为“骨头”要好得多。
2.“土司”一词的译法是“Chieftain”,“女土司”是“Female Chieftain”,“土司们”则为“The Chieftains”。“土司”一词在汉语中是一个专有名词,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代表一个官职,而“chieftain”是指酋长或首领,代表有特殊地位的人。译者这样处理的原因是考虑到了外国读者的接受度,同时起到一个吸引更多读者的作用。而且,也减少了注释的环节,降低了文化异质性造成的理解难度,同时有利于降低文化误读的可能性,是一种积极为之且有建设性的翻译方式。
3.“有颜色的人”译为“Colored People”。这种译法来源于译者对中国政治的认知,在中国文化语境中,“颜色”代表不同的政党,或者说指在政治上有所倾向的人,如:红色代表共产党,译者译为“The Red Chinese”;“白色”代表国民党,译者译为“The White Chinese”。实际上这种译法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反而更容易产生文化误读,他们会先入为主地想到“有色人种”(race)的概念。根据语境和语义,译者没有译为“People Who Has the Political Orientation”,一是因为这种译法相对较长,字数较多;二是因为这种译法过于抽象,不好理解。原文关于“颜色”一词的句子有如“颜色在各人心中”,或许译为“Colors in the Hearts”更为合适。
4.《尘埃落定》作为书名被译为“Red Poppies”,作为章节标题则译为“The Dust Settles”。前者属于直接更换书名,取了Red Poppies这种艳丽妖娆,充满神秘异域风情的意象,目的还是为了吸引读者,为了满足外国读者猎奇的心理。后者则遵循了直译原则,缺点是较为抽象,不好理解。其实,纵览全书可知,其中大智若愚的“傻子”出现了263次,“傻瓜”出现了61次,“鸦片”出现了54次,“罂粟”出现了88次。单从文本中这几个意象出现的概率而言,“傻子”出现的次数最多,再者,“罂粟”出现的概率较低,并且“罂粟”在文本中仅仅起到了“催化剂”——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而“傻子”一词不仅出现次数最多,“傻子”也是文中的主角,从头到尾都是以他的视角来进行创作的。如此,考虑到既“实化”书名,又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度,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可能把书名译为“傻子(The Idiot)”较为合适。译者之所以未能如此翻译的原因可能是“傻子”这一经典形象在美国文化中已经出现过,如:阿甘这一傻子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Red Poppies这一译法可能是作者多方面考虑的结果,一方面满足了西方世界对于西藏这一神秘文化圈的审美心理,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借这种文化异质性来吸引更多读者的考量。然而一昧的“讨好读者”的翻译方法终不能持久,读者早晚会产生所谓的“审美疲劳”,最终对这种“谄媚读者”,倾向于销售量的做法感到厌恶,适得其反。市场需要导向,读者也是需要引导的,所以比较好的做法是:力求忠实于原文,试图引导读者的阅读品味,同时考虑一定的市场导向。忠实原文和市场导向并非二元对立,当可兼而顾之,但二者在重要程度方面具有先后顺序之别,即忠实原文应是最主要的,市场导向次之。忠实原文未必就会产生不好的市场,消极的市场导向反而会消解读者的阅读品味。
译者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必然会考虑到小说主题的问题,对小说主题的深入认识,有利于在翻译过程中对特殊文化意象进行准确而有效的处理。对于小说主题方面,原作作者阿来认为“《尘埃落定》不只体现了我们藏族人的爱与恨,生与死的观念。爱与恨、生与死的观念是全世界各民族所共同拥有的,并不是哪个民族的专利。当然,每个民族在观念上有所区别,但绝非冰炭不容,而是有相当的共通性”。诚然,《尘埃落定》中反映出的困境并不仅限于世界上某一个民族,而是人类共同的困境。这可能给将来的译者提供了主题方面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