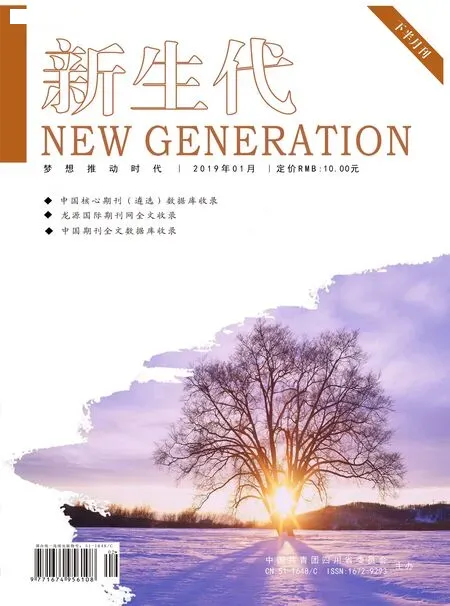浅析明末清初儒学的公私观
宁静 西安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西安 710021
明末至清末作为公私观发展的重要时期,其研究热度久居不下。一直来,研究者认为明末至清末公私观的意义在于"私"的晒起。不可否定明末“私”观念的幡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亡国、亡天下的双重背景之下,不管是上层阶级,还是普通民众,对“私”都有了新的认识和需求
许多学派的思想家,在建构他们的理论体系时,都对这个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明末清初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学派也不例外,它们在大体相同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各具理论特色的公私观。本文讨论儒法公私观的几个问题,希望从公私观这个侧面评说儒法两派学说,并通过分析历史留给我们的这一宗思想材料,加深我们对公私关系的理解。
一、明末清初公私观主要观点阐述
儒学思想总是在“困境一出路”这一驱动力下曲折发展,明末至清末,中国的思想家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是宋明理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派别繁多,积弊己久,明末思想家正是在试图解决宋明理学流弊的过程中,开启了公私观的新篇章。稱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论》的序文中特别指出晚明的数十年是宋明道学转向清代朴学的枢纽。世人但说清代博学考古的风气是明儒空腹高也的反动,而不知晚明学者己经为清儒做了些准备工作,而向新时代逐步推移。余英时认为明清思想变迁有其“内在理路”,萧塞父在80年代发表的《略论晚明学风的变异》中认为,晚明阳明也学的急剧分化,显示出儒口学风的变异及其再生的活力。另一当面,满清入主中原,遂使堂堂天朝上国,竟沦亡于化外索據,而兆亿神明华育,亦不免刹发易服之辱。对于黄宗義、顾炎武、王夫之等一代大儒而言,眼前的横逆,便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异姓改号”的“亡国”,而且还是“仁义充塞”、“伤礼拜教”的“亡天下”。如果说,“亡国”只关系到一家一姓的兴亡,除皇室与高官等少数“肉食者”之外,绝大部分国人并不必对此负责,那么,天下关系到整个华夏礼乐教化的绝续存亡,如何防范于未萌之先,及搔救于既亡之后,便成了全体国人无可规避的义务和责任。
(一)以“私”的立场论“私”
李贺是明末率先为“私”正名的思想家,他从个人的立场出发,从“心”这一概念对公私观进行颠覆。他认为:“私者,人之心也”,李贺颠覆性的从理学根基“心”入手,毫无顾忌地把“私”规定为“心”的本质,为“私”寻找本体论上的依据,由于“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以把“私”纳入到人“心”的范畴,就为“私”获得了正当性。在阳明心学中,心被认为是至善至公,绝不掺杂任何私意,被认为是“无善无恶心之体”,心的内容就是天理。朱子认为“心统性情”,性是至善至公的,情则有善与不善,性是心的本质规定,而由于性即理,心的内容即是天理,心同样是至善至公的。
陈确从个体角度明确对“私”进行肯定,在《私说》,开篇明义地说:“有私所以为君子。惟君子而后能有私,彼小人者恶能有私乎哉!”初看此命题,无疑有些极端,发现其与儒家传统的君子观不同,君子小人之分一直是儒家的经典论题,不管在哪朝那代,君子都是不与民争利,大公无私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孔子看来,君子是不与民争利,没有私心的。在宋明理学那里,有德行的才能成为君子,志在义便是公,志在利便是私,有意为公亦是私。但陈确对私进行了解释,便会发现其所要表达的思想并未脱离儒家的轨迹。在陈确看来,所谓的“私”是偏私、偏爱的意识 。
(二)以“公”的立场论“私”
“公”之实然义原指君国,“私”之实然义指个人,针对“公”与“私”的这层含义,“公利”这一概念指的就是君国利益,而“私利”指的是个体利益。黄宗羲认为“公”具有普遍意义,代表着“天”或“天下”,“公利”指的应该是万民之利。黄宗羲认为,在君国产生之前的原初状态中,人各自自私自利,人人趋利避害、好逸恶劳,因此没有人愿意来承担社会责任。后来,出现了君主,君主的出现改变了社会的原初状态,那么君主承担的就是社会责任,其职责在于“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君主需要牺牲自己的私利来“兴天下之公利,除天下之公害”。显然,君主是区别于个体的,其职责就应该和普通个体区别开来,君主的职责更多在于兴公利而不在于谋一己之私利。
和黄宗羲比较起来,顾炎武为“私”的辩护更为有力,其“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被后世广为引用,到近现代常也常作为顾炎武肯定“私”的证据,此话原出自于《日知录》。不过,和黄宗羲相同的是,顾炎一武对“私”进行肯定和辩护,其目的是为了对当前制度进行改革。顾炎武认为“私”首先是人的自然属性,“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既然“私”是人的自然属性,“私”在历史的实践中也己经证明其正当性,那么就不应该用外在的手段对私进行禁止。四、自由灵动的教育方式构成文化自信的灿烂源头
二、儒家学派明末清初公私观的特点
(一)公私的道义性
与日本的公私概念相比较,这一点会显得更清楚。日本的公私“是显露与隐藏,公开与私下,相对于公事、官方身份的私事、私人之意。进入近代以后,乃是与国家、社会、全体相对的个人、个体,不涉及任何道义性。虽然有公私纠葛和矛盾,但这是人情问题,绝非善、恶、正、邪之对立。”相对于国家来讲,某集团的事情就是这个集团的私事;但对于集团内部来讲,这件事情就是公事。公私之间是可以转化的,不存在道义的普遍性、恒定性。儒家的公私具有善与恶、正与不正的普遍性,无论何时何地,善行都是受到褒奖、赞扬的行为;反之,恶行是永远遭到唾弃的,如同岳飞的忠和秦桧的奸。
(二)崇公抑私
儒家公私的道义性决定了崇公抑私的格局,因为弃恶扬善是人类共同的道德准则。只是,儒家的公私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含义。如前所述,儒家的“公”,在春秋时期多指君主、国事,战国时期的荀子把它上升为“道”,指一般道德规范。儒家的“私”,在春秋时期指大夫及其家事,并不涉及普通百姓;战国时期的私利涉及了一般百姓,但也仅涉及生命和财产层面的,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社会权利的含义。如《论语·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厩起火,孔子首先关心的是有没有人受伤,这说明孔子对百姓生命的重视。孟子主张行仁政,“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
(三)公私对立
在儒家思想中,公私一直是一对对立的范畴,这从荀子时代的“以公义灭私欲”(《荀子·修身》)就开始了。从内容看,公私对立在政治(包括伦理道德)、经济等方面都有所表现。因此,西汉韩婴说:“公道达而私门塞,公义立而私事息。”(《韩诗外传》卷六)公道盛行,那种为私人利益找门路找关系的事就杜绝了。公义昌明,那种只顾私人利益的事就少了。这是告诉人们,要守原则,存公道之心,行公平、公正之事。后汉荀悦说得更详细,他对君主提出这样的要求:“人主有公赋无私求,有公用无私费,有公役无私使,有公赐无私惠,有公怒无私怨。”
三、儒家学派明末清初公私观的基本价值取向
正是从“天下为公”的社会道德理想出发,儒家在公私关系问题上反对自私自利,强调大公无私、立公去私,提倡崇公抑私、公而忘私。在儒家的价值理念中,“大公无私”不但是一种理想境界和道德要求,也是天地万物所遵循的根本法则 。《论语》中记载孔子的话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这里指出了“天”或自然在“大公”方面的天然性和普遍性。《礼记·孔子闲居》载:“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在孔子看来,上天覆盖一切,大地承载一切,日月普照一切,天道本身就是最为公正无私的,人类社会是天道的一部分,人类之大公就包含于天道之内,因此,人类应当遵奉和效法天之大公,并以此要求自己,也以此劝勉天下。周敦颐说:“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周子通书·公》)在周敦颐看来,天地自然具有“至公”的品性,万物皆因天道各得其生,各得其成;而人作为天地间的一分子,其德性品行也是在对天地的仰慕与效法中成就的,因此,圣人之道自然应当是“至公”的。“至公”既是依据天地的品性对圣人品性德行做出的判断,也是给普通社会成员提出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因为任何人都应当遵循和奉行天地自然之道。可以说,大公无私、崇公抑私是儒家公私观的核心所在,也是儒家公私观的最高道德要求和基本价值取向。
明末李蛰、陈确等人从个体的立场上进行了肯定,将个体对私的追求视为天理之必然。到了清末,清末启蒙思想家肯定个人拥有自主之权,国权是民权的合集 。但明末至清末,思想家们仍然难以处理私与公、私与私的关系。由于我国传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公与私的相对性,公与私的界限暖昧不清,个人私的范围也难以划分边界。李蛰等人在对私进行肯定时,对“私”持有一种乐观精神,正如陈确所言“惟君子而能后有私”,将对公与私的把握寄希望于主体的道德品质。清末同样如此,以天赋人权来解释“私权”的来源,随后又将《中庸》的率性而不违众和絮矩之道视作个体“私”的准则。将“私”的边界和标准寄托于主体的道德品质,就需要主体通过修身来提高道德,如果将道德标准回归到天理上,那么“私”的标准是天理,“私”就是公。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谐社会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一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公私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儒法二家的公私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