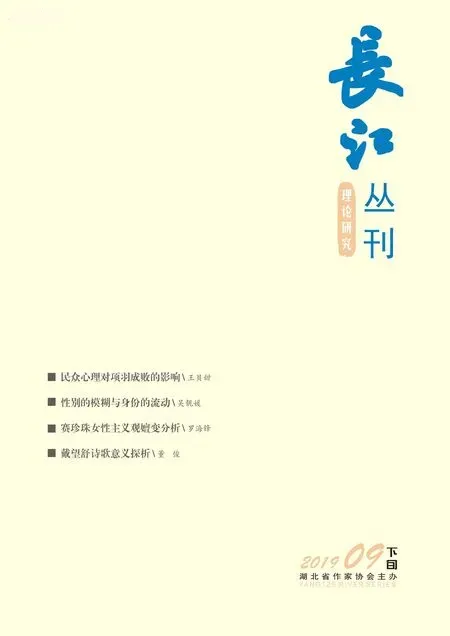赛珍珠女性主义观嬗变分析
■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赛珍珠作为一名长期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出生三个月就被父母带到了中国,她从小接受了中美两种文化的熏,成年后就读于美国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获得文学学士,1917年与约翰·洛辛·巴克结婚,婚后与丈夫在华北农村生活了五年。1934年,定居美国,因为写中国题材的小说而闻名于世,先后获得了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其小说真实再现中国妇女的性格和社会处境,打破了西方关于中国的固有形象,瑞典学院常务秘书佩尔·哈尔斯曾经对其作品《大地》做出评价,“一个最严肃、最忧郁的问题是中国妇女的地位问题”。
《大地》、《论男女》和《群芳亭》这三部作品蕴含了作者对女性地位的关注,反映了作者不同时期女性主义思想的嬗变。本文拟结合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以及赛珍珠不同时期的作品及论述,以早期作品《大地》的阿兰、1941年作品《论男女》中的论述和1946年《群芳亭》中的吴太太为例,通过女性自我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历史客观地再现赛珍珠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嬗变,即从“无我教女性”到女性在自我实现与为他人尽责之间追求和谐的转变。
一、“无我教”女性——阿兰
赛珍珠女权意识源于她早年的经历,父亲赛兆祥重男轻女,脑袋里充满了男性从属于女性的圣保罗教义,因此其童年充满了对父亲性别歧视的不满,在“希望之门”的志愿工作使其女性主义意识得以萌芽生长,伦梅女院也是美国社会对赛珍珠的精神洗礼的地方,同时赛珍珠的女性主义思想在随后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为赛珍珠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地》是赛珍珠早期的一部作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阿兰是赛珍珠早期塑造的一个女性角色,是全书的道德中心。正如彼得·康认为的那样,“她毫无怨言地履行着好妻子、儿媳和母亲的职责,把个人欲望深藏,无条件地服从丈夫,尽最大努力扮演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但是她勇敢、坚韧、顽强和勤奋的性格特征在丈夫王龙在危急时刻软弱性格的衬托下,更加突出,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
阿兰从结婚之日起到生命结束那一刻,一生都像一个既忠诚又沉默寡言的女仆。在结婚当日,离开黄家时,阿兰尽管拿不动箱子,但仍然坚持把箱子扛起来,在王龙发出指令 “我来拿箱子,你拿着篮子。”时,阿兰便默默地把篮子提上,毫无主见,他们的第一次相会便决定了他们以后夫妻相处的基本模式,即既嫁从夫,即使丈夫的要求再不合理,她仍然毫无怨言地顺从接受。
他们婚后不久,发生自然灾害(旱灾),一家人坐火车逃荒到南方,为了生存下去,穷人不得不卖掉女儿,阿兰发誓宁愿女儿饿死也不让她到大户人家去当丫头。但是当她知道要实现丈夫回家的愿望,除了卖女儿别无选择时,她违背自己的初衷,把痛苦深埋心底,仍然违心地决定要卖掉了自己的女儿。
阿兰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女性,她认为自己为丈夫尽到了做妻子的职责,因为她生了三个儿子使王家的香火得以传承,同时勤俭持家、无私奉献把全家人聚合在一起。从对家庭贡献的角度来看,阿兰在家中应该与王龙地位平等,财产平等拥有。事实上,她不仅与丈夫王龙同甘共苦一同下地干活,而且是她首先发现了王家的发家之本即地主藏在墙里面的珠宝,但是阿兰认为财产都自然归丈夫拥有,自己无权支配,即使自己的两颗珍珠也被王龙拿去送给小妾,当阿兰听说治病需要五百银钱时,“立刻从昏睡中醒来,她虚弱地说:‘不,我的命不值那么多钱。那能买好大一块地啊!’”难怪姚锡佩认为:“《大地》第一部中的女子,无不带着奴性,没有独立的人格”。
阿兰一生几乎默默无闻,然而她每次发声都拯家庭于水火,使全家人转危为安。在全家人处于饥饿边缘,王龙不忍动手杀牛,全家人束手无策,是阿兰拿刀杀牛,为全家提供了食物,度过难关;当王龙叔叔趁火打劫,威逼王龙卖地时,王龙既恼怒又束手无策,这时阿兰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对方:
“我们肯定不会卖地的,”她说,“不然我们从南方回来时,我们就没有养活我们的东西了。”
阿兰的坚定和镇静熄灭了对方买地的阴谋,王龙的土地才得以保全,就这样阿兰把家里仅剩的家具卖掉之后,全家人才有机会坐火车逃到南方,继续生存下去。
阿兰尽管在丈夫面前百依百顺,毫无自我,但在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面前却毫不妥协,尽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当阿兰发现曾经伤害过他的杜鹃与小妾荷花一起来到她家时,阿兰只烧够了除杜鹃和荷花两人之外的热水,在杜鹃去取热水时锅里已空空如也,在王龙质问她时,她以“在这个家里,我至少不是丫头的丫头。”回应了王龙。
阿兰体现了赛珍珠女士早期朦胧的女性主义意识,在她身上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无我教形象,“在中国,一个真正的妇人,不仅要爱着并忠实于她的丈夫,而且要绝对无我地为她丈夫活着。事实上,这种‘无我教’就是中国妇女尤其是淑女或贤妻之道。”同时赛珍珠又赋予她勤劳、勇敢、坚韧、隐忍的可贵品质,又体现了女性意识的微弱觉醒。
然而阿兰的形象与同时代美国的自由女性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美国人吉尔曼早就要求美国女性要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同时美国社会也涌现了冲出家庭,实现自我的新女性,中国也出现了冲破封建礼教走出家庭的新女性。因此当时中美两国的知识分子对赛珍珠的看法各不相同: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赛珍珠只是一名传教士,对中国的认识浮光掠影,并质疑其书写中国的真实性,而美国作家则称之为“中国通勃克夫人”,以与其为伍为耻,至今赛珍珠仍游离于美国文学之外。
二、女性走出家庭,实现自我的探索——“火药型”妇女
上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经济一片萧条,找不到工作的人比比皆是,女性对男性依赖减少,其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到40年代,美国经济复苏,原有的社会分工(男主外,女主内)也随之回归,美国男性极力主张女性回归家庭,试图维护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另一方面,部分女性认为女性应该依靠丈夫生活,兴起了一场“回家去”运动,在此背景下《论男女》应运而生,在这部作品中赛珍珠批判了传统社会的性别分工,呼吁女性冲破家庭的藩篱,走向社会,追求自我,实现自我的价值。
《论男女》由九篇论文组成,从多方面分析当时美国妇女面临的问题,在这部作品中,她把美国妇女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天才女性:意志坚定,不满空虚生活,不愿浪费光阴,不能忍受任何不足。第二类是家庭妇女:这类妇女囿于家庭,相夫教子,孩子成人后又开始照顾下一代,安于家庭生活,以家庭为主。第三类是“火药型”妇女。她们无需外出挣钱,也无特殊才能;而又精力旺盛,不知如何运用,她们常常感觉空虚、焦躁不安、易受刺激、处于亚健康状态,私下有些愤世嫉俗,怀着儿时的梦想,之所以被称为“火药型”妇女,是因为她们精力旺盛,储集在体内,却不能以恰当的方式爆发。
在《论男女》中把美国女性定义为“火药型”妇女,她们因自我的缺乏而躁动不安、得不到满足;与《大地》中的女主人公阿兰相比,“火药型”妇女是赛珍珠在这一时期女性主义思想的真实写照,即她们在家庭中无法得到满足,需要与男性一样进入社会,以实现自我的价值。
三、自我实现与家庭责任完美和谐——吴太太
1946年赛珍珠发表小说《群芳亭》,再次探讨家庭与女性自我的关系,女主人公吴太太融中国传统美德和美国自由主义思想于一体,是赛珍珠在融合了中美两种不同的文化后所形成的理想女性形象。
《群芳亭》中的吴太太出身名门,16岁嫁到了吴家,二十多年来帮丈夫打理吴家,尽量让丈夫高兴,以实现吴老太爷的教诲“把心思用到让我儿子高兴上面”,无我的为丈夫活着,吴太太在40岁生日当天宣布结束与丈夫的肉体关系,为自己的丈夫吴老爷纳妾,并从他的卧室搬出来,搬入吴老太爷生前的书屋,准备享受一份精神上的轻松与独立,开启了寻找自我的精神之旅。女性主义作家伍尔夫认为:“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的话,她就必须有钱和自己的一间屋子”,与伍尔夫相似,吴太太也渴望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在那里她的思想可以自由遨游而不会受到任何干扰,独立的空间把吴太太从社会对女性的束缚中短暂解放出来。这标志着吴太太女性意识的觉醒,从四十岁之前的无我教女性向追求自我的独立新女性的转变。
在这部小说中,吴太太没有放弃自己对家庭的传统责任。她的女性意识在 “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下得以生根发芽,领悟了心灵解放和自由的真谛,从此不再被动地为家庭负责,而是重新管起这个家,照料、培养安德鲁生前收留的孤女,用博爱之心关心别人,把独立和自主的精神送达他人。
因此赛珍珠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就是吴太太,她在个人价值和家庭责任之间寻求平衡,追求和谐。张子清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吴夫人 “虽然享受富裕生活,但不留恋物质财富,时刻不忘精神生活中的求索,勇于破除陈规旧俗。赛珍珠从各方面把吴夫人塑造称一个自觉自为的非同寻常的女强人的形象”“吴夫人的所作所为无不烛照了作者的精英心态和美丽理想”。
四、结语
赛珍珠精通中美两种文化,经受了中美两种文化的洗礼,赞赏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尤其是她们对家庭的无私贡献。她在《大地》、《论男女》和《群芳亭》中所表现的女性主义思想的转变即从早期的“无我教”女性到“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既显示了她对中国文化中的家庭哲学的认识,也反映了她对女性如何处理自我与家庭义务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思索,认为女性自由不能通过脱离家庭获得,而是在追求自我与家庭责任的平衡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