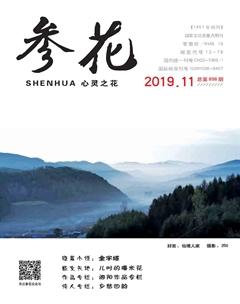苇叶荷花香溢远
陈泉宇
成子湖,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洪泽湖北岸;成子湖,像一位慈祥的母亲,抚育着世代沿湖百姓。出生于此的我,血液里流淌着深深的成子湖情结,个性中张扬着浓浓的成子湖情怀。
忘不了成子湖悠悠碧水,忘不了成子湖万亩荷花。忘不了成子湖芦苇清香。
荷花、荷叶、莲藕、莲蓬,对于生长在湖边的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小时候无论沟渠还是河塘,春夏之际抬眼望去,总有那么一些荷叶,或三三两两,或溢满水面。湖边更是一望无垠的荷塘花海。要么摘一片荷叶,顶在头上防雨防晒;要么摘几朵荷花,放在房间香飘四壁;要么偷几个莲蓬,小伙伴私下分吃。最令人伤感的是寒冬腊月,冰冷的水面零星伫立着一些残荷,在凄厉的北风呼啸之下,显得那么无助、凄凉。陌生的是随着求学、工作的远离,看到一望无际的荷塘已经是一种奢望,只在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诗句中念叨家乡的万亩野荷塘。
夏日午后,相约回到家乡的十几位老同学,簇拥着老师,驱车沿成子湖大堤看万亩荷花,师生们逗留在万亩荷塘边上的芦苇荡不忍离去。抬眼望去,一片片芦苇在微风中轻轻颤动,苇叶随风摇曳沙沙作响,给静谧的湖畔散发跳跃的思绪。
芦苇在我的记忆里很深。春来一望无垠的芦苇像逶迤的青龙沿岸而伏,一片翠绿;端午前后,勤劳的母亲们摘下苇叶,用糯米便可包出黏糊糊的粽子来;秋日灰白的苇花迎风摇摆,手背拂过,柔柔的苇花夹带着一缕暗香沁人心脾;冬天的芦苇荡一片肃杀,滞留的积雪在苇叶上苟延残喘,不知芦根正在为下一季的蓬勃积蓄力量。最快乐的莫过于小伙伴们,此刻可以轻而易举地捉到野鸭和大雁,拾到成窝的野鸭蛋。
印象中的芦苇对我们农家生活帮助很大,盖房子的时候用干芦苇扎成五六米长的柴籽,排列在房梁上,上面再用几十公分长、粗点的芦苇沾泥一层层码积上面,完全替代瓦。这样的房子虽然不富丽堂皇,却冬暖夏凉。有手艺的人会用芦苇编成席子、节子(农村用来盛粮食的)卖掉补贴家用。最难忘怀的是老人们用苇花做成的毛窝子,比棉鞋还暖和,一直陪伴我到高中毕业。
顺着芦苇荡向里,望不到边的水面上,无际的荷叶在微风吹拂下轻轻摆动。近处小小的蜻蜓迎风站在荷叶边,青蛙跃起溅出的水珠滴落在荷叶上晶莹剔透。已过荷花盛开季节,还有一些荷花含苞待放,白的,红的相映成趣,在青荷的襯托下更显婀娜多姿。虽然有的荷叶开始枯萎,但依然影响不了师生们寻求童趣的兴致。
原来的万亩野荷塘早已因围湖养蟹的开发不复存在,我们看到的是近年来政府高效农业政策驱动下的人工栽植。承包荷塘的是一个稳重小伙,已经在这里奋斗几年。他说莲藕全身是宝,青荷经过加工可以泡水喝,既减肥又去火;荷花制干可做枕芯,有明目的功效;藕不仅做菜还可以做成藕粉畅销海内外;莲子更是不可多得的补气食材。
古往今来,咏莲的诗文比比皆是,文人墨客常常自喻高洁。我无意附庸,更多的在想,作为扶贫示范区的家乡,随着交通的便捷,靠水吃水的优势日益凸显。高效生态农业与旅游观光农业既让乡亲们更加富裕,也给久居都市的人们提供休憩的港湾。闲来携侣呼友,泛舟荷海,嗅着沁人的清香,吃着鲜嫩的莲子,在水天相连的意境里,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真是快意人生。
碧绿的苇叶依然沙沙作响,荷塘的清香依旧沁人心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