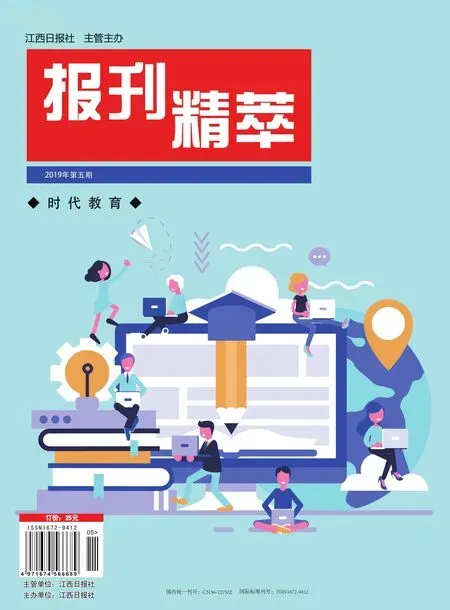关键期假说”对我国七年级英语教学的启发
李周玲
天津实验中学滨海学校 天津 滨海 300451
一、引言
我们可以经常见到一些在国外长大的孩子回国后,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你很难听出他有什么口音;而那些成年以后再出国的留学生说英语,语音里却经常夹杂着自己的特色口音。再比如说香港、澳门等地方的孩子从小就接触英语和粤语两种语言,他们在二语的发音、流利度、语言思维方面比内陆的孩子要好很多。这些现象引发了一个思考:学习语言的关键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对语言的习得又有什么影响?
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的基本概念
关键期假说源于生物学,最初是从动物实验中提出来的,它指的是有机个体对某些外部刺激的在某个时期最为敏感,我们称这个时期为相关外部刺激的关键期。而如果这种刺激早于或者迟于该时期,产生的效果会大大折扣。
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的先驱Penfield&Roberts 认为,人类的语言能力是与大脑的发育密切相关的,语言习得的最佳年龄应该是在4-12 岁之间。在此期间,人们可以在自然环境里,无须教授,自然轻松地掌握一门语言。而过了青春期,大脑左右半球因为生理发育会被赋予不同的功能,掌握一门语言的速度和程度会逐渐减退。
三、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与二语习得的相关性
一直以来都有学习要趁早的说法,我国古诗中就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种警惕性的诗句。那么,关键期假说是否在二语的习得中成立,学习二语是否要越早越好?而过了学习关键期以后是不是如何努力学都无济于事了呢?
Snow 和Hoefnagle-Hohle(1978:14-28)对三组母语是英语的人(儿童,青少年和成人)在自然环境下习得荷兰语的人进行了10 个月的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在荷兰居住三个月之后,成人和青少年的测试成绩明显好于儿童;在词汇和句法方面,青少年做的最好,成人次之,儿童最差;在语音方面没有很大的差别。
由此可见,关键期假说与二语习得的相关性既有正面的依据,也有反面的辩驳。有研究表明,儿童和成人的二语习得在本质上面有着差异性。根据关键期假说,青春期之前,自然语言的学习机制是发展的最高峰,这时候对外界的语言刺激是最为敏感的,儿童可以在自然而然的情况下,不须教授的情况下,无意识的习得某种语言,我们把这种学习称为隐形学习,这时候儿童对于语言更多地是一种语言能力的习得。青春期过后,自然语言的学习机制被逐渐关闭,二语的学习更多地是借助通用的认知模式和信息处理系统等其他机制进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显性学习来完成,更多地是一种语言表现的习得。
更多学者认为环境因素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至关重要,是决定语言发展关键点之一,也就是说儿童与成人语言方面的差异并不是语言习得机制本身造成的,而是语言机制的外部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说这种二语方面的关键期,与其说是早期教育的成果,还不如说是环境优势的产物。
四、关键期假说的研究成果对我国七年级英语教育的启示意义
中国的二语教育,更准确的说法是外语教学,它是属于课堂教学,与二语习得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二语习得更多的偏向于二语真实语言环境下某种语言的习得,比如移民学习当地语言;而外语学习则是在缺乏真实语言环境下,在教室教学中进行的语言学习。虽是如此,但是关键期的假说仍然给了七年级英语教学很多启示。
正如上面所说,我国的英语教育是属于缺乏真实外语环境的课堂教学,学生在学习二语时所启动的机制还是以通用的认知模式和信息处理系统为主,内陆的二语学习,不比香港、新加坡等有二外环境的地区或国家,因此母语的习得是与外语的学习密切相关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因为对于一个学习者来说,没有母语的支撑,就没有外语的学习。七年级英语教学处于小学英语和初中英语的过渡阶段,教材的内容也是小学与初中的知识衔接,绝大部分七年级的学生正好12 岁、13 岁,而这个年龄正好处于语言习得关键期的末端,此时大脑对语言学习的机能逐渐关闭。七年级的英语教学应该抓住语言习得关键期的最后阶段,多多关注学生的语音教学。学生已经在小学阶段完成了他们的母语习得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母语是有一定的基础保障的,此时学生适当地学习国际音标是不会和拼音混淆的。七年级教授一定的语音知识,更有助于学生掌握英语单词的发音和背单词的技能。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多让学生模仿课文磁带的语音语调进行单词和课文的朗读,同时还可以鼓励学生通过一些英语学习的APP,例如英语趣配音、盒子鱼等软件,给一些影视作品配音打分,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也训练了他们的语音语调。学生经过七年级一整年的训练,不断地形成了相应的英语“语言肌肉”,这对他们后续的中学英语学习乃至整个英语学习影响深远。
结束语:
在笔者看来,二语习得的关键期年龄只是二语习得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并非决定性的。而在我国,更应该认清二语和外语的区别,给予不同的教学处理,既不能超过青少年期才开始外语教学,也不能过早地学习外语而忽视了外语可能会对儿童母语学习和逻辑思维发展方面产生的负面作用。并且在七年级阶段,英语教学更多的是注重可理解性的输入和语音的练习,配合学生在关键期阶段的语言系统特点,让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在七年级英语教学上发挥积极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