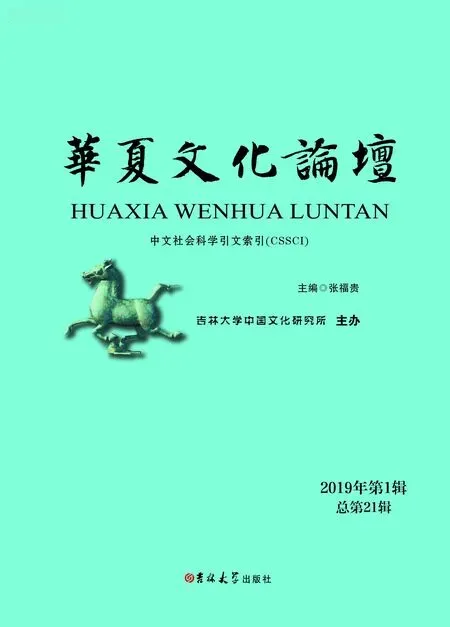《子君走后的日记》:《伤逝》的互文式书写
王桂妹 李昫男
【内容提要】《子君走后的日记》是李素刺于1931年刊载在《现代学生》杂志的一篇日记体小说,与鲁迅的作品《伤逝》形成互动式文本。小说以子君为第一人称视角,补充了涓生对子君记忆的断点与空白,既延续《伤逝》的小说内容,又与鲁迅的小说内涵构成反差,两篇小说独特的结构形式形成互动式文本的形态意义,同时又是鲁迅小说叙事主题的一种映射,其存在价值值得挖掘。
在鲁迅研究史上,《伤逝》作为鲁迅小说中唯一一篇描写五四青年男女爱情的作品,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钟爱。在传统的研究视野中,《伤逝》是被用来解读五四时期精神觉醒者所面临的社会困境和精神困境的一个重要视角。随着近些年来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一些研究者开始从另一个视角把“一体化”的觉醒者——“涓生和子君”分开来对待,或者说研究者带着对“男性视角”和“男权主义”的反思,把研究重点由“涓生”转向了“子君”,质疑涓生作为启蒙主体和故事讲述主体的可靠性,从“子君”这样一个“被启蒙者”和“被讲述者”的视角寻找故事的空白和断点,进而替子君“发声”。这种新的阐释视角既有新的发现,也带有一种“后来者”的同情和想象。自然,伟大的作品往往是无限敞开的文本,在不同时代读者的阐释和想象中不断增加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伤逝》中觉醒者的困境,尤其是最令人同情的子君何以会走向死亡?在启蒙者/被启蒙者、男性/女性、丈夫/妻子、传统/现代……等等这些看似简单而又微妙的关系中,如何看待那个时代的人生境遇?这些问题始终是研究者的兴趣所在。同样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发现了《子君走后的日记》这篇小说。《子君走后的日记》是1931年刊载在《现代学生》“读者园地”栏目的小说,作者是李素刺,山东省立高中的一名学生,作品写于1930年,小说题目下标着“二次中学征文第四名”的字样。《子君走后的日记》是鲁迅写作《伤逝》的五年后出现的互动性文本,这也是“子君”的同代人对于《伤逝》中觉醒者困境的一种回应,为后来研究者理解《伤逝》提供了一个切实的参照。
如果说写于1925年的《伤逝》是鲁迅对于“五四”以来思想启蒙的一次反思,那么写于1930年的《子君走后的日记》则是一位《伤逝》的读者对于“反思”的反馈。《伤逝》是1928年收录到《彷徨》中才与读者见面的,三年后刊载的《子君走后的日记》显然是在《伤逝》经过了最初社会发酵的过程后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小说,都是以“日记”体形式呈现的,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学的发展阶段,“日记体小说”作为“现代小说”的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也在此时愈加成熟,并涌现出大量的作品,庐隐的《蓝田的忏悔录》《曼丽》、石评梅的《林楠的日记》、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沈从文的《一个妇人的日记》《篁君日记》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小说。当现代的研究者们以时代精神为尺度去找寻文学演变的轨迹,首先找到的就是诸如以上具有鲜明的历史印记的名家作品,实际上,在文学发展的长河中,除了这些标志性的小说之外,存在更多的没有被人发掘,但也同样折射着时代精神风貌的创作,这些“不著名”的作品也许在艺术上缺少更纯熟的技巧,缺少更深刻的文学价值,但仍因其写作的内容和形式而映射着时代之光并拥有自身的历史价值。《子君走后的日记》正是这样沉默着的无名文本。
一、互动式文本结构的形态内涵
“一部小说讲述的事件是内容的组成部分,而它们被组织进情节之中的方式大概就是形式的组成部分”《伤逝》与《子君走后的日记》不仅在内容上形成了互动式文本,结构形式上也构成互动式书写。而作为作品的形式“不能仅被当作技巧的总和来研究,它不是纯粹激发美感的,甚至也不是纯粹语言学的;因为它投射了一个由母题、主题、人物和情节组成的‘世界'”。在《伤逝》的原有故事世界中,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悲剧实际不仅仅在于思想的差异,经济的窘迫使他们苦苦挣扎在柴米油盐中并互生怨恨,我们不禁假设,如果他们生活富足,子君不必忙于家务,是不是能够读书学习?是否能提升思想,成为时代的先行者?涓生说:“人必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生存困境恰恰不是单指人的经济困境或者精神困境,而是双向的,鲁迅在小说中指出的是当人们越来越热衷于只凭意志或精神在行动时,更应该看到实际的经济困境。相比于更多的启蒙者对于青年人“出走”的呼喊,鲁迅更想让年轻人看清楚社会形势,并指出忽略经济权的抗争只能酿成“回来”的悲剧。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提到“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事实上,鲁迅的创作始终关注着国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在鲁迅看来,‘现在中国人的生存'是‘第一义'的,这构成了“五四”时期鲁迅的一个基本观念,也是他的思考的中心。”子君与涓生走出家庭和道德的束缚自由结合,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经济问题,这是鲁迅,也是后来的鲁迅研究者对《伤逝》做出的明确阐释。李素刺的《子君走后的日记》所延续的是《伤逝》的故事,二者从形式到内容都构成互文,文本形式的互动如何实现是小说主题的外在体现。
日记体小说最惹人注目的形式就是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视角的意蕴,第一人称的叙事往往能够深入地表达叙述者的内心情感,并以对全知视角的摒弃来更加突出“个人”,《伤逝》中涓生化作“我”这个能够进入读者内心的称号渐渐缝合了读者与叙述者的距离,使得读者能身临其境地感觉到涓生的情感流动,但是同时人们也遗憾,通过“涓生的手记”也只能透过涓生的单方面述说来拼凑子君的形象。《子君走后的日记》则恰恰采用了以“子君”为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全文都没有出现涓生,而是仅仅通过子君的回忆、想象、推测来完成涓生可能的结局。值得注意的是,在《子君走后的日记》中,子君回忆吉兆胡同的生活用了“穷困”来限定,这是李素刺笔下的子君对当时生活刻骨铭心的记忆,同时也是对《伤逝》中大量渲染子君、涓生同居窘迫日常的映射。众所周知,涓生对那段生活的回忆是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饭,菜饭都是不够的,油鸡们没有食物喂,只能成为菜肴,阿随也不得已送走,甚至也要为冬天的煤炭发愁。《子君走后的日记》则通过子君的视角叙述着俩人同居的艰苦生活,吉兆胡同两间“冰冷”而“空洞”的小屋,“满尘的旧衣裳”,涓生“瘦黄”的脸……从表面上看,没有生活来源,无法生存是《伤逝》铺开而延续到《子君走后的日记》的共有情境,透过日记的讲述者“我”的所见所感表达了个体生存的艰难。
生存困境的描写之所以把读者深深带入其中,为涓生感慨,为子君怜惜,小说的结构方式实际上起到了很大的功用。《伤逝》作为日记体小说,没有明确的日期标注,是以叙述者涓生的情绪流动来结构小说的,并以段落之间的空白来分小节,以此来完成小说时空的转换,因此,小说不以具体时间来推进故事的情节,回忆中幸福快乐的时光以“去年的暮春是最为幸福”为起句,油鸡们成为菜肴后看到子君的颓唐忍不住感叹“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呵!”子君终于离开后,心绪是“有些轻松,舒展了”,得知子君死去的消息,涓生想,要真有地狱鬼魂,他就可以“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情绪的流动结构出叙述话语,情绪的转折推动故事前进,而作者的情绪也容易与讲述者分离和重合。故事的时间虽然相对模糊,却也有一条时间的轴线,“一年之前”“交际了半年”“去年的暮春”“双十节”“五星期”“冬春之交”“初春”,这种写作策略被认为充满了“抒情性”,同时也获得了读者对“忏悔”的认同,进而增加了读者对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认同,这也引发了研究界的讨论,周作人甚至认为小说是在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子君走后的日记》则与《伤逝》的写作方式不同,有明确的日期标注,并且不间断地从“一月十日”写到“一月十四日”,子君就在离开涓生的5天后在家中死亡。这样紧迫的日期标注方式,作者显然是想以紧凑的时间体现小说的张力,从形式上来推进小说中对子君步步走向死亡紧迫感的渲染。虽然形式与《伤逝》不同,但是其结构方式仍然是聚焦在讲述者——子君的情绪流动上,《子君走后的日记》显然是一篇情绪小说,只有寥寥无几的对话穿插其中。子君在第一篇日记中就直接抒发“回家”的苦闷:“我颤抖着跨进了家门,唉!今天呀!今天,我的命运注定;今生的幸福之梦消逝了,无望了!天啊!我可以休息了吧……虽然外面飘荡着的春风,吹嘘进温柔的阳光;雀鸟振刷着翅膀,向蔚蓝的苍穹,奏着他们的自由之歌。但这于我,不过倍加悲痛,苦闷。”回到家族的痛苦与爱情失败的痛苦交织在一起,作者把这一情绪贯穿在小说的始终,并逐步把子君的心绪引入死亡。代入式的写作,最大程度体现了子君在“家”的每一天都是巨大的折磨,从而指出子君的绝望与死亡必然的罪魁祸首。总体看来,两篇小说的结构方式都在意图营造叙事的“真实”。
互动式文本并不是新鲜的事物,甚至在日记体小说范围内也不是,如1921年《礼拜六》139期刊出王建业拟女性作者写的《侬之日记》,姚庚夔有感做一篇《一个懦夫的日记》来回应。但《子君走后的日记》与《伤逝》只是在文本上的对话,并无作者间的私下交流,作者李素刺是一名高中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高中生已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她的生活阅历可能有限,但是她的知识结构和广度却并不狭窄,她的认知来源大多是来自阅读、聆听以及他人的影响,《子君走后的日记》是一次征文比赛的作品,李素刺必然要把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作品展示出来,而选择写作《伤逝》的续,也说明是《伤逝》给了她很大的震撼和触动。同时,这也是当时的“知识女性”对鲁迅问题的一个回答,因此,作为《伤逝》的一个呼应性文本,《子君走后的日记》体现的思维价值远远超过了其故事情节的艺术价值。
二、生存空间的隐喻与文本间的对话
涓生与子君的议题除了性别批判、启蒙批判之外,还有更多的讨论层次。比如“为什么要在男性与女性之间进行一种角色/权力的分配,使得‘男性—知识空间—启蒙—新生'与‘女性—日常生活—反启蒙—死亡'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逻辑得以建立?”这似乎是历代社会变革中新的价值观念的确立必然否定另一种价值观念在文学中的投影。在这种对比之外,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是鲁迅在“五四”时期的一个重要着眼点。钱理群认为《伤逝》“有强烈的知识分子的自忏自省性,而且也充满了对人的生存困境的追问”是最具“鲁迅气氛”的小说之一,涓生在“诚实”和“说谎”之间选择,悲哀的是无论如何选择终究避免不了人生的“虚空”。经济的窘迫似乎是《伤逝》中涓生和子君“不爱”的重要原因,而实际上,精神的困顿更引人深思。涓生说“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涓生的“忏悔”是想表达什么?不只是心中悲哀的抒发,不只是需要读者对“忏悔”的认同,更多的是需要灵魂的自视,自我的救赎,只有这样他才有继续前行,获得反抗绝望的勇气。因此,《子君走后的日记》虽然是对《伤逝》单向式的互动,但这不妨碍作者李素刺表达自己的观点,她抓到了《伤逝》中涓生记忆的空白和断点,把子君归家到死亡这一情节叙述出来,补充了子君在“涓生”的讲述中并不清晰,进而也“并不重要”的形象。
鲁迅的生存哲学首先是要正视生存困境,他对生存空间的设定与人物的精神困顿一表一里,其隐喻超越了男女爱情的故事,体现了“个人”在社会中孤立无援、无所依托的生存境况。《伤逝》中出现三个重要的生存空间,会馆,吉兆胡同的小屋,通俗图书馆。会馆是“旧时都市中同乡会或同业公会设立的馆舍,供同乡或同业旅居、聚会之用。”在旧时相当于集体宿舍,聚集了一群在一个城市没有“根”而又收入微薄的外乡人,“破窗”“半枯的槐树”“败壁”,这样破败的会馆却是一个年轻人在城市打拼生活的起点,当涓生失去子君,这又成了他无处可去的归处,也是涓生在回忆中痛苦,在痛苦中准备前行的所在。吉兆胡同的小屋是小说主要的生活空间,这虽然不是理想居所,但也是子君和涓生几经寻找最终不得不将就的独立处所。在这里,子君和小官太太“明争暗斗”,虽然触及的也是谁家的鸡多吃了两粒米,谁家的狗瘦弱受到嘲笑这样的小事,却揭示出中国几千年的市井生活,看似精明实为笑谈的人性的丑陋一面。涓生认为“这样的处所,是不能居住的”。通俗图书馆似乎是涓生灵魂的暂歇之地,一是图书馆符合自己读书人的身份,在这里能够找到自我认同,二是图书馆似乎脱离了琐碎的生活,在这里思考人生、得以反省“人生的要义”。但图书馆的书“却无可看”,都是陈腐的旧书,只是一个知识空间的壳子罢了。
《伤逝》中破败的会馆、不适合居住的住所、空壳子式的图书馆,反常规的生存空间展示了人生的荒谬感与无力感,涓生一直找寻“新的生路”,为此宁愿抛弃子君,承受背叛的罪恶。但一个疑问油然而生,在这样反常的生存空间中涓生能找到生的希望吗?李素刺在《子君走后的日记中》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在《子君走后的日记》中,作者首先剥离了子君与启蒙思想的关系。她写出了子君对于被抛弃的怨念与愤然,“涓生对我实在太残忍了,不爱我了,还不如把我像油鸡似的杀了痛快。我为爱他而坚忍刻苦的劳动,以致这样憔悴了!他呢?不爱我了……”但笔锋一转,子君也在“忏悔”了,“我的错误吧!?他不是表示过他的真挚的爱吗?但我在人生之路上不能分担一部分的责任,不但不能帮助他,反叫他增加负担,唉!我——可恶的女人”这是一个附庸于男人的女人的自怨自艾与自暴自弃,真实地反映出涓生的冷暴力让子君极度地否定自我,并在自我否定中丧失了自我的尊严和价值。涓生一度希望子君能够在自己的启蒙下获得自我的独立,但子君却只能止步于启蒙的第一阶段——走出封建家庭,无法实现的“二次启蒙——以人的觉醒为基础的女性的再次觉醒”,在李素刺笔下,子君与“启蒙精神”被剥离得更远。阅读体验使李素刺对鲁迅塑造的子君进行高度的模仿,并在价值上深度认同,子君半新半旧的思想被作者更加放大了“旧”的一面,李素刺在塑造了清晰的子君人物的同时,也失掉了人物应该有的复杂性。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李素刺的描写则进一步让人确认:子君的思维模式与人性预设和新文学思想启蒙关系不大,她勇敢地走出家门是因为对涓生的爱,这种“爱”有时并不具有“现代性”,莫若说反倒具有一种“古典性”“古老性”乃至“原始性”。
与《伤逝》形成对应,《子君走后的日中》唯一的生存空间就是“家”,这个家中有父母、兄嫂、学走路的侄子和天真的小妹妹。子君一反原有文本中的沉默,控诉着这个无法逃离的家:“我还有什么祈求,期待,留恋?!像囚犯似的又坠陷在这黑暗的牢笼里;回到这威严的,冷酷的家中,我还有什么话说?!冰似的面孔与眼光处处在塞着你的嘴”,“父母对他女儿的爱,已被礼教,名誉,金钱,整个的社会,剥夺去了;兄嫂弟妹,哪里还认识,亲近。”父母的冷酷、兄长的漠视、嫂子的嘲讽把这个封建家长制的家庭勾勒出来,而还在学步的侄儿与年幼天真的妹妹则代表了还未被这个家庭腐蚀同化的新生力量,但他们的未来也未可知。在这一层面,《子君走后的日记》更趋向鲁迅《狂人日记》的主题,控诉封建家长制对人性的摧残,并以《狂人日记》为中心向外辐射到包括《祝福》《药》等小说以及一系列的杂文创作,集中投射了鲁迅对“吃人的社会”不遗余力地抨击。《子君走后的日记》中子君大量控诉了封建家庭对其精神与生命的扼杀,她被拘禁在一所小屋,吐血后也没有得到家人的关心,母亲斥责她出走的行为“简直禽兽”,“父母对女儿尚且这样的残酷;世界上还有谁怜悯我?”子君就是被这样“吃人”的家庭夺走了生命。应该说,除了小说开篇对涓生的哀怨以外,小说已经去除了涓生对子君的“抛弃”而导致子君归家死亡这一线索,转而向无情的家庭和封建社会发起了攻击。追其根源,一是“封建家庭问题”本身就是《伤逝》中的隐性主题,涓生在自诉中几次提到了子君的家庭,并认为父亲是“儿女的债主”,如“烈日一般的威严”主宰着她的人生,只不过这些本来是作为背景的线索被李素刺抻出并加以正面的补充,而这一补充实际是应和了当时新青年和新文学中有关“家”共有的主题——封建家庭对青年的压迫。同时,“家”也隐喻了整个“吃人的社会”,子君认为涓生在“这样的社会也是很难生存的,他像恢复自由的囚犯一样,为人轻视,不能站立在高贵的人们中,除了死亡。”子君并不认为涓生的“生路”像他自己所想象的那样会实现,“最好也不过同阿随一样。”虽然子君并不具备涓生式的精神困境,但是“失掉勇气”的她面对黑暗的社会仍有着自己的人生体验和人生思考,她一语道破了涓生以及思想启蒙者们心中隐藏的恐惧——即使背负忏悔也要追求新生,但在既有的社会中希望终究渺茫,恐怕无望。
结 语
李素刺的《子君走后的日记》虽然近乎是一个无名的文本,但是却有着多重的意义,一是展示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非职业作家对日记体小说这一文体的应用程度,二是读者对鲁迅小说《伤逝》的解读和回应,三是当时青年(女)学生对五四新文学的一种理解。《伤逝》是涓生的“手记”,是他与自我灵魂的对话,《子君走后的日记》则是《伤逝》多层次主题中一种主题的具体化,李素刺笔下的“子君”对鲁迅笔下的“涓生”是一种和解,是对他“忏悔”的接受。在涓生的启蒙语境下,子君作为“被启蒙”式的人物特征在《子君走后的日记》中被消解,转而通过子君的控诉侧重展示了个人的生存与社会的矛盾,这个矛盾不仅使子君葬送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也使得涓生终将与子君一样,处于没有生路的命运。这篇文学性并不出众的小说,它的存在意义值得继续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