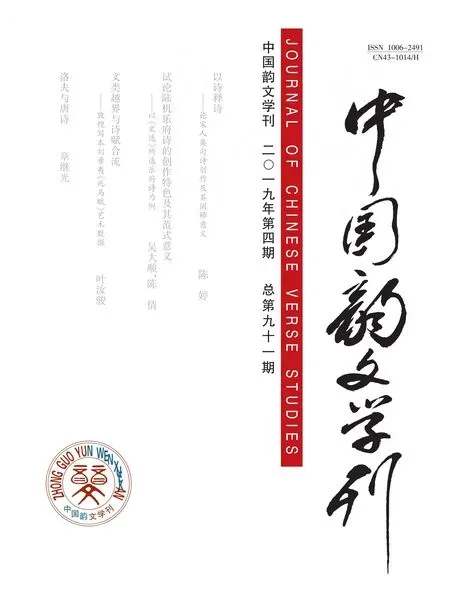“词格”、“蕴藉”与“浑成”
——论晚清民国词人俞陛云的词学观
王 凯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宝山 201900)
晚清民国词人俞陛云(1868—1950),字阶青,号乐静、斐盦,晚号乐静老人、存影老人、娱堪老人,室名乐静堂。原籍浙江德清县南埭村人,清代著名经学大师俞樾之孙,近现代著名文学家俞平伯之父。俞陛云幼承家学,诗文、书法、绘画皆通,在词学上亦卓有成就,所著《乐静词》和《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在民国时期颇为词学界所重。夏敬观《忍古楼词话》云:“钱塘俞阶青编修陛云,曲园先生之孙。其词清空,颇有家法。”陈声聪《论近代词绝句》评俞陛云曰:“早岁荣归自玉堂,东华坐阅海生桑。剪红刻翠身难老,陶鞴风花作道场。”又云:“柔曼婉贴,吉祥止止,无一毫轻薄怨苦语,故福人也。”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云:“地英星天目将彭玘。乐静词安雅俊爽,犹有朱、厉遗轨。所为《宋词选释》,剖析词人用心,颇中肯綮。”晚清民国时期,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呈现出共存与交融的趋势,俞陛云在积极融合浙、常两派词学之长的基础上,受时代风气影响,极力主张以“词格”“蕴藉”“浑成”评词。这成为他词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词格”评词,推崇词格高的作品,对词作的审美特征格外重视;以“蕴藉”评词,强调词作含蓄蕴藉,与词之本色及常州词派“意内言外”有着深厚渊源;以“浑成”评词,对气高而浑、较少雕琢的唐五代词赞赏有加。俞陛云以这三种范畴评词,且能有效兼顾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两个方面,反映出晚近词坛浙、常两派共存与交融的时代潮流。
一 “格高气盛”:俞陛云的“词格说”
“格”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审美范畴,源于魏晋,与“风”“骨”“清”“秀”等词一起被用来概括人物的个性气质和精神面貌,后逐渐运用至诗文批评中。“格”被引入词学批评,大致始于北宋中期。苏籀在《书三学士长短句新集后》中评秦观词云:“落尽畦轸,天心月胁,逸格超绝,妙中之妙,论者谓前无伦而后无继。”此后,有宋一代的陆游、朱熹、张炎、陈振孙也都曾以“格”论词,而“格”真正作为词学批评范畴被广泛应用则是在清代。厉鹗《论词绝句十二首》评张先、柳永词云:“张柳词名枉并驱,格高韵胜属西吴。可人风絮堕无影,低唱浅斟能道无。”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评陈克词云:“不甚有重名,然格韵绝高,昔人谓晏、周之流亚。”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词法之密,无过清真。词格之高,无过白石。”况周颐《蕙风词话》云:“词格纤靡,实始于康熙中。”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也多以“格”评词,如评欧阳修、秦观词“虽作艳语,终有品格”;评柳永《八声甘州》和苏轼《水调歌头》“伫兴之作,格高千古”;评蒋春霖《水云楼词》“小令颇有境界,长调唯存气格”等。这些论述逐渐促使古典词学批评中的“词格说”趋于成熟。
俞陛云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中评词,多次提及“词格”这一概念,这成为他词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在《五代词选释叙》中说:“论其词格,承六朝乐府之余响,为秦、黄、欧、晏之传薪,其文丽以则,其气高而浑,卓然风人之正轨也。”是以“词格”对五代词做出的总体评价。即在俞氏看来,辞藻华美而有法度、气质高雅而又浑成的作品才是“风人之正轨”,也属于词格高的作品,而五代词就具备了这一特点。在品评各个词人某一具体词作之时,他也时常使用“词格”这一概念,指向内容却不尽相同。评李白《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以词格论,苍茫高浑,一气回旋”,是就词作整体所造词境而言;评和凝《天仙子》(洞口春红飞簌簌)“写闺思而托之仙子,不作喁喁尔汝语,乃词格之高”,是就词作不主故常的写作内容而言;评晏殊《清平乐》(红笺小字)“以景中之情作结束,词格甚高”,是就词作收束词意的技法而言;评史达祖《万年欢·春思》“‘烟溪’二句从对面着想,颇似清真词格”,是就词作着笔角度的构思而言。具体指向虽有所不同,但大体而言,都是对词之品格、风范等方面做出的评价。
俞陛云以“词格”评词,还多以“格调”称之。如评孔平仲《千秋岁》(春风湖外):“此词和秦少游韵,格调不让秦郎也。”评程过《满江红·梅》:“下阕‘暮云残角’句以下,人与梅合写,低回咏叹,格调清逸。”评姜夔《满江红》(仙姥来时):“此调用平韵,为白石所创,格调高亮。”此处所谓之“格调”,主要是就词作格律、声韵及用调而言。除这之外,俞氏也曾从词作整体品格、笔法等层面论及“格调”。如他对周邦彦《法曲献仙音》(蝉咽凉柯)一词赞赏有加,在评语中云:“后阕虽寄怀宛转,而纯用疏朗之笔,绝无缋饰,见格调之高。”从该评语可知,俞氏认为用疏朗自然之笔写出且又毫无雕饰的词作,才称得上“格调”高的作品。这反映了俞氏对“格调”的一些基本看法。
俞陛云论及“词格”,常以“高”“气”二字为修饰语,故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中多次提及“高格”“气格”等字眼。但就具体词作而言,“高格”“气格”所体现的侧重点也均有不同。如评冯延巳《归国谣》(何处笛)(江水碧)《长相思》(红满枝):“以上三词,皆挥毫直书,不用回折之笔,而情意自见。格高气盛,嗣响唐贤。”此处所谓之“格高”主要是就词作的笔势、章法而言,属于词作艺术形式方面。评冯延巳《抛球乐》(霜积秋山万树红)(尽日登高兴未残)(坐对高楼千万山)三首:“写离索之感,能于劲气直达中含情寄慨,故不嫌其坦直,此五代气格之高也。”评李煜《长相思》(一重山):“以轻淡之笔,写深秋风物,而《蒹葭》怀远之思,低回不尽,节短而格高,五代词之本色也。”此二例提到的“气格之高”“节短而格高”主要是就词作所蕴含的低回不尽的深厚情感而言,属于词作思想内容方面。评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举怀人恋阙,望远思归,悉纳其中,而以清空出之,复一气旋折,深得唐贤消息。集中之高格也。”此处所言“高格”是就情感内容和写作章法两方面而言。评晏殊《清平乐》(金风细细):“惟结句略含清寂之思,情味于言外求之,宋初之高格也。”评吴文英《极相思·题陈藏一水月梅扇》:“‘水清月冷’三句水月梅合写,格高而韵远,一洗南宋慢体之习。”这二例中的“高格”“格高”主要是就词作构思与技法而言。由此可以看出,俞氏推重“词格”高的作品,其所言“词格”总体依托词人笔法、气势而生,却也能兼顾词作所写内容与情感等方面。
邱美琼、胡建次在《中国古典词学批评中的词格论》一文中指出:“清代后期,词学批评中对‘格’予以理论阐说的著作和篇什较多,其阐说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对‘格’作为词作审美之本的标树、对词格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及对词格创造与生成的考察方面。”俞陛云所论之“词格”主要侧重词作笔势、章法等写作技巧,属于词作的审美艺术层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俞陛云“词格说”体现了晚清之时“词格”批评实践的普遍风尚。同时,俞氏之论又存在一定的进步性。清末四大家之一的况周颐极力倡导以“词格”论词,他在《蕙风词话》中说:“重者,沉著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此处所谓之“气格”,是对“重”做出阐释,主要指词作所蕴含的沉挚的思想感情。俞陛云在以“词格说”重点探讨词作审美艺术之时,对词作的思想内容也并无忽视,他的“词格说”正是晚近词坛浙、常两派共存与交融的产物。
二 “风流蕴藉”:俞陛云的“蕴藉说”
“蕴藉”亦作“酝藉”“温藉”,最早被用来形容君子气质,意为含而不露。《汉书·薛广德传》云:“广德为人,温雅有酝藉。”《后汉书·恒荣传》云:“荣被吸儒衣,温恭有蕴藉。”后来,“蕴藉”一词被引用至文学批评,用以形容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又颇具弦外之音的语言艺术,成为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审美范畴之一。“蕴藉”应用于词学批评,大致始于宋代,黄叔旸评谢懋词云:“居士乐章吴坦伯明为序,称其片言只字,戛玉敲金,蕴藉风流,为世所赏。”明清时期,将“蕴藉”作为词学批评范畴的现象更加普遍。陈霆《渚山堂词话》云:“‘绿阴深树觅啼莺,莺声更在深深处’,语意蕴藉,殆不减宋人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清真之劲敌,南宋一大家也。”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张玉田词清远蕴藉,凄怆缠绵。”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云:“其大旨在于有寄托,能蕴藉,是固倚声家之金针也。”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引吴枚庵语云:“大旨瓣香竹垞,而小令婉丽,慢词蕴藉,兼有南北宋之长。”等等。经过以上诸人的提倡和努力,以“蕴藉”作为品评词作艺术水平高低的实践逐渐趋向高潮。
俞陛云受晚清“蕴藉”词学批评风尚的影响,也提倡以“蕴藉”评词。他曾说:“含蕴不尽,词家妙诀也。”这一论说与清代沈祥龙对含蓄的看法有些类似,沈祥龙说:“含蓄无穷,词之要诀。含蓄者意不浅露,语不穷尽,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其妙不外寄言而已。”实际上,所谓“含蓄”“蕴藉”“含蕴”要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即要求作品要曲折委婉、含而不露、留有余味。俞陛云对这类词作尤其欣赏,如评张先《浣溪沙》(水满池塘花满枝):“‘玉窗’句丽不伤雅,情味在含蕴中。”评李玉《贺新郎·春情》一词时引黄玉林语云:“风流蕴藉,尽此篇矣。”评吴文英《青玉案》(短亭芳草长亭柳):“此词‘残杯’‘青塚’三句,同一荒茔酹酒,以蕴藉出之,沈伯时所谓词家‘用字不可太露’也。”评王沂孙《高阳台·和周草窗寄越中诸友韵》:“此词前半首平叙初春怀友,其经意在后半首以蕴藉之笔,致缠绵之怀。”评张炎《高阳台·西湖春感》:“‘新愁’二句怅王孙之路泣,何等蕴藉。”评周邦彦《忆旧游》(记愁横浅黛):
先将窗外之秋声,闺中之愁态,细细写出,以“两地魂消”句彼此开合,遂与下阕衔接一气。“朱户”三句迨“为郎憔悴却羞郎”,妙在不说尽。“拂柳”“吹桃”等句,仍寄情于空际,弥觉蕴藉。“巢燕”句感光阴之易过耶?抑喻人事之更新耶?词境入空明之界矣。夏闰庵云:上阕之结句,不可无此顿挫;下半阕一气带出,其得势在此。
周邦彦《忆旧游》(记愁横浅黛)是一首离别相思之作。该词上阕回忆与心上人离别之事,下阕站在心上人角度写离别之后的相思之情。词中“朱户”三句乃是“也拟临朱户,叹因郎憔悴,羞见郎招”,委婉含蓄地道出了女主人公对自己的思念程度之深,别有风味,俞氏称其“妙在不说尽”。而这之后的“旧巢有新燕”“杨柳拂河桥”“东风竟日吹露桃”三句仍是以含蓄之笔出之,“新燕”“杨柳”“河桥”“露桃”皆带有象征意味,俞氏称“巢燕”句是“感光阴之易过耶?抑喻人事之更新耶?”然作者并不道破,全凭读者自己去领会揣摩,以致俞氏称赞此词是“寄情于空际,弥觉蕴藉”。
俞陛云以“蕴藉”评词,对词作结语是否“蕴藉”十分重视,他在评毛熙震《清平乐》(春光欲暮)一词时曾经说过:“结意含蓄,自是正轨。”可见,在俞氏看来,追求结语“蕴藉”才是词作应有之正道,这甚至成为他评鉴一首词作好坏与否的圭表。俞氏在评其他词作结语时,也多以“蕴藉”评之,如评冯延巳《采桑子》(酒阑睡觉天香暖):“下阕在孤灯映月、低回不尽之时,而以东风梅绽、空灵之笔作结,非特含蓄,且风度嫣然,自是词手。”评苏轼《青玉案·和贺方回韵送伯固归吴中》:“结句尤蕴藉多情。”评周邦彦《浣溪沙》(日射敧红蜡蒂香):“结句以含蕴出之,尤耐寻挹。”评王易简《齐天乐·客长安赋》:“结句欲写春愁,而付诸‘小楼夜雨’,语殊蕴藉。”评张炎《八声甘州·坐客索赋歌妓桂卿》:“结句‘明月妆楼’尤见含蕴。”除此之外,在评一些词作时,俞氏虽不提“蕴藉”“含蕴”等字眼,但亦可看出他是以“蕴藉”为标准对词作进行考察,如评张先《浣溪沙》(锦帐重重卷暮霞)结句是“不说尽”“尤耐寻味”;评周邦彦《南乡子·咏秋夜》是“纯以风韵胜,情味把挹弥永”;评贺铸《忆秦娥》(晓朦胧)是“妙在不说尽,味在酸咸外矣”等等。这均可看出俞氏对结语“蕴藉”的重视。
俞陛云提倡以“蕴藉”评词,对那些坦率直白、抒情直露的词作,也委婉地提出了批评。如评李珣《浣溪沙》(红藕花香到槛频)云:“作者言情之词,尚有《酒泉子》《西溪子》《河传》《巫山一段云》诸首,皆意境易尽,不若此词之蕴藉。”俞氏将此《浣溪沙》词与李珣其他作品进行横向比较,得出《酒泉子》等词不若此词“蕴藉”的结论,他的《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对这几首词作也并未收录,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俞氏在评高观国《玲珑四犯》(水外轻阴)一词时,称“花里再看仙侣”一句是“虽应有之意,稍嫌说尽”,也暗暗指出了该词不够含蓄蕴藉、缺乏弦外之音的特点。
俞陛云倡导以“蕴藉”评词,与词体之本身特征有着深厚渊源。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彭玉平先生在阐释这句话的含义时指出:“所谓要眇宜修,应该是指词体在整体上呈现出来的一种精微细致、表达适宜、饶有远韵的美。”常州词派张惠言所倡导的“意内言外”也是对词体这一特性的发扬,《词选序》云:“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俞陛云所谓之“蕴藉”正与词体“要眇宜修”的特性相吻合,侧面体现出俞氏对词体本色的重视。同时,俞陛云论词向以常州词派为宗,他的“蕴藉说”更多地受到了常州词派“意内言外”说的影响。不同的是,常州词派提倡的“意内言外”多是由词作的思想内容出发,强调“低回要眇”的情感基调,而俞氏的“蕴藉说”则不仅着眼于思想内容,还对词作之艺术特性多有强调,主张用艺术审美的眼光去欣赏词作之含蓄蕴藉。从此方面来讲,俞陛云的“蕴藉说”融合了浙、常两派的思想,促使中国古典词学中的“蕴藉”批评更趋完善和成熟。
三 “秀雅浑成”:俞陛云的“浑成说”
“浑成”一作“混成”,最早源于老子《道德经·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意为天然生成之意。后逐渐演变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审美范畴,用以形容文艺作品的浑化无迹和自然天成。宋代时期,以“浑成”评论诗歌已较为常见,如蔡正孙《诗林广记》云:“摩诘诗浑成,胜退之诗。”洪迈《容斋诗话》云:“语虽纪实,然太露筋骨,不若前两章浑成也。”释惠洪《冷斋夜话》云:“渊明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浑成风味,句法如生成。”宋末时期,张炎把“浑成”引用至词学批评,他在《词源》中说:“美成词只当看他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魄。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至清代,以“浑成”评词较之前有所增多,郭麐《灵芬馆词话》云:“姜、张诸子,神韵相同,至下字之典雅,出语之浑成,非其比也。”况周颐《蕙风词话》云:“凡余选录前人词,以浑成冲淡为宗旨。”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先舒语云:“词家意欲层深,语欲浑成。作词者大抵意层深者,语便刻画,语浑成者,意便肤浅,两难兼也。”综合来看,清代以“浑成”评词虽较前代明显增多,但若将其放在词学著作如林的清代仍属个别现象,与前面所论“词格说”和“蕴藉说”相比,也远不如前两者使用频率之高。
俞陛云在倡导“词格说”“蕴藉说”的同时,也学习和借鉴了在诗学批评中广泛使用的“浑成”一词,并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中加以大量运用,这在晚清民国时期可谓独树一帜。俞陛云十分推重唐五代词,他在《五代词选释叙》中评五代词时强调:“其文丽以则,其气高而浑,卓然风人之正轨也。”鲜明地指出了五代词“文丽以则”“气高而浑”的特征。在俞氏看来,“五代词句多高浑”,这正是唐五代词成为“风人之正轨”的原因之一。因此,他在品评唐五代时的词作时,常以“浑成”论之,如:评李白《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是“苍茫高浑,一气回旋”;评王建《三台令》(池北池南草绿)(鱼藻池边射鸭)二首是“其浑成处,想见盛唐词格”;评冯延巳《采桑子》(马嘶人语春风岸)“落日高楼”句是“尤为浑成”;评冯延巳《临江仙》(秣陵江上多离别)是“自有高浑之度”。在评温庭筠《更漏子》(玉炉香)一词时,俞氏指出结语“空阶滴到明”一句被后人用入诗中,但俞氏特别强调,该诗“语意说尽,不若此词之含浑”,委婉含蓄地道出了批评之意,也从侧面反映出俞氏对词作“浑成”的重视。
俞陛云在品评两宋词人作品时,遇见“气高而浑”的作品,也不乏赞美之词,偶时还会将这类词作与唐五代词相比附。如评苏轼《洞仙歌》(冰肌玉骨):“全篇好语穿珠,清丽而兼高浑,风格似南唐二主。”是将苏词比附南唐二主。评贺铸《谒金门》(花满院):“前、后阕分写情景,以高浑出之,不事雕饰,五代遗韵也。”评贺铸《小重山》(帘影新妆一破颜):“‘斜阳’二句颇高浑,有五代遗意。”是将这二首词作比附五代词。虽说唐五代词仍处于词的启蒙阶段,与宋词相比,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还不够成熟。但是,正因为此,唐五代词少了一些句法、章法上的雕琢痕迹,而多了一些浑成、自然。实际上,就唐五代词的整体风格来看,也确实如此,它们大都直写景物,清朗自然、不事雕绘、含思凄婉,所谓浑然天成,不求工而词格自高。这也正是俞陛云所欣赏的。
俞陛云以“浑成”评词,多指向词作句法,这反映出他对词作艺术的重视。如评张景修《选冠子·咏柳》“章台”“灞水”三句,“浑成而有逸宕之致”;评辛弃疾《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句法“浑成而兼倜傥”;评史达祖《临江仙·闺思》,“句法浑成而兼韵致,殊耐微吟”;评史达祖《西江月》(一片秋香世界)上阕前两句,“秀雅而浑成”;评周密《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山川”“心眼”二句,“句法高浑,且含无限悲凉”;评周密《水龙吟·白荷》“霁月三更”句,“不事雕饰,句法雅切而浑成”;评王沂孙《醉蓬莱·归故山》“故国如尘,故人如梦”二句,“以浑成之笔写之”;评王沂孙《八六子》(洗芳林)结语,“余韵不尽,句亦浑成”等。除此之外,俞氏所论之“浑成”也指向词作内容,且主要指写景,如评贺铸《谒金门》(花满院):“前、后阕分写情景,以高浑出之。”评赵长卿《眼儿媚》(楼上黄昏杏花寒):“上阕‘燕子’三句写景浑成。”评严仁《水龙吟·题盱江伟观》:“‘数峰’三句写景浑成。”俞氏以“浑成”论词,不仅强调词作艺术,同时也兼顾词作之思想内容,这体现了俞氏兼容并包、风格多元的词学面貌。
俞陛云虽以“浑成”论词,但对“浑成”并未做出系统全面的理论阐释,对“浑”字的意义也没有进行过深入探究。郭绍虞先生曾说:“浑,全也,浑成自然也。所谓真气内充,又堆砌不得,填实不得,板滞不得,所以必须复还空虚,才得入于浑然之境。”俞氏所论之“浑成”当也是此意。综合来看,在当时词学批评中的“浑成说”还不算十分流行的情况下,俞氏标举“浑成”论词,颇有一番新意。与郭麐、王又华等人主要将“浑成”着眼于词作语言方面相比,俞氏“浑成说”的范围要显得更为广阔,其不仅涉及词作的语言、句法、章法等艺术层面,在谈及词作内容时也常以“浑成”论之,有效地体现出他融合浙、常两派词学之长的词学观念。同时,俞氏还为词作之“浑成”找到了一个标准的范式,即以唐五代词为“正轨”,这在当时是具有较大进步性的。
结 语
陈水云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词学转型——俞平伯家族的词学史》一文中称“或是站在常州派的立场却注意作品的艺术分析”,指的正是俞陛云。陈先生此言恰巧委婉地道出了俞陛云以常派为宗亦兼容浙派之词学理念的多元化的词学风格,可谓十分中肯。俞陛云在积极融合浙、常两派词学思想的过程中,极力倡导以“词格”“蕴藉”与“浑成”评词,这三种审美范畴零散而又广泛地分布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中,其意义不可谓不大。综观俞氏之论,其重心主要是对前人理论作更为深入地阐释和发展,有关自己的原创理论并不多。与同时代陈廷焯的“沉郁说”、况周颐的“重、拙、大”和王国维的“境界说”等理论相比,俞氏的“词格说”“蕴藉说”与“浑成说”均未能升华成完备的词学理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俞氏在以三种范畴评词的时候,能有效兼顾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两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晚清民国时期浙、常两派余绪共存与交融的时代潮流,在融合浙常两派词学之长、推动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转型的过程中,俞陛云的价值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