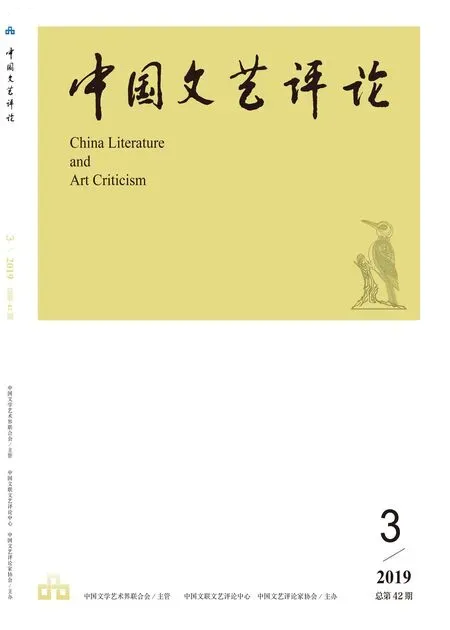从“谦卑”中获得自尊
——论乔治·斯坦纳的文艺批评思想
张 芬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 1929— )是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翻译家、作家。他成长于多语言环境的犹太家庭,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屠杀。斯坦纳在这种惨绝人寰又隐秘残酷的环境中得以逃生,成为后来他口中的“幸存者”。本着儿时的文艺经验以及敏感、聪慧的天性,他辗转在欧洲、美洲求学并崭露头角,最终在文学研究领域取得辉煌成就。斯坦纳是一个富有强烈人文气息的文学批评家,我们常常能够从他的文字中读到充满焦灼感的道德追问。他广博的文学视野、纵横捭阖的言说方式、对文学语言异常原始而充满热情的敏感、警觉,他飘逸而深邃的文风以及富于人文关怀的文学思想,都给一般读者带来极大的挑战和快感,同时也令惯于探根究底的学者感到一丝不明就里的惶惑。作为学院内部看起来自由不羁的写作者,斯坦纳的文字也颇受同行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斯坦纳的文学批评的独特个性是无法被取代的。
斯坦纳被中国读者广泛关注,主要还是他那著名的“四步骤”翻译思想。《巴别塔之后》(After Babel
, 1975)最为中国研究者所熟识。近年来,他的早期文学批评被逐渐翻译进来,例如《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Tolstoy or Dostoevsky: An essay in the Old Criticism
, 1959)、《悲 剧 之 死 》(the Death of Tragedy
, 1961),以及表现他文学和文化批评思想的《语言与沉默》(Language and Silence
,1967),乃至借助于风靡的哲学主题而被较早引进中国的《海德格尔》(Heidegger
, 1978)等。除了这些作品之外,据说上世纪80年代之后,斯坦纳较为专注于文化批评,不少作品尚未被翻译到国内。只有一部半自传性质的《斯坦纳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Errata: An Examined Life
, 1997)被翻译进来。目前,相对于其他同时代我们花费了较多精力介绍的欧美批评家,有关斯坦纳整体文艺思想的介绍除了《语言与沉默》的翻译者李小均的“札记”之外,所见不多,似乎还有大量翻译、研究的余地。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的斯坦纳,还没有在国内露出水面。有关斯坦纳的深入研究,尚停留在局部。一、批评及其“谦卑”
正如萨义德所说,斯坦纳的文学批评带有某种“遗老遗少的人文主义气味”。斯坦纳有对经典文艺谙熟的童年记忆。他从小就在多语言的环境(英、法、德)中长大,六岁之后,父亲就带他朗读荷马史诗、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戏剧等19世纪以前的丰碑式作品。他在这些多语言的精彩片段的涵咏中长大。这使得他后来的文学批评尤其尊重由原作生发的情感和信念。这些“经典”记忆也使他更愿意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来理解文学。因此,他似乎并不相信什么理论,他说:“在人文学科、历史研究即社会研究或是品评文学及艺术,要从‘理论’入手,我觉得是虚伪不实的。”他相信每一次的文学阅读和研究经验都是独立、独特的。他的博士论文《悲剧之死》出版后,他就以致谢父亲的方式,表达出了自己迥异于当时学院派主流文学批评的一面:“最重要的是,父亲用亲身经历教导我,伟大的艺术并不专属于行家和学者,毋宁说,它会被那些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所领会和深爱。”既然文学属于每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那么,这种阅读必然要求阅读者和作品(作者)跳过任何“中介”性元素,实现尽可能的“身心统一”。在这之中,他毫不隐讳地谈到了文学批评和伟大的文学创作者的不对等:
当批评家回望,他看见的是太监的身影。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如果能焊接一寸《卡拉马佐夫兄弟》,谁会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敲打最敏锐的洞见?如果能塑造《虹》(Rainbow
)中迸发的自由生命,谁会跑去议论劳伦斯的心智平衡?这种看似刻薄的语言,正是来源于作者对经典体悟的“心向往之”而“不能至”。基于对创作者这种尊重乃至敬仰,他建议批评者保持一种“谦卑”的姿态。斯坦纳对当时学院环境中存在的文学批评家傲慢而自成体系的姿态保持警惕:“批评家相互吹捧。聪明的年轻人不再视批评为挫败,不再视批评为与自己有限的才华的灰沙逐渐忧郁地妥协,他们认为批评是声明显赫的志业。这不仅好笑,结果也有害。”他甚至认为,再好的文学阐释还是文学批评,都是派生的“次级”活动。他说,“文学批评必须以谦卑之心,带着经过不断更新的生命感,回归这些传统”。基于这种“谦卑”,斯坦纳要求读者对文本给予足够的尊重,并希望在一种整体性中来观察文学。他反对那种一厢情愿的决定性的阐释。他认为好的文学永远是开放的,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斯坦纳看来,文学批评家和文学作品理应处于一种奴仆关系。读者或文学批评家应发动身心去阅读,给出足够的反应和回响,从“谦卑”中获得自尊。他经常在文字中引用D.H.劳伦书信中的一句话:
我常常觉得,自己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让万能的神的火焰穿过自己的身躯。那是一种相当美妙的感觉。一个人要成为艺术家,必须笃信宗教。
如果说,创造者必须怀着这种虔诚之心,那么作为批评家的读者,也应该怀着这种谦卑的虔诚。“当艺术品进入我们的意识、存在于我们心底的某种东西被点燃,我们接着作出的响应是提炼最初的认知飞跃,将它表达出来”。
斯坦纳指出,处于“谦卑”位置的批评具有“重要”的三个功能:第一、“批评向我们表明什么需要重读,如何重读。……批评要发现并维系那些用特别直接或精确的话语与现实对话的作品”。第二、“沟通”。“在技术交流迅速掩盖了顽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障碍的时代里,批评家可以充当中间人和监护人”。第三、“关注于对同时代文学的判断”。针对第三个对接同时代文学的批评任务或功能,他说:
……显然,批评家对于同时代的艺术有特殊的责任。他不但必须追问,是否代表了技巧的进步和升华,是否使风格更加繁复,是否巧妙地搔到了时代的痛处;他还要追问,对于日益枯竭的道德智慧,同时代艺术的贡献在哪里,或者它带来的耗损在哪里。作品主张用什么尺度来衡量人?这不是一个容易系统阐述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能够用万能的策略对付的问题。……
因此,批评家不仅要和作品对话,还要具备一种对接当下的能力。既要回答审美范畴内的具体问题,又要带有所在时代的审视,正如他这样界定文学体裁之一的小说,“是历史最重要的远亲”。
我们在阅读斯坦纳的文学批评时,能够被其深厚的文艺素养所震撼,又被其充沛饱满的表达热情所吸引,他的很多论述带有对艺术作品的普遍的整体性的精密、准确的把握,令人读起来感到正是对原作“生命感”的重新诠释。例如谈论契诃夫戏剧:
契诃夫的戏剧总是趋向音乐。契诃夫剧作首先并不瞄准冲突或争论的表现,而是试图将某些内心生活的危机具体化,让感觉变得可见。人物在一种可感受语调最轻微转变的氛围中行动。他们就像在磁场中穿行,每一句话、每个手势都能引发精神力量的混乱或重组。……一场契诃夫的对话就是富于感情的嗓音而谱写的一份乐谱。它时而加速,时而减速。音调和音色往往与明确的意思一样富有意义。此外,情节的结构是复调的。数个明确的行动和多种层面的意念在同一个时刻展开。
斯坦纳似乎善用譬喻以“回报”作品带给他的感官体验,在文艺作品面前,他绝不害羞、矜持,而是打开自己,以一种竭诚的姿态,让“作品的火焰,穿过自己的身躯”,希望能够以等量齐观的“虔诚”“补偿”作品,以免令其“陷入沉默”。
一方面,他自己用一种近乎“再创造”的方式解读他所感兴趣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他似乎又对自己的这种文风表现出了某种警惕和反省。他曾经在《F.R.利维斯》(1962)一文中提到专业的批评家应富于“对话”“批判”等人文主义特质。他说,利维斯并不执着于文学史或批评理论而是个案:
他的目标在于遭遇文本的时候,作出完全的反应,保持意识的镇定和勇敢。他前进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注意力格外集中,但也随时修订立场,重新进行价值判断。判断来源于反应,判断并不引起反应。
他认为利维斯有一种“高贵的丑陋”,因为他“拒绝华丽的辞藻,拒绝将批评代替创作”。基于这样的“专注”,斯坦纳甚至接着坦率地说,“在大多数伟大的批评家身上,都有个缺席的作家”,他们将“创造性写作”置入文学批评,而利维斯不在此列。
有意思的是,也曾尝试过文学创作的斯坦纳,是否属于这个“大多数”之列呢?他的文学批评的“判断”是否引起了太多的“反应”?不管怎样,近年,有评论者认为,斯坦纳的小说创作和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关系:当他的批评越来越走向“封闭”和“正统化”之时,小说增补了他的这种“开放”和“谦卑”。
斯坦纳的翻译思想也是建立在这种“谦卑”之上的。他认为,好的读者是“翻译家”,好的翻译家也是好读者,解释和翻译始终如一地贯穿在语言的历时(diachronic)和共时(synchronic)现象中,翻译要经过“信赖、侵入、吸收、补偿”,正是以另一种语言的“阅读”过程。“补偿”是为达到解释的平衡。在《两种翻译》(1961)中,他比较了洛威尔翻译拉辛和菲茨杰拉德翻译《荷马史诗》,认为翻译应当“适度”,“适度是翻译的本质。越伟大的诗人,他对原文的服务态度越忠诚”。他甚至不吝笔墨支持菲茨杰拉德在译文中“补偿”一些文字,只要“增加的东西与原文的内在情感和语调严格保持一致”。可见,他对译者作为“阅读者”的“解释”能力有较高要求。也就是后来不断被斯坦纳的翻译思想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翻译主体性”。那么,问题是,当一个译者不能“全情投入”理解另一语言文本时,退而求其次的亦步亦趋的“硬译”,是否就是一种较差的翻译呢?
基于此,我们正可以把斯坦纳的文学批评和翻译思想结合在一起,当进入文本之后,最重要的是语言背后能够引起共通思想的部分。同一种语言体系中的阅读、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从文学到文化,从文化到哲学,他都抱以一种开放而自信的态度。
很显然,如果硬要说斯坦纳有一种文学批评“理论”的话,那么,它不是一种直接有效的用来“入手”的“理论”。毋宁说,这是一种方法、态度或思想。这种方法(或思想)背后有强大的人文素养和并不因前者的深广而被破坏的主体的直觉天分、表达欲求。因为这种方式带有强烈的“主体性”,所以,它所呈现出来的样貌又是变动不居的。在斯坦纳看来,每一次阅读,哪怕面对的是同一个作品,都会遭到“经典”的同样追问:“你负责任重新想象了吗?”
二、文艺与道德
作为巴黎大屠杀中逃脱的班级里唯有的两个犹太儿童之一,斯坦纳时时在这种“劫后余生”中体会到一种“幸存者”的重负。他总结犹太人的“离散”的宿命,并不在特定的“空间”而在“时间”的“六千年的自我意识”中。他常在文中为沉埋在历史废墟中的犹太人及其他不幸亡魂进行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的批判性反思。作为一个“幸存者”:他有多么幸运,他就有多么急迫肩挑此责。
这种“幸存者”身份,总是和他的文学批评中的道德自觉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他的思考主题常常是,人类文明精髓、包含文学在内的人文遗产本身的现世(人文主义)价值。斯坦纳在30岁之前就开始研究19世纪俄罗斯文学和早期的戏剧经典(古希腊、柏拉图戏剧和莎士比亚戏剧),这在他看来,是人类文学的“三大辉煌阶段”,它们都共同思考着在上帝面前人的尊严。他的第一本专著《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深入地思考了托尔斯泰文学整体的内部的道德力量的一致性。《悲剧之死》中,他说,真正的高悲剧(High Tragedy),就是命运本身,不是“深谙暴力、悲伤和天灾人祸”的东方艺术,也不是“充满暴行和仪式性的死亡”的日本戏剧,它不需要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救赎”“补偿”,体现的是人类在毁灭面前存在的尊严:
这是对人生可怕的、严峻的洞察。然而,正是在人类遭受的过度的苦难中存在着人类对尊严的诉求。一个被逐出城邦的盲乞丐,无能为力、落魄潦倒,却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庄严感。
和犹太文化的探讨相应,斯坦纳甚至从古典悲剧中看到了人类的负重所带来的庄重、决绝与尊严感。人类(观众或读者)只有在这种悲剧面前才能恢复反省。上世纪70年代,针对给新批评带来重大影响的艾略特的文化研究(《有关文化再定义的札记》(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 1948),斯坦纳写了《蓝屋子城堡:有关文化再定义的讨论》(In bluebeard’s Castle
,1978)探索欧洲反犹思想的根源,认为所谓“纳粹”思想是欧洲人对犹太人的“复仇”。他呼吁在新的文化主题下清理纳粹文化。就这样,清除了“宗教幽灵”,他将这种“重负”放在体现在整个欧洲人文成果中的语言、文学、文化、哲学当中去。在经历了大屠杀时代之后,斯坦纳对封闭、一元的东西充满了警惕,正如他自己所说,应该克服那种“自由”必然性中的“强迫”。所以,阻隔人类触及“上帝秘密”的“巴别塔”崩塌之后,人类的尊严还体现在多语言的阐释、翻译的交流的有效性之中(他甚至以亲身经验,指出儿童在多种语言环境下成长的益处)。只有保持永远的乐观、自信的开放态度,人类才可能避免集权的屠戮。
因此,他强调文学阅读、研究、批评中比较的重要性和必然性。面对庞大的多语境下的世界文学遗产,他对在同一种语言文学环境下的文学批评持谨慎和不满足态度。在《利维斯》中,除了对利维斯文学批评中的冷峻而简洁的风格给予赞许之外,他还对其囿于纯粹的英国文学研究表现出了不满。他认为一个好的人文学者或文学批评家应眼界开阔。他觉得英国文学批评的视野应该扩大到英语国家的文学,望向传统和现代,同时看到其他民族国家,例如汉语这门“重要的外部语言”。他说汉语文化是“最古老的文化之一,这种文化由地球上最大民族的能量孕育,许多特性表明它将主宰下一个历史时代”。斯坦纳反对“狭隘的地方主义和逃避现实”,“因为文化中的沙文主义和孤立主义,与政治中的一样,都是自杀性的选择”。
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判,是斯坦纳文艺批评的必然路径。作为一个被文学浸透了肉体和灵魂的犹太人,一个20世纪灾难的“幸存者”,斯坦纳多次进行这样的反省:阅读中体会到的文学中的痛苦,也许比邻人的痛苦更真实。文艺给欧洲精英人士带来的在灾难面前的麻木感也许比带有行动力的责任感更为强烈。由此出发,他开始思考涵盖了文学、哲学、艺术的欧洲文明和集中营、纳粹之间的关系(就像在任何时代动荡和变革面前,罹难者开始清理自己的文化一样)。这种追问和反诘,是当时欧洲知识分子,尤其是更多的犹太“幸存者”如汉娜·阿伦特等人的共同特质。于是,斯坦纳写了一系列反思文章,在西方文化的“除魅”方面做出了不少思考。饱含着这种痛苦和纠结,斯坦纳开始关注大屠杀背景下的文学,并写出带有悼文性质的悲伤的评论文字,甚至有时显得喋喋不休(当然他自己也尝试创作过有关希特勒的戏剧)。我们能够在美国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的神经质的、封闭性的作品后看到斯坦纳的有关大屠杀的联想与引申。基于此,他似乎不满足于文学批评本身。他的文学批评往往包含了从语言到文化、哲学思考,并且使得它们身上带有强烈的伦理色彩。他就曾在他的哲学思考背后认识到了所有的哲学亦是一种文学表达。海德格尔“存在”观念的启示,让他能够重新回到文学表象,人的尊严在于对“存在”的肯定。对“存在”的肯定又意味着对文学的敬畏和思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处理文学背后的哲学或道德命题时放弃了对具体文学作品的文学质素及其记忆的把握。正如他说托尔斯泰,当道德诉求在艺术创造之上,作为相对失败的艺术品如《复活》中的道德因素,有如从天而降的“陨石”,发挥更多的是教育功能。同样带有伦理色彩的,有关对文学和现实的思考中,最为严正的莫过于当时盛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斯坦纳对此依然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他曾撰文对以本雅明、卢卡奇、托洛茨基等为代表的不同向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文艺理论进行深刻反思。
马克思主义批评为传统的历史主义批评带来了重要升华:卢卡奇区分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本雅明洞察到技术和大众化再生产对个体艺术的影响;异化和非人化的概念应用于20世纪文学和绘画。但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为美学贡献了一种规范的历史意识和一种普遍彻底的乐观主义(托尔斯泰的《文学与革命》可为证),而不只是逻辑连贯的认识论。
我们知道,斯坦纳一开始所致力的批评,迥异于当时盛行的“新批评”,但又从“新批评”中吸收养料,他很早就在《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中表达了这一愿望,“全面恢复意识形态语境和历史语境具有的权威,恢复文学创作的实际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权威”,这些论调很容易让斯坦纳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找到对这种宏大视野和内在有机结构分析的某种认同,但同时斯坦纳也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将自己区别于此。例如,他从卢卡奇文学批评思想中看到了其缺陷。那就是,他在处理那些看起来带有“神秘主义”和“超验色彩”的迥异于屠格涅夫或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另一种“现实主义”(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会感到棘手和无奈。
三、“沉默”与未来
斯坦纳这位人文主义者,这位“老派”的文学批评家,不仅像他早期带有追忆和悲情色彩地宣布“悲剧已死”一样,他还多次谈到了“沉默”的重要性。这种“沉默”不仅表现在文学或语言在暴行面前的无力后的反应,还表现为一种古老的来自东方的带有神秘哲学气息的语言学:“大音希声”。斯坦纳还说,既然语言与行动必然要发生关联,那么“沉默”则是另一种带有决绝意味的“行动”。他还举出另外两个更古老的“沉默”先驱:30岁以后的荷尔德林和兰波。当然,这种“沉默”还表现为一种文学质素,斯坦纳在世纪之交乃至现代的文艺中,看到了一种“静默”的典范,例如契诃夫、贝克、梅特林克,都是对时代的回应。更重要的是,面对新的时代,对这位深谙19至20世纪每座文学丰碑的“老牌”批评家来说,寻找经典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困难。斯坦纳带着美好的文学记忆和历史记忆的创伤,流露出对新时代语言环境的不适,流露出对文学语言未来的一种悲观。他认为,真正的文学,尤其是小说,无可置疑地在新的时代面前变得无力,正以加速度消亡。讲故事的人和现代小说家也没有了那种讲述的安静氛围:
每日的新闻,从四面八方砸向我们,将即时传递的震惊影像强加给我们,让我们沉浸于戏剧性的原始感情;这样的效果,任何经典故事都不敢奢望。只有耸人的黄色小说或科幻小说才能够在促销刺激的市场上竞争。想象力已经落后于花哨的极端现实。
斯坦纳认为,过去的“悲剧”依然“超越任何其他体裁,成为形而上学和文学的交汇”逐渐离我们远去。而小说这种世界文学史上曾经辉煌的体裁,“面对动荡廉价的情感”也开始“向内转”,“力求高难度的技巧吸引我们的注意”。这时候小说作为文学的独立性和悲剧一样,逐渐陷入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模糊地带。而在他看来,可视化的艺术正在崛起,这种崛起的典型是“当代戏剧”,当代戏剧可能容纳了多种文艺样式,更顺应时代的是,它身上所具有的“大众色彩”。尽管这一判断可能受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实验戏剧热潮的影响,但“可视化”的判断似乎较为准确,而且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愈演愈烈。在这种悲观心境下,斯坦纳试图重新寻找打破沉默的突破口,将其文学批评趋向新时代。他预言新的小说将不仅仅陷在相对封闭的自恋般的语言之中,它还应包含音乐、哲学、数学等未被“污染”的领域。他甚至带着这种乐观的预设,对新的小说样式尝试进行积极的批评。布洛赫的小说就是这类文体实验的代表。斯坦纳认为,它“打破了德语文体习惯性的重负和凝滞”。但显然,正如“小说的衰落”一样,他的这些批评成果并未能像他早期对自己熟稔的文学丰碑饱含热情的回应那样有力和成功。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斯坦纳这种在新时代面前的总体的悲观和疑惑,在新世纪仍然没有被改变。文学的基础上,他延伸出“文化素养”(Literacy)新解释,他说,未来的科学与艺术的不断结合,让将来的人文教育必然包含“数学、音乐、建筑”。而人文遗产尽管在历史灾难面前没有承担足够的责任,但这种人类的“乐趣”“将与体育、与最为残暴、危言耸听的大众娱乐在共同的尊荣尺度上竞争”。直到2015年,斯坦纳仍然出版了《一种欧洲观》,继续思考着新时代下欧洲文化的去向。也就是说,斯坦纳从未保持沉默。
斯坦纳从语言到文学,再到语言,然后到哲学,再回到文学,实际上都是在书写人为对抗“存在”的“苦恼”而进行的尝试,一种基于“存在”回应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上说,他仍然是一个“谦卑”的读者,一个“谦卑”的写作者。斯坦纳的这种人文主义视野下的文艺批评,恰恰给了在新时期批评高度专业性和碎片化的今天,一种回到作品本身的整体观。在这种整体关照下,每一个读者能够通过阅读直接获得反应。而且,这“反应”不是来自作为批评家或者学者的知识分子,而首先是作为对生活、对文学、对人道及对其关系,保持着高度敏感、警觉和深沉思考的个人。基于此,这种带有高度“尊严”的“谦卑”,不仅仅属于批评家,还属于任何一个普通读者。
平心而论,斯坦纳对作家及独立知识分子的影响可能大过广泛的学院派学者。例如英国作家杰夫·戴尔(Geoff Dyer):《一怒之下:与劳伦斯搏斗》(Out of Sheer Rage: in the shadow of D.H. Lawrence,
1997)就是这样一部践行斯坦纳文艺思想之作。他以谦卑同时平等姿态建立的“文学批评”,同时又是小说或散文,因而能够重新回馈给作为艺术创造者的劳伦斯。杰夫·戴尔在《然而,很美》(But Beautiful: A Book about Jazz
, 1991)中曾引用乔治·斯坦纳的《真实存在》(Real Presences
, 1989):“对艺术的最好解读是艺术”。于是,我们看到了他建立在这些文学、音乐巨擘基础上的文学创造和回馈。不仅仅是文学批评,还包括音乐、美术等其他艺术门类,斯坦纳的这种敞开的态度,给艺术创造者以启示。这不仅在于斯坦纳对创造者给予一种尊敬和共情的态度,还在于斯坦纳的文字中激荡着一种很强的艺术表现力,足以唤起敏感的艺术家新的感动和创造力。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对待“记忆”的方式,引起一种“回忆”的动力,而且这种动力来自于当代,斯坦纳反思道,文学研究不应该是一种“温文尔雅的职业”,不应该是一种“保持中立的人文主义”,他引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不能变成礼物的过去,不值得记忆”。在斯坦纳看来,即便是细部研究,也应该从每个个案背后看到一幅广阔的文学甚至文化、历史、哲学幕布。文学给我们的回馈永远是敞开的“自由”。这使得我们不会被蒙蔽双眼,以至于忙于摆设学术的刀俎,让作品除了被碾碎成“粉末”之外,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