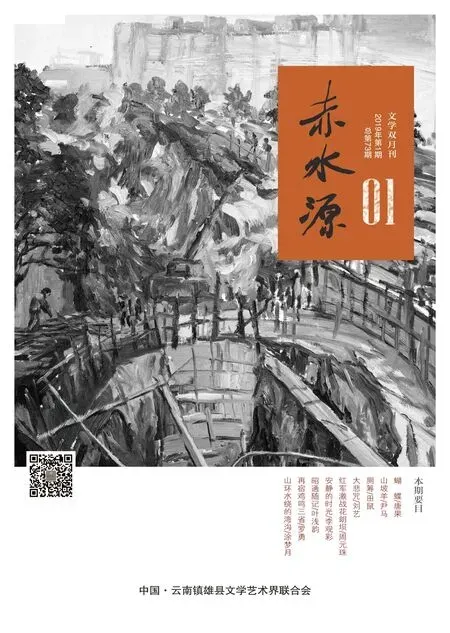安静的时光
散文 李观彩
安静的时光
清晨,鸟声一帘一帘地袭来。也许有的鸟儿是急性子,倏忽之间叽叽叽几下就停了,不晓得它要表达什么。这样的声音常在我心底留下疑问,它是飞走了呢还是低头觅食?正当你情思悠长、天马行空之时,它又出声音了,瞬间拉你回至林间而随着心旌摇动。有的鸟鸣叫起来就情谊绵长得多了,我凝神细数,它竟是不断气息地发出一段九字长音。我学着它来一调,也只有自讪而已,它的肺活量和音韵极佳,我这五音不全者是真不能及的。你绝想不到它那小小的身板下藏着的会是怎样喷薄的力量。称它为“歌唱家”吧,可能会碍了它的悠闲,称它为“韵律家”吧,可能会破了它的随性。你竟不知道了,它只是林间一个精灵,自在地婉转吟唱,任眼波流动,任清风拂体,任夜露微晞……此时,我的心是柔的,一怀慈悲。似有身披袈裟的老方丈赐我偈语,而它,无意之间成了送语的小童僧,逶迤而来,圆满而去。
林间鸟不多,从声音判断,它们各栖一枝,相隔不远。你一声我一语的应和而响,像是拉家常也像是自抒才情。你知道我捕了几只虫子,我晓得你几时初睡。这令我想起了在乡下生活的那些时光,邻里之间,每天都要见上好几回,我们就站在走廊上闲聊,眼前有白崖,崖上有田畴亩种,崖下有细波轻流。有时在月夜,有时在雨中,有时光影极好。我们常常搬把藤椅坐着聊,只见崖上人家的灯火、炊烟、房屋,一切都是静的,我们的心也是静的,只有嘴在呓语,不知都说了些什么。面对山崖,我常常一个人独坐,崖仍是白的,树仍是长的。绵绵的山脊横着走,向左右延长、再延长。长的尽头有时是白雾,有时是霞光,根本没觉得是深渊是不可测的魔魇。我的思绪常在那里游荡,万千不明所以的东西就在这时诞生了,比如想象,比如胸怀,比如眼界……现在想来,我的不懂人情不善言谈也跟这段时光有很大的关系。
那时,我家楼下住着老校长。他行止优雅,情思高蹈。一天黄昏,他从楼门口吟着诗句向我走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此时的落日圆圆的、红红的,远山一片暮蔼,一切却又清晰可辨。我脱口说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老校长说,来,我们一起托住它。他伸出右手,一点一点地调整手心与太阳的角度,他侧身斜眯着眼,陶陶然的样子。夕阳有时像静止的图画,有时又像急速下落的圆球。它终归去了,去迎接黎明。老校长回我,知道“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是谁的句子不?然后离去,独我一人留至深夜思索着时光。
乡间生活的日子是愉快而灵动的。登高望远,入林觅果,下河摸鱼。采野草山花编花环,捋流云霞光做霓裳,细雨来了当丝条,清风来了如故人……陶渊明曾自我发诘“问君何能尔”,也曾自我作答“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我即如此,自得其乐,不觉时光流失,人至中年。
如今幸也!窗下绿草离离,修木渐长,鸟雀常驻。虽说望不及远,但有鸟鸣啼耳,绿阴润目,也是极其好的事情。谁说过“人作为一个物种,在融入大自然的时候,会本能地感觉心情愉悦”,如此,隐得一份童真,又复何求?鸟声又起,此时,它们正集体吟和,宇宙光明万丈,一片热闹。
周末暇语
1
大周末的,正午3 点,阳光毒得辣眼睛,会议室里空气潮热,股股烦闷直涌各种感官,挑战各位同仁。大家互递眼色以显其躁意。小声嘀咕的同时,肚中的腹诽似乎也快喷薄而出。人肚子藏在桌肚子内侧,只能看到它每一次深呼吸的凹凸与间隙。可是有人在脸上绽开鲜花,有人的语调极为悦耳,有人的眼神流露崇敬……我用耳朵认真聆听,竟同时地想起一个俗段子:A 是玩具工厂的劳模,是车间的标兵,做工又快又好,尤其装B 的时侯。这样的幽默真是简明扼要,看来,人类自嘲的智慧还真不是天生的,有什么样的场景就会诞生什么样的业界精英!
2
散会时,刮来一阵凉风。疾步走出会议室的各位皆神色匆忙,有人要奔赴菜市场,有人要辗转于超市,有人要去培训班接孩子回家,有人渐渐地放慢脚步,有人的眼神四处打量,有人伸胳膊踢腿,有人长舒郁气释放重量……要是不散会,大家都只有一个主题,是不是就不用诸般匆忙。事,总得有人做,就看在这个时间的节点上,你,有空没!
3
每天都围着工作转,不转不行,不转,更不能体会山野的生趣和时光流转。有友邀约去不远的山间游逛,才蓦然惊觉,樱桃早已过市,李子正在成长,枝柯已茂,绿阴恰浓。风像稚气未脱的孩童,轻牵裙裾,乱撩发丝,青山、高云、房屋、藤架、笑语……一切柔情得刚刚好。我们往高处走,把城市的车水马龙放在背包之外。走走停停,芫荽花散发的迷香,像飘逸的风衣;看青果身上的绒毛,细致得泛出亮光;去沟垄间看洋芋花花,鹅黄的粉蕊点染在它薄透的花瓣上。绿如排笔铺就的长毯,只敢奢求在上面小憩一觉,又怕压坏了它,此时,最该化成一只蝶,亦或一滴露,如此,方不负此行。
4
说到不虚此行,该讲讲那天去泼机赏麦之因果。微群中一好摄之人之一图:白云高天,黄麦阔地、农人勤作、孩童闲手。此图惹得我心痒难当,急欲赴之。幸得周六午后,我与某人驱车赶往。却不料,车行半途,狂雨猛至。我这心,瞬间体会到何为“凉凉”。回来,去净美屋,与小朱聊黄麦灿灿、青麦莹莹。哪知,和这小妞言语契合,我们互展想象,极端地挑战视觉之各路神经以及吃货之万千味蕾。妞说,如有粒粒青麦混炒肉沬……更恨时不成行,怨天不作美。其实,我真的是想去做个割麦人:体会一季庄稼生长的不易,体会镰刀的光影在丰收的喜悦中游弋,想更真切地感知水到渠成的沉稳。就算播种者啥都不跟我说,我也愿意。突然就想起木心先生语:上帝不掷骰子,大自然从来不说一句俏皮话。也许,这才是洪荒宇宙的本来面目吧。在浮躁虚空的时间里混久了,在急功近利的肆铺中熏染了,我,更多地渴望着安静。
人生于世,与草木春秋有何异!岁月短长,时令节气,该怎样长还得怎样长,没有谁的取舍一直赢利,也没有谁的坎坷一直败北。时光能给人的,从来都只是生或者死,并无第三选项。有人在艰难中熬过来了就继续艰难,熬不过来的也就脱离苦海,有人在胜利中挥师前进了又怎知总是一路凯歌?于此而言,说到人的存世。我只知我存于世,不欺心,不罔昩,不张扬夸行也不畏缩垢病。今日小满,说至此话题,似冥神安排。二十四节气中,有大寒小寒,有大雪小雪,有小满却无大满。大者,盛矣,盛极必衰。既大且满,还不早早衰亡?古有杨修,聪明机谨而外显,终因鸡胁泄了天机而消亡。万事不宜大满,这是古人处世之智慧。“谦受益,满招损”,“天道忌满,人道忌全”……小满之时,寒气已退,暑气未至,和风惠畅,绿阴犹长,天地万物,欣然生长渐趋成熟。一切谦逊得不畏缩,骄傲得知进取。如果说立夏是加冠的男孩,明朗而蓬勃;那小满就是及笄的女孩,明丽且温柔。我愿以这样一颗心,期许年华。
5
那日问花花:要是穿越到宋,三千后宫来选后,谁矣?
一向爽朗的花花害羞得只管笑,这家伙,似乎只懂爱情。既说挑,当称自家心意。
文哥是最好的谏言师,说,当然选苏轼,理由:苏轼是“暖男”。还说林语堂先生也曾夸奖苏同学有蟒蛇的智慧和鸽子的温柔敦厚。从这点上说,花花的柔情与才学也相应的有了安放之所。绝配!
我也想,苏同学更是个有情趣又机敏的人,一句“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其幽默善解之玲珑及纵横捭阖之眼界,也足可令后宫安稳。再则,苏同学一贯初心不改,少年永存。不光调侃自己“去年一滴相思泪,今年犹未到腮边”,还调侃老友“一树梨花压海棠”,还会给朋友起歪号。其才情、人情、风情也是花花之专长。
按情侣间的“共生”法则,就他了,花花。
突然感觉,这就干成了包办婚姻。其实,当皇帝也不是什么乐事。
6
翻看旧照片。
那些年,光阴还没有老。每个人都像极了树上的嫩枝,一天一个新模样,努力的向四周伸展生长。我们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把读书当成了业余。爬山坡、卧草窼、戏温泉、逐清风……觉得自然是个欣欣的世界,它和我们的脉膊一起跳动;夜观流星来丈量天际,高谈阔论以彰显情怀,常看电影而体会酸甜……我们以为生活是恣情逍遥的,白天玩,晚上玩,一帮一伙的玩,听鸟鸣溪响于山林,看白骨坟坑于荒野,闻野花腐木于深丛。我们登山不怕腿软,闲聊不惧口渴,吵闹不避他人……那时候,可以在短时间内去同一个地方很多回,天气不同去一次,心情不同去一次,意见不同去一次,每一次回来都感觉力量不同了,认识不同了,笑颜不同了。我们学着成长,学着交往,学着成熟,像一棵桃树一样历经时间的安排,该开花就开花了,该结果就结果了,该长大也就长大了。
长大并不是一件值得欢欣的事,桃李熟透了就落在地上任蚂蚁搬食,偶或还会被地上的尖石块刺破而流出殷红的汁液;茂草熟了就籽落杆垮,偶或野火焚烧而化为黑灰。有谁又能想到生命的稚嫩与鲜活?世道还不是要用一双世俗的眼看你的而今!人长大了还不是一样。这就是“套路”。所谓的“套路”绝对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日月沧桑喂养的一只怪兽。它舔人间之温暖,它食本我之真心,它饮爱情之蜜意,它行走在人们一行一行的泪路之上且路数娴熟。人们在“套路”的世界里深陷泥沼,颠扑挣扎。好在,你扑倒时我已站起,我扑倒时你方喘气,我们帮扶而行,相互取暖。大家都成了战士,只愿盔甲完整,金创药极佳。而它,却不断地把自己锻炼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妖魔!真不知有哪个真人何时横空出世,用大瓶封了这孽障的黑烟。
依然一笑作春温
她说“好累”的时候,声音也跟着累,听着就不忍再让她累下去了。想舒开她紧皱的眉,想抹去她暗沉的色。
累,是许多事的重叠,是重叠之事在同一时间内无法共融的伤怀。我习惯在累的时候抓重放轻,因为人没有三头六臂。实在无法承受之重时,不如放开它,好好睡大觉,或另辟蹊径而化解。跟“累”打持久战,人必定败得体无完肤。战斗中的痂疤也会长期提醒那曾经的过往,让你重温“累”的时光。
她爱说“好在过了”。是啊,那时那事,总是属于过去的。她笑着说的时候,像历劫重生的凤凰。有时我在想:“劫”有大小有生死。只要不是后者,何苦那么为难自己。经历那么多,难道还不足以“往”为鉴。何苦逢“累”就颓丧之气日盛。苏轼说“依然一笑作春温”,是阅历,是智慧,是胸怀,是气度。
我喜欢苏轼。在《论古诗人困顿落魄的形与义》一文中,他是困顿落魄的终极者。他融儒道释为一炉,于中自由进出,积极入世的同时不忘安抚自己的内心。往大了说,他是一座不可企及的高峰,往小了说,他是陪你漫坐长夜的摆渡人。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身披盔甲的战士。鲁迅先生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他说的是那些文过饰非、愚昧盲动的军阀政府。而市井生活之中,哪里又没有些明火执杖、暗渡陈仓之类的人呢,其所作所为只有自己想不到,没有渣人做不到的。在“人”的世界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让别人都少受伤害。写了这句,突然发现自已善良得傻气。又因为这份傻气,就常被流弹所伤。可我仍愿意“一笑作春温”。
愿你我安好,愿世界安好。
车流声里谈皈依
在房间里听隆隆的车流声,它时而尖利时而轰鸣,开车人的心绪是不一样的。渴望疾驰向前、渴望破除桎锢、渴望一帆风顺……车流声里的渴望太多。这些渴望浮在城市的腹地,无法张开想象的翅膀,只能在亦步亦趋的同时显露自己的个性,就越来越把自己活成一张张哀怒的脸。这些脸上有得意有不平,有太阳难以照亮的暗,也有细雨不易洗去的尘。
讨厌滚滚的车轮,亦如讨厌唾沫横飞的演说;讨厌嘟嘟的喇叭声,亦如讨厌在血肉间行走的手术刀;讨厌突突的发动声,亦如讨厌西洋调调的交响曲……其实,我不光讨厌有关车的一切,我还讨厌我自己。我,无数的我,在无数的时刻,缩在车里,微闭了一双眼,任汽油点燃我的梦想。这时,我讨厌的一切都变成了助推器,要么载我拓疆开土要么载我驶向毁亡。于是,我苦闷着晕车,我艰涩地微笑。我戴着似笑非笑的面具看穿一场场的悲欢离合和荣辱得失。
生活应该是山间的一辆慢火车,它不应该行至平地,更不要说来到都市了。一切乘上时间之轨的快车,渐渐地就丢掉了柴火、厥菜、清流、鸟鸣和树阴,渐渐地就丢掉了冷暖、心意、酣眠、清澈和宁静……慢慢地,只剩下一双双惶惑的眼在日夜觅拾,却无所找寻;只留得一张张无表情的脸涂满粉底,却无处绽颜。我们都语调平缓的同时心神狂乱、互相猜忖。心烦之时,慌张之时,得意之时,车,成了避难所,成了发泄地。在这个窄小的空间里,人,方才有点思想!
所有的“狂飚”都只为“减速”,所有的“尖利”都只为“清脆”,所有的“轰鸣”都只为“宁静”……祈盼所有驶向郊外的车,都能如愿回归!
二叔
这应该是我第三次写到二叔。第一次是在我初中二年级时的作文竞赛场上,题目是“记一个平凡的人”,二叔的形象一下子就从脑海中蹦出来。现在想来,二叔是有特点的人,要不然,他不会如此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第二次写二叔,是在他去世后两天,他似乎仍活着从没离开过我。现在,距离那悲伤的一天已过去了八年,他虽身化鹤归,却仍是我最亲爱的二叔。
二叔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我的印象中,二叔从没穿过一件光洁的衣服。他的衣服上,不是补丁就是泥点。爸爸曾送衣服给他,可二叔不是嫌衣服新了就是嫌布料好了,后来直接说:你给一件旧衣服,我还要开心点。二叔总在地里劳动,忙得没时间让一件新衣服与土坷磨合。他从地里回来,就忙着洗头、擦汗、洗衣服。为此,他没少挨我二婶的白眼甚至数落。那时,家里吃水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要去半坡才有一水井,泉眼极小,人多时,要等好久。二婶惜水却极少去挑水,都是二叔,他总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去挑,那时几乎没人,一去就回。好多个深夜,二叔会往我家缸里装水。水入缸时的哗声,总令我幸福而踏实,转而又沉入梦乡。
二叔是爱我的。我从小寡言又孱弱,他就总把我带在身边,这让小我一岁的堂妹很不开心。这样的次数多了,堂妹也似乎觉得她是该走路的,我是该上背的。只记得一次,堂妹说脚痛,站着不走只光哭。那哭声真是大啊,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还常在我耳边回响。二叔把我和她都背在背上,一人一半。平时宽大无边的背脊此时也并不显得拥挤。二叔说我们是两只小蚂蚁。两姊妹趴在背上,互相望着,都不说话。二叔的喘息声,双脚摩地的声音,山林野虫声,一一响起,所谓美好,也就是这样吧。我们偶尔去老远的地方看场露天电影,二叔背我来去,堂妹就没这个待遇了。看电影时,就轮换骑在他肩上看,地上的一个就紧紧拽着二叔的衣角。回家途中就谈电影,两姊妹就你讲一段我讲一段,如此串联起来,电影才完整。二叔会笑我们,但从不用心地纠正我们的错误。他一笑,我们也跟着笑。此时,山月溶溶,树影婆娑。走得累了,歇下来,我们一左一右靠在他的腿上,时而言语,时而傻笑,只见眼波晶莹,四溢流转。
二叔不光喜欢劳动,还特别地喜欢读书。他从地里回来,收拾停当,就看《小五义》、《隋唐英雄传》、《聊斋志异》……邻里若有红白喜事时,大家聚在一起帮忙,二叔就一定是“总管”,他会读会写会说。闲暇时,他就讲故事跟大家听。故事中的侠义、奇异、人情、风物,是我们那贫穷的小山村所没有的,但又似乎就发生在大家的村子里。故事中的美丑、善恶,在大家的应和声中得到理解和包容,善良的村民们用如水的清澈、如泥的宽厚来看待外物的风云诡谲。他们的言谈里从没有鸡鸣狗盗,没有尔虞我诈。后来,我离乡出走,自是染了许多“恶习”:会抱怨、会隐藏、会自私,会挑剔,会出恶言……每当我要回到那小村庄时,越接近越胆怯。至后来,村庄离我越来越陌生。再去,也只为埋于泥土的我的奶奶、我的母亲、我的二叔。他们,留在我记忆的最深处,从不敢用心地去怀念,我怕思念如锤,砸得我全身生疼。
我的二叔,苦命劳作了一辈子,终而回归他热爱的土地。那年写下的几行小字,再贴于此,用以怀念我的二叔。
叔叔,
我在众人之间听到你告别的声音
撒架的钢筋铁骨没有声响
是一张纸迅速盖上
叔叔,纸上面写满了
你忠厚良善的秉性
我读着心痛地笑着
为叔叔您送行
茫然的目光已经穿过丛林
晃过了山谷河川
以至遥远的天幕
那里有芬芳的野花整齐的田畴
翩飞着长羽翼的七色鸟
葱茂的柏树结满了晶莹的脂球
还有你喜欢的泥尘蓑衣几卷油书
我看见你轻盈的去一路青草相迎
而我对你的真正的思念
才刚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