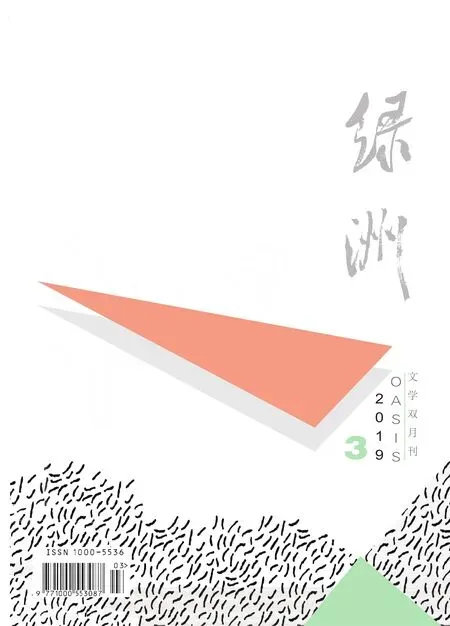群蜂飞舞
——“临沂诗群”的酝酿和勃兴
每个城市,都是一个能量体。
每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小至方寸一室,大至村镇省城,因为有了“人”的存在,便由纯粹的物理空间转升为具备某一特殊精神气质的文化单元。从诗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为世界命名”的程序。——“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刘禹锡敏锐地发现“陋室”这个半公共空间,在两种对话语境中(鸿儒/白丁)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意义。相对于陋室而言,承载1124万人生息繁衍的临沂城在现代语境中的辗转腾挪更为复杂。这个地理空间在最近二十年迎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对话:沂州古城数千年承续下来的古东夷—郯—莒—费—兰陵—琅琊文化、魏晋风度、红色沂蒙精神诸元素,在“南义乌北临沂”急管繁弦般的游商漩涡中不断坍塌、融化、重组。如同波德莱尔漫游其间的幼年版现代巴黎所经历的,骤然加速的现代化进程给这个城市镀上了一层令人目眩神昏的“光晕”。只要它尚未完全被现代城市模板所宰制,其文化身份就始终处于一种未定状态:多义、杂糅、变幻。这种特殊的身份以及它所带来的焦虑感,酝酿出一眼喷薄而出的盛大诗泉。
从临沂的诗歌写作现场来看,写作者内在的能量激发体主要是诗人对自身身份的困惑。这种强烈的困惑感如此坚硬,以至于很难被其它文学形式所消化,只能凝结成一团沉郁的诗情。与其说他们选择了诗,倒不如说诗选择了他们,——这群被困惑所鞭打的敏感者,犹如一群野蜂,毫无退路地飞进诗语的旷野。
2006年《我们柒》诗集丛书的出版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在这套丛书的序言里,江非如此介绍他们结集的初衷:“怀着共同的诗歌理想,走在不同的诗歌道路上”。由此,江非、邰筐、轩辕轼轲、刘瑜、白玛、朱庆和、辰水以及将随后出版诗集的郁笛、蓝野、王黎明、芦苇泉、瓦刀、曹国英、尤克利、子敬、也果、苍城子、陈建新、苍鹭、田暖、孙梧、渠志国、聂松泽、赵国际、李洪光、老四等诗人,迅速形成中国诗坛上令人瞩目的诗群方阵。这个野生的诗群,并不依赖某一条精神谱系来凝聚,联结他们的仅仅是“临沂城”这个抒情的块茎。艺术家,固然就像布罗茨基所宣称的,各自拥有“表情独特的脸庞”:“如果艺术能教会一个人什么东西(首先是教会一位艺术家),那便是人之存在的孤独性”。但就在这次演讲中,布罗茨基详细列举了他的艺术生命与彼得堡附近五位诗人的特殊关系。临沂诗群的酝酿和勃兴也是如此,诗人彼此亲密而紧张的倾诉和对话,缓慢地建立了一份既宽博又扎实的诗歌理想草案。
这份草案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江非的诗学提纲。江非尝试将风雅颂的抒情传统与西方深度隐喻系统进行融合,恢复诗对世界的干预能力。在他著名的《劈柴的人还在劈柴》一诗中,诗人如此回忆那场成人礼:“我已忘记了这是哪一年冬天的情景/那时我是一个旁观者/我站在边上看着那个人劈柴的姿势/有时会小声地喊他一声父亲/他听见了/会抬起头冲我笑笑/然后继续劈柴”,后置叙述为这首诗赋予了神启的气氛,让年轻的“我”预感到“第二天/所有的新柴/都将被大雪覆盖”。诗人和原乡之间的紧张内化为一种诗意的焦虑,促使他一次次重新回到这个原始场景:“劈柴的时候,我没有像父亲那样/咬紧牙关/全身地扑下去,呼气”,而选择“轻轻地把镐头伸进去/像伸进一条时光的缝隙/再深入一些/碰到了时光的峭壁”(《花椒木》)。“劈开”这个动词,是一个与他“平墩湖”院落旁杨树林相关的实用动词,又是一个由海子赋予了精神深度的动词。在当下的诗歌语境中,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反抒情的拧转,一种写作上的奋不顾身。江非的诗习惯于在重复中凸显思想的顿挫,——一种结结巴巴的愤怒,一团正在形成的困惑,给他的语言带来了一种沉郁之美。
由此,我们可能会联想起希尼善于使用的那个动词:“挖掘”。相比“劈柴”,“挖掘”是一个缓解性的动词,带着更多追忆性的抒情调子,将对自身身份的困惑转移为对父辈乡土生活的沉思。这就是辰水的诗:挖掘泥土的锨,也挖掘泥土下的灵魂;在梦中见证祖父的悲欣、与墓中的父对话,最终证实自己作为“祖父的偏旁”的那一部分。对于辰水来说,世界是“一个倒置的大海”,而他以笔为锨,日夜“敲击”着这扇晦暗的大门。
选择文学史的纵向角度对这个块茎进行流派式的切片分析几乎是无效的,有必要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对纵线条的“文学编年史”结构予以解构,将写作者与原乡的关系编织到诗人与原生空间、漫游空间、想像空间,甚至私人空间和共同空间的复杂关系中,祛除历史阐释模式对诗和诗人的钳制和凌驾。
同样面对这块土地,远居新疆的诗人郁笛善于在缓行的步履中将乡愁压进坚劲的线条,于沉静的节奏中不经意地爆发蓄积的力量,——人直面大地的沉思和领悟:“在万物之上,无限的尘土乘着阳光的翅膀/扑面而来。这就是你的降生之地,在尘土的故乡/树木们顺从了一粒沙,在田野上安睡”。乡愁被称为尖锐的情歌,诗人别出蹊径,巧妙地将遥远的物理距离转喻为时间的乡愁:“这些饱满,还是坚硬的褶皱里,停留着一枚核桃墨玉般的光泽/就像你多年前探望过的,一位乡下的旧眷”,沉静的海面下万籁俱寂,唯有冰峰耸立。
长期生活在家乡沂南的诗人尤克利则具备另一种美学的自觉:他天才地揭示了乡土潜藏的巨大能量,“我猜想大地在春天奔跑时是一部发动机/有火花在身体里骤然开放/……/我猜想一旦给春天起一个火花塞的名字/它的马达会转得更欢,它就会更像一台/不知乏困的大机器”。朴素有力的修辞力量与其承载的物象的生命力生成一种愈来愈紧密的共振,大地的伟力与蒸腾的诗情在这个瞬间奇妙地完成了统一。
天马行空的轩辕轼轲吝于长篇大论的理论阐释,他以惊人的年均近千首的写作速度将组诗写作推升为一团一团巨大无比的“组诗云”,书写了另一体式的诗学提纲。轩辕轼轲对诗仙太白的形象情有独钟,——这是一个几乎完全超越了现实的诗人形象,即使放置在世界文学的空间里都极为夸张充盈。无论从哪个诗歌流派来看,轩辕轼轲的诗歌写作方式都显得非常极端。其著名的长诗《广陵散》《临沂城又逢江非》诸篇什中,诗人以发濡墨、尽情挥洒,笔下万物奔腾、收纵自如,完全进入了超现实的白热状态。在他信手拈来的短诗中,诗人轻松摆脱现实身份的及物性,获得纵身天外的轻盈之感:“我干得最得意的/一件事是/藏起了一个大海/直到海洋局的人/在门外疯狂地敲门/我还吹着口哨/吹着海风/在壁橱旁/用剪刀剪掉/多余的浪花”,奇幻的想像与现实稍有指涉即跳荡开去,挥发出神秘而魔幻的气息。作为“下半身写作”的中坚,轩辕轼轲却并不纯然是身体性的写作者。关乎现实“事象”的日常诗章,他基本上都是在进行二度创作。与轩辕轼轲一起创办民刊《中间》的诗人朱庆和长居南京,他的诗以思想的朴素和坚实见长,诗句峻拔劲健,自然流露出清癯之美。尤其是短诗《苜蓿》,被其老友韩东盛赞为“宗教式的”,“它不可能属于朱庆和,但它又是属于朱庆和的,属于写出它来的那个幸福时刻”。
刘瑜身兼诗人与观念艺术家,二者的混合给予他双重的困惑:既是对自身身份的困惑,又是对世界谜团的困惑。对于外部世界,他有一个极具深度的乌托邦构想。这个乌托邦富含某种理性的力量,使他的诗行天然地具备一种重压的质感:“阳光甚好,新植的明日草开始拔节/书页中一场大雨占用了太多描述/包括雾气、深渊与整个世界的反面”(《九月的书页》)。诗人的写作源自于他双重的愤怒和怒意的突围:对凡庸者的斥责、关于自身的自我搏斗。令人击节的是,刘瑜极善于精准地控制这种古典诗情的释放,“对一本书而言,注定有几处败笔/我因孱弱而梦想着——/那些被抛于荒野的情绪,归于日常”,犹如王铎的草书,于迅疾中顿挫,在矛盾间获取自我对话的智慧和平衡。
本雅明将现代诗人定义为“游手好闲者”。这是一个天才的定义。诗人与现实的疏离感不再是贬义的,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原动力。他们被迫成为现代程序化进程的“旁观者”,这一角色不仅意味着诗人获得了摄影师似的客观取景视角,同时也赢取了一份与时代错位而被抛离的孤独感。在现代都市的元场景:巴黎街道上,本雅明发现了真正理解都市现代性的人是其间的“漫游者”:诗人、出租车司机、妓女……这些人是邰筐代表诗作《凌晨三点的歌谣》中的主人公,“他们最后都要在一张餐桌上碰面”,吞咽迟到的晚餐,“然后各付各钱,各自走散/只剩下一张空桌子,陷入了黎明前最后的黑暗”。漫游者随意游走于街巷,城市乐意为这种漫无目的的行动敞开,他们因此大量获取偶然性的城市经验,在这些碎片中窥见了都市的中心秘密:它是一个虚空,一个非实体,一个搅动盲动、想像和欲望的强大的在场,一个意义的黑洞。它不仅吞噬了设计者最初对它的定义,更吞噬了人类传统上对个人精神生活的构想,甚至最终吞噬所有跻身其间者关于意义的确认感。分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分裂的角度和力度。将邰筐定义为城市诗人,多少低估了他诗作的分量。我不相信现代文明是不可言说的。如果不可言说,那就意味着它不可穿透。邰筐长居北京之后,诗作中常流露出对身份的新的发现和新的困惑。也许诗人与环境的融合,永远是一个伪命题、一种理想状态。这种遥远的困惑可以直接追溯到陶渊明。
如果我们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定义为出世和入世的二分法,那么我们对于自身的解放将永远是徒劳的。关于这一点,瓦刀在他的诗歌中进行了充分的思考。他发现他的身份就如身边任意一个人的身份一样,是一个永恒的复合体:“一个上半生无所事事,/下半生写过几首烂诗的人;/一个图谋不轨,/包藏诗人野心的反对未遂者。”诗人觉察到父辈、甚至更遥远的先祖们,也是某种复合体;只是他们自身未曾察觉。
从波德莱尔开始,我们生而游荡,因此我们的降生就隐喻了随后即将发生的一切,一系列关乎异乡的叙事。这是现代生活的原型;脱离母体、在大地上毫无指望地游荡,是这个原型自然而然的展开。“我生来如此生来就是你的情人/厌倦了孤旅 写字 通心菜的晚餐/我是你身后穿素衣的沉睡的女人/难以逃过一个梦见羚羊的雨夜”(白玛《雨夜》)。也许,孤独的漫游缓慢地改造着我们自身。但这个过程却是颠倒的,我们经验的外部逐渐澄明,而对于我们自身命运的领悟却最终成为最深的黑暗。早慧的女诗人写了太多的诗篇,她踏着自己铺就的阶梯一步步远离了多氧的平原。海拔愈来愈高,同行者愈加稀少,对话的声音便完全消失了,使她不能不发展出富有穿透力的咏叹的歌喉:“写一首诗给传说中的海妖和她颈间的花环/再写一首给贫穷的木匠和他做针线活的哑巴女人/再写一首给孩子的伙伴大灰狼和狒狒/写一首给丛生的杂草和灌木,给柿子树和榆树/如果我活得更久,就写一首诗向某个人示爱……(《写一首诗》),博喻召唤出他们,并在吟唱中完成了“元诗”的凝合。指向灵魂的写作,几乎是一份神赐的痛苦,饱含恩宠的苦涩。“那我就不写啦。只想在欢笑和快乐的时候写一首诗/给稍纵即逝的美、给向着土地鞠躬的身体/写一首给燕子,艳羡它那精心裁剪的晚礼服/写一首给乡下的水牛和放牛老汉/如果我目光不再短浅/就会写一首给激动不已的火车,写一首给出海的水手/必要时我会写一写我的少年/幸福和痛苦穿插其中;我想写一首给众多早逝的人/他们在天上飞来飞去,能否收到我的诗?/他们在天堂里吹着口哨奔跑,含着泪互相拥抱/我想写一首诗说说生命和死亡,还有那捉摸不定的爱情”(《写一首诗》)。对于中国白话新诗,白玛带有古典色彩的诗歌体式是一份丰厚的馈赠,同时又是一个响亮的启示:歌咏能将语言带到一个极为丰富多义的境界,它所蕴含的精神力量相较于瑞恰兹式的隐喻系统毫不逊色。
对于女性而言,歌唱是重要的。她们无法解释自身的美。在传统的抒情文本中,女性的美有赖于男性的揭示和爱慕。美,天然地偏爱女性,也成为了她们自身的桎梏。吊诡之处就在于此,——女性很难深入地书写自身,并非因为外在道德的钳制,而是因为这种书写一向被阐释为顾影自恋、毫无意义。在男性主导的文学史中,他们自证其美,又反对女性自证其美。而对于自身的美,必须由女性自己来发现、揭示和证明,子敬(《一个女人极简主义》)、也果(《变压器》)和零夕(《信仰》)正是在这一空间彰显出诗对于女性建构自身的意义。
对于古老的临沂城来说,临沂大学崭新得如同天外来客。从这所新型学府里,正涌现一批年轻的诗歌面容,他们的诗坦率、清新:“想摆张摇椅在阳台/不是说说而已/这些年晕车、晕蓝光/偶尔也晕一只炎夏的飞虫/和小男孩尖叫的声音”(王晖《小小幻想家》)。成年人所忧惧的学院派诗歌批评与诗歌写作实践的对立,在他们这里似乎并不存在。外国诗与本土诗,阅读、批评与写作实践,成为年轻人体验、感悟世界的天然元素:“青春是口是心非的少女/一只手捂住嘴巴/另一只手写下难言的笔画/“丿丶乛……”重复的、省略的,破碎的,一笔一画。我呀——”(王晖《海盐味的象声词》),即使书写自己的履历,她的诗行也带有某种智慧的调侃,一种并不世故的轻逸。回想北岛的《履历》、于坚的《零档案》,歌哭与超脱已经是老年人的词汇。青年诗人们的明朗与轻松,对于沉重的汉语诗写作,或许是一份恰当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