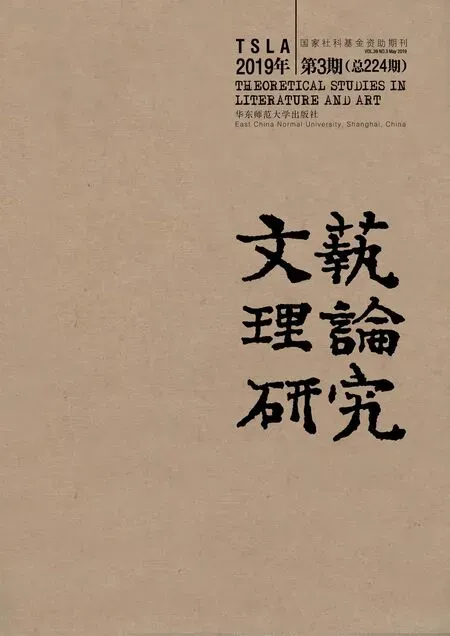先秦文论元典之“人”义重释
李建中
据统计,《全唐诗》收录诗作48,900余首,出现频率最高的字是“人”:共出现39,195次。汉字的六书,象形为首;象形字之中,“人”字为要。姜亮夫指出:“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姜亮夫 68)今天所能见到的甲骨文,表人的占五分之一以上。从殷商甲骨文到唐代诗歌,中国文化及文学之重“人”是有目共睹的。问题是,汉语文化及文学的“人”,其“义”何在?其“言”何在?其“命”又何在?这些问题,在古典时期已因三教分殊、诸子杂陈而其异如面。五四之后,由于西学东渐尤其是人本主义思潮的进入,使得汉语的“人”面目不清:其“义”歧出,其“言”悖立,其“命”乖谬。西方近现代哲学,从尼采的“上帝之死”到福柯的“人之死”,在消解先验主体论传统的同时企图否定自轴心期以来的人学传统。因此,如何拨开历史与现实的迷雾,返回语义现场,重新发现“人”,似为当下之要务,学术之使命。
一、“人”义多“方”
卡西尔(1874—1945年)《人论》在谈到学界关于“人”的定义歧出时指出:“我们近代关于人的理论失去了它的理论中心。我们所得到的只是思想的完全无政府状态。[……]一个可为人求助的公认的权威不再存在了。神学家,科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人种学家,经济学家们都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著作家个人的气质开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欲望人人有之,每一位作者似乎归根到底都是被他自己关于人类生活的概念和评价所引导的。”(卡西尔 18)在卡西尔看来,关于“人”的定义之所以歧义百出,一是因为学科化,二是因为个人化:二者合起来酿成同一个结果:不同学科的“人”或不同气质的“人”或不同学科(气质)的“人”互不通气,各自得出关于“人”的不同界定和阐释。卡西尔《人论》出版于1944年,讲的是近现代关于“人”的定义。实际上,“人”之定义歧出,早在轴心时代就开始了。
轴心时代的柏拉图在讨论“美”之定义时曾感叹:美是难的。关于“人”,我们可以说同样的话。从逻辑上讲,“人”之定义的困难在于这一“定义行为”(或曰“阐释行为”)所必然具有的悖论性质,颇似罗素那个家喻户晓的“理发师悖论”。人给自己下定义,有点像理发师给自己理发。当然,理发师可以为自己理发,人也可以为自己下定义。问题是,当“人”(作为阐释主体)为“人”(作为阐释对象)下定义时,“人”的因素会影响到定义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准确性。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在感叹“知音其难”时,列举了“知音者”常犯的三种错误:文人相亲,贵远(古)贱近(今),信伪迷真。刘勰谈的是文学阐释,我以为也适用于“人”的阐释。“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结果自然是“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范文澜 714)。
刘勰这里所讲的“会己”和“异我”,大体上属于个人气质性格或者胸襟识见等主体性缘由;而“一隅之解”与“万端之变”的对举,则与阐释者所属之学术门户和所持之学术见解相关。《庄子·天下》篇讨论上古学术史,有“道术”与“方术”的分别。道术是解决整体性甚至本体性问题的,是要拟“万端之变”的(范文澜 714);而方术则为一方之术,一得之见,也就是刘勰所讲的“一隅之解”(714)。正如“方术”不能解决“道术”的问题,站在某一门户的立场或者囿于某一学派成见,是很难给“人”下定义的。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岂止是“文学”?从宽泛的意义上讲,人文社会科学之中,任何一门学科都可以说是“人学”。从轴心期时代到互联网时代,研究“人”的“学”(学科)越来越多,研究“人”的人(学者)也越来越多,但离“人”的真谛、真义和真相则越来越远。即使是专门研究“人”的学科也是如此,比如人类学。既有科学的人类学,又有哲学的人类学,也有神学的人类学,后来还有文学的人类学,心理学的人类学,历史的和文化的人类学……“它们彼此之间都毫不通气。因此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观念。从事研究人的各种特殊科学的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与其说是阐明我们关于人的概念,不如说是使这种概念更加混乱不堪”(卡西尔 29)。
就汉语学界关于“人”的阐释而言,有没有一个“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观念”?关于人的概念是否“更加混乱不堪”?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问题。可以确定的是,汉语阐释界关于“人”的定义是模糊不清的,是变动不居的,是因时因世因人因势而异的。究其缘由,除了前述“人”之自身所具有的种种局限和现代学术分科治学的种种弊端,还有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原因:近代西学东渐之后,西方种种关于“人”的定义对汉语“人”义的冲击。“人”是什么?古希腊先哲说人是爱智者,中世纪神父说人是上帝的恩赐,16—17世纪之交莎士比亚说人是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18世纪卢梭说人生而自由而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9世纪达尔文说人是生物进化、自然选择的结果,20世纪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21世纪赫拉利说人是算法的动物……近代以来,西方学界关于“人”的种种定义,关于“人”之阐释的种种思路及方法,深度地影响了汉语学界。“茫茫往代,既沉予闻;眇眇来世,倘尘彼观”(范文澜 727),汉语学界如何在“人”的阐释领域解决“沉予闻”“尘彼观”的问题?回到轴心时代,回到华夏元典,在中华元典中重新发现“人”,重新阐释“人”,既与西方人本主义和先验主体论传统平等对话,亦与20世纪以来关于“人”的解构主义思潮平等对话。
按照冯天瑜先生的说法,中华元典主要指先秦两汉的五经和诸子书。先秦两汉元典关于“人”的定义是多元的,《说文解字》:“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此籀文,象臂胫之形。凡人之属皆从人”(许慎 365)。关于“人”之字义(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段注曰:“禽兽草木皆天地所生,而不得为天地之心。惟人为天地之心,故天地之生此为极贵。”(365)关于“人”之字形(象臂胫之形),段注曰:“人以纵生,贵于横生,故象其上臂下胫。”(365)“纵生”贵于“横生”,直立行走之人贵于仆伏爬行之兽。段玉裁说“人”形,其实还是在说“人”义。许慎和段玉裁都没能见到甲骨文,但他们对籀文之“人”的解释却与甲骨文之“人”的本义暗合。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对“人”的解释是“象人侧立之形”,并引《说文》“(人)象臂胫之形”而称“《说文》说形近是”(徐中舒 875)。
段玉裁注许慎“人”说,大量征引《礼记·礼运》篇之“子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阮元 1423),又“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1424)。段注所引《礼运》之“子曰”,还讲到了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为“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何为“人利”(讲信修睦),何为“人患”(争夺相杀)(1422),等等。
凡人之属皆从人,原始儒学的关键词“仁”是“人之属”,故“从人”。而儒学之“人”义,其核心之处在于“人”与“仁”互训。孔子多次讲“仁者人也”,孟子也讲“仁也者人也”。《说文》许慎说“仁”:“仁,亲也,从人二。从人,刃声。”(365)段玉裁认为“仁”是一个会意字,会“人耦(偶)”之意。何为“人耦”?段注曰:“人耦犹言尔我亲密之辞,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365)段注还引了《中庸》“(子曰)仁者人也”和《孟子》“仁也者人也”来证明他的“仁”与“人耦”之关联。
先秦文论元典说“人”,儒家的“人”是在世的,道家的“人”是超越的。《老子》《庄子》等道家文论元典主张“人法自然”,强调人的天性及逍遥。后来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王先谦 393),是说在“天”与“人”二者之中,庄子重“天”而不重“人”,所以其《解蔽》篇欲解庄子“人”义之蔽。他如《墨子》崇尚“人”的非乐与节欲,《列子》宽容“人”的感性与放纵,《韩非子》规训“人”的法、权、势等等,既酿成先秦“人”论之另类,又构成中华元典“人”义多元之景观。从观念的层面论,有“人”的仁性(儒家)、天性(道家)与悟性(佛家);从经验的层面论,有“人”的生命(管子“人者身之本也”)、劳作(孟子“劳力者治于人”)和语言(庄子“言隐于荣华”)。前者是人的超越与无限,后者是人的在世与有限:二者共同构成大写而真实的人,立体而多元的人。
二、“人”言在“我”
中华元典中,《尔雅》被称为“五经之训诂”,《释诂》《释言》《释训》三篇释“词”(普遍词语),余下诸篇释“物”(百科名词)。《尔雅·释诂》关于“我”的训诂共有九个同义词:“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阮元 2573)。《诗经》的毛传和郑笺亦训“言”为“我”。《淮南子·泰族训》称:“言者,所以通己于人也。”(刘文典 689)如果说,《淮南子》的“通己于人”还只是强调“言”对于“人”(人际交往)的功能性或工具性价值;那么,《尔雅》的“言,我也”(阮元 2573)则是关于“人”的本体性和本质性规定。《大戴礼记·易本命篇》有“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王聘珍 259—60),王充《论衡·商虫》篇约言为“倮虫三百,人为之长”(黄晖 716)。较之于“虫”,“人”长于何处?言也。借用前述许慎的话来设问:天地之生(性),人何以极贵?言也。
易有八卦,乾居其首;乾之三爻,人居其心。在会意的层面上说,“乾”卦或可读作“人”字:一位立地顶天之人,一位性灵所钟之人。《周易·系辞上》列举“《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而首标“以言者尚其辞”(高亨 531)。《系辞上》又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544),人之言辞何以能鼓天下之动?千年之后,刘勰答曰:“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范文澜 3)《文心雕龙·原道》在追溯了从伏羲画卦到仲尼翼易的华夏文明史之后,总括出关于“文学”的定义:“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1)。
刘勰关于“文学”的定义有两个关键词:“人”与“言”。刘勰的“人”来自《周易》乾卦所呈现的宇宙结构,“人”为天地之心、三才之魂,是为“心生”;天地宇宙之中,唯“人”能“言”,唯“人”有“辞”,是为“言立”;当人开始言说之时,是为“因文以明道”,人类文明方始彰明,方始灿烂,方始文明以止,是为“文明”。从“心生”到“言立”,从“言立”到“文明”,既是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过程,也是“人”的身份和价值得到确证的过程,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言”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先秦文论元典“人”义多“方”,关于“言”的言说亦因人(言说者)因方(学派)而异。这种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言”之本(本体、本质),二是关于“言”之体(体类、体貌)。就前者而言,有孔子的“慎辞”与庄子的“忘言”之别;就后者而论,则有诸子之言的才性异区、其异如面。而这两大方面的差异性,又可归源于一个共同的缘由:“言”者在“我”。
前面提到,《尔雅·训诂》列举出“我”的同义词共有九个,加上紧随其后所列举的“身”和“予”的同义词,《尔雅》用来表现“人”之身份定位即自我确证的汉字共有12个。“言”者在“我”,不同的“我”有不同的“言”,不同的“我们”更是有不同的“言”。就“人”言在“我(们)”而论,先秦文论元典中最大的差异当然是儒、道之异。孔儒有立言、文言和慎言之说:立言者,求之不朽也;文言者,传说经典也;慎言者,宝重其言也。三言所指,指向“言”对“人”的三重意义:不朽之因、经典之翼和交通之要。道家也有“三言”,即庄子的寓言、重言和卮言。从表现上看,庄子的三言属于言说方式,属于言之体;但溯其根源,则“三言”之本根,在于道家对“言”者在“我”的本体性认知。寓言是借外而言之,重言是借他人而言之,卮言则是随其俯仰、任其自然而言之。察其共性,究其根本,“三言”论者对“言”持一种方可方不可、无为无不为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必然要通向“忘言”或“无言”的。
言之本有两家之别,言之体则有百家之异。不仅是不同的“我们”(即各家各派)有不同体貌不同风格的言,即便是同一类“我们”,也会因“我”之不同而“言”各有体。比如,同为先秦儒家文论元典,《尚书》是训诰式,《论语》是对话式,《孟子》是辩难式;同为先秦道家文论元典,《老子》是诗体式独白,《庄子》是谐体式卮言。综合儒道,可将先秦元典“人”的语言性存在表述为训诰与对话、辩难与独白、诗言与谐言的悖立式整合。总体上说,先秦文论元典中的“人”之“言”,无论是“人”言在“我”还是“人”言在“我们”,其核心精神都是相通的:就表层而论,是孔子说的“不言,谁知其志”;其深层意蕴则可引申为:不言,谁识其“我”。言者,我也。
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在20世纪有一次语言学转向。就中西比较的层面而论,这种有后现代意味的转向,其实是转向了前现代即人类的轴心期。卡西尔《人论》有一章专论“语言”;关于“人”言在“我”,卡西尔的主要观点有五,而每一个观点都与先秦文论元典的语言观有可通约之处:其一,人类世界,语言占有中心地位,要理解宇宙,必须理解人的语言(不言,谁知其世);其二,语言就其本性、本质而言,是隐喻的(寓言十九);其三,语言是一种能(energy)而非一种功(work)(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其四,语言有共时性(规律和规则)、历史性(个人和个性)和创造(创生)性等功能(字者,孳乳也);其五,人类语言因上帝的巴比塔(The Tower of Babel)而交通其难哉(绝地天通)(卡西尔 151—74)。21世纪问世的《人类简史》,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时空领域讨论“智人”的语言问题,将“河边有狮子”“八卦”和“虚构”这些“言”之功能,作为“智人”的根本性特征(赫拉利 23)。从卡西尔到赫拉利,我们看到“人”言在“我”的(中西)可通约性。
三、“人”命关“天”
前面谈到,《易》之“乾”卦可视为“人”,视为天地之心的“人”。《易》以“乾”为首,“乾”以“人”为心,三才之心不仅是“人”的定位,更是“人”的使命和运命。《说文》:“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段注曰:“颠,人之顶也,以为凡高之称。”(许慎 1)天既从人又从大,《说文》释“大”,称“天大,地大,人亦大焉,象人形”(许慎 492)。故就字形、字义而论,“天”与“人”是一体的:“天”字出生伊始,便与“人”字浑然一体、须臾不离。“天”在“人”的头顶(“仰以观于天文”)(阮元 77),也在人的心中(君子心“畏天命”)(杨伯峻 174),既是人的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 64)亦是人的疑窦(“天何所沓?十二焉分?”)(董楚平 48)……作为“人”之巅顶的“天”,既超越式地标举人的位阶甚至永恒,亦宿命般地规定人的顺从甚至仆伏。
“人”命关“天”。《说文》许慎说“命”:“命,使也。从口从令。”段注曰:“令者,发号也,君事也。非君而口使之,是亦令也。故曰命者天之令也。”(许慎 57)命从口,故与“言”相关;命从令,又与“天”相关。“令”既可以来自“君”亦可以来自“非君”,而无论来自何处,既曰“命”则为“天之令也”。命,使也;使命,天之令也。故《礼记·中庸》开篇便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所离非道也。”郑玄注曰:“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阮元 1625)郑玄将“天”之五行(木金火水土)与“人”之五性(仁义礼信智)一一对应,既是建立华夏文明“天人合一”的语义学根基,更是为了强调“天命”在宇宙论意义上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在从郑玄到段玉裁的汉语阐释史中,“人”之“命”有着两个层面的语义内涵:一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一是哲学意义上。就前者而论,性命亦为生命,故“天命之谓性”方可解释为“天所命生人者也”;就后者而论,性命又是道之命亦即形而上之命,故“天命”亦可解释为非君和非非君的“天之令也”。
“人”命关“天”,儒道皆然;不同的是,先秦道家文论主张法天,儒家文论则是畏天。《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 64)在老子那里,道即自然,故这段话可约言为“人法自然”。老子讲“上善若水”,主张人法水道,不争而无尤;老子又讲“天地不仁”“圣人不仁”,是说圣人应该如天地一般无所偏爱,顺其自然。道家的庄子,接着老子讲天钧、天籁、天德、天机、天人。庄子最推崇的“道术”其根本特征便是“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郭庆藩 1064)。被誉为儒家“五经”之首的《周易》其实也有“法天”之内涵。八卦起首两卦,乾义为健,坤义为顺,故乾卦的《象传》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的《象传》有“地道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天如何,地如何,人如何”的法天式思维及言说,可谓贯穿《周易》之始末。
当然,儒家文论的“人”命关“天”,最为核心的理念是孔子的三畏之首:“畏天命”。如果说,“天”在老庄那里,还是自然的,素朴的,虽不可说却是可知可感的。在孔子这里,“天”反而是神秘的、主宰的、宿命的,“巍巍乎!唯天为大”(杨伯峻 82)。《论语》中,“天命”出现三次;“天”字出现18次,其中有16次是讲“天帝、天神或者天理”(杨伯峻 221)。上天是不能得罪或欺骗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27),“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63)。上天主宰着人的运命与死生,故颜渊殆而孔子悲叹:“天丧予!天丧予!”(111)故畏于匡而孔子不惧:“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87)说到底,天是不言而成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85)
老子的法天与孔子的畏天,路径虽异,旨趣却是相通的,所谓殊途同归是也。归于何处?命也。法天或者畏天,就消极的层面论是人的宿命,就积极的层面论则是人的使命,合起来讲则是人的命运。而就人的命运而言,先秦文论元典中几个与“人”相关的汉字,既修辞性地赞颂“人”命的伟大(如“健”与自强之人,“圣”与大通之人,“道”与求索之人),又形象化地泣诉“人”命的悲怆(如“民”与为奴之人,“臣”与屈服之人,“刖”与刑余之人)。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语境中,我们才可能理解,为什么继北方的老子“法天”、孔子“畏天”之后,南方的屈原要发出疑“天”之“问”:“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董楚平 50)。屈原的《天问》是文学作品,兼有诗人之哲思与哲人之诗性;与老庄孔孟同处人类轴心时代,屈原之问“天”,其对人之命运的质疑和对人生道路的求索,是既关乎天道亦关乎人事的。卡西尔的《人论》指出:“为了研究人类事务的秩序,我们就必须从研究宇宙的秩序开始。”(卡西尔 18)在西方有哥白尼的日心说,在东方有刘勰《文心雕龙》的“原道”:后者追源“文明之元”,从“天”开始说起:所谓“玄黄色杂,方圆体分”(范文澜 1),所谓“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1)。在刘勰的文学理论之中,既有“人”命在“天”(从天之文到人之文),亦有“人”言在“我”(心生—言立—文明),二者皆指向“人”义多“方”(才性异区,其异如面)。于是,我们看到先秦文论元典的“人”义、“人”言和“人”命对后世文论及文化的巨大影响。
注释[Notes]
① 这还不包括前述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尼采(上帝之死)和福柯(人之死)。
② 除了上引《礼记·礼运》篇,《礼记·表记》篇亦有子曰:“仁者人也”,后者见《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39页。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Cassirer,Ernst.An
Essay
on
Man
.Trans.Gan Yang.Shanghai: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1985.]董楚平:《楚辞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Dong,Chuping.Songs of Chu: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
.Shanghai: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1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Fan,Wenlan.Annotations
to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58.]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
[Gao,Heng.Annotations
to
Great
Commentary
of
The
Book
of
Changes
.Jinan:Qilu Press,1979.]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Guo,Qingfan.Variorum
of
Chuang
Tzu
.Ed.Wang Xiaoyu.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2012.]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
[Harari,Yuval Noah.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Trans.Lin Junhong.Beijing:China CITIC Press,2017.]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Huang,Hui.Annotations
to
The
Balanced
Inquiries
,with
Variorum
by
Liu
Pansui
.Vol.3.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90.]姜亮夫:《古文字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Jiang,Liangfu.Chinese
Palaeography
.Hangzhou: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84.]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冯逸、乔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Liu,Wendian.Variorum
of
Huainanzi
.Eds.Feng Yi and Qiao Hua.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8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Ruan,Yuan,ed.Thirteen
Classics
with
Exegesis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80.]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Wang,Bi.Annotations
to
Lao
Tzu
’s
Tao
Te
Ching
.Ed.Lou Yulie.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2008.]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Wang,Pinzhen.Interpretations
of
Dai
the
Greater
’s
Book
of
Rites
.Ed.Wang Wenjin.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83.]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Wang,Xianqian.Variorum
of
Xunzi
.Eds.Shen Xiaohuan and Wang Xingxian.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88.]许慎:《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Xu,Shen.Explaining
Graphs
and
Analyzing
Characters
,with
Annotations
.Ed.Duan Yucai.Shanghai: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81.]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
[Xu,Zhongshu.A
Dictionary
of
Oracle
Bone
Script
.Chengdu:Sichuan Lexicographical Press,2006.]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Yang,Bojun.Analects
of
Confucius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