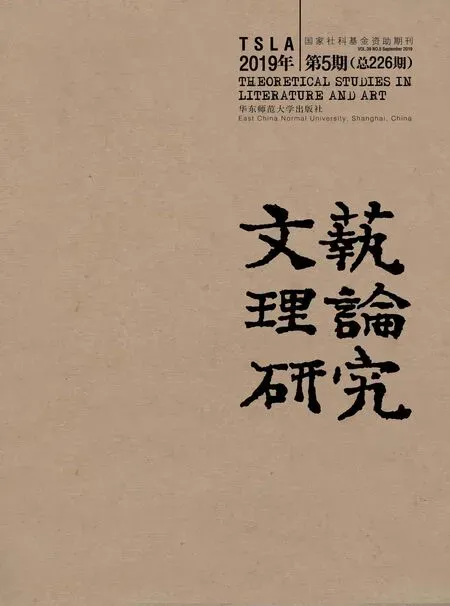“上帝死了,一切都不被允许”: 齐泽克的赛博空间批判
戴宇辰
关于赛博空间(cyberspace)及其衍生的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理论探讨已然成为当代媒介理论研究进路中的核心话题。横跨哲学、文艺学、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试图诊断由赛博空间兴起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文化效应。当然,这对于有着“文化研究领域的猫王”之称的当代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来说也不例外。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那时候赛博空间还只是一种合理的科学设想,齐泽克已经在一系列作品中对于赛博空间有自己的一系列论断。同时代的理论家们从媒介技术视角关注赛博空间的解放潜能及其所带来的可能的社会变化,与他们不同,齐泽克更多的是从“主体”出发,讨论个体如何适应由赛博空间所营造的虚拟现实的生活。而到了新千年之后的著作中,齐泽克则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赛博空间批判理论,认为赛博空间的崛起带来的是一种“主人能指”(signifier of Master)功能的悬置,亦即主人发布禁令从而规训个体的作用衰退。进而,主体身处的是一个“大他者退却”(the retreat of Other)的时代: 再也没有发挥“主人”作用的大他者来保障个体的行事规范了。
新媒体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出现使得技术决定论者欢欣鼓舞。他们欢庆于信息的自由流动以及社会象征禁令的解除,将其视为个体自由解放时代的到来。与之相左的是,齐泽克认为这带来的是一种使个体更为沉重的负担。因为“主人的主要功能在于告知主体他所欲求的”(“What Can Psychoanalysis”801),一旦主人的功能衰退,不再有人告知主体所真正欲求的事,那么主体有效的选择也将随之消除,主体承受了曾由大他者代理选择的重担。齐泽克甚至转引了拉康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改写(“如果上帝死了,一切都不被允许”):“如果不存在被迫的选择来定义自由选择的领域,那么选择的自由也将消失。”(“What Can Psychoanalysis”801)同样,针对精神分析理论所言的“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来说,普遍流行的看法在于赛博空间的到来破除(或者潜在瓦解)了俄狄浦斯情结对于主体的形塑作用,主体不再经受以象征性阉割为象征的禁令而进入了自由选择的认同阶段。齐泽克对此看法截然相反,他认为宣称赛博空间使得俄狄浦斯情结向更为复杂的版本转变,并且选择哪一个版本必须由当前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来预先决定。
基于此,齐泽克事实上确立了比较系统化的赛博空间批判理论,从而与技术决定论倾向的学者们对于赛博空间的理论定位拉开了距离。当然,为了理解齐氏的“诊断”,我们必须先从当代媒介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关于“虚拟现实”的讨论中——着手。
一、 虚拟现实: 一个糟糕的概念
在本·怀特(Ben Write)指导的齐泽克出镜的讲座纪录片《虚拟之现实》(The
Reality
of
the
Virtual
)中,齐泽克在一开始便毫不讳言的指出,当今热点的所谓“虚拟现实”的话题是一个很糟糕的概念。因为,它仅仅意味着“让我们在一个人工数字媒介(artificial digital medium)中再造我们的现实(reality)。”也就是说,我们只是在另一个象征环境中去重复所谓的“现实”中的生活。与此相反,我们应当考虑一个与“虚拟现实”相对的概念,即“虚拟之现实”(the reality of the virtual)。这两个概念从中文翻译角度理解很难发现差别,但是倘若我们回到英文本身,可以发现:“虚拟现实”中,“虚拟”(virtual)修饰的是“现实”(reality),也就是说该概念的主词是“现实”,我们只是在另一个“虚拟的”环境中模拟了该“现实”;而在“虚拟之现实”中,主词显然是“虚拟”(the virtual),这也意味着我们真正的现实生活本质上是“虚拟的”。当然,齐泽克所谓的“现实”并不是指某种惰性存在的客观物体(例如建筑、森林、交通工具,等等),而是指“现实的效力、效果和实际发生的影响。”(The
Reality
of
the
Virtual
)“虚拟之现实”意味着现实对主体的实际影响并不是由存在的客观物体产生,而是由某种虚拟存在的效力产生的。既然“虚拟现实”概念仅仅意味着对于现实的二手仿制,那么在认识该概念之前我们必然需要回到所谓的现实中去,去考察为何现实本身就已经是虚拟的了。齐泽克在此借助的是拉康的想象-象征-实在(the Imaginary-the Symbolic-the Real)三元组,也就是说,现实本质上存在着“想象的虚拟”(imaginary virtual)、“象征的虚拟”(symbolic virtual)和“真实的虚拟”(real virtual)三个维度。
首先来看何谓“想象的虚拟”。齐泽克举例我们日常生活中与人打交道的时候总是会采用一种近似“现象学”的交往手段。我们与他人相遇的时候,必须抽象化、抹除他那带有具体特征、令人难以忍受的形象。例如,在与某人谈话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某人正在排泄、流汗、身上散发出气味等等,但实际接触中,这些印象将会被统统抹除。这也意味着在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并不是与“真实的”(real)他者交流,而是与其经由我们中介过后的“虚拟的”形象相处——这一形象事实上乃是我们在抹去他人难以忍受的特质后想象出来的。
其次是“象征的虚拟”。它是社会有效的象征性运作方式,但为了有效运作,它又必须被保持为“虚拟的”状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于权威的体验。比如说,父亲的权威为了有效的运作,真实的产生效用,必须保持为虚拟的状态。因为一旦权威过于直接,它便会体现出一种无力的悖论。例如父亲在特定的场合并不需要打骂你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他只需要保持自己的在场,仅仅通过怒视你的行为,便会使你顺从,不敢轻举妄动;相反,如果当父亲不再正襟危坐而是冲你咆哮、打骂你的时候,尽管你的身体上承受着疼痛,但你会发现父亲的愤怒行为中暗藏着某种可笑的无力感,这正是权威丧失效力的表现。
最后是“真实的虚拟”。第一,齐泽克认为“真实”(real)这一概念并不是某种内容性的展现(例如某物是“真实的”意味着它象征规定其本质的客观属性),而是一个形式范畴。它象征着某种纯粹的差异,为了掩盖这一差异,现实才出现了两个拥有差异内容的部分。这两个部分的存在是为了掩盖差异其中的张力,也就是说,形式上的差异是先于其内容的;第二,既然“真实”本身是纯粹形式的,那它只能在事后的活动中回溯性的构建,它并不是在实际上存在的,而是一种“向后看”的产物,因此它又是“虚拟的”。齐泽克以物理学中的吸引子(attractors)举例。倘若我们将许多小铁片放在一个磁场的周围,它们便会根据一定的形状运动,不断地接近那个形状。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一磁场的形状在实际中并不存在,它仅仅是观察者通过观察从铁片的抽象运动中提取出来的。这就是“真实的虚拟”,它仅仅以抽象的形式存在,但它又预先决定了周围实际存在物(小铁片)的分布方式。
三个虚拟维度的澄清使得齐泽克更好地描述了现实之虚拟性。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个体的行动离不开“象征界”的支撑。象征界(或者说大他者)是一种类似于“语言”“文化”“习俗”等等自治的领域,是纯粹的“结构主义式”的自律体系,个人又不得不生存在这个体系之中,受这个体系支配。象征界对于个体社会活动正常运作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大他者为了保持其有效的现实效力,又必须依赖于其自身的虚拟性(象征的虚拟)。除去权威之外,齐泽克还举出了关于信仰的例子。齐泽克认为当今的时代已经没有人真正相信民主了,但我们仍然希望维持现状。好像社会中存在一些被保持在无知状态的虚拟实体(virtual entity),而为了不令其失望,我们必须假装相信民主。吊诡地是,尽管无人真的相信那些信念,但这已足够使每个人都假定其他人是相信它们的,这些信念因此便“成真”了。它们因此便构造了现实,它们在现实中起作用了。大他者只要仍然是虚拟的,那么它就能实际起作用,一旦个体开始在社会维度严肃认真讨论起信仰的对错来,那么很可能就是大他者终结的时刻。
象征界之在场强调的是个体的现实生活依赖于一定程度大他者的委任。倘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发现某个个体与其委任身份发生冲突之后,事情会如何?齐泽克举了一个法官的例子。倘若我们在“真实生活”中发现这个法官是个懦弱、胆小怕事的人,我们会作何选择?齐泽克认为我们依然会遵从这个法官所下达的一切指令,而将其懦弱、胆小怕事的一面当成该法官的“表象”(appearance)。因为,一旦他带上他的象征委任之时,通过他说话的就是大他者本身,而这个法官“每一个实际行动呈现为另一种‘不可见的’力量的‘表象之形式’(a form of appearance),这一力量的状态是纯粹虚拟的。”(The
Plague
194)因此,正因为大他者本身是规制现实社会效力的象征体系,它就一定必须被保持为“虚拟的”,一旦它走上前台,“袒露自身”,它所拥有权力的社会效果将受到动摇(例如大发脾气的父亲是他所代表的父权体系无能的一种体现)。那么赛博空间所塑造的“虚拟现实”出现了何种问题?齐泽克认为,虚拟现实的“糟糕”之处并不在于它不够“真实”——这意味着它对现实模拟因技术手段等原因没有达到真正的“真实的”体验,而恰恰是因为它不够“虚拟”——这是因为现实本身已然是足够“虚拟的”,而所谓的“虚拟现实”则抹平了现实中表象和本质的对立,将现实本身的虚拟性消解掉了。这意味着,我们在“虚拟现实”的体验中,遭遇的是一个“没有虚拟性的现实”(a reality without the virtual),这使得个体产生了难以忍受的负担。齐泽克论述道,我们在“虚拟现实”中面临的是一种“主人能指的悬置”(the suspension of Master Signifier): 再也不存在一个可以保障意义的一致性,稳固化能指链的漂移,阻碍其朝向不确定性的主人能指了。主人功能的中止使得主体陷入一种“自我授权”的危机之中: 不再有一致性的大他者来保证他是谁,他的欲望是什么,以及他将如何行事,等等。总而言之,主体拥有的是一种自由(大他者主人功能的悬置)之负担(再也没有保证主体一致性的象征坐标)——而这恰恰是齐泽克所言的“没有虚拟性的现实”。我们也可以用几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例如,个体在虚拟现实中体验到最大快感莫过于身份极端的不确定性,个体可以在互联网上任意的改变身份,可以是一个老师,一个学生,一位企业家,一个服务员等等,甚至于可以任意改变自己的性别,更不用提在网络游戏中个体所扮演的角色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不死的”生物(游戏中个体所代表的人物总是可以通过某种机制“复活”)。而在现实中,个体总是需要通过大他者的登记去获取某个象征身份,这一点在虚拟现实中被完全打破,正如齐泽克所说,我们在虚拟现实中经历的是“大他者退却的时代”。
齐泽克也举了网络中“超文本”(hype-text)来说明这个问题,超文本的泛滥意味着文本意义的不固定性,这可以从网络中出现的大量现实文本的改变与再造看出。例如,某个加州黑客团体潜入了《星际迷航》(Star
Trek
)系列电视剧的后台,通过一些露骨性的性场面的改写更改了官方电视剧版本的故事线(比如,在两个男主人公进入房间之后,出现了上演的同性恋场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改变并不是为了伪造或者嘲弄电视剧,而是揭示了某种隐含的预设: 这一同性恋场景在很多观众看来都是“自然而然的”。换言之,这些变化并不依赖于直接的技术条件的提升,而是揭示了“主人功能的悬置”: 在赛博空间里再也不存在一个保持文本意义一致性的主人能指了。人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甚至创造能力,改写出不同的“超文本”,并且每一个文本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这一情境在盛行的网络文学、网络改变电影中正频繁上演。更为重要的是,在赛博空间中,一旦大他者的功能悬置,将不再有任何“主人”来保证主体的欲望,主体陷入了一种盲目而不自知的情况。齐泽克提醒我们:
主人的主要功能是告知主体他想要的是什么——对于主人的需求是因为主体的迷惑而产生,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当不存在什么告知你真正需要的人时,当所有的选择的重担都落在你身上时,大他者才完全统治了你,同时,所有的选择则彻底消失了——被仅仅是它的表象的事物所替代。(“What Can Psychoanalysis”801)
主人的缺席在表面上生产出一种完全开放和自由的空间——再也不存在任何的权威告知你应该做什么,应该欲求什么,以及如何做出你的选择。但齐泽克却阐述道,这一后果是无法忍受的,令人窒息的封闭。因为一旦主体不存在选择的标准,他将会直接丧失任何选择的能力。虚拟现实的诞生威胁了现实的虚拟性,主体进入了一个主人功能停止的空间,因而完全承担了大他者退却的负担。也正因为此,齐泽克强调,虚拟现实的悖论在于: 它还不够“虚拟”。
二、 赛博空间中的三重威胁
赛博空间虽然标榜着通过新兴技术塑造一个“虚拟的”现实,但通过齐泽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赛博空间恰恰比现实更为“真实”: 它悬置了现实中大他者的主人功能,从而使得主体在其中无所适从,最终威胁了现实本身的“虚拟性”。在这种对于虚拟性的侵害中,齐泽克特别关注的是赛博空间中频繁上演的媒介中介的交流(mediated communication)。的确,在今天,通过互联网与朋友、亲人、陌生人交流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媒介的瞬时性使得交流摆脱了距离的限制,真正在互联网上做到了及时发生。但是正是由于交流的直接、及时、不受限制使得齐泽克反思这其中的危害: 主体必须通过大他者赋予的语词(能指)来表述自身,主体在进入象征界的时刻就总是已经被语词所绑定;但倘若大他者的功能悬置,那么能指和主体的束缚关系也将断裂,用齐泽克的话说,赛博空间的第一重威胁就是,对于主体“语词失去了其述行性效力。”(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195)根据言语行为理论的观点来看,主体在交际的过程中同时可以完成一定的行为。说话人通过话语来执行诸如请求、陈述、命令、提问、道歉、祝贺等实际行为,并且这些行为可能对听者带来某些影响和后果(Austin,How
to
Do
1-11)。也就是说,当我在说话之时,我总是表达了除却说话本身之外的某种含义(一种示好的姿态,一种愤怒的感情,一种诱惑等等)。述行性要求的是交流的两者有着一致的语义空间,亦即存在着一个大他者保证双方交流的畅通。我们可以以马克·赫尔曼(Mark Herman)的电影《奏出新希望》(Brassed
Off
)为例。男主人公在晚上约会后送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士回家,在她的公寓门口,女士假装殷勤地问道:“要进来喝杯咖啡吗?”。男主人公回答道:“有个问题,我不喝咖啡。”她笑着回应道:“那不是问题,我也没有咖啡。”显然,女士的第一个疑问的要点自然不在“交流的内容”中(是否要喝杯咖啡),而是通过这一内容展示某种类似性暗示的述行性姿态。男主人公在第一个回答中显然误解了女士的含义,“坦率的”将交流的述行性行为忽略,才造成了女主人需要通过第二次否定来化解这种尴尬。无论如何,这一交流始终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大他者作为保护——即双方知道“喝咖啡”以及“没有咖啡”意味着什么。而回到赛博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大他者的悬置导致了语词述行性的失效,即语词和其关联的主体之间的关系产生断裂。换句话说,主体在进入赛博空间的那一刻起就从与语词的关联中脱钩,语词再也不能被“主体化”(subjectivized)了。对此齐泽克论述道:
虚拟空间交流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我可以撒谎(例如一个丑陋的老妇人将其描绘为一个美丽的年轻少女),而且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地投入(engage in)过这种交流中,因为我可以随时将自己回撤,从这种束缚中解脱[……]也许,象征交流的“电脑化”迫使我们面对述行性的问题: 主体间交流的逐渐“电脑化”会如何影响我们最为基本的象征宇宙,以及对于“服从”“投入”“信任”和“依赖某人的话语”的基本判断?(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196)我们知道,在赛博空间主体常常发出的感慨就是“这一切不过是虚拟的、虚幻的交流。”也正是从这里出发,齐泽克发现了这一“从未真正投入的交流”对主体象征宇宙的侵害,我们事实上在虚拟现实的交流中丧失了最基本的共享的象征空间,主体可以轻易地选择退出并不付出任何责任。齐泽克在这里用精神分析治疗中的“分析师”和“分析者”的谈话作为类比。在分析师和分析者的对谈中,分析师并不关注分析者到底说了什么——这意味着分析者可以谎话连篇或者对分析师说出侮辱性的言词,而是需要从分析者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关联处找到其内在的不一致性——即分析者自身的“症状”。在双方的交流中实际上有一个“先验的”(transcendental)的姿态: 双方都不会将这次交流看成是一场真正的交流——分析师对分析者话语的述行性效应毫不关心,而分析者只是进入自己的自由联想中,通过不断言谈来面对沉默的分析师。也就是说,这一交流只是一种无效的交流: 正常主体间性交流中话语的述行性在这里被悬置。
一旦主体从其语词的关联中解脱出来,那么可以想象的是,赛博空间就成了一个实现主体内心欲望的场所——主体不再需要为自己在赛博空间的任何行为负责。对此,齐泽克认为赛博空间的第二重威胁在于主体幻象(fantasy)对现实(reality)的入侵。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幻象是支撑主体欲望的场所。而为了使主体的欲望坐标得到保证,幻象必须是在保持其“潜在性”,这意味着幻象必须与现实分割开来,成为一种隐藏在现实表面下的“场景”。拉康曾以弗洛伊德提及的小安娜的梦说明幻象对于主体的重要作用。小安娜在梦中梦到了自己津津有味的吃着弗洛伊德买的蛋糕,拉康对此分析道,这不是说明小安娜的欲望在于吃这个蛋糕,而是说她很享受吃蛋糕的过程(因为她吃的时候父亲会慈爱的看着她)。因此,小安娜的真正欲望在于父亲对她的欲望,父亲希望她享受蛋糕正是她的幻象,而这个幻象使得小安娜的欲望有了清晰的坐标——吃草莓蛋糕。因此,当小安娜在现实中欲望吃草莓蛋糕之时,有一种隐蔽的幻象(父亲对她的欲望)必须被隐藏起来,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感,正如齐泽克所言:“要想发挥功效,幻象就必须被保持‘隐匿’状态,必须同它所支撑的表层结构保持一定的距离。”(The
Plague
24)但当主体进入赛博空间以后,因为一切都变得“唾手可得”,这种幻象与现实的距离就被消融了。主体可以尽情地将自己内在的幻象投射在屏幕之上,而无需付出任何的现实负担。例如,一个办公室温柔和善的女性白领在赛博空间的网络游戏中很可能会扮演为一个杀人如麻的凶手,一个在真实社会关系中安静、害羞的人在虚拟游戏中可能会采纳一种愤怒、侵犯性的形象。这些问题不在于说是某个“现实形象”是安静害羞的人在虚拟现实中实现一种“虚拟的”愿望(例如他可能在某个游戏中扮演一个愤怒的杀手),而是说,他的所谓“现实形象”本身就是“虚拟的”,是经由大他者中介所形成的一种“象征性身份”。而在赛博空间中,支撑这种象征性身份的隐秘幻象(一个愤怒的杀手)被彻底外化在电脑屏幕上,主体遭遇的是幻象对现实“表层结构”的入侵。同样,在盛行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爱”(virtual sexuality)中,主体将自己某种潜在的对于伴侣(或性幻想对象)的性幻想内容直接投射屏幕之上,因此获得一定程度的性满足。齐泽克认为,这一经由电脑中介的性交行为所带来的危害性并非传统观点所批判的过渡网络色情和暴力(例如主体直接暴露在大量的色情信息之下),而是主体直面了支撑自身现实性行为的性爱幻象——正是这一将主体隐秘幻象外在化的仪式使得主体面临着更深层次的不安与无助。因此,齐泽克总结了赛博空间对于幻象与现实之间距离的消解:
今天,赛博空间社会功能的问题在于,它潜在地填平了这样一道沟壑,即主体的公共象征性身份(public symbolic identity)和其幻影背景之间的距离: 幻象被越来越多的直接外化于象征公共空间之中;隐秘的私人领域被越来越多的直接社会化。(The
Plague
212)换句话说,丧失了隐秘状态而被彻底实现的“幻象”将不再是“幻象”,主体的欲望在赛博空间中也将随着幻象的终结而终结。
这一填补沟壑的行为所带来的第三重威胁就是“文本意义的消失”。虚拟现实的潜在特性使得主体可以将幻象直接付诸实施。那么蕴藏在网络空间中文本的“表面意义”和其“潜在意义”之间的距离就将消失不见。齐泽克认为,一个文本的“效力”依赖于其“已说的话”和“未说的话”之间的微妙平衡: 已说的话总是需要其未说的话进行补充。但在赛博空间中对于《星际迷航》之类的“超文本”改写中,文本中未说的话将被完完全全的以一种“逼真的”方式展露在屏幕上(门关上了,《星际迷航》中的两位男主人公在里面做了什么),也就是说,“已说的文”——这里指代着某种公开性的象征话语,与“未说的文”——这里指代着其隐秘的幻象性补充,之间的距离在赛博空间中被消解了。正如当前网络空间中出现的“信息厌食症”(information anorexia): 个体在面临不断的信息轰炸之后开始有意识地拒绝任何信息的获取。齐泽克认为,主体绝望地拒绝信息象征着赛博空间中的空洞被过度填充——这表现在文本的虚拟维度被潜在的废除了,主体面临的是充斥着“表面意义”的诸种文本。这样以来,以文本所构建的大他者就不存在潜在的虚拟性,而是直接对主体开放。主体在直接面对大他者的过程中丧失了真实的“意义感”——再也不存在“词不达意”(语词的述行性)的情况。也就是说,信息的盛宴带来的是一种更为基础的对信息的恐惧。
因此,赛博空间瓦解了主体与大他者的距离,使得保证生活一致性的大他者之虚拟性被废止。这最终导致了其对现实生活的三重威胁: 语词不再能够被主体化、主体幻象与现实的距离消解以及文本意义的丧失。令齐泽克更为忧虑的是,在赛博空间自由和公开的表象下蕴藏了一种对于主体更为深刻的禁锢,那么,究竟主体在赛博空间中享受了“绝对的自由”还是“充分的禁锢”呢?齐泽克倾向于从精神分析中所描绘的履行禁令功能的“俄狄浦斯情结”开始谈起。
三、 俄狄浦斯向何处去
赛博空间对于述行性、欲望和意义的三重威胁共同标示出象征界在赛博空间中的退场: 能够保障主体交流、欲望和行动的大他者(或言其功效)在赛博空间中被潜在废除了。齐泽克将主体与精神病的结构关联起来,认为赛博空间带来的是一种对“父之名”的预先排斥(the foreclosure of the Name of the Father)。对于拉康来说,“父亲”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而总是一种隐喻,象征着将孩子与母亲分离开来的某个能指。“父之名”是一个绝对的能指,象征着某个结构中的一个位置。幼儿在摆脱与母亲的二元关系进入语言世界之时必须遭到一种“阉割”(castration),这意味着它必须认同存在一个不以他为中心的象征世界。换句话说,他必须通过阉割定位某种超越自身的东西,并且认识到他与母亲的二元关系之外存在着一个超出的象征网络——这就是拉康所言的大他者。父之名是承担阉割功能的能指,它使得幼儿可以摆脱想象界进入象征界的世界中。而所谓“预先排斥”意味着在象征界构筑的过程中,父之名这一能指一开始就遭到了排除,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于象征界中。
俄狄浦斯情结象征一种父权性的律令利用父之名对于幼儿展开阉割的运作过程。它是一种主体化模式,向幼儿确立一种思想: 世界并不以幼儿与母亲的二元关系为转移,而是存在着一个拉康定义为象征界的“第三者”。这一第三者通过语言调节了幼儿的欲望、言说和行动,使得他能够成功地融入象征网络所构筑的象征世界中。经由“俄狄浦斯情结”的主体确立了象征界的存在,也就获得了大他者所指定的象征性身份(例如我是一个男人、女人、异性恋等等)。而在精神病者的精神结构中,父之名这一承担阉割功能的能指遭到预先排斥,那么主体的象征界中必然呈现出一个空洞——曾经由父之名所占据的位置所遗留的空洞。一旦主体在生活中遭遇了某种唤起“父性观念”的情境: 例如一个男人成为父亲,一个人在工作上的升迁,或者他在象征世界中所发生的变动,所有这些情境会向主体的父性辖域发出召唤。但是由于父之名被预先排斥,那里什么都没有,主体只能面对着一个空洞,一个缺口,因此便产生了精神病中的“世界末日”之感。
赛博空间使得调节主体的大他者被潜在瓦解,这也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俄狄浦斯过程对主体的阉割作用。那么在赛博空间中,主体真正成为不受大他者调控,以自身为中心的自由主体了吗?齐泽克认为,在当今流俗的看法中,我们的确得到了关于“俄狄浦斯终结”的赛博空间叙事,这意味着“在那里发生的一切都是从象征性阉割的结构向某种新兴的后俄狄浦斯力比多机体过渡。”(齐泽克285)但是如何看待这一叙事,还要依据不同理论家的不同立场而定。据此,齐泽克提供了关于赛博空间中“俄狄浦斯是否终结”的三个不同版本的论断。
第一个版本是以让·鲍德里亚和保罗·维利里奥为代表的后现代哲学家。他们关注的是在数字化世界中想象界和实在界的直接融合。这导致了赛博空间文化展现出一系列的“拟像”效应,即文化的生产从对现实的模仿转向以自身内在逻辑为基础的生产。鲍德里亚关注的是由现代媒介所塑造的影响已经代替了“现实”本身。因此,影像并非对于“现实”的模仿,而是一种直接的创造,鲍德里亚将其命名为“超现实”(hyperreality)。基于对拟像的分析,鲍德里亚认为再也不存在任何的实存物,“影像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博德里亚尔8)此外,维利里奥还通过对拟像世界的批判表达了一种对于原初本真体验的怀旧式渴望。对于这一版本的解读,齐泽克认为他们的问题首先在于混淆了“表象”与“现实”之间的区别: 现实总是已经经由象征性的中介,呈现为某种“表象”。也就是说,不存在维利里奥等人设想的一种“本真的现实”,当现实被呈现出来之时,它就已经是“表象”了。因此,齐泽克认为,在赛博空间中,“受到威胁的不是‘现实’,因为‘现实’已经溶解在其拟像的多样性中了,而是表象”(齐泽克,287);其次,表象使得崇高的超验之维得以可能,而拟像则将这些超感官的逻辑淹没。用拉康的话说,表象是特定的象征性虚构,而拟像则是想象界和实在界混合的产物。实在界(这里指超验之物)只能通过表象(象征性虚构)得以返回,倘若表象被替换为拟像,实在界则被淹没在想象界塑造的影像中。因此,在拟像所主宰的数码世界中,实在界越来越与其想象性的混合产物难以区分,不再有一种崇高的文化体验。
第二个版本是由以桑迪·斯通(Sandy Stone)和谢里·特克尔(Sherry Turkle)为代表的网络女性主义者。她们强调网络已成为社会的实验室,人们可以通过网络的虚拟现实进行自我塑造,创造新的自我身份。“俄狄浦斯的终结”意味着主体不再受到某种禁令的调配,从而拥有单一的象征性认同。主体在网络中转向一种任意跨越身份,并释放欲望的认同之中。齐泽克认为,这一版本的叙事继承了福柯式的“自我关照”(care of the self)术,即将自我的建构塑造为一种审美式的自由。这意味着,在赛博空间,“主体并没有被呼唤去占据在社会-象征性秩序中预先授予他或她的位置,而是获得了在不同社会-象征性身份之间转移,把其自我建构成美学作品的自由。”(齐泽克288)因此,赛博空间成功地塑造了一种意识形态,即它可以将“我从生物学制约的残迹中解放出来,并提高了我自由地建构自我的能力,以及在众多变化身份中做出选择的能力。”(齐泽克288)
如果说前两个版本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俄狄浦斯在赛博空间的终结,那么支持第三个版本的理论家们则认为赛博空间延续了俄狄浦斯所规定的主体化模式。他们的要点在于,由电脑屏幕所构筑的“界面”(inter-face)延续了现实实体世界中的大他者的作用: 首先,我在赛博空间中采用的“身份”从来都不是“我自己”,这意味着我在网上浏览和参与虚拟共同体的活动之时仍然存在着阐述主体和被阐述主体之间的裂隙: 即赛博空间中的“我”从来不是现实中的“我”,我仍然受制于“界面”所召唤的象征性身份;其次,对于我的交流对象来说,他们也存在着本质上不可判定性: 我从来不能确定“他”是否就是他所描述的那个样子,在屏幕背后是否存在一个“真实的”他者,抑或我们与我们交流的他者乃是某种数字性的虚拟实体。简而言之,界面在赛博空间的存在仍然使得主体在虚拟世界中面对着谜一般的大他者,他使得主体的身份认同总是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了,并且他永远无法确定与他交流的他者的欲望究竟是什么。齐泽克也以此为依据去反对第二个版本关于“俄狄浦斯终结”的自我关照理论:
不错,在赛博空间中,“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一切”,你可以自由选择象征身份(屏幕人),但你必须选择其中之一,而它在某种程度必定背叛你,而且它永远不可能是完全恰当的[……]不错,在赛博空间中,“一切都是可能的”,但要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假定存在着某种基础性的不可能性: 你无法囊括界面及其“迂回”之调停,它把你(作为阐述主体)与你的象征性替身永远隔离开来。(齐泽克290)
齐泽克认为,这三个相互矛盾的版本实际上涉及了精神分析中的三种精神结构: 第一个版本是精神病(psychosis)的结构,它声称“赛博空间承载着普遍化的精神病症状”(齐泽克292)——这意味着赛博空间悬置了主体的象征界使得主体的想象界直接融入实在界的快感之中;第二个版本是性倒错(pervert)的结构,表明“赛博空间打开了全球化多重性倒错的解放视野(齐泽克292)”——这意味着主体彻底摆脱了与大他者的关联,成为了“自由漂浮的”主体;第三个版本是歇斯底里(hysteria)的结构,宣称“赛博空间依然停留在使得主体歇斯底里的谜一般的大他者的范围内”(齐泽克292)——这意味着主体仍然不能摆脱大他者的束缚,受制于大他者质询的象征性身份。究竟哪一个版本更为符合赛博空间中的“俄狄浦斯”叙事呢?齐泽克认为,这三个版本都存在各自的问题,因为它们涉及到两种对于赛博空间的标准式回应: 前两个版本认为赛博空间中的俄狄浦斯已经终结,而第三个版本则认为俄狄浦斯以某种方式在赛博空间中得以延续。这两种回应一个是“太强”,另一个是“太弱”。据此,齐泽克提出了第四个版本的俄狄浦斯叙事,它强调的是以更加严格的方式发展赛博空间(第二个版本)的性倒错结构。
拉康关于性倒错的定义包含两个要点: 首先,性倒错是处于精神病和神经症中间的一种症状。这意味着与精神病完全拒斥象征性阉割和神经症完全接受象征性阉割不同,性倒错主体部分接受了阉割。但他/她却以“否认阉割”的姿态行动,对于性倒错者来说,律令并不能完全在其身上起作用,从而大他者并不能完全的调节其欲望构成。其次,正是因为律令无法完全对他/她起作用,这种精神体验倒置为一种欲望的构成,对于性倒错者来说,他/她的欲望在于完全“融入律令”,“其欲望的客体就是律令本身,他/她想得到律令的完全认可,融入到其运作之中。”(齐泽克293)
以倒错性行为中的受虐狂(masochism)为例: 首先,受虐狂不能(或者说只能部分)从正常的性行为中获得快感,这意味着由象征性的律令(这里指正常的性行为)并不能完全调节其性行为中的欲望;其次,受虐狂在性行为中获得快感的方式往往是向性爱对象制定一整套的“受虐规则”,也就是对方越是按照这一规则对其“施虐”,他/她就越是能获得额外的性快感。从受虐狂的精神结构中可以发现,尚未完全建立的律令恰恰是其“欲望客体”,他/她希望通过自身去构筑律令,完成阉割。而在这种“填补律令”的过程中,受虐狂获得了超量的快感。
再回到赛博空间的论述中来看,齐泽克将赛博空间的“俄狄浦斯叙事”诊断为蜕变成一种性倒错结构之时是想表明两个要点: 首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阉割对于赛博空间的主体来说“不起作用”。主体在赛博空间中成为了一种不受象征性束缚的自由主体(我可以在虚拟现实中选择任意一个象征性身份),从而实现了一种跨越身份认同,将自身的欲望释放在“自我关照”之中的新行动;其次,但是这一“自由漂浮的主体”并不如网络女性主义者暗示出一种新的解放姿态,而是需要通过“构筑律令本身”调控自身的欲望。这一点也可以从赛博空间中不断浮现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行动中看出: 许多“自由连接的”网络中的主体可以因某一特定的主题集聚在虚拟社群中,不断地重复这一发明出来的网络“仪式”。例如《江南Style》歌曲流行期间,出现了大量的网络和线下的以该歌曲为主题的快闪活动。尽管这一歌曲不包含任何标准的“审美”元素: 它是单调的机械化迷幻舞曲,歌词是对无意义的时尚风尚的嘲讽,但却出现了大量的重复这一无意义歌曲舞步的网络组织活动。再比如国内网络频繁出现的民粹主义运动,例如2016年年初的“帝吧出征”活动,均暗示出一种新的“仪式性”行动在赛博空间的出现。齐泽克在其中发现的是赛博空间中的主体对于快感(jouissance
)的享用: 标准的象征性阉割在主体身上失效之后,主体通过一种无意义重复的宣泄性行为,确定一条内在律法,并将这一律法的制度化行为视为自身的欲望客体。齐泽克断言,倒错的行为远非潜在破坏了象征性律法(symbolic law),而是象征着一种绝望的尝试,主体旨在设置一个律法展演的舞台[……]正是因为阻止直接的(“乱伦式的”)对于快感的享有的律法之能力不断衰退,唯一的支撑律法的手段是对于那些具身化快感的“物”(Thing)展示出认同。(“What Can Psychoanalysis”823)
因此,“现实生活”中的标准俄狄浦斯在赛博空间中并非终结或持续存在,而是转变成一种新的倒错式结构。主体也并非成为了摆脱律法阉割的“自由的”主体,而是在一种绝望的发明(制度化)律法的过程中获取与之相伴随的快感。
结语: 在赛博空间中穿越幻象是可能的吗?
事实上,在当代理论界对于赛博空间的深度考察中,存在着三种差异较为显著的研究取向: 第一种即赛博空间研究的“后现代主义”转向,即将赛博空间的虚拟维度与现实世界并置,考察虚拟性对于现实的入侵所带来的种种威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鲍德里亚对于“拟像”的分析;第二种是赛博空间研究的“福柯主义”转向,即考察赛博空间中摆脱现实规训的“自我”如何获得相应的(新的)主体性身份,以及这种主体性构建过程中所依据的内在动力机制是什么,像谢里·特克尔的“第二自我”(the second self)概念就是一例;最后一种是赛博空间研究的“新制度主义”转向,即考察作为现实规训机制的“俄狄浦斯情结”如何继续在赛博空间中发挥作用,并且它是如何作为新的大他者(继续)调节赛博空间的主体化进程,例如杰里·艾琳·弗利格(Jerry Aline Flieger)对于“俄狄浦斯在线”(Oedipus Online)的研究。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正如齐泽克提供的“第四个版本”的俄狄浦斯叙事一样,他对于赛博空间的批判性考察的落脚点也与上述三条路径不同: 首先,齐泽克关注的是赛博空间对于“虚拟性”的侵害,正是由于“大他者的退却”使得赛博空间中的主体无法获得适当的欲望支撑,从而陷入了“上帝(大他者)死了,一切都不被允许”的深层次禁锢之中。如此以来,齐泽克恰恰走在了宣扬自由解放的媒介技术主义者的反面。其次,齐泽克也同时反对上述对于赛博空间的三个版本的“深度”思考。他强调,单纯的考察俄狄浦斯情结是否终结(即考察赛博空间主体的主体化过程是否受到第三者的调控)忽视了拉康对于性倒错之精神结构的论述: 赛博空间的主体在俄狄浦斯阉割衰退的情形下并没有获得全然自由的解放或者陷入全然封闭的禁锢,而是转向了一种新的倒错式结构,即主体试图通过“发明律法”来维持自身快感获得的可能性。这样以来,齐泽克事实上完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赛博空间批判。在他看来,赛博空间带来的新问题已然导致了现实生活中的三条边界变得模糊不清。
其一是自然与人工的边界。在技术盛行的赛博空间中,已经不存在纯粹自然的生命现实和人造的现实之间的分野。诸如依托基因技术改造自然物乃至人类的科学事实(或前景)展示出,“技术不仅仅在模仿自然,而且它揭示了生产自然的潜在机制,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自然的现实’本身成为了‘被模仿’的东西。”(The
Plague
170)也就是说,在今日之“现实”中,生命的本性已经是一种可以从技术上加以操控的事物,从原则上来看,这将最终导致自然与人工技术产物重叠在一切,不在有“活生生的自然物”与“现实的人造物”之间的区分。其二是现实和其表象的边界。某物现实与表象的分野在于其“现实效力”和其“呈现方式”之间的差别。表象是指该物的“象征性构型”,它是一种在大他者中介下的象征性属性;而其“现实效力”则要依赖于其象征性元素的述行性成分而定。诚如我们上文的分析,有时候我们往往“词不达意”: 语词的表象(这里指能指与所指的链接)不一定就是其现实效力的表达。但在赛博空间中,我们面临的是一种由媒介所构筑的“超现实主义”(hyperrealism)图景:“我们只能领会颜色和轮廓,而不再是深度和内容。”(The
Plague
171)这也意味着,在赛博空间的信息轰炸中,我们丧失了辨别信息其中的述行性要素的能力,从而陷入了被信息淹没之表象的洪流中。其三是自我与他者的边界。赛博空间中的多用户网络游戏破坏了自我的概念: 个体不再拥有作为一个思考主体的单一身份(我往往可以是一个骑士,一个凶手,一个律师,等等)。“自我”(Self)最终被分散为大量相互竞争的网络代理(agents)之中,成为了一座漂浮的孤岛。但问题也接踵而至,在所谓的虚拟交往中,我们会逐渐发现,在“大量不断变换的身份之后,没有‘真正的’人的面具,并因此经验到了生产自我的意识形态机制,以及这种生产/建构的内在暴力和武断。”(The
Plague
171)齐泽克忧虑的是这三条被威胁的前线之间逻辑上的关联性: 首先是在“客观现实本身”中,“生命的”实体和“人工的”实体两者之间的界限被破坏;然后“客观现实”和其表象之间的差别逐渐模糊;最终,思虑某事(它的表象或者它的“客观现实”)的自我实体崩溃了。这一渐进的“主体化”(subjectivization)进程与其对立面——主体性身份硬核的逐渐外在化(externalization)紧密相关[……]今天,由于虚拟现实和生物技术的出现,我们面对的是区分内部和外部之界面的消失。这一缺失威胁到我们对于“自身身体”的最基本领会: 即认为它与周遭坏境息息相关。(The
Plague
171-72)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赛博空间为主体的内在幻象的展演提供了一个舞台: 主体在其中“释放”了自身最为隐秘的内核。在拉康那里,“穿越幻象”(traversing the fantasy)是精神分析意义上唯一的伦理性行动。幻象乃是结构主体现实的框架——主体的“现实感”依靠幻象来赋予,穿越幻象意味着主体摆脱幻象的奴役,与最真实的“本体自我”(noumenal Self)相遇。这时的主体遭遇的是一种拉康所言的“主体性贫乏”(subjective destitution): 这意味着不再存在构筑主体象征界一致性的幻象框架,主体否定了自身的象征性身份。在上文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赛博空间抹平了“表象”与“幻象”之间距离,那么在赛博空间中,主体究竟是否能完成一种“穿越幻象”的伦理性行动呢?齐泽克对此的回答却是十分模糊。首先,齐泽克强调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赛博空间中对于幻象的展演是一种“距离性的展演”,也就是说,主体从来没有认真“投入”(engage in)到赛博空间的活动之中——这意味着主体可以随时从这种象征交流的循环中回撤(“这一切不过是虚拟的、虚幻的交流”)。也“正因为我们没有直接置身其间,因为我们与它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我们才觉得可以自由地外化、展示我们内心隐秘的幻象。”(齐泽克298)
其次,我们必须意识到,“幻象”并不处于与“现实”对立的一极——这意味着“幻象”是模糊“现实”的某种想象性效应,主体必须通过一种反思性行为来穿越幻象,获得对现实事物本真状态的感知;相反,“幻象”是主体获得“现实感”的条件——正是通过幻象才能够赋予主体现实的一致性。那么因此,穿越幻象意味着“我们对想象领域的过度认同: 在它那里,通过它,我们打破了幻象的限制,进入了可怕、剧烈的前综合想象领域。”(齐泽克298)沉湎于赛博空间的行为允许我们得到这样的体验: 我们通过不断地将自身的想象力外化在屏幕之上,可能会潜在破坏支撑我们现实一致性的幻象框架。
最后,最重要的是,穿越幻象并不是置身于赛博空间主体的必然结果。因为赛博空间本身总是受制于它所处的政治权力统治的网络中,互联网的全球普及正是一系列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个体用户越是被允许进入普遍化的社会空间,那个空间就会被越是私有化。”(Living
in
the
End
Times
407)我们得到的仅仅只能是赛博空间自身技术性特征所开辟的诸种可能性(俄狄浦斯的终结,俄狄浦斯的延续,穿越幻象,等等),而这些可能性最终如何导向现实,始终必须视当前社会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斗争而定。正如比尔·盖茨宣布赛博空间引领的是一种“无摩擦的资本主义”(friction-free capitalism)——参与者的社会身份差异被抹平,权力关系被掩饰,对于赛博空间的社会文化分析必须始终与其所处的现实政治场域产生勾连。因此,对于赛博空间的未来,齐泽克忧心忡忡地总结道,“赛博空间将如何影响我们,这并没有直接刻入其技术特性之中;相反,它是以(权力与统治的)社会-象征性关系网络为转移的,而这个网络总是已经多元决定了(overdetermine)赛博空间影响我们的方式。”(齐泽克299)注释[Notes]
① 详情请参考〈http://www.imdb.com/title/tt0419142/〉,2017年6月10日访问。本讲座的中文版字幕参考了网络上的译文,有改动,具体请参见: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7471661/〉,2017年6月10日访问。除特殊注明外,关于此讲座的引用均出自以上译文,下文将不再标注。
② 精神病结构在精神分析中指的是主体的父之名被预先排斥,而面临着象征界的空洞。
③ 性倒错结构意味着“父之名”所带来的阉割对于主体无法起作用,本应承担阉割功能的律法成为了主体的欲望对象
④ 歇斯底里是神经症结构的一种,主体接受了父之名的阉割,但却不能明白自己对大他者意味着什么,从而产生一种面对谜一般大他者的焦虑。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ustin, John Langshaw.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Baudrillard, Jean.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让·博德里亚尔: 《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年。
[Baudrillard, Jean.The
Perfect
Crime
. Trans. Wang Weimi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0.]Flieger, Jerry Aline.Is
Oedipus
Online
?Surfing
the
Psyche
.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4.Turkle, Sherry.The
Second
Self
:Computers
and
the
Human
Spirit
.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5.斯拉沃热·齐泽克: 《实在界的面庞》,季广茂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Žižek, Slavoj.The
Grimaces
of
the
Real
. Trans. Ji Guangmao.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4.]Žižek, Slavoj.Living
in
the
End
Times
. London: Verso, 2010.- -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On
Schelling
and
Related
Matters
. London: Verso, 1996.- - -.The
Plague
of
Fantasies
. London: Verso, 2008.- - -.The
Reality
of
the
Virtual
. Directed by Ben Wright. Ben Wright Film Productions, 2004.- - -. “What Can Psychoanalysis Tell Us about Cyberspace.”Psychoanalytic
Review
91.6(2004): 8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