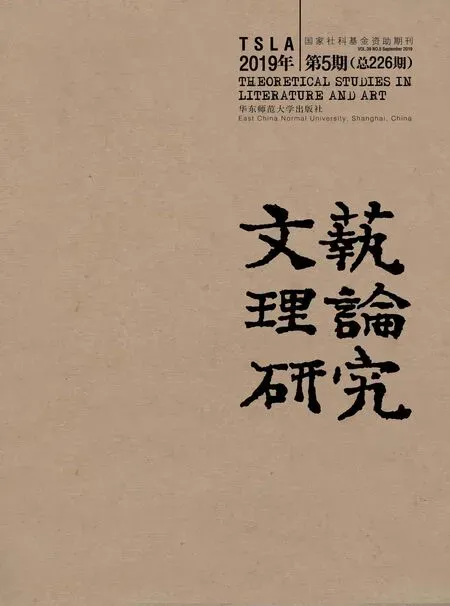为什么是土地测量员?
曾艳兵
《城堡》是卡夫卡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也是最能代表卡夫卡创作思想和艺术特征的作品,当然,也是卡夫卡最难理解、被阐释最多的作品。正如小说中的主人公K.一次次地试图进入城堡,但又一次次无功而返一样,许多读者一次次打开这部书,又不得不一次次将它合上。米兰·昆德拉说:“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读《城堡》,这本书后来再没有像当时那样使我兴奋,尽管它包含的广泛的知识(卡夫卡现象全部真正的意义)对于当时的我是难以理解的: 我仍然感到眼花缭乱。”(113)时至今日,有关《城堡》的著述已经非常丰富了,但有一个问题人们似乎还关注不够、研究不够,那就是小说主人公K.的职业。“文本本身就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K.究竟是不是一个土地测量员,他是真的得到了任命,还是在说谎,他是偶然到来的,还是带有什么目的,等等。在全世界的卡夫卡学者中,解释的方法和观点,可谓林林总总,纷繁多样……”(昆 延斯282)。但对于这一问题终归没有令人信服的、深入的思考和探究。于是,我们不禁要问: K.的职业为什么一定就是土地测量员呢?为什么卡夫卡让他笔下的主人公从事的是这样一种古老的职业?
一、 “无地可测”的土地测量员
K.来到附属于城堡的村子的当天晚上,就曾明确地说过,“我是伯爵招聘来的土地测量员(the land surveyor),明天我的几个助手就要带着各种器件乘车随后跟来”(卡夫卡4)。虽然K.的身份在后来并没有得到确认,并且他也似乎并未真正从事过任何与土地测量相关的工作,但是,他自始至终都是以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在隶属于城堡的村子里逗留和居住。问题是,K.的职业何以是土地测量员,而不是其他任何一种更为常见的职业?卡夫卡为什么让他小说的主人公拥有,或希望拥有这样一种职业?卡夫卡有关土地测量员职业的灵感来自何处?这种职业有何特别的所指或寓意呢?
具体而言,在《城堡》中对K.的职业问题的描述,主要有以下几处地方: 小说开篇,K.自称是伯爵大人聘来的土地测量员,但人们只是将信将疑。为此,城堡副主事弗里茨的儿子,施瓦尔策还专门打电话询问过城堡里的官员。城堡那边的回话,一开始是否认,随后承认了K.土地测量员的身份。不久信差巴纳巴斯捎来城堡官员克拉姆的信,信上说,城堡已经聘任了K.,但他的直接上司是村长。于是K.去见村长,村长则说: 此村根本不需要土地测量员。“我们这些小家小户的土地界线是划定了的,一应事项已全部有条不紊登记在案。产业易主的事极少发生,小的边界纠纷我们自己解决。所以我们要土地测量员干什么?”(卡夫卡66)K.便被打发去学校做校工。正当K.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与克拉姆见面时,巴纳巴斯又交给K.一封来自克拉姆的信。信上写道:“大桥酒店土地测量员先生鉴: 对您迄今为止进行的土地测量工作我深感满意。二位助手的工作也值得赞扬……此外请放宽心,酬金问题指日可获解决。我将继续关注您的情况。”(卡夫卡129)K.觉得这是个误会,因为他还什么也没有做呢。的确,K.一天到晚东跑西颠,疲于奔命,但没有干过任何与土地测量有关的事情。土地测量员究竟是一份什么职业?小说中信差巴纳巴斯的姐姐奥尔嘉曾非常惊讶地说:“什么,来了个土地测量员;这名词儿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卡夫卡251)。后来,接替弗丽达在贵宾楼酒吧做女招待的佩碧,在提及土地测量员时也说,“他学过点什么,可是他有这套本事在这里什么都干不了,这种本事还不是跟没有一样?”(卡夫卡329)以至最后在小说彻底中断前,酒店老板娘曾询问K.:
“你是不是学过裁缝?”
K.说:“没有,从来没有过。”
“你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
“土地测量员。”
“这是干什么的?”
K.对此做了解释,老板娘听了直打哈欠。“你没有说真话。为什么不说真话?”
“你不也没说真话吗?”(卡夫卡348—49)
K.并没有直接回答老板娘,而是反过来说老板娘也没有说真话,这意思仿佛是承认自己说了假话,承认自己并非是土地测量员,或者并非是城堡聘请来的土地测量员。奥地利学者海因茨·波里策在论及卡夫卡小说的主人公时说:“有一次主人公甚至是个土地测量员,换句话说,是个不依据人与土地的自然关系(播种、收获)来看待土地的人,而是依据理智的测量和估计这样第二层关系。甚至连这个职业也只是自称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真的懂行还是不过冒充而已。”(叶廷芳133)1965年,埃尔文·斯坦伯格在期刊《大学英语》中发表了题为《〈城堡〉中的K.: 伪装的土地测量员》。他认为,“几乎没有证据证明K.自称的土地测量员的身份或他被城堡雇用的身份。对于他不是测量员、没有被雇用倒是有些证据可以证明。”(丹穆若什219)看来,K.的身份在小说最后也没有得到确认。
诚然,有关K.自称“土地测量员”(landvermesser)的身份也曾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奥地利学者埃里希·海勒指出:“卡夫卡为他的主人公选择这一职业绝不是偶然的。这个字可以唤起多重联想: 首先是一个土地测量员的职业活动本身所产生的那一切联想。他的职业活动充分表现在K.拼命地追求而从未实现的事业上: 即在尘世生活的明确界限内寻找秩序,在占有欲的冲突中实现可接受的妥协。Vermesser(测量员)也暗指Vermessenheit,即Hybris(傲慢);也暗指形容词Vermessen(胆大妄为);又指反身动词sich vermessen(犯有骄傲的过错),但是也指: 测量有误,用了错误的尺度。”(叶廷芳185)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海勒的文章可谓点到即止,并未就此展开具体深入地分析和阐述。
卡夫卡给他的主人公K.选择这一职业或者也有现实的原因。1912年7月8日至29日,卡夫卡在哈尔茨山区施塔佩尔堡附近杰斯特的荣波恩自然疗养院疗养。有一天,一个皮肤黝黑、看上去很快乐的大胡子高个儿走过来和他说话,自我介绍他的职业是土地测量员。“卡夫卡曾经看见过他躺在草地上,面前同时放着三本打开的《圣经》并不停地做笔记。看过他写的心得后,卡夫卡走过去和他攀谈,小心翼翼地带着尊敬的语气问他为什么自己看不到宽恕的前景。那个测量员对他望了望,说就快看见了,要倾听内心的声音。”(周双宁148)可见,有关土地测量员的职业并非纯属于卡夫卡的想象或虚构,而是有其现实依据的。不过,这个现实中的土地测量员除了职业之外,与小说中的主人公似乎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莫里斯·布朗肖在《从卡夫卡到卡夫卡》一书中写道:“实际上,我们很清楚城堡的故事是卡夫卡采自一个他在青少年时期所读到的小说。标题为《祖母》的小说,出自捷克作家波采娜·涅姆科娃,讲述城堡和赖其维持的小镇之间的纠葛关系[……]比较这两部著作有助于理解: 在卡夫卡的作品里,明显而且是最神秘的创作,也许并不是城堡而是小镇[……]K.来自第三世界。他是双倍、三倍的奇异——在城堡的奇异中的奇异,在小镇的奇异中的奇异,也是在他自身中的奇异——因为他难以理解地决定切断与自身的亲密,如同被这些领域所牵引而前进却不被任何需求所吸引,这导致他无法自圆其说。”(251)这里的小镇在卡夫卡的小说应当指的是村庄。布朗肖承认,这两部作品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因为卡夫卡的小说重心在于K.这个形象,这个“奇异中的奇异”形象,而这个形象的奇异之处就包括了K.的职业: 土地测量员。
K.的身份问题是理解小说的关键,正如人的身份问题是理解人的关键一样。K.的身份不确定就是现代人生存的根本处境。“对现代人说来,无论世界还是他的自我,都不是既定和确定的。K.像任何人一样,为了生存,必须得到承认,并作为一个个人与整个社会相处;他必须有一个专门的职业。为了能受到召唤,他必须已经是个人物,一个被认可和需要的专家。然而K.自己知道没人叫他,因此什么也不是。他是个异乡人,一点关系也没有,纯属多余——被Schloss(城堡)关在外面,Schloss一词在这儿起的是它基本词义‘锁’的作用。一个人不可能永久生活在人类社会之外,所以K.不顾一切地需要进入,即成为一个被需要、被承认的人。”(叶廷芳676)土地的确定需要测量、界定;人的确定需要身份,而最能确定身份的就是职业和专业。测量土地是K.的身份,而K.的身份尚需确定,因而身份不确定的K.永远无法测量土地。K.能否确定自己是城堡聘请来的土地测量员,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也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情节。
然而,就是这个基本情节在小说中也是充满疑问,并且,何止K.的身份没有确定,小说中的一切似乎都不确定,进而言之,似乎卡夫卡的小说都具有某种不确定性。正是由于诸多的不确定性,所以需要测量,需要土地测量员,但是,因为土地测量员已经是过时的职业,因此,几乎没有地方需要土地测量员。土地测量员应该就是测量土地的人。“他是这样一个世界里的土地测量员: 但他所生活的世界却不愿让人就它的度量提出异议,他生活在用不着度量的世界上。所以他这个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得不到任何人的承认[……]在这个登记得十分精确的有的世界里,每个人,无论他是地主、农奴或职员,都永远被关闭在自己的边界之中,任何移动界石的企图都是一种会引起怀疑和愤怒的破坏行为。在这个固定的世界里,自以为适合做土地测量员的人被逐出村庄。有的世界拒绝度量,存在的世界不用度量。”(加洛蒂132)这正如小说里所描写的,“首先土地测量员K.必须力求在村里站稳脚跟。这并不容易,因为没有人需要他干的那种活儿”(卡夫卡412)。于是,土地测量员只能在大地上漫游,无家可归。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从何处而来,当然我们知道他肯定无法进入城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昆德拉说,卡夫卡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而是一位“存在的勘探者”,就像《城堡》中的那个土地测量员K.一样。“卡夫卡的世界与任何人所经历的世界都不像,它是人的世界的一个极端的未实现的可能。当然这个可能是在我们的真实世界背后隐隐出现的,它好像预兆着我们的未来。因此,人们在谈卡夫卡的预言维度。但是,即便他的小说没有任何预言性的东西,它们也并不失去自己的价值,因为那些小说抓住了存在的一种可能(人与他的世界的可能),并因此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干什么。”(昆德拉42—43)“无地可测”的土地测量员原来像卡夫卡一样,是人类存在的勘探者。他勘探的是人的出身和身份,人的价值和意义。正是在这个“存在的勘探者”身上凝聚了活着的人的无数希望。“他引起了猜疑、恐惧,但同时对于顺从和昏睡的人们来说又是一种新生活的预言者,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晕。”(加洛蒂132)
二、 存在的勘探者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教授考夫曼就在其编著的《存在主义》一书中将卡夫卡纳入其中。考夫曼说,“卡夫卡介于尼采和存在主义各家之间: 他描绘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人被‘抛入’世界,萨特的无神世界,以及加缪的荒诞世界”(122)。以《城堡》为例,考夫曼接着说:“在小说的开头,我们知道这个城堡是Westwest伯爵的城堡,但往后这个伯爵在故事中就不再出现了。德文的‘west’这个词意思是‘腐烂’。我以为在《城堡》中,上帝是死亡了,而我们却面对着普遍性意义的缺乏”(122)。“《城堡》这部作品旨在描写一个人,即土地测量员K.想在一处以前‘从未有人居住过’(恩斯特·布洛赫语)的地方获得居住权,也就是说,他想居住在一个上帝与人,以及人与人相互和解的世界里。”(昆 延斯311)卡夫卡所描写的就是上帝死亡之后个人的存在,普遍意义失落后对意义的追寻或探测。西蒙·德·波伏瓦说:“我们还不完全明白,我们为什么感觉到他的作品是对我们个人的关怀。福克纳,以及所有其他的作家,给我们讲的都是遥远的故事;卡夫卡给我们讲的却是我们自己的事。他给我们揭示了我们自己的问题,面对着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我们的得救已危在旦夕。”(Pawel422)萨特则认为,在《城堡》中,“卡夫卡成功地揭示了世界的苦难的本质,表现了挣扎在生活的漩涡中的人类,对于希望和自由的无限渴望和追求以及这一追求的最后的幻灭”(高宣扬85—86)。德国文学批评家赫伯特·克拉夫特说:“K.这个人,他知道,只有一个脱离了超验内容的存在才是人道的;只有在天堂和地狱的彼岸才能生活,否则只能受苦度日。”(67)总之,K.不仅测量土地,更测量人性、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言之,就是测量“存在”。
卡夫卡,这位“存在的勘探者”,“他(卡夫卡)常常自认为是一个不健全的人,这种不健全导致了他对极端的寻求: 高度和深度,围墙和地洞,阁楼与昆虫。在这方面,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测量员,实际上是《城堡》中的K.所扮演的最后一个角色”(卡尔335)。卡夫卡就像一个探测人类灵魂的测量员,他进入了这座灵魂的迷宫,但却无法进行明晰精确的测量。城堡是一个封闭的迷宫,正如灵魂的容器总是有限的,但进入城堡的路却是无限的,正如我们永远也无法到达灵魂的最深处。从这个意义上说,K.就是卡夫卡,卡夫卡就是K.。“可以说,《城堡》虽指向无限界,但仍不愧为一部描写内心世界的意识流小说。”(336)
作为土地测量员,K.的遭遇和命运也可以看作是对犹太民族漫长的受难史的高度概括和描述,是“犹太人寻找家园的譬喻”(叶廷芳51)。正是K.的土地测量员的职业和身份透露了这方面的隐秘和信息。作为土地测量员(Das land vermissen),他与词源上不同的“叹息没有土地、渴望土地”(Das land vermissen)是互为一体的(平野嘉彦185)。“土地测量员”这个词在希伯莱语中是mashoah。在德语中,土地测量员还有一个次要的意义,指测量失误的人由于冒失或放肆而犯罪的人。在希伯莱语中,这个词和另一个词“弥赛亚”(mashiah)词形相似。布罗德说,“K.以可怜而又可笑的方式遭到了失败,尽管他曾以那么严肃而又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他始终是寂寞的。在这部长篇小说经过的所有不愉快的场面之上,在所有无辜得来的不幸上隐隐约约地晃着这个口号: 这样不行。要想扎下根来,必须寻找一条不同的途径。”(布罗德192—93)关于这位土地测量员,布朗肖写道:“他始终处于运动中,永不停止,几乎毫无气馁,在——致使无止时间的冷却焦虑地——不懈运动中从失败走向失败……因为土地测量员不断地犯下卡夫卡视为最严重的错误,即急躁。”(布朗肖178)K.“从失败走向失败”,失败的原因在于急躁,而急躁则是人类的原罪。卡夫卡曾经在他的箴言中写道:“人类的主罪有二,其他罪恶均由此而来: 急躁和懒散。由于急躁,他们被驱逐出天堂;由于懒散,他们无法回去”(卡夫卡3)。K.最后疲惫不堪,但离目的地则似乎越来越远。“枯竭的疲惫,是这种疲惫的无法停止,是这种甚至无法朝向死亡安息的疲惫,因为在这个安息中,即便超支了却仍继续作用,就好像K.欠缺那种为了结束必须需要的力量之微。”(布朗肖208)K.刚抵达村子,便立即出发以求瞬间达到目标。“K.对于中段的无所谓,当然这是一种优点(朝向绝对的爆发力),然而只凸显了其——误把中段当做终点的——差错……K.总想在等待目的之前先达到目的。这种未熟结局的要求是具体化的原则,其孕育影像或称为是偶像,故随之而来的厄运就等同于偶像崇拜所招致的结果一般。人想要瞬间求得整合——在分离本身中就想要如此——,他自己再现之,而此再现整合之影像又瞬刻重整让他逐步混乱的散落元素,因为影像之为影像则不能被触及,此外,影像向人遮住影像的整合,并且透过自返回不可接近而使整合变成不可接近的,以便终使人与整合分离。”(布朗肖179)因为K.在追求目的的过程中,永远在途中,最后中途代替了目的。
犹太人是一个失去了自己的国土的民族,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始终是外来人,陌生人,他们也因此而受尽了排斥和歧视。对于K.而言,他就是这样一个永远的陌生人。他找不到适合于自己的工作,寻觅不到爱他的妻子,没有家,没有儿女,没有归属,永远是一个孤独的不被人理解的“漂泊者”。“打从一开始,这位执拗的主人公就在我们面前被描写成永远放弃其世界,包括其故土以及妻子和孩子的生活。因而打从一开始,他便无法得救,他属于流亡,此意味着他不仅不在自家处,还在自身之外,在域外本身,一个——所有存在皆似缺席,一切以为可能把握之物都逃开——内在被彻底褫夺之域。”(布朗肖176)卡夫卡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那一代人的“具有典型犹太特征的”代表。“犹太人作为社会中的陌生人、不受欢迎的人、被以怀疑眼光看待的人、多愁善感的人,想要适应社会,却又总是遭到敌视……”(昆 延斯288)。卡夫卡对犹太人的遭遇和处境感同身受。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流亡的孤独与肥沃的土地紧邻而居。1922年1月28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因为我现在已经是这另一个世界里的居民,这另一个世界与平常世界的关系就如荒漠与耕地的关系(我现在从迦南浪游出来已是四十岁了,看来是作为外国人归来,我自然在那另一个世界里……)。尽管如此,我肯定是不可想象的吗?我是肯定找到了来这里的路吗?我要是能不因为‘放逐’在那里,并由于受拒绝的牵连被压死在这里的边界上多好啊……‘也许我可以留在迦南’,但我早已身处荒漠,这只是绝望的幻想,尤其当我在那里(荒漠)成为所有人当中最痛苦的人的时候,迦南必然是唯一的希望之乡,因为第三故乡对于人类是不存在的”(卡夫卡450—51)。卡夫卡自认为,“他就是从这块土地上被放逐出来的。尽管如此,这却是一个不想放弃父辈土地的在荒漠中流亡之人;他是一个孤独的作家,但又是一个犹太人”(昆 延斯315)。
土地测量员所面临的两种处境总使他左右为难:“要么他被村里的居民同化,在那里劳动、结婚,陷于异化的昏沉之中;要么他继续徒然地要求回答他先前向城堡提出的问题: 什么是他真正的地位?他应该遵从什么秩序?什么是他生活最终的理由?”(加洛蒂136—37)在卡夫卡小说结尾的延续部分,那个车夫盖尔斯泰克这样评价K.:“你,一个土地测量员,一个有学问的人,还是穿着又脏又破的衣裳,没有皮外衣,又黄又瘦,看着都叫人伤心”(卡夫卡362)。那么,这一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对此,旅店老板娘一针见血地对K.说,“您一不是城堡的人,二不是村里的人,您什么也不是。可是可惜的是您又确实是个人,您是一个外乡人,一个多余的人,一个在这里处处碍事的人,一个不断给人找麻烦的人……”(54—55)
最后,没有土地可以测量的土地测量员成了存在的勘探者,仿佛成了一个存在主义的先行者。在卡夫卡笔下,“人在一个陌生的世界漂浮着,在那里人的存在是无力的、矛盾的、取决于无限的其他作用力……他肯定是独自一人;因为只有孤独才是他的救赎”(丹穆若什213)。K.似乎是一个犹太人的代表,但又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人类的代表和缩影。他对人类的勘探,就是对自身的勘探。卡夫卡不是存在主义作家,但他的确又是存在主义作家思想和创作的灵感和源头。
三、 阿甘本说: K即kardo
意大利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思想家、美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对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K.有专文论述。阿甘本是语言学家,又是法政治学家,因此他对卡夫卡《城堡》的研究就从这两个角度切入: 语言学与法政治学。他在《K》一文中写道:“由于涉及到边界或界线的确定,土地测量员在罗马非常重要。为了成为一个土地测量员(agrimensor或者gromaticus,该词来源于他使用的仪器),人们必须通过艰辛的考试,若无证执业可处死刑……在民法和公法里,土地测量员要区分领地边界、界定并分配土地(ager),以及最终解决边界争端,这一可能性决定(conditioned)了法律的实施。因此,只要土地测量员是一个出色的制定者(finitor),他稳定、建立、确定了边界,他就可以被称为法律的创建者(iurisauctor),一个完美的人(virperfectissimus)”(Agamben22)。在罗马法中土地测量员非常重要。他测量土地,是疆域的界定者,规矩的制定者,也可以说是法律的制定者。
罗马第一大学罗马法教授桑德罗·斯奇巴尼在《罗马法上的土地制度》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土地的归属,是任何社会和法律制度都会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古罗马的法学家们也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例如公元四世纪杰出的法学家赫尔莫杰尼安在其著作《法的摘要》中,列举了万民法的调整内容,其中写道:‘根据万民法……建立了王国,区分了所有权,划分了地界。’”“土地的归属及其份额中‘自己的’这一内涵作为构成人的群体(家庭、氏族或城邦)自主性的实质性要素,要求其他人必须通过向土地所归属的主体请求而获得,因此可以说土地归属从某种意义上是独立和自由存在的前提”(汪洋1)。“可以说,土地的归属问题,是建构所有权和其他单个他物权法律制度的摇篮和源泉,也涉及到许多公法维度的问题,如‘罗马人民”作为多个具体市民组织的集合体”(4)。
土地测量员不仅在罗马法中非常重要,在古希腊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职业。土地测量员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职业,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就提到了“量地师”。一次,苏格拉底与绰号“美男子”的雅典青年尤苏戴莫斯(Euthydemus)谈到了量地师(geometrician):“也许你非常想当个优良的量地师,像赛阿多拉斯那样。”(143)这里提到的赛阿多拉斯是居兰尼人,曾教苏格拉底量地术。苏格拉底后来又谈到量地学。他说:“一个人学习量地学,只须学到在必要时,能够对于买进、让出或分配的土地进行正确的丈量、或者对于劳动量进行正确的计算,这是很容易学会的。任何专心研究过量地学的人,都会知道一块地有多大以及它是怎样测量出来的。”(183)柏拉图不相信感官感觉,他也谈到测量和衡度,“使用远近光影的图画就利用人心的这个弱点,来产生它的魔力,幻术之类玩意也是如此……要防止这种错觉,最好的方法是使用度量衡。人心只能就形似上揣测大小多寡轻重,使用计算,测量,或衡度,才可以准确”(柏拉图80)。量地师、量地学、度量衡,在古希腊早已是家喻户晓的职业和概念。
土地测量员作为一个职业,在古希腊文学中亦有所反映。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中就有一名土地测量员。《鸟》可以说是阿里斯托芬最富想象力、抒情美和风趣的喜剧。该剧的主题是逃避现实的苦恼生活,在海外寻找一个完全不同的城邦,这就是“云中鹁鸪城”(Cloud-cuckoo-land,杨宪益妙译)。两位雅典人走进密林中,遇到了曾经是人而现在变成了鸟的戴胜,以及大群飞鸟。雅典人向戴胜及群鸟建议,“建立一个鸟类的城市国家,然后筑起一圈像巴比伦样的高大砖墙,围住整个大气和天地之间的广阔空间”(阿里斯托芬657),恢复昔日鸟国的荣耀。他们将禁止宙斯家族的诸神经过这里,到达人间;也不许人类献祭牺牲的香味上升到天上。这个“云中鹁鸪国”建成后果然不同于人间,这里的“鸟”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时诗人、预言家纷纷前来祝贺,索取礼物。也就在这时,来了一位空气土地测量员,名叫墨同(Meton)。他携带着一些土地测量器具,譬如尺子和圆规,从雅典来到“云中鹁鸪国”,“丈量大气,给你们划分土地”(to land-survey this Air of yours, and mete it out by acres)。这位墨同自称闻名于希腊和克洛诺斯。这位土地测量员同时又是几何学家,几何学家自然成天忙于计算。自由自在的“云中鹁鸪国”自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他被驱逐出去,落荒而逃。我们知道,卡夫卡对于古希腊文化是非常熟悉的,他的土地测量员K.或许受到过阿里斯托芬的启发也未可知。
那么,土地测量员与卡夫卡的《城堡》又是怎么一种关系呢?阿甘本认为,土地测量的中心点往往就是未来城堡的建造地。“罗马土地测量员使用的仪器是groma(或者gruma),即一种十字架,它的中心对应着地面的某一点(称作umbilicus soli),四端系有绳子,绳子上悬挂着一定重量的物品……两条相互交叉形成直角的基本直线,一条称作轴(kardo),南北走向;另一条称作准(decumanus),东西走向。两条线的交叉点就是的城堡(castrum)的建筑地(即筑城之地或者城堡,castellum是castrum的小词,也是军营),在两条主干道周围人们(就军营而言,即士兵的帐篷)聚集而居”(Agamben22)。“土地测量员”一词源于测量工具,测量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轴,轴(kardo)的首字母就是K,因此,土地测量员就是K.,K.就是所有土地测量员的名称。
1814年,布鲁姆、拉赫曼和鲁道夫,这三位伟大的语言学家和法学史家在柏林编辑出版了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罗马土地测量文集。文集中收录有大量插图,其中关于城堡“castrum”的插图格外引人瞩目,它有29种变化。我们今天观看这些插图仍然很容易联想到卡夫卡对城堡的描写:“它既不是一座古老的骑士城堡,也不是一座新式的豪华建筑,而是一座宽阔的宫苑,其中两层楼房为数不多,倒是有许许多多鳞次栉比的低矮建筑;如果事先不知道这是一座城堡,那么可能会以为它不过是一个小城镇。K.只看见一座塔,它究竟是属于一所住宅还是属于一所教堂,就无法看清了”(卡夫卡10)。因此,阿甘本说,这些插图“以一种令人惊愕的方式呈现出《城堡》第一章K.对城堡的描述”(Agamben22)。
随后,阿甘本让我们认真考虑一下《城堡》主人公的职业。他说:“在土地测量员的语言里,K就是轴(kardo),‘因为它直接对准天空的神圣基点’(quod directum ad kardinemcaeliest)。K.所关心的是‘确定边界’,这是他的职业,是他对城堡的公职人员带有挑衅意味的宣称,也被城堡视作一种挑衅。这一冲突——如果确有冲突的话,这是一个冲突的问题——也并非像布罗德的草率建议所言,与在村里居住并被城堡接受的可能性无关,而与边界的设立(或僭越)有关。再一次根据布罗德的说法,如果城堡便是这个世界‘神圣政府’的恩典的话,土地测量员并没有用仪器,而是用‘手边放着的一根拐杖’,以一种义无反顾的特殊的‘建立界限’的方式与城堡,以及城堡的官员就城堡的限度进行斗争”(Agamben23-24)。
土地测量员既可以确定边界,又可以打破边界;测量是确定边界,重新测量就是重新划定边界,重新确定边界就是以新的边界打破旧的边界。《城堡》中K.所做的就是重新确定边界。城堡,包括附属于城堡的村子的土地都早已测量过了,他们不再需要土地测量员。因此,K.作为土地测量员是不请自来,他的工作是自己派给自己的。他要重新测量土地,这是对城堡的宣战,也是对村子的宣战。
当然,K.对城堡或者村子宣战并非针对城堡的最高统治者,而是针对那些代表着城堡的官员;这正如卡夫卡并不挑战宗教的最高权威上帝,而只是质疑那些围绕在上帝身边的天使、信使一样。在小说中,城堡的最高权威者威斯特-威斯特公爵并未真正露面,他的权威也并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挑战和威胁。与K.发生矛盾的是那些代表城堡的官员,这些官员代表着有关神性的谎言,“这些谎言就是他们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界限、隔离和障碍,而这也正是土地测量员质疑的对象”(Agamben25-26)。K.所面对的是一大批与城堡有关的人员,除了各种各样的“城堡姑娘”,譬如弗丽达、佩碧之外,还有一位副城管、一位信使、一位秘书和一位名叫克拉姆(Klamm)的主管,这个名字也有点像测量工具中的那个轴(kardo)。K.所质疑的便是这些所谓的城堡的代表,而城堡以及城堡的最高当权者他连见也没有见过。
最后,阿甘本认为,土地测量员的职责就在于制定界限和破坏界限。在英国当代学者基斯·特斯特看来,定界与破界总是纠缠在一起,如影随形,这是与人类的求定意志与求知意志密切相连的。他认为,“说到底,后现代性意味着对于某些界限的超越,正是这些界限奠定了基础,使人们认知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界限,完全有可能出现不可能存在任何理解的状况)。如此一来,后现代性作为对于现代种种界限的超越,意味着一种特殊的境况,其中存在的东西无法被说明或解释。它只能被视为一种无法变更的简单事实。在后现代境况中,现存的东西是没有界限的”(169—70)。如此看来,土地测量员既是现代的,又是后现代的。
土地测量员的兴趣在于那道将二者分离又联接的边界,他想废弃它,或者说使之无效。似乎无人知晓这条界限从哪里穿越,事实上,也许它并不存在。但是,它像一道无形的门横亘在每一个人之间,藏在人的内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重读一下卡夫卡的《在法门前》。在卡夫卡的小说《新律师》中,新律师布塞法鲁斯“埋首于那些废弃不用的法律书籍”,而作为“新土地测量员”K.,他的职责就在于“使那些既分隔又联系高层与底层、城堡与村庄、庙宇与住所、神圣与人类、纯洁与不洁的边界和界限失效。一旦门(就是那规范他们之间关系的法律体系,那些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失效了,那么,高层与底层、神性与人性、纯洁与不洁将会怎样呢?”(Agamben26)。的确,没有了界限,人与上帝、人与人、人与自然将是怎样一种关系呢?这是阿甘本所设问的,大概也是他所猜想的卡夫卡笔下的这位土地测量员所想到的,应该也是卡夫卡所关注并充满疑惑的问题。
当然,阿甘本基于语言学、词源学考察了土地测量员与罗马法之间的关系,进而勘探了人与土地、人与人、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语言学既是阿甘本的分析方法,也是他的直接证据;罗马法既是阿甘本探究的内容,又是探讨卡夫卡小说内涵的必然路径;神学是阿甘本与卡夫卡共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阿甘本的理论与卡夫卡的小说在这里完全可以互文、互看、互释。阿甘本对卡夫卡的解读可谓别出心裁,让人感觉耳目一新,但是,这也只是众多理解和阐释卡夫卡的方式之一,且论证方式有些简单,论证材料也不够丰富。诚然,卡夫卡思想创作与语言、法律和宗教密切相关,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与卡夫卡相关的远不止这些,即便就是这些领域,阿甘本的论述也还是显得有些单薄,有些单调,有时也显得有些勉强。
行文至此,笔者想再补充一点: 众所周知,卡夫卡的这部小说并没有写完。据布罗德说,小说的结尾处还有这样一段: K.同车夫盖尔斯泰克一起走出贵宾楼,盖尔斯泰克对K.说:
“你有活儿干了吗?”
“有了,”K.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在哪儿?”
“在学校。”
“可你不是土地测量员吗?”
“不错,我现在这个位置也只是暂时的,等接到土地测量员的聘书时,我就离开那里。你明白吗?”
“明白。到那时还要很久?”
“不,不,不会很久,聘书随时都可能来……”(卡夫卡361)
到末了,小说主人公K.最忘怀不了的还是他那份土地测量员的工作,以及那份他所期盼的土地测量员的聘书。如此看来,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K.,作为《城堡》中的主人公,并非是卡夫卡突发奇想、随意为之之事,而一定是经过精心设计、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至于卡夫卡真正的创作动机和目的,我们今天只能通过各种推测和猜测去接近它,完全的领会和掌握是不可能的。这正如K.永远也无法进入城堡,只能在附属于城堡的村子里不停地转悠一样。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gamben, Giorgio.Law
,Literature
,and
Life
. Eds. Justin Clemens, Nicholas Heron, and Alex Murra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8.阿里斯托芬: 《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6卷),张竹明、王焕生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7年。
[Aristophanes.The
Complete
Works
of
Ancient
Greek
Tragedy
and
Comedy
. Trans. Zhang Zhuming and Wang Huansheng. Vol.6. Nanjing: Yilin Press, 2007.]莫里斯·布朗肖: 《从卡夫卡到卡夫卡》,潘怡帆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Blanchot, Maurice.From
Kafka
to
Kafka
. Trans. Pan Yifan.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马克斯·布罗德: 《卡夫卡传》,叶廷芳等译。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Brod, Max.Franz
Kafka
:A
Biography
. Trans. Ye Tingfang et. al.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7.]弗雷德里克·R·卡尔: 《现代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主权1885—1925》,陈永国、傅景川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Carl, Frederic R.Modernity
and
Modernism
:The
Sovereignty
of
Artists
1885-1925
. Trans. Chen Yongguo and Fu Jingchua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0.]大卫·丹穆若什: 《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Damrosch, David.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 Trans. Zha Mingjian, Song Mingwei et. al.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高宣扬: 《萨特传》。北京: 作家出版社,1988年。
[Gao Xuanyang.A
Biography
of
Jean
-Paul
Sartre
.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1988.]罗杰·加洛蒂: 《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
[Garaudy, Roger.On
Limitless
Realism
. Trans. Wu Yuetian.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8.]平野嘉彦: 《卡夫卡——身体的位相》,刘文柱译。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Hirano, Yoshihiko.Kafka
:The
Position
of
the
Body
. Trans. Liu Wenzhu.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2.]弗兰兹·卡夫卡: 《卡夫卡全集》,叶廷芳主编。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Kafka, Franz.The
Complete
Works
of
Franz
Kafka
. Ed. Ye Tingfang.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6.]沃尔特·考夫曼: 《存在主义》,陈鼓应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7年。
[Kaufman, Walter.Existentialism
. Trans. Chen Guying 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7.]赫伯特·克拉夫特: 《卡夫卡小说论》,唐文平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Kraft, Herbert.On
Kafka
’s
Novels
. Trans. Tang Wenp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4.]汉斯·昆 瓦尔特·延斯: 《诗与宗教》,李永平译。北京: 三联书店,2005年。
[Küng, Hans, and Walter Jens.Poetry
and
Religion
. Trans. Li Yongp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5.]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孟湄译。北京: 三联书店,1992年。
[Kundera, Milan.The
Art
of
the
Novel
. Trans. Meng Me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2.]Pawel, Ernst.The
Nightmare
of
Reason
:A
Life
of
Franz
Kafka
,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84.柏拉图: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Plato.Plato
’s
Literary
Dialogues
. Trans. Zhu Guangqi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0.]基斯·特斯特: 《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李康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Tester, Keith.Life
and
Multiple
Times
in
Postmodernity
. Trans. Li Ka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汪洋: 《罗马法上的土地制度》。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
[Wang, Yang.The
Land
Policy
in
Roman
Law
. Beijing: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2012.]色诺芬: 《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年。
[Xenophen.Remembering
Socrates
. Trans. Wu Yongqu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4.]叶廷芳:“寻幽探秘窥《城堡》——卡夫卡的《城堡》试析”,《外国文学评论》4(1988): 46—52。
[Ye, Tingfang. “A Glimpse of The Castle: An Analysis of Franz Kafka’s The Castle.”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4(2018): 46-52]叶廷芳编: 《论卡夫卡》。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 - -, ed.On
Franz
Kafka
.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8.]周双宁: 《看不见的城堡——卡夫卡与布拉格》。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Zhou, Shuangning.Invisible
Castle
:Franz
Kafka
and
Prague
.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