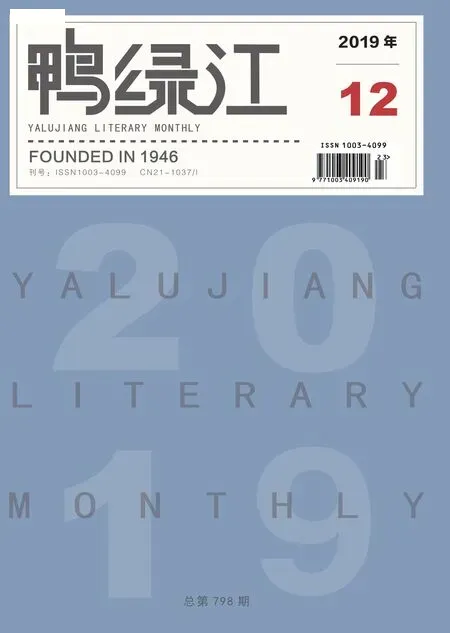驶向心中的灯塔(对谈)
2019-11-12 14:18王可田丁小龙
鸭绿江 2019年23期
王可田 丁小龙
王可田:
一部《浮士德奏鸣曲》,将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及其命运串联起来,更是主人公张天问一段生命历程的见证,而且,他的学者身份也与这部诗剧产生某种关联。另外,音乐形式在小说中也有表现,像勃拉姆斯《德意志安魂曲》、标题中的“奏鸣曲”。在我读过的你的另外几篇作品中,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元素大量涌入,不仅作为小说叙事的背景出现,更以斑斓的色调铺陈出人物命运以及文本的深层意蕴。也就是说,你的小说人物要么是艺术家、学者,要么是热爱文艺抑或哲学的有独立思想的现代青年。应该说,这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属于小众群体,对你来说这算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吗?丁小龙:
是的,你的总结非常精确。在我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写这个所谓的小众群体。比如,《空心人》与《浮士德奏鸣曲》关注的是有哲学背景的青年人。当然这两个小说也有区别,前者是有哲学思辨能力的罪犯,而后者则是名副其实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再比如,《幻想与幻想曲》写的是钢琴家的艺术生活,《万象》展示的是画家的日常思索,《世界之夜》《物与象》与《鲸》关注的则是诗人的存在困境,等等。回顾了一下自己前几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确实有一部分关注的是这个小众群体,但是,他们对我而言又是非常熟悉的一群人。在写作过程中,我会制造陌生感,与所创作的人物保持艺术上的距离。其实,我有很多作品写的不是艺术家,不是作家,也不是知识分子。比如,《天涯倦客》写的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的晚年生活,《少年骑士》写的是两位少年的成长简史,《同尘》写的是失去儿子后的悲痛往事,《脸》和《迷航》写的都是中学教师的人生境遇,等等。除此之外,我还写过科幻小说,比如《旅》;写过荒诞小说,比如《荒年纪事》。我对人感兴趣,对各种各样的故事都很着迷。关注人类的存在困境与探索艺术的无限可能,是我创作的最原始动力。王可田:
诗人锤炼语言,冶炼词语的黄金,对于作家而言,语言同样重要。甚至在一部作品中,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话语风格,这就要求小说家的语言库存更为丰富甚至驳杂。你的语言给我的印象是,更多地融合了诗性与哲思,呈现出一种诗性叙事的特征或倾向。能谈谈你创作小说时的语言追求和具体实践吗?丁小龙:
准确。这种准确有着多层次的含义。不同的人物需要不同的语言,这是一种准确。每个作品的语言都需要符合作品本身的气质和风格,这也是一种准确。对我而言,福楼拜、伍尔芙、马尔克斯和三岛由纪夫是我在这方面的文学导师,他们的语言恰到好处,特别准确。比如,在我创作《空心人》这部八万字的小说前,我心里其实并没有对语言过多地预设。经过长久的思索,我对主人公有了感同身受的认知,甚至会觉得主人公就是我的某种化身。写完开头的两千字之后,我突然明白了自己需要怎样的语言风格,需要怎样的文学结构,这可能就是所谓天启时刻——不是我选择了语言,而是语言选择了我。王可田:
读你的小说,几乎可以说在结构上每一部都是崭新的,绝少雷同,给人非常特别的阅读快感和体验。这部《浮士德奏鸣曲》有四个章节,没有单独命名,仅以数字标出,是否借鉴了奏鸣曲的曲式?另外的作品,像《万象》以“水、土、金、火、木”的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结构文本,《世界之夜》以“冬、春、夏、秋”生命年轮的四个剖面展示主人公的一生。你如何看待小说的结构,创作中又是如何运用的?丁小龙:
是的,《浮士德奏鸣曲》借鉴了奏鸣曲的结构。四个部分,相当于四个乐章,每个乐章的内容不同,速度不同,人物也不同,却因为同样的主题而关联成篇。其实,我特别注重作品的音乐性,这种音乐性不仅指文字间的韵律,词语间的奏鸣,也指这种音乐结构的形式感。在我看来,结构是小说的骨架,是撑起小说建筑的钢筋水泥。没有了结构,再深刻的文学主题,再优美的文学语言,也会轰然倒地。当然,小说的结构不仅仅是外在形式,还有内部的精神经络。比如,在我的中篇小说《万象》中,主人公是油画家,是视觉艺术家,因此,用她的“金象”“木象”“水象”“火象”“土象”这五幅画作为章节名,不仅是结构的需要,更是内在精神的需要。王可田: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叙述的方式当然是重要一环。在实际的创作中,作家除了对语言和结构精益求精,在叙述视角方面也会煞费苦心。我们知道,现代小说多以“我”的视角进行叙述,这种角度呈现的视域并不宽广,不适合用以描绘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但第一人称特有的主观性能够深入人物内心,展露意识深处的暗涌,呈现多层次的心理结构。我感兴趣的是,你在应用不同的叙述视角时,都会产生哪些不同的写作体验?丁小龙:
你的看法很有道理。在我目前创作的作品中,第一人称偏多,其次是第三人称,当然,我还尝试过用第二人称写作。用第一人称写作时,主观性比较强,也容易把作者和读者带入文本的世界。用第一人称创作的难度就是如何区别作者与主人公的视角差异,避免将两者混为一谈。第三人称写作就能很好地避免这个视角混淆的问题。在写《浮士德奏鸣曲》时,我原本打算用自己更熟悉的第一人称去写。然而,在写了一千字的时候,总感觉有地方不对劲。于是,我改变了方法,用第三人称来写这个故事,随后的创作过程也变得顺畅很多。有时候,我也说不清其中的缘由,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艺术直觉,也是艺术的魅力所在。在写《万象》的时候,我从一开始就决定用第二人称写作,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全新的艺术体验——你要沉浸其中,又要抽离自我。王可田:
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在呈现生活的细节和形态以及人的社会性方面是有优势的,但对人的精神性传达往往乏力。物质性的现实是现实,内心现实同样也是。现代小说应该面对现代人复杂的生存现实,同样也应该并有能力呈现和揭示现代人复杂的内心体验。你的小说不摹写现实,重在揭示人物内心,并触及意识和潜意识层面。你是如何为自己的写作寻找并确定主题的?丁小龙:
不是我寻找主题,而是主题寻找我。这也可能是艺术上的直觉。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艺术的人,喜欢古典音乐,喜欢电影,喜欢绘画,也喜欢造型艺术和摄影艺术。所有的艺术都有某种共同的精神特质,会给我的创作带来很多启发。比如,《幻想与幻想曲》的灵感来源于舒伯特的《幻想曲》,《押沙龙之歌》的灵感来源于《圣经》故事与舒曼的《童年情景》,《风知道名字》来源于偶然看到的插画,《万象》则来源于某次在清华大学看到的画展,《长夜短歌》来源于安东尼奥尼的某个电影场景,等等。因此,对于作家而言,所有的经验都是有用的,都会带有某种神启的特质。王可田:
就中国文学的发展来看,在文体意识、文体自觉方面,诗歌始终走在前头。当然,小说也有各种形式、技巧以及主题方面的探索,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80年代的先锋小说。但新世纪以来,曾经活跃的先锋小说家纷纷回归现实和传统,只有极少数的作家如残雪,仍保持着先锋性和探索性的锐度和深度。那么,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作家,你如何看待小说文体的探索性或实验性?丁小龙:
对小说文体的探索是我始终追求的艺术理想。在我看来,小说的先锋性与传统性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艺术特质,好的艺术作品可以同时容纳这两种品格,甚至可以说模糊二者的边界。先锋不一定意味着深度,而传统也不一定意味着保守。比如,我非常喜欢帕慕克的文学作品。在那部《我的名字叫红》的长篇小说里,他讲述的是16世纪伊斯坦布尔的故事,按道理来说,是回归传统之作,然而他的写法是如此迷人,用第一人称多声部的方式讲述了谋杀、爱情和绘画等多个主题。因此,即使在最现实最传统的作品里,所用的艺术手法也可以非常多样,探讨的主题也可以非常现代与深奥。王可田:
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写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整整一个社会。”以此观照小说创作,能否这样说:作家塑造人物就是自我的分裂,每一篇小说中出场的主人公,实际上仍是戴着不同人格面具的作家本人?丁小龙:
是的,我同意这种看法。福楼拜曾经说过,“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他的这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冲击力。刚开始,我并不理解这句话。随着写作的深入,我越来越觉得小说中的所有主人公,其实就是作家的不同分身。因为只有真正地深入人物灵魂,才能够理解人物、塑造人物。与此同时,也要从人物中抽离出来,在远处观察人物、刻画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所有的小说作品,都是作家某种形式的自传。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当我写作时,我就忘记了我自己,成了他人。忘记自我,才能认清自我。忘记主体,才能构建真正的主体。王可田:
经年累月地写作,整天跟自己虚构的人物生活在一起,他们会不会也如幽灵一般扰乱你的心神,甚至产生一种错觉:小说是真实的,而现实是虚幻的?丁小龙:
小说是谎言中的真实,而生活是真实中的谎言。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感受,我一直觉得我所创作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在我创作之前,他们就存在于这个世界,等待着我的发现;在我创作之中,他们诉说,他们沉默,他们欢笑与流泪,而我在其中发现了生命的意义,通晓了万物的秘密;在我创作之后,他们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而我会在某个时刻想念他们,祝福他们。比如,《浮士德奏鸣曲》中的张天问,我以后可能会写另外一篇关于他的故事。在我看来,优秀的小说要比现实更接近真实,更靠近存在的核心。王可田:
小说是虚构的,是虚构性的叙事文本,但它也有真实的一面:对事物真相的揭示和表达上的真切。有的人强调小说的客观性、真实性,也即对生活和现实真相的披露,但有的人声称只对美(艺术性)负责。你在创作实践中,是如何顾及或平衡“真”与“美”的?布罗茨基曾经说过:“美学是伦理学之母”,善、恶的范畴也是你所考虑的吗?丁小龙:
在我看来,小说的种类是多样的,小说的功能也是多样的,因此,才会诞生多种流派的小说。现实主义小说、现代主义小说以及后现代主义小说,只是其中最概括笼统的划分,里面还有很多更细致的子类。每一种类型的小说,对真实和美都有自己独特的追求。在我自己的创作中,“真”和“美”是不可分的双生花,是我艺术生活的双重追求。在我看来,你抵达了“真”的核心,就会领悟到“美”的本质。另外,伦理学的困境也是我小说创作的中心。我对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事件没有多少兴趣,我感兴趣的还是人性的灰色地带。王可田:
现在很多作家都痴迷于长篇小说的写作,好像容量更大的长篇才能证明和实现他们的文学雄心。事实上,在我们阅读卡夫卡或博尔赫斯的中短篇甚至小故事的时候,都能感受到象征和隐喻所构成的深度空间,就像把一个质量和能量都非常巨大的物体,压缩进一个非常小的物理空间,需要更大的智慧和高强度的处理手段。你也出版过长篇小说,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丁小龙:
我喜欢卡夫卡和博尔赫斯,也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大江健三郎。我可能不是特别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优秀的长篇小说更需要智慧、能量与耐心,更需要隐喻和象征。在我看来,《卡拉马佐夫兄弟》肯定要比《变形记》更具有挑战性,《百年孤独》也肯定比《沙之书》更难把握。当然,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与短篇小说都有各自的难题与各自的魅力。有一种观点是,短篇小说是练笔场,是为长篇小说做前期准备。我也不是很同意这种看法。我非常欣赏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因为她写出了出色的长篇小说,比如《使女的故事》《盲刺客》等,也写出了很好的短篇小说,同时又是诗人和学者。她所关注的文学主题与艺术探索让我非常着迷。王可田:
作家王蒙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曾呼吁“作家的学者化”,时至今日,我们的很多作家痴迷于写作,却很少读书,他们的写作资源基本上是生活本身。你的阅读广泛而深入,且有系统性,这在你的小说叙事中很容易辨认出来。阅读和写作的关系你怎么看?你能列举出一些对你产生影响,或者说你偏爱的作家、艺术家吗?丁小龙:
阅读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写作。没有阅读的写作就是在空中建造楼阁。在我二十五岁之前,最喜欢读的还是文学作品,主要的还是小说。特别是在本科学习阶段,经常泡在图书馆,一本接一本地读小说,读诗歌和散文。那时候,读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印象最深刻的是伍尔芙的《到灯塔去》与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也就是在那个迷恋文学的大学时期,我开始了自己的写作之路。二十五岁之后,我开始有计划地阅读哲学、美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方面的著作,对电影、音乐和美术也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为了读懂加缪和杜拉斯的书,看懂戈达尔和侯麦的电影,我还特意学习了法语。与此同时,我还翻译过一些英语文学作品。我所偏爱的作家和艺术家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因为他们从不同方面影响了我写作。比如,作家中有托尔斯泰、黑塞与莫里森,音乐家中有巴赫、马勒与拉赫玛尼诺夫,导演中有伯格曼、安东尼奥尼与黑泽明,画家中有伦勃朗、莫奈与弗里达,等等。当然,这只是长名单中很小的一部分。王可田:
你的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主,随笔、诗歌数量不多,但品质很高,我也非常喜欢。对于写作你有明确的规划吗?今后一段时间的写作计划能否透露一下?丁小龙:
今后还是以小说为主,偶尔会写随笔与诗歌。对于写作,我永远都是自己的陌生人。我有一个文档,名为“到灯塔去”,里面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随笔”与“诗歌”这几个子门类。每个子门类里都有一个创作手记,里面装着我关于写作的全部秘密。对我而言,写作就是驶向心中的灯塔。猜你喜欢
文学自由谈(2022年5期)2022-09-28
上海人大月刊(2022年5期)2022-05-19
小说月报(2022年2期)2022-04-02
意林(儿童绘本)(2020年1期)2020-02-14
文学少年(原创儿童文学)(2019年4期)2019-05-23
中国篆刻(2016年5期)2016-09-26
新高考·高三数学(2016年1期)2016-03-05
诗选刊(2015年4期)2015-10-26